鄱阳湖丰水期着生藻类群落空间分布特征*
钱奎梅,刘 霞 ,陈宇炜
(1:徐州工程学院,江苏省工业污染控制及资源化重点实验室,徐州 221018) (2: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南京 210008) (3:南昌工程学院,南昌 330099)
着生藻类(periphytic algae)也被称为周丛藻类,是附着在水体基质上生活的一些微型藻类. 着生藻类是水体中重要的初级生产者,对于水生环境的固碳、初级生产力、养分循环和食物网都十分重要[1,2]. 同时,着生藻类在湿地漫滩中比浮游植物对初级生产力的贡献更大[3]. 着生藻类受到水流的影响较小,对水环境变化快速敏感,是理想的水环境监测生物指标,并已被广泛用于海洋、湖泊及河流等水体的生物监测中[4-6]. 由于着生藻类固定在一定位置,在流速较大的水体中,它们能比浮游植物更为准确地反映水质状况[7].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吞吐性、季节性和通江性淡水湖泊,鄱阳湖上承赣、抚、信、饶、修五河之水,下接长江,水位受“五河”入湖水量和长江水位顶托双重影响,年内水位变幅巨大,在我国淡水湖泊中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 鄱阳湖河湖转换会导致鄱阳湖湿地出现不同的区域特性,而这会导致不同区域的着生藻类有不同的群落结构特征. 近年来,鄱阳湖部分湖区已经出现富营养化现象,蓝藻水华在鄱阳湖主航道都昌水域、康山湖、撮箕湖、战备湖等湖区水面均被发现[8]. 有关鄱阳湖的生物监测已经有很多报道,但大部分是以浮游植物、浮游动物以及原生动物作为监测指标[9-11];对于鄱阳湖着生藻类的分布情况鲜见报道,仅吴召仕等[12]报道了鄱阳湖局部湖区的水网藻水华现象,而近20年来有关鄱阳湖着生藻类的资料几乎为空白. 为了解和丰富鄱阳湖着生藻类背景资料,本研究于2017年7-8月对鄱阳湖不同湖区的着生藻类群落结构和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同时对水环境因子进行监测,对鄱阳湖的水质状况进行分析评价,旨在为鄱阳湖水环境保护和水资源合理利用提供基础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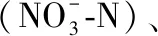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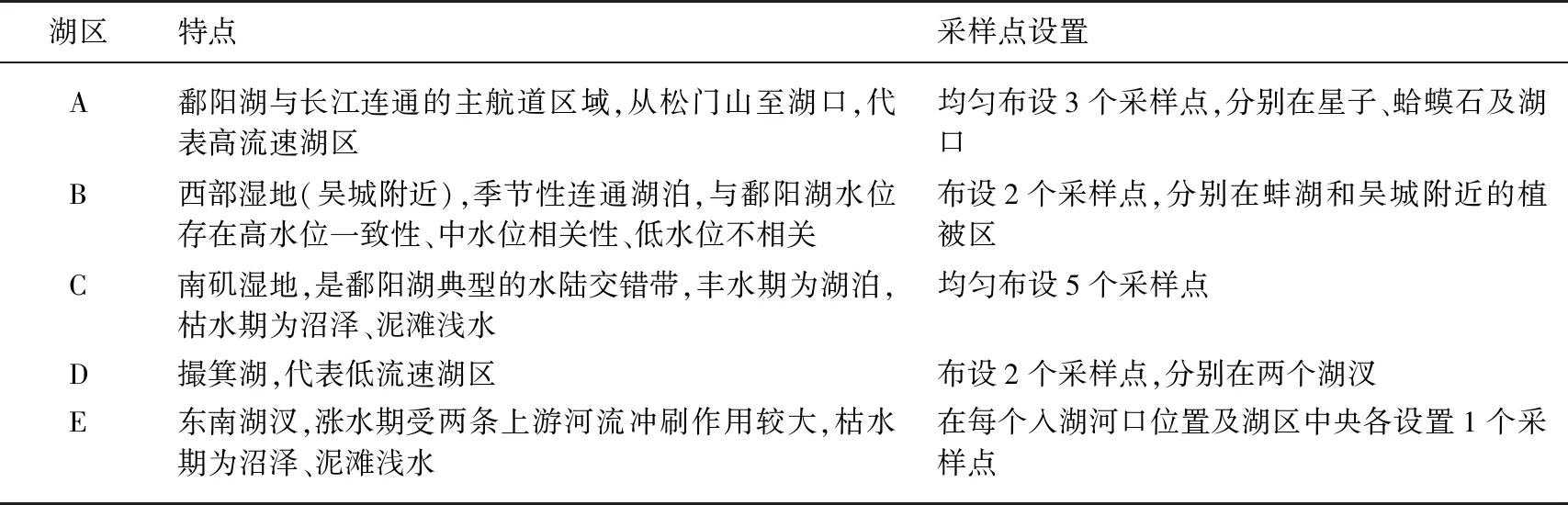
表1常规采样点布置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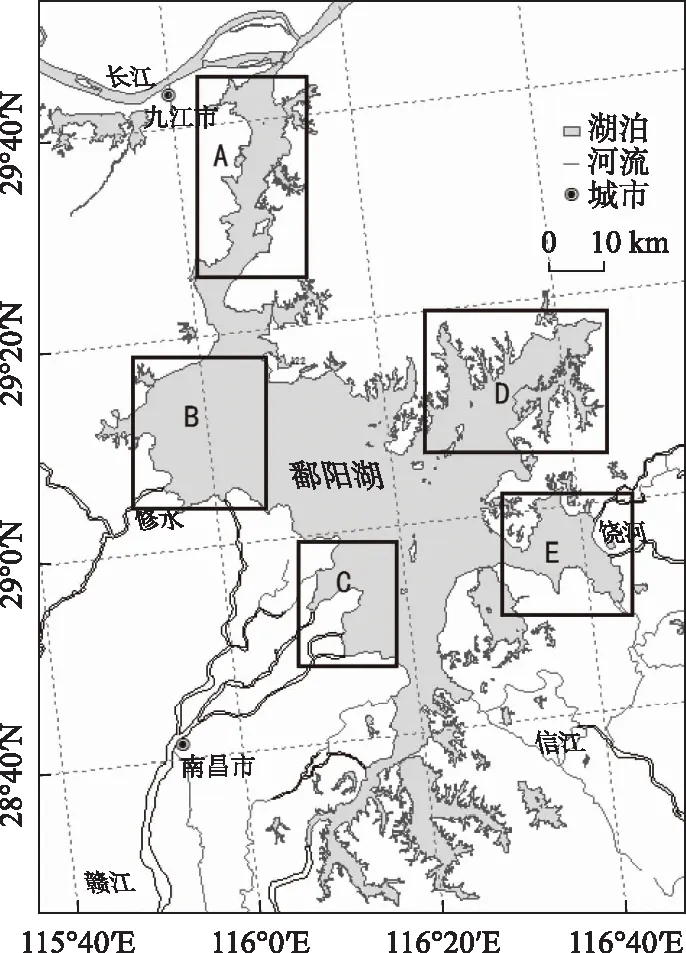
图1 鄱阳湖采样区域分布Fig.1 Distribution of the sampling areas in Lake Poyang
着生藻类采用以下方法进行采样[14-15]:在湖泊中选择附有藻类的石块,用毛刷将石块上藻类刮到样品瓶中,并用蒸馏水将基质冲洗多次,用鲁哥氏液固定,定容到 100 mL,同时量取刮下着生藻类的石块面积. 将处理好的着生藻类样品在显微镜下观察,用面积为 20 mm×20 mm、容量为 0.1 mL 的计数框计算着生藻类的细胞丰度. 计数方法为目镜视野法,随机计数500个视野,并使视野均匀分布在计数框内. 每个样品计数2片,取其平均值为最终结果(若2片计数结果相差15%以上,则进行第3片计数,选择其中个数相近的2片取平均值). 着生藻类定性定量分析参照《中国淡水藻类——系统、分类及生态》[16]和《藻类学》[17],最后计算出基质上每个采样点的藻丰度(cells/m2). 着生藻类生物量按照《淡水浮游生物研究方法》[18]计算,假定藻类比重为1,采用细胞体积转化法计算单位面积内藻类生物量(mg/m2).
生物多样性分析采用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19]:
(1)
式中,ni为i种藻类的个体数,N为群落中全部藻类的个体数[18].
Pielou均匀度指数:
J=H′/Hmax=(-∑pilnpi)/lnS
(2)
式中,S为物种数目,pi为属于i种的个体数占全部藻类个体数的比例.
物种丰富度指数:
dMa=(S-1)/lnN
(3)
式中,S为物种数目,N为所有物种的个体数之和.
使用SigmaPlot(12.0版)软件制作图表,使用SPSS 17.0软件进行不同水域的着生藻类差异显著性分析,利用R语言的vegan包进行着生藻类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冗余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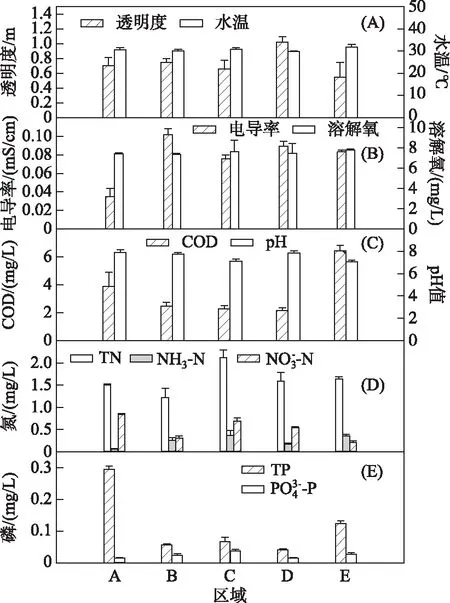
图2 鄱阳湖水体理化指标的区域差异Fig.2 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dicators of water in Lake Poy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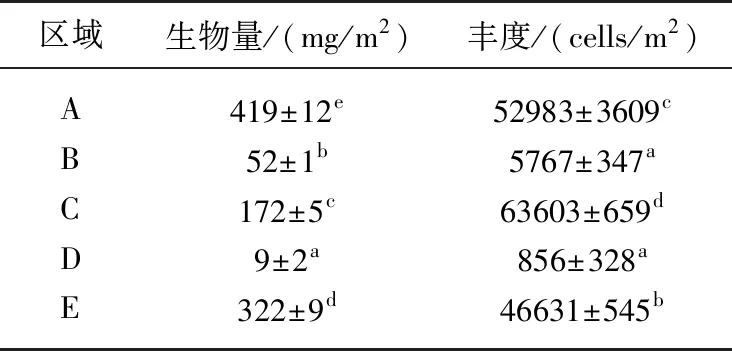
表2 鄱阳湖不同区域着生藻类总生物量和丰度差异
2 结果
2.1 鄱阳湖不同湖区水体的理化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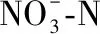
2.2 鄱阳湖着生藻类群落组成
鄱阳湖着生藻类共检出6门67属101种,其中绿藻门34属60种,占总藻类的59.4%;硅藻门17属20种,占总藻类的19.8%;蓝藻门6属13种,占总藻类的12.9%;裸藻门4属5种,占4.9%;甲藻门和隐藻门分别为1属1种和1属2种,占鄱阳湖着生藻类总藻类的1.0%和2.0%. 不计着生藻类相对生物量小于1%的种类,硅藻门相对生物量高达41%~94%,其次为绿藻(32%~53%).
2.3 鄱阳湖不同湖区着生藻类的生物量比较及优势种分布
鄱阳湖各个水域的着生藻类生物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表2). 主航道区域(A区域)着生藻类生物量相对最高,平均为419 mg/m2;其次是东南湖汊(E区域),为322 mg/m2;而撮箕湖(D区域)的总生物量相对最低,为9 mg/m2. 鄱阳湖着生藻类丰度有着明显的区域差异(表2). 南矶湿地(C区域)着生藻类丰度相对最高,平均为63603 cells/m2;其次为主航道区域(A区域),平均为52983cells/m2;西部湿地(B区域)和撮箕湖(D区域)相对最低,分别为5767和856 cells/m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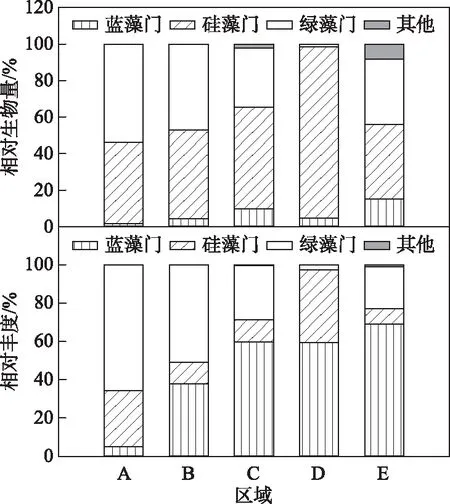
图3 鄱阳湖各门类着生藻类生物量和丰度的区域差异Fig.3 Spatial variation of biomass and abundance of each phylum periphytic algae in Lake Poy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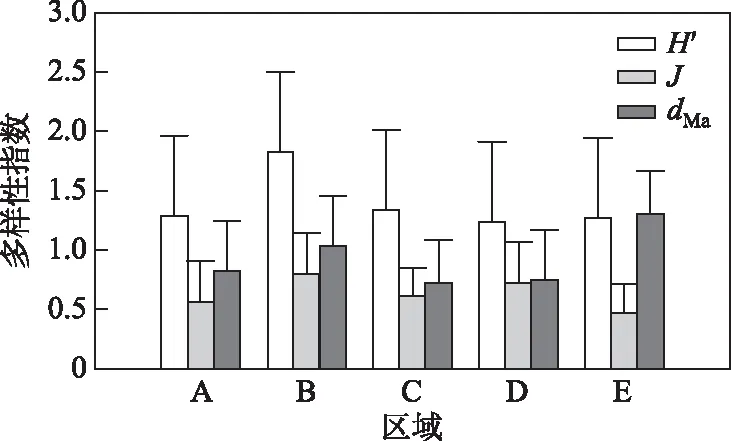
图4 鄱阳湖着生藻类Shannon-Wiener种类多样性指数(H′)、Pielou均匀度指数(J)及物种丰富度指数(dMa)的区域差异Fig.4 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Shannon-Wiener species diversity index (H′), Pielou evenness index (J) and species richness index (dMa) of periphytic algae in Lake Poy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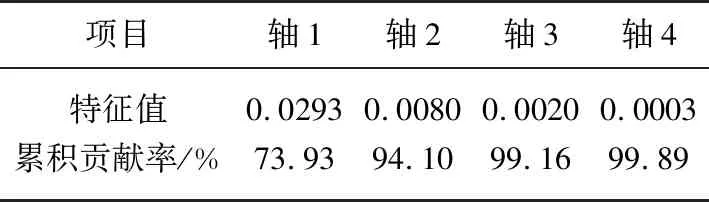
表3 鄱阳湖不同水域的着生藻类群落结构与环境因子的典范对应分析结果
鄱阳湖不同水域着生藻类的群落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图3). 就生物量而言,硅藻在西部湿地(B区域)、南矶湿地(C区域)、撮箕湖(D区域)、东南湖汊(E区域)4个区域最高,其中,撮箕湖(D区域)硅藻的相对生物量为94%,而其余几个区域硅藻的相对生物量为41%~56%. 绿藻在主航道区域(A区域)的相对生物量最高,为54%,其次为硅藻(44.5%). 就丰度而言,绿藻在A、B两个区域的相对丰度较高,分别为65.77%和50.94%,而蓝藻在南矶湿地(C区域)、撮箕湖(D区域)和东南湖汊(E区域)3个区域的相对丰度较高,分别为59.86%、59.47%和69.05%. 硅藻门常见属有脆杆藻、针杆藻、舟形藻、异极藻、布纹藻、羽纹藻、直链藻、小环藻,其优势种为中型脆杆藻(Fragilariaintermedia),尖针杆藻(Synedraacus)、短小舟形藻(Naviculaexigua)、弯羽纹藻(Pinnulariagibba)、颗粒直链藻(Aulacoseiragranulata)和粗壮双菱藻(Surirellarobusta);绿藻门常见属有鞘藻、转板藻、刚毛藻、丝藻、棒形鼓藻,其优势种为普林鞘藻(Oedogoniumpringsheimii);蓝藻门常见属有鱼腥藻、微囊藻、束丝藻、浮丝藻、颤藻,其优势种为固氮鱼腥藻(Anabaenaazotica)、阿氏浮丝藻(Planktothrixagardhii)、铜绿席藻(Phormidiumaerugineo-coeruleum)和鱼害微囊藻(Microcystisichthyoblabe).
2.4 着生藻类群落多样性及水质评价
鄱阳湖5个区域着生藻类的 Shannon-Wiener 生物多样性指数在 1.18~1.89之间,其中西部湿地(B区域)的Shannon-Wiener 种类多样性最高,平均为1.83,其余几个区域相差不大,为1.18~1.40,总体处于中等污染状态. 主航道区域(A区域)、西部湿地(B区域)、南矶湿地(C区域)和撮箕湖(D区域)的均匀度指数为0.45~0.82,属轻度污染状态;东南湖汊(E区域)的Pielou均匀度指数最小,说明该区域处于中污染状态. 东南湖汊(E区域)和西部湿地(B区域)的物种丰富度指数较大,说明这两个区域处于中污染状态(图4).
2.5 着生藻类群落结构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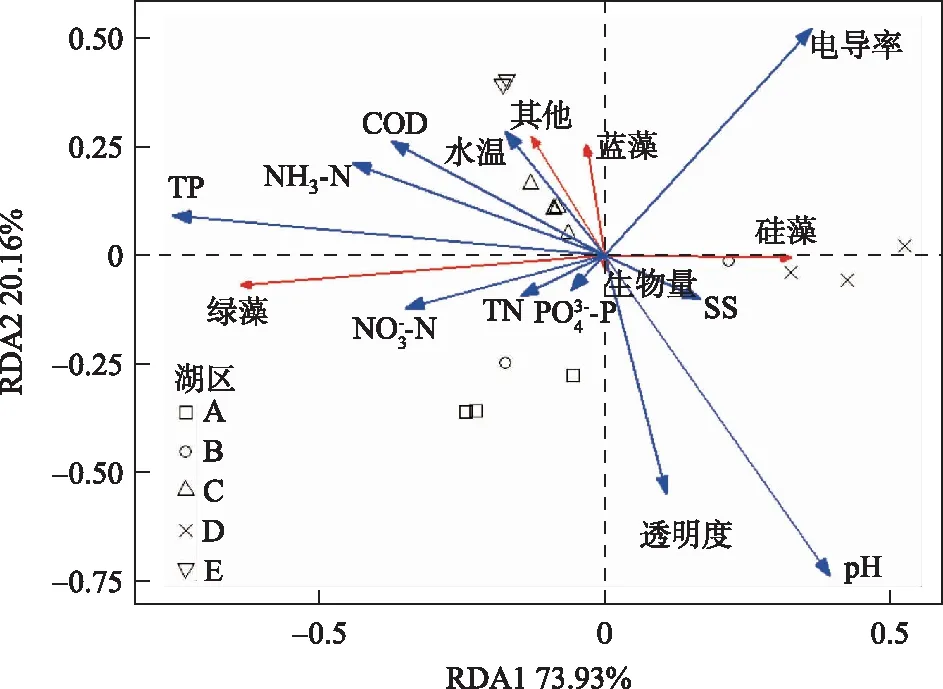
图5 鄱阳湖不同水域的着生藻类群落结构与环境因子的冗余分析Fig.5 The redundancy analysis of periphytic algae community structures and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in Lake Poyang
3 讨论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吞吐性、季节性和通江性淡水湖泊,其水位受“五河”入湖水量和长江水位顶托双重影响,年内水位变幅巨大,会导致鄱阳湖出现河湖转换的奇特景观,从而改变鄱阳湖的重要生境——水陆交错带的环境特征,进而会对其中的着生藻类产生巨大的影响. 本研究中,A区域为鄱阳湖与长江连通的主航道,从松门山至湖口,代表高流速湖区;B区域为西部湿地(吴城附近),季节性连通湖泊,与鄱阳湖水位存在高水位一致性、中水位相关性、低水位不相关;C区域为南矶湿地,丰水期为湖泊,枯水期为沼泽、泥滩浅水;D区域为撮箕湖,为典型的碟形洼地,是鄱阳湖典型的水陆交错带,丰水季节与主湖区水体连为一体,枯水季节独立蓄水,水位比较稳定;E区域为东南湖汊,涨水期受两条上游河流冲刷作用较大,枯水期为沼泽、泥滩浅水. 这些特殊的生境对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多样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着生藻类一般存在于附生、缠结或移动的着生生物基质中,并且由于群落中物种的组成和附着形式的差异,可形成不同的三维结构——缠绕、附着等[20]. A区域为鄱阳湖与长江连通主航道,该水域即使在枯水期也不与鄱阳湖的大湖面断开,因此,水流冲刷作用一直存在. 一般来说,丝状绿藻的定植和生长速度通常较慢,因此它们出现在较老的植物群落中[21]. 在主航道,牢固附着的着生藻类占优势地位,如鞘藻属(Oedogoniumsp.). 一般牢固附着种类在演替过程的开始就具有较强的粘附强度,如鞘藻(Oedogoniumsp.)通常附着在牢固的基质上[22]. 同时,这些物种在演替过程中还可以作为附着基质,为其他种类定植提供支撑或附着基质,这种方式使得它们不容易受到水流的物理扰动影响[23]. 高水位时期,在热分层条件影响下,丝状绿藻鞘藻会形成优势种群,因为它们一般垂直生长,从而能够接受到更多的光照和营养物质[24]. 另外,夏季较强烈的光照和较高的水温会促进丝状绿藻(如鞘藻)的生长[22]. 因此,主航道的着生藻类总生物量相对最高,且绿藻为优势种群.
无论着生藻类的原始群落结构如何,其群落构建都是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从敏感物种转变为更耐受的物种[25]. Pfeiffer等[25]对多瑙河漫滩的研究表明,水流扰动大大地改变了藻类群落,硅藻在春季占据主导地位,而由丝状绿藻组成的群落在夏季迅速生长并占优势. Dunck等[24]对亚马逊巴拿马运河洪泛平原的研究显示,席藻(Phormidiumsp.)和水绵(Spirogyrasp.)等多细胞藻类在高水位时期为优势种群,而钝脆杆藻(Fragilariacapucina)、爪哇脆杆藻(F.javanica)和鞘藻属(Oedogoniumsp.)等牢固附着种类在低水位时期占优势地位. 本研究中,西部湿地、南矶湿地、撮箕湖和东南湖汊4个区域的着生藻类生物量相对于主航道低,硅藻门占优势. 这4个湖区在丰水期与大湖面是连通的,枯水期与大湖面隔离. 这4个湖区的着生藻类在鄱阳湖的水位波动期间,会受到涨退水的影响. 首先,退水期间着生藻类被冲刷到下游,待枯水期时,着生藻类群落以重新定植的松散附着藻类为主,主要为具有高迁移率和繁殖率的硅藻(R策略)[26],如单细胞藻类由于其较小的尺寸而成为优势种群,并且由于它们具有移动能力,促使其在着生藻类基质内位移以寻找可用资源[24]. 枯水期这4个湖区与鄱阳湖大湖面隔离,其中的着生藻类不受水流扰动影响. 之后,在涨水期的水流冲刷作用下,这些松散附着的着生藻类被冲到下游. 本研究的采样时期为丰水期,在着生藻类的短期演替过程中,着生藻类同样以重新定植的松散附着藻类为主,这与Dunck等[24]的研究结论相同,即高水位时期着生藻类的优势种群以松散附着藻类为主. 这也是西部湿地、南矶湿地、撮箕湖和东南湖汊4个区域着生藻类总生物较低且其主要优势种群为硅藻的原因.

在水体持续混合的富营养化湖泊中,丝状绿藻为着生藻类的优势种群[36-37]. 本研究也有类似现象,大型丝状绿藻鞘藻、转板藻、刚毛藻、丝藻为常见属,鞘藻属为优势种. 有研究指出,富营养化会导致着生藻类大型物种的丰度高于微型物种[37-39]. 同时,本研究中着生藻类的优势种为中型脆杆藻(Fragilariaintermedia)、尖针杆藻(Synedraacus)、颗粒直链藻(Aulacoseiragranulata),这些均为中等富营养化水体的典型代表[36],因此,这也表明鄱阳湖具有一定程度的富营养化. 多样性指数是反映丰富度和均匀度的综合指标,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Margalef多样性指数、Simpson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等在湖库评价中应用较多[40]. 一般认为,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大于3时,水体为轻污染或无污染,指数为1~3时为中度污染,指数为0~1时为重度污染[40]. 鄱阳湖5个区域的Shannon-Wiener 生物多样性指数在1.18~1.89 之间,其中西部湿地的Shannon-Wiener种类多样性最高,其余几个区域相差不大,为1.18~1.40,水体处于中度污染状态[40]. 主航道区域、西部湿地、南矶湿地和撮箕湖的均匀度指数为0.45~0.82,属轻度污染状态;东南湖汊的Pielou均匀度指数最小,说明该区域属于中污染状态[41]. 东南湖汊和西部湿地的物种丰富度指数较大,说明这两个区域属于中污染状态[42].
4 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