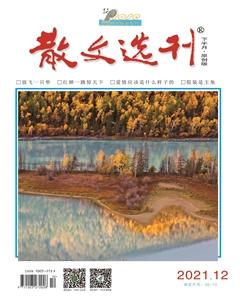走过古街
魏青锋

一个关系很好的同学,连着给我写了几封信,信末都不经意地提到她在小镇做一个前景很好的旅游项目,还特地说要在下个月提车,问我是大众好还是丰田好。朋友的信,对我产生了极强的诱惑力,在单位过得并不如意的我,跟经理请了长假,坐上了通往古镇的长途汽车。
跟同学七绕八拐,走进了半山腰的一栋居民楼的四楼,推开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张看到新人又泛着亮光的布满血丝的眼睛,三间房子打着地铺,地铺上放满了男男女女的行李,有几个挂着胸牌的男女,收走了我的身份證、钱包和行李。我狐疑地四处找同学,刚才还一脸温柔体贴的同学已不见了踪影,我紧紧抓着行李不撒手,突然,有一个身体壮硕、满脸横肉的胖子从里间冲出来,一耳光扇得我眼冒金星。
三天后,我在古镇的邮局给家里发了第一封电报,只有几个字:爸,速汇一千六百八,急用。在钱收到的五天后,又发了一封电报,这次是要3960 元,交了这笔钱,我就从业务员升为主管,在随后的日子,我的主要工作是上午听课,下午趴在凳子上给同学、朋友、亲戚写信,实际上是抄写,照着打印好的模板一遍一遍地抄,每天下午五点前,有人提了装满信的麻袋去邮局发。
半个月后,我被两个人一左一右押着,在古镇的邮局,给家里发了这个月的第三封电报。文质彬彬、一脸和颜悦色的刘总说了,交了这6800 元,我就可以升为主任了,三个月后,每个月就有工资和提成,等公司上市了还有股份和分红,可是我知道家里的情况,磨磨蹭蹭不想去,胖子又在我跟前晃来晃去,两个人就押着我去了邮局。
这次,钱一直没有收到,胖子又逼着我给家里写信,一天一封。
过了大约有一周时间,早上上课时,有人敲门,说是抄电表的,在外面转转又走了,人走后,房间里突然紧张起来,之前都是房东查电表水表,这次是个陌生人,再说电表在门外,打声招呼就行了,胖子带着几个人追了出去,一会儿胖子满头大汗地回来了,大家听到命令,立即开始收拾东西。
正在大家手忙脚乱的时候,派出所和工商所的一大群人冲进了房间,在一群人中间,我居然发现了满脸胡茬的父亲,父亲上前抱着我,眼泪扑簌簌地落在我的背上手上,有人握住父亲的手说:“谢谢你,老同志,你的伤要不要去卫生院包扎一下?”父亲忙不迭地掏出一包烟给大家发:“没事的,这点小伤。”我这才注意到父亲的手背蹭掉了一大块皮,裤子也烂了一个大洞,父亲领着我走出去,看着我疼惜的目光,故作轻松地说:“没事,刚才他们追我,摔倒了。”
天不知何时下起了雨,还刮着细细的风,我跟父亲在古色古香的古镇上走着,我才发现这是一个极其古典优美的古街,中间一条乱石嶙峋的小河,一股细流汩汩地流淌着,街两边都是雕梁画栋的老房子,房檐下的店有卖特产的,有饮食店,有超市,古色古香中又不失现代感。跟着父亲拐来拐去,居然进了一间香火缭绕的庙宇,父亲跪在一尊神像前,有些哽咽,一直在重复着:“儿子找到了,感念神。”我也跪着,头和手伏在地上,跟父亲不同,我的眼泪湿了脸,我心里在不断地忏悔。
从庙宇出来,在街口,我跟父亲在一个小摊上要了两碗米线,摊主像是跟父亲很熟的样子:“老哥,找到儿子了!”父亲脸上堆着笑:“谢谢你,找到了!”“那就好!”摊主先给父亲端了一碗米线,我的米线端上来时,摊主把碗“噔”的一声搁在我的面前,气愤地说:“这么大人了,搞什么不好,搞传销,你爸都来了五天了,一家一家找,每天晚上就在庙里的地上过夜,唉!”吃着米线,我的眼泪又不争气地掉下来,吧嗒、吧嗒地滴在碗里,良久,一双大手伸过来摩挲着我不断抽搐的肩背。
父亲要领我回家,我沉默了半天说:“爸,我不想回家,我就回单位了,我会好好的,你让妈不要操心。”父亲知道我爱面子,只叹了一口气,就在河边上了轮渡。看着轮渡消失在烟雨中,我眼睛红红地转了身。当天,我就离开了古镇,后来辗转很多地方,做医药销售,一步一步,五年前在汉江边的四线小城开了一家小医药公司。
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父亲那天上轮渡以后,下午又返回了古镇,在古镇不远的一家煤矿下了半年矿井,直到腊月二十九才回到老家,赶在除夕之前把借亲戚的五千多元还了。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里,我经常想起那时,父亲陪我走过那段古街,陪我走过那时的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