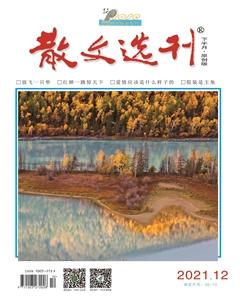小镇时光
徐群
浙东运河的足迹从春秋时期的山阴故水道悠悠走来,一艘艘满载的商船从这里出发,既可衔接京杭运河贯穿南北,也可抵达东海之滨,连通那条海上丝路。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喜欢上这片秦始皇南巡越地时驻跸饮马于潭的土地,还有,与京杭大运河同样悠远的浙东运河。
镇上的老街仍旧飘散着一种属于老底子的味道。街面石板铺地,店铺沿河而建,一家紧挨一家。店屋临河的一面皆杉木板壁,不上任何饰料或油漆,裸露着木材的原色,即使已被岁月染黑,木纹路也隐约可辨。窗是木的窗,门也是木板拼的,一切那么原始朴拙。
洞桥桥堍一爿古色古香的老茶馆,门口七星灶上坐了好几把茶壶,店主提壶续水进进出出忙碌。老茶馆像一个顿号,停顿在老街上。镇上的人,有事无事愿意去茶馆闲坐。一壶陈茶,二三旧友,也可泡个半日。日子如茶,苦涩过后终有回甘,浮浮沉沉皆是生活的滋味。
木桥弄旁的印糕店,味道最正宗。雪白米粉做的糕,豆沙、白糖芝麻的馅,糯柔甜香,印着“吉祥如意、福禄寿喜”等红字,不吃看着也舒服。
街河转弯处有家老式的早餐店,店里的生煎包实在好吃,外焦里嫩,皮香馅鲜,常常需排队等很久。有时我坐在店堂吃生煎,望见外面,大人手牵着背书包的孩子焦急地等在锅边,几双眼睛盯牢店主的每个动作,一直到丝丝缕缕的香味从木盖缝隙飘出来。随后,他们提着还烫手的生煎包,兴高采烈地离去。
“服装加工”几个字用毛笔写在一块旧纸板上,店门口摆着的那台老式缝纫机,一看便知是家裁缝店。阿娟的这个裁缝店,已经开了30 多年,从她一头秀发到如今的花白头发。以前小镇人做新衣裳都去她的铺子里,老老少少都喊她一声“阿娟姐”,一叫叫了这么多年。那时还没有缝纫机,做衣服全靠一针一线手工缝制出来。
立于村中老桥之上,满目的山水风光,那么生动、自然。眼前的这条河,一出镇便与姚西平原上的湖泊相交汇,水域变得宽阔大气,豁然开朗。没船也没有风的时候,清澈的河水如一面明镜,倒映着农舍、古树、炊烟、晚霞。有归鸟掠过天空,也有渔舟从夕阳的那头划来,意境深远。
几个老人坐在石栏上看渔家撒网,黝黑的脸上刻着饱经风霜的皱纹,眼神如面前的河水一样波澜不惊。桥下一群孩子正在水中追逐嬉戏。
废弃的船埠常有垂钓者,我总喜欢在一旁静静地观看。时间久了,自然便相熟了。一位叫老竺的钓友,天天出门,阴晴雨雪,从不间断。
即使钓了许久,也不见浮漂有半点动静,他照样不急不躁地盯着水面,有时一天下来,没有一尾鱼儿钓起,他也仍旧乐呵呵的,完全那种任来者来,随去者去的淡然。
听人家背后议论,他曾是省城一中学的美术教师,被错划“右派”,在监狱里度过了青春岁月。平反后分配到国营渔场,之后,娶妻生子,在小镇安家落户。
有一天,老竺突然告诉我说,不知为什么,当年整治他的那些人,早已像尘埃一样归于黄土了,唯有自己却健健康康地活着。所以他觉得,现在生活给予他什么,他都会淡然去接受。我知道,淡然并非天生的,那是经历跌宕起伏之后的感悟和超脱,或许只有历经了风雨的心,才能够领会和懂得淡泊的乐趣。
小镇至今还保留着老戏台,鲁迅先生笔下的那种,戏台半个搭岸上,半个在河里。
在新城区,前年建成了大剧院,请明星大腕儿来演出,票价上百元,还一票难求。有朋友请我看过一回,座椅很软、很舒适,但空间局促,腿腳难以伸展。我忍了,但忍不住场内令人窒息的空气。
在小镇的老戏台看戏,多在星空璀璨或月色朦胧之夜。微风吹来,带着一丝凉爽和河底水草淡淡的清香。“锵锵锵”的开场锣鼓一敲,戏文便开演了。
看戏最较真的要数老人及妇女们。其实这些戏文他们看过好多遍了,情节唱词莫不烂熟于胸,但唯有如此,才甘于接受,更乐意欣赏。演到哀婉凄绝时,看戏的禁不住伤心落泪;唱到精彩动情处,台下的也忍不住跟着哼起来,一时台上台下响成一片,热闹极了。
时光就这么不经意地从小镇最平凡的日常中溜走。现代都市的拥堵嘈杂,传统山村的偏僻闭塞,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小镇,恰到好处地把日子过得平静、真实,又充满暖意。这样的日子,令城市人向往,无疑也是我最钟情的生活方式。
尽管不愿意,我还是从街弄间斑驳的古旧建筑中,一眼认出它掩不住的沧桑与摇摇欲坠。那些蕴含着人文历史与风土民俗的灵魂已被光阴,或者某些比光阴还要残酷的东西所侵蚀。我开始有些担心,与小镇相安无事的清润日子还能过多久?
幸好我已听说,关于小镇修复改造的一个远景规划正在有序地推进。但另一种忧虑又隐隐地产生了,不久的某一天,曾经安逸风雅的小镇,会不会改建成一座仿古建筑的小镇,俨然商业旅游小城呢?
也许,是我想多了,但我依然想做点什么。我发了几张小镇的旧照片到网上,不承想,居然得了好多赞。也有人一个劲问我在哪?我故意不告诉,让她自己去猜。
面前的这条河缓缓流来,又款款逝去,从不问身边的悲喜,始终做着它自己的一个沉睡了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