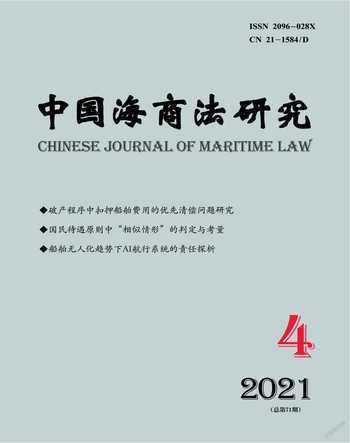商事条约的约定适用: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的二元路径
张普
摘要:意思自治源自于契约自由,而又有别于契约自由。当事人可以基于契约自由将商事条约约定为合同的一部分,也可以基于意思自治将商事条约选择为准据法。虽然两种路径均能够实现条约的约定适用,但不同的法律基础导致二者在适用范围、条约查明与举证责任、条约的具体适用与解释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与契约自由路径相比,意思自治路径中当事人对商事条约约定适用的条件更为严格,但从司法效果来看,该路径更有利于商事条约的充分适用。
关键词:条约适用;约定适用;契约自由;意思自治
中图分类号:D997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28X(2021)04-0100-10
The application of commercial treaty based on agreement:
the dual path of freedom of contract and autonomy
ZHANG Pu
(School of Law,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Autonomy originates from freedom of contract, but differs from it as well. With the freedom of contract, the parties can incorporate the commercial treaty into the contract. Based on autonomy, the parties can select the commercial treaty as the applicable law. Although the parties can realize the application of commercial treaties through both freedom of contract and autonomy, different legal bases of the two paths lead to differences in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treaty identification and burden of proof, and specific appl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eaty. Compared with the path of freedom of contract, if the parties choose the path of autonomy, they will have more strict condi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commercial treaty,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dicial effect, this path of autonomy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full application of commercial treaty.
Key words:application of the treaty; application from agreement; freedom of contract; autonomy
一、問题的提出
随着商事条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当事人约定适用条约的现象十分常见。商事条约能否被当事人选择成为准据法是国际法领域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对于该问题,传统国际私法理论持否定态度。然而,受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近年来国际上也出现了承认当事人选择商事条约作为准据法的观点和立法动向。就中国法律体系而言,对于条约适用问题的规定一直模糊不清,[1]而对于商事条约能否被当事人选择成为准据法的具体问题更无明确规定。总体上讲,中国学界不乏秉持传统国际私法理论的观点,但是司法实践却呈现出认可当事人选择商事条约为准据法的态势。
基于对私法自治原则的坚持和善意适用条约的国际法义务,在当事人约定适用条约的情况下,法院应当积极考虑适用条约。然而,又因条约性质、效力等因素,并且诉讼自身也有别于完全以私法自治为基础的商事仲裁,法院又不能完全依照当事人的选择而适用条约。如何平衡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处理条约约定适用问题的关键。
事实上,由以上问题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均值得思考。例如,当事人能否约定适用商事条约?何为其法律依据?当事人又如何约定适用商事条约?何为其约定的方式和时间?当事人约定适用商事条约将产生怎样的法律效果?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研究鲜有涉及,但又都是商事活动与司法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笔者首先对私法自治领域内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的内涵及发展进行分析,在对二者共性进行透析的同时,更加侧重于对二者差异的辨析。之后,以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二元性为逻辑起点,明确商事条约约定适用的二元路径,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为核心的契约自由路径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简称《法律适用法》)为核心的意思自治路径。其后,对两种路径的区别加以分析和评判。最后,依据《民法典》《法律适用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对两种路径的具体实现进行阐述。
二、契约自由路径与意思自治路径下商事条约约定适用的理论基础
(一)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的内涵与发展
合同实体法领域的契约自由与国际私法领域的意思自治是私法自治的两大体现。契约自由是指合同的成立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为必要,合同权利义务仅以当事人的意志而成立时,才具有合理性和法律上的效力。[2]而意思自治是指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自由选择支配合同的准据法。[3]从内涵与发展上看,意思自治源自于契约自由,而又有别于契约自由。
以法律思想与立法形式为表征的法律更迭,其根源都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商品经济的出现促使社会秩序形态发生转变,从而形成了以个人合意为特征的新的社会秩序。[4]在这种新的社会秩序下,人们可以通过订立契约为自己创设权利和义务。[5]25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理念,契约自由在罗马法中得以确立、发展和传承。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罗马法就是契约自由思想由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生成史。[6]而这种思想历经千年,至今仍然焕发着生机。
随着契约自由理念的不断成熟,其影响面也逐渐扩大。意思自治即为契约自由逐渐向国际私法领域延伸和渗透的结果。长时间以来,意思自治都是国际私法中合同领域确定准据法的首要原则。20世纪后,意思自治逐渐被广泛认可和接受,其也逐渐突破传统的合同领域,向其他非合同领域拓展,如侵权、动产物权、婚姻家庭、继承等。在私法自治理念的进一步推动下,近年来意思自治呈现出多维度、深层次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其一,意思自治已经突破冲突法领域而向国际民事诉讼程序等领域拓展。如在国际民事诉讼管辖问题上,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已经赋予当事人选择法院的权利;其二,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而选择法律的范围也有增大的趋势。将准据法选择范围严格限制于国内法的传统国际私法理论之基础已经开始动摇,国际上已经出现承认当事人选择商事条约作为准据法的观点和立法动向。
早在1986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起草时,就曾出现过允许当事人选择商事条约等非国家法作为准据法的提议。1994年《美洲国家间关于国际合同法律适用公约》通过后,该公约的制定者之一Parra Aranguren教授也曾表示,“合同应受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支配”中的“法律”不仅包含国内法,还包含商事条约、国际惯例等非国家法。[7]以上提议与学者观点虽然并未在立法中得以呈现,但可表明传统理论已经开始遭到质疑。
2015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原则》(简称《海牙原则》)首次突破性地明确对商事条约作为准据法的认可,其第3条规定:“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可以是国际、跨国家或区域范围内作为一套中性、平衡规则被普遍接受的法律规则,除非诉讼地法律另有规定。”并且,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还在对《海牙原则》第3条的注释中举例明确了当事人选择《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简称CISG)的准据法效力。[8]虽然《海牙原则》作为“软法”,只能在法院地法许可的范围内得以适用,[9]但是其顺应当下国际商事发展而对当事人选择法律范围进行拓展的立法理念值得各国认真研究和借鉴。
(二)商事条约约定适用的二元路径
契约自由是民商事法律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①,也是合同法的根基。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契约自由贯穿于合同法的始终。[10]虽然中国合同法的呈现形式几经变迁,但均对契约自由予以确立和保护。作为契约自由的有机组成部分,确定合同内容的自由被《民法典》第470条所明确承认:“合同的内容由當事人约定。”并且这种依法成立的约定,应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①。基于这种契约自由的思路,当事人可以将商事条约并入合同成为合同的一部分,进而明确权利和义务。该方式又被称为“实体法上的选择”或“实体法上的指定”。[11]
与之相对应的是“冲突法上的选择”,又称为“冲突法上的指定”。该方式是基于国际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对商事条约的约定适用。就意思自治而言②,其在中国立法中的确立体现于《法律适用法》第41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基于这种意思自治的思路,当事人又可以通过约定将商事条约选择为准据法,进而实现对该条约的适用。
对于这种基于意思自治而约定适用商事条约的方式,传统国际私法理论并不认可。传统理论认为,准据法的选择应严格限制在各国国内法的范围之内,当事人并不能选择商事条约作为准据法。其原因主要有:[12]182其一,从立法目的看,国际私法是为了解决国家法之间的冲突问题,因而只能在国家法中选择准据法;其二,从法律条文看,一些国家的国际私法所表述的是“国家的法”或“地(法域)的法”,而不包含商事条约等非国家法;其三,从作用效果看,允许当事人选择商事条约可能出现规避强行法的现象;其四,从条约特征看,条约类型多样、性质各异,可作为准据法的标准难以统一,[13]且条约也缺乏明确性、完整性和体系性。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均遵循传统国际私法的观念。多数国际私法性条约,如1980年《关于合同之债准据法的公约》(简称《罗马公约》)、2008年《关于合同之债准据法的规则》(简称《罗马I规则》)等也如此规定。但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将商事条约约定为准据法往往会得到法院支持。即使选择的是中国未缔结或加入的条约③,一些法院也会将其当作准据法来看待。正如2004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涉外商事审判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简称《广东高院指导意见》)第43条所规定的那样:“当事人在合同中选择我国未参加的国际公约作为合同准据法的,只要所选择的公约是一个能够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国际统一实体法公约,而不是一个关于程序法或冲突法的公约,并且适用该公约不违反我国的公共秩序,就应当认定当事人的法律选择有效。”这种司法实践及观点,亦有学界的支持。如有学者认为,中国法院应当允许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而将商事条约作为准据法,并且当事人不但可以选择对中国已经生效的条约,还可以选择对中国未生效的条约。对于对中国生效的条约,允许当事人进行选择是法律规定的应有之义。而至于对中国未生效的条约,只要不与中国的公共秩序相违背,就应当允许当事人进行选择④。尽管《广东高院指导意见》与以上学者观点并未得到统一认可,学界和实务界对当事人法律选择的范围尚存争议,但从中国司法实践来看,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将商事条约选择为准据法的做法是被认可的。
综上,就商事条约的约定适用而言,在中国存在两种路径。一种为契约自由路径,当事人可以将商事条约并入到合同之中成为合同的一部分。另一种为意思自治路径,当事人可以选择商事条约作为合同的准据法。
(三)意思自治路径下当事人选择商事条约的范围
虽然中国允许当事人选择商事条约作为合同的准据法,但是当事人能够选择什么样的商事条约作为准据法呢?对此,《法律适用法》并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简称《法律适用法解释》)也并未说明。实务界实践不一,学界更是观点各异。因此,有必要对该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就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而言,《法律适用法》第9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不包括该国的法律适用法。”该条款只是将准据法的选择范围限定于实体法当中,而排除冲突法的适用。其解决的是国际私法中的反致问题,并不涉及条约的可选择性。
笔者认为完全否定商事条约准据法适格性的保守观点与赋予所有商事条约准据法适格性的激进观点均有待商榷,对于该问题的回答难以一概而论,也不应一概而论。传统观点完全否定当事人选择商事条约作为准据法的做法已不合时宜,而对商事条约不加区分认为其均可以作为准据法的观点也有违国际法的基本原理。
从国际法角度看,国际私法的目的确实是为了解决国家间的法律冲突问题。20世纪以前,商事条约并不多见,因而当事人选择条约的可能性很小,[12]182当时处理法律冲突问题也多是通过各国国内的冲突法规则来解决。因而传统国际私法理论是以冲突法解决方式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但随着20世纪以来私法统一运动的发展,商事条约大量出现,其发展也日渐成熟。当前,解决国家间法律冲突问题的途径已经不再局限于通过冲突法选择准据法,制定统一的商事实体条约亦是一种方式。[14]从国内法角度看,国际私法的形式与内容完全可依据国家的立法主权进行确立和调整。一国对于是否承认当事人意思自治、如何实现意思自治等事项具有绝对的管理权。现代国际私法领域中“直接适用的法”、公共秩序保留、单边冲突规范等制度和立法技巧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规制,从而实现特定的立法目的。可见,随着国际私法内涵的丰富与立法技巧的提升,传统国际私法法律选择的观念也应有所转变。另外,契约自由向意思自治的演变也好,意思自治的多维拓展也罢,私法自治内涵的发展历程展现出这样一个事实:尽可能地满足当事人对于私法权利的自由与自治需求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海牙原则》的产生即是对当下国际商事发展需求的回应。
同时,又必须承认条约类型多样、性质各异,以及国际法碎片化的特点确实使得条约的适用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国际法并不像国内法一样体系完整。另一方面,条约类型的多样化可能使得当事人甚至是法院并不能准确适用条约①。然而,不论条约的呈现形式与适用多么复杂,一个基本的逻辑和事实是,国家可以通过综合考量而选择性地缔结或加入某一条约,也只有对于缔约国生效的条约才应被遵守和适用。故而,对于中国生效的条约,中国法院将其作为法律而进行适用是理所当然的。而至于对中国尚未生效的条约,自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实践中,当事人选择中国未缔结或加入的条约时,中国法院做法不一。有法院将其视为准据法,有法院将其视为合同的一部分,更有法院将其视为国际惯例。而最高人民法院曾在该问题上进行过一定阐述:“既然是对我国尚未生效的国际条约,该条约对我国没有拘束力,不能将其作为裁判的法律依据。”[15]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条约能否当作准据法的问题上言辞含糊,但至少已经明确不能将尚未对中国生效的条约作为法律。有鉴于此,当事人若要约定适用对中国尚未生效的条约时,将其作为合同的一部分则更为保险。
基于对国际法基本理论和中国司法实践的考量,笔者认为意思自治中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应包括商事条约,但应当只包含对中国已经生效的商事条约。而对中国并无效力的商事条约,应否定其作为准据法的适格性。
三、契约自由路径与意思自治路径下商事条约约定适用的本质区别
不论将商事条约當作合同的一部分还是当作准据法,如果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依法有效,便均能够实现依据该条约来判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目的。由此可见,两种方式在明确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上的作用是一样的。在法律推理的三段论中,二者均属于“大前提”②, 是法院对法律事实进行评判的理由和依据。然而,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不同的理论根源与法律基础使得二者在适用范围与法律效果上将产生一定的差异①。
(一)法律基础与适用范围
将商事条约并入到合同的法律基础为《民法典》所秉持的契约自由,其本质是私法领域内当事人对民事权利的行使。契约自由路径下,当事人将商事条约当作合同的一部分而进行约定是一种民事行为。因而,只要当事人对于条约进行约定适用的行为不违反中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公序良俗即可。事实上,合同领域的实体法多为任意性规范,强制性规定并不多见。《民法典》也对私法自治给予了充分认可和保护,因而当事人将商事条约并入合同的阻碍并不多。
将商事条约选择为准据法的法律基础为《法律适用法》所承认的意思自治。从法律性质上看,《法律适用法》与《民法典》最大的不同在于国际私法的强制性,即不以当事人的意志而定,法院应当强行适用。与私法领域所秉持的“法无明文规定即自由”的理念不同,国际私法的适用应遵循“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对于这种“授权”应作两个层次的理解:是否允许当事人选择准据法应由《法律适用法》来决定②,当事人如何选择准据法也应当由《法律适用法》来决定。依据《法律适用法》与前文对当事人法律选择范围的分析来看,当事人若要将商事条约约定为准据法,应当满足两个条件。
其一,合同具有涉外性。这是由《法律适用法》的涉外性所决定的。《法律适用法》是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因而只有涉外合同才允许当事人选择商事条约作为准据法。
其二,条约已经对中国生效。条约生效是中国法院对其进行适用的基础。也只有对中国生效的条约才能被法院“放心”适用。在缔结或加入条约时,中国往往会通过声明保留排除对中国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条款的适用。而对中国未生效的条约很可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15]
综上,契约自由路径与意思自治路径的法律基础并不相同,前者的法律基础是《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而后者的法律基础是《法律适用法》的相关规定。与意思自治路径相比,契约自由路径中的“自由”可体现于两方面:其一,当事人可以对任何合同进行内容的约定,不论其是否具有涉外性;其二,当事人可以将任何商事条约并入到合同之中,不论其是否对中国生效。可见意思自治路径的适用条件较为严格,因而适用范围较窄。当事人只有在涉外合同中将对中国生效的商事条约约定为准据法才能被认可。而将商事条约并入到合同的方式并没有这些限制。
(二)条约查明与举证责任
在涉外民事司法实践中,法律的查明问题一直都是制约审判效率的瓶颈问题。[16]商事条约约定适用中该问题应至少涉及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谁有义务去查找或提供条约?其二,不能查找或提供条约的后果如何?
当事人依据意思自治而将商事条约约定为准据法时,条约的查明问题应由《法律适用法》来规定。《法律适用法》对于外国法的查明采取了以法院查明为原则,以当事人提供为例外的态度③。具体而言,中国法院应承担外国法查明的义务,而只有在当事人约定适用外国法的情况下才应当由当事人提供外国法。事实上,根据绝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一般理论,法官均负有查明准据法的责任。对于在当事人选择外国法为准据法时由当事人提供外国法的规定,多是从及时而正确地适用外国法的政策性考虑出发的。[12]179至于当事人约定商事条约作为准据法时的条约查明问题,笔者认为由法院进行查明更为合理。首先,当事人能够约定为准据法的商事条约应当是已经对中国生效的条约,适用该条约是中国法院的国际法义务,这种义务自然包含查明该条约。其次,CISG等对中国已经生效的商事条约已经成为中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④,法院应当具有知法、查法的国内法义务。最后,外国法种类繁多,形式各异,法律要求当事人提供外国法是为了及时、正确地适用该外国法,而条约相对于外国法更为清晰、明了,法院也更易查明。《广东高院指导意见》就曾规定了法院的条约查明义务①。
《法律适用法》第10条第2款规定:“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此,当作为准据法的商事条约不能被查明或者该条约内容并不涉及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时,当事人将商事条约当作准据法的目的也将难以实现。此时,法院应当直接适用中国法律,而断不能拒绝裁判。
如果当事人将商事条约并入到合同中,其实质是将该条约作为合同中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整体性概括。在诉讼中,合同的内容需要当事人进行主张并举证。[1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而,当事人依据作为合同内容的商事条约而主张权利时有义务提供证据,即提供相应的条约内容。此时,法院可能会基于以下原因并不适合主动查明条约:其一,条约在中国并不发生效力,中国法院并无适用条约的义务;其二,对于中国未缔结或加入的条约,法院可能并不熟悉;其三,当事人可能会基于契约自由而对条约的相关规则进行“改造”,此时当事人应结合条约明确其合意,以防止法官主观推测。
如果当事人不能提供相应的条约内容或提供的条约内容不够明确,则法院可以驳回当事人的主张。此时,当事人对于商事条约的约定并不产生任何国际私法上的效果。至于法律的适用问题,应当依据中国法律进行判定。
(三)条约的具体适用与解释
在意思自治路径下,商事条约可以作为法院裁判的准据法。因而法院是将该条约作为“法律”来判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此时,法院应当注重条约作为一个小型法律体系的内部自洽性,同时还应当注重适用和解释条约时的统一性。因为商事条约的目的即为解决各国法律冲突问题,进而建立统一的国际商事秩序。商事条约的制定和接受只是条约在形式上的统一,而各国法院统一适用和解释条约才能实现实质上的统一。[18]243故而,法院在适用商事条约时应当对条约的官方说明、指引,甚至是其他国家的判例予以主动、充分地考虑,即使这种判例并不具有约束力和决定性,也应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19]在解釋条约时,法院应当适用适合于商事条约自身解释的原则、规则和方法,而不应受国内法中相关规则的限制。[18]240事实上,从目前商事条约的实施来看,国际组织为了各国法院统一适用和解释条约也经常对条约的适用进行一定的说明和指引。例如,为了统一和准确适用CISG,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简称贸法会)已经发布了四版《关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判例法摘要汇编》(简称《摘要汇编》)。《摘要汇编》不仅就CISG的具体条款进行了解读,还配有案例说明。此外,贸法会还建立了“判例法数据库”以提供各国适用CISG的案例。虽然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这些案例对中国也并无约束力,但贸法会的《摘要汇编》与案例指导应成为中国法院适用CISG时的重要参考和依据,法院也应当主动对它们进行考量。
当商事条约被当作准据法时,不论是基于缔约国的条约适用义务,还是基于国际私法的基本原理,法院都负有统一适用与解释条约的职责。如果法院对于商事条约的适用或解释有悖于该条约的基本原则,或与官方说明、指引、其他判例等有较大出入,则有可能被认定为是适用法律的错误,当事人有理由对此提起上诉,并应得到支持。
在契约自由路径下,商事条约只是被整体纳入到合同之中。此时,该条约已经褪去了“法律”的属性而成为“合同的内容”。法院在依据条约内容来判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时,应当更加注重对当事人合意的真实还原,而非意思自治路径下对条约适用时国际性和统一性的首要追求。条约的官方说明、指引、判例等往往需要当事人提供给法院,法院一般不会主动进行查明和参考。因为,此时的条约已经不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法律”,法院并不承担适用条约的义务。在需要对条约内容进行解释时,除非条约自身规定了解释方式②,法院更多的是依据《民法典》中对合同进行解释的相关规定进行解释③。可见,在契约自由路径下对商事条约的适用与解释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国内法的规定,而缺乏意思自治路径下的自我体系化。
此时,由于商事条约被当作合同的一部分,当事人有责任提供条约的内容。诉讼中法院的任务在于依据当事人的主张对事实和证据进行查明,其并无统一适用和解释条约的义务。而且,基于对因约不必充分原则的考量①,在裁判中如果法院对于条约内容的判定与其他判例、指引,甚至是官方说明有所不同,只要当事人予以认同,并不违背他们的依法合意,则不应是事实认定的错误,更不可能是法律适用的错误。
四、契约自由路径与意思自治路径下商事条约约定适用的实现方式
(一)商事条约约定适用的表现形式
如前文所述,当事人将商事条约选择为准据法应满足合同具有涉外性和条约对中国已经生效两个条件。因而,意思自治路径下对于商事条约约定适用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为当事人明确约定将对中国生效的商事条约作为涉外合同的准据法。
对于并不满足以上两个条件的情况,当事人应当将商事条约作为合同的一部分。具体而言,有如下情况。
其一,当事人在非涉外合同中载明约定适用的商事条约的内容。《法律适用法》的基本目的是明确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②。因而,意思自治应严格限于涉外合同的准据法选择中。依据《法律适用法解释》的规定
③,《法律适用法》中的“涉外性”是指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法律事实三个要素中至少有一项具有涉外因素。对于以上三要素均无涉外因素的非涉外合同,当事人断不能将商事条约约定为准据法,而只能将该条约的内容纳入到合同之中。
其二,当事人将对中国不具效力的商事条约的内容并入到合同之中。不具效力的条约包括已经生效但中国未加入的条约、中国已经加入但尚未生效的条约、中国已经加入但已失效的条约。该情况下,如果条约内容不违反中国公共利益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应当依据条约内容来确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④。此时,这些商事条约应当被视为当事人之间合同的组成部分⑤。[15]就具体做法,最为稳妥的方式是将所选商事条约中那些不違背中国法律中强制性规定的内容以合同条款的形式加以确定。实践中,由于某些商事条约具有较多的缔约国,且条约自身规定了较为宽泛的适用条件,当事人容易误以为即使中国没有加入这些条约,也可以将其中的规定按照国际商事惯例来适用。因而只是在合同中笼统地提及适用该条约,甚至并不加以约定而认为法院会自动适用。如此约定适用商事条约的做法存在一定的风险,甚至是错误的。[20]因为这些条约中的规定不一定是国际商事惯例,而且纵然是国际商事惯例,也并不能当然地约束当事人,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还需要以当事人明示约定为前提。[21]
此外,当事人还可以通过约定将商事条约适用于那些其本不应当调整的合同。与一国完整而缜密的法律体系不同,商事条约往往只是就某一特定法律关系而制定的。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将商事条约适用于那些本来因为不符合适用规则而不应当适用该条约的合同。例如,CISG虽然并不适用于以个人使用为目的的货物销售合同⑥,但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将CISG适用于该合同。此时应当将该条约当作合同的一部分,而不能作为准据法⑦。因为如此适用商事条约往往源自于对契约自由的认可,而非意思自治。但此时应当注意,合同与商事条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匹配度越低,当事人对于条约的选择越应当慎重,因为为特定法律关系量身定制的商事条约可能并不适合当事人的合同。例如,CISG中对当事人法律救济的体系是专门为“货物销售”合同而定制的。[22]
(二)契约自由路径下商事条约约定适用的实现方式
基于契约自由对商事条约的约定适用, 其本质为合同的订立,即将商事条约并入到合同的行为应内化于合同的订立过程。因而,此时对于商事条约的约定适用应当依据《民法典》有关合同订立的相关规定。
1.约定的方式
依据《民法典》第469条之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民法典》对于合同订立方式的规定较为宽松,尤其是“其他形式”的兜底性表述。据此,当事人可以采用上述方式对商事条约进行约定适用。但此时还应遵守《民法典》第135条之规定,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特定形式的,应当采用特定形式。例如,如果当事人已经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方式进行合同的订立,那么当事人也必须以书面形式来对商事条约的适用进行约定。
至于何为书面形式,《民法典》第469条第2款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电报、电传、传真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可见,当事人对于商事条约适用的约定只要可以被有形地表现出来,则应当被认可。实践中,虽然书面形式有多种,但当事人通常更倾向于采用订立合同书的形式进行商事条约的约定适用,以避免“口说无凭”的情况。
近些年,随着数字经济,尤其是跨境电子商务的兴起,电子合同所涉及的条约适用问题也日渐突出。为满足对电子合同的法律规制,《民法典》也将“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归为书面形式的范畴。在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为依托的电子合同中,当事人也能实现对商事条约的约定适用,但应当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对于商事条约约定适用的合意应当能够有形地表现出来,这是由书面形式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其二,对于商事条约约定适用的表述应当可以随时调取查用,这是由数据电文虚拟性的特征所决定的。如若涉及条约约定适用的数据电文不能被调取查用,也就丧失了书面形式内容明了、便于取证的优势。将“可以随时调取”作为有效约定适用商事条约的条件也符合国际做法。例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第6条就规定,假若一项数据电文所含信息可以调取以备日后查用,即满足了书面形式的要求。
2.约定的时间
在中国,合同的订立采用要约与承诺的方式。《民法典》第483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故而在合同成立之前,当事人均可以对商事条约的适用问题进行约定。
此外,在合同成立后当事人也有可能对商事条约的适用进行约定,此时应当将这种约定视为对合同的变更。这种变更是为《民法典》所认可的①,但需满足“明确”的要求②。如果当事人未对条约的适用达成明确的合意,或虽然达成合意,但对条约项下权利义务关系并未进行明确,则实难认定为当事人对合同进行了有效变更,此时对于商事条约适用的约定也就不能发生效力。
(三)意思自治路径下商事条约约定适用的实现方式
基于意思自治的商事条约约定适用,其本质是对准据法的选择。此时,应当根据《法律适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来进行对商事条约的约定适用。
1.约定的方式
就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法律适用法》第3条作了较为笼统的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可见,中国只承认当事人明示的选择。至于何为明示,《法律适用法》与《法律适用法解释》并未说明。一般认为,所谓明示选择,即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等明确的方式进行法律选择。书面形式可以参考《民法典》之规定。当事人以书面形式选择商事条约为准据法的行为应认定为明示的选择。口头形式的实质与书面形式并无区别,都为当事人对于法律选择的合意。只是与书面形式相比,口头形式的合意往往存在举证方面的困难,[23]只有存在确凿证据足以证明当事人确实已经就将商事条约选择为准据法达成了合意,才能承认其效力。但口头形式与书面形式一样,都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
在实践中,还可能存在一种特殊的情况,即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援引相同的商事条约且均未对法律适用问题提出异议。该情况下,笔者倾向于将其认定为明示的方式而认可当事人将商事条约作为准据法的选择。对于该情况的规定可参考《法律适用法解释》第6条第2款:“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 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该条款所指“相同国家的法律”中的“法律”应当包含对中国已经生效的商事条约。因为对中国生效的商事条约应为中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该情况下,“相同国家”的“法律”應具体为对“中国”已经生效的“商事条约”,进而认定为当事人已经选择了准据法。之所以将其认定为明示的方式,原因有三:其一,就法律选择的方式而言,应当关注的是行为,而非结果。所谓明示,即行为本身的明确。事实上,当事人也只能支配自己选法的行为,至于其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应由法院进行判断,当事人往往既无能力也无权利来认定。只要当事人有意思自治的行为,就应当认为进行了法律选择。其二,默示选择之所以不被普遍认可,主要原因是对于默示意思表示的确认是由法官来推断,因而很可能产生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甚至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而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援引相同商事条约的行为并不会造成法官的自由推断,反而使得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更加明确。其三,将该种行为归为明示选择也更利于规则之间的自洽。《法律适用法》第3条已经明确规定了中国采纳明示选择的意思自治方式。如果将上述行为认定为对默示选择的认可,则有悖于《法律适用法》之规定。
2.约定的时间
当事人通常会在订立合同时对法律的适用问题进行约定,而至于合同订立后当事人还能否协议选择或变更适用的法律,答案应当是肯定的。《法律适用法》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拓展后,有必要对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时间进行明确。[15]然而,《法律适用法》对此并未规定。而随后的《法律适用法解释》对该问题进行了说明: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协议选择或者变更选择适用的法律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该规则对于商事条约的约定适用问题有两层含义:其一,就时间节点来说,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均可以对商事条约的适用进行约定;其二,就选法效果来说,当事人对于商事条约适用的约定既可以是对准据法选择的初次确认,又可以是对已选法律的再次变更。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律选择的时间问题上,有些国家的法律和条约允许当事人在“任何时候”或“随时”(at any time)作出法律选择,如《联邦德国关于改革国际私法的立法》①、《瑞士联邦国际私法》②、《罗马公约》③以及《罗马I规则》④等。有学者认为以上规定应当允许当事人在二审过程中选择法律。[24]基于此,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应当进一步放宽当事人选法的时间限制。[25]事实上,在西方法律文化中,“at any time”是指法院未就实质问题作出判断前的任何时候,而并非整个诉讼的任何时候。[5]32在中国,法院对于实质性问题进行判断也正是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之后。因而,中国关于当事人选法的时间规定与上述国家的法律与条约规定并无本质区别,且《法律适用法解释》的表述也更为精确。
五、结语
为了尽可能与世界接轨,中国众多法律的制定都借鉴了相关条约,如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等。[26]但这尚不能达到制定条约的预期。在商事活动中,适用条约仍具有较大的优势。具体而言,当事人可以通过契约自由路径和意思自治路径实现对商事条约的约定适用。基于对契约自由的尊重,当事人可以将其希望适用的任何条约内容纳入到自己的任何合同中,只要当事人觉得这些条约内容可以解决问题即可。然而,基于意思自治对条约的适用要受到《法律适用法》的约束,其对条约约定适用的条件也较为严格,但司法效果更有利于条约的充分适用。
从根源上讲,中国条约适用问题的困境源自于中国法律体系中相关规定的欠缺。《民法典》对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的放弃使得该问题更为突出。至于商事条约的约定适用,目前更是无法可依。这也就直接造成在当事人约定适用商事条约时,中国法院裁判不一,学界也观点各异的局面。从国际私法的基本功能看,当事人能否选择适用条约应由《法律适用法》予以明确。虽然传统国际私法观点对此持否定观点,但是从中国司法实践与意思自治的最新发展动态来看,允许当事人在一定情况下选择商事条约作为准据法更为合理。在中国力争国际法话语权的当下,[27]涉外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已为中国司法国际化搭好了戏台。至于如何唱好这出戏,商事条约的适用水平、法律体系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将起到很大作用。就现代化而言,中国立法应当顺应商事发展的需要,尽可能满足当事人对于私法自治的追求。就国际化而言,中国立法应重视与国际法的衔接,进而实现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车丕照.《民法典》颁行后国际条约与惯例在我国的适用[J].中国应用法学,2020(6):2.
[2]李永军.从契约自由原则的基础看其在现代合同法上的地位[J].比较法研究,2002(4):1.
[3]韩德培.国际私法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214.
[4]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11.
[5]徐伟功.法律选择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的运用[J].法学,2013(9).
[6]蒋先福.契约文明:法治文明的源与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90-91.
[7]JUENGER F K.Contract choice of law in the Americas[J].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1997,45(1):204.
[8]HCCH.Principles on Choic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EB/OL].(2015-03-19)[2021-05-17].https://www.hcch.net/en/instruments/conventions/full-text/?cid=135.
[9]SYMEONIDES S C.The Hague Principle on Choice of Law for International Contracts:some preliminary comments[J].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2013,61(4):894.
[10]江平.民法学[M].2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582.
[11]李旺.国际私法[M].3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63.
[12]李旺.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国际条约的适用[J].清华法学,2017,11(4).
[13]森下哲朗.国際商取引における非国家法の機能と適用[J].國際法外交雑誌,2008,107(1):35.
[14]李双元.走向21世纪的国际法——国际私法与法律趋同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6-27.
[15]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人就《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答记者问[EB/OL].(2013-04-23)[2021-05-07].http://www.court.gov.cn/shenpan-xiangqing-5275.html.
[16]高晓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解读[J].法律适用,2013(3):44.
[17]石黑一宪.國際私法[M].新版.东京:有斐阁,1990:286.
[18]杜焕芳.国际私法条约解释的路径依赖与方法展开[J].中国法学,2014(2).
[19]STRUYCKEN A V M.Interpretation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treaties:introductory remarks[C]//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Hagues 750th Anniversary.Hague:T. M. C. Asser Press,1999:135.
[20]傅廷中.国际海事惯例的适用之反思[J].社会科学辑刊,2020(5):108-110.
[21]车丕照.国际惯例辨析[J].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6(5):58.
[22]SCHLECHTRIEM P,BUTLER P.UN law on international sales: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s of Goods[M].New York:Springer-Verlag,2009:21.
[23]田晓云.意思自治原则确定涉外合同准据法比较研究[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3):23.
[24]秦瑞亭.国际私法[M].2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193.
[25]凡启兵.《罗马条例I》研究[D].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3:159.
[26]徐峰.民法视野下海上运输中货方合同履行责任之法理内涵[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9,30(4):66-68.
[27]车丕照.国际法的话语价值[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56(6):35.
① 民商法三大基本原则包括所有权绝对原则、契约自由原则以及过错责任原则。
① 《民法典》第465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② 《法律适用法》对意思自治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拓展,由传统的合同领域延伸至委托代理、信托、仲裁协议、夫妻财产关系、协议离婚、动产物权、侵权责任、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知识产权转让与许可、知识产权侵权等领域。文中所称“意思自治”专指“合同领域的意思自治”。
③ 当事人选择对中国已经生效的商事条约(如CISG)时,法院往往将其视为准据法,如新加坡大光行(私人)有限公司与江苏省机械进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1999)经终字第448号民事判决书;Royalbeach玩具和体育用品销售有限公司诉宁波中轻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参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甬商外初字第276号民事判决书;上海裕庆服饰有限公司诉CORPORATEFUNDINGPARTNERS等买卖合同纠纷案,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2)浦民二(商)初字第S2384号民事判决书。当事人选择中国未加入的商事条约(如《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时,一些法院也将其视为准据法。如五矿东方贸易进出口公司诉罗马尼亚班轮公司海上货物运输损害赔偿案,参见广州海事法院(1993)广海法商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中国·安徽省服裝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诉法国·薛德卡哥斯公司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索赔纠纷案,参见武汉海事法院(2001)武海法商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
④ 不少学者持此种观点,如徐伟功:《法律选择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的运用》,发表于《法学》,2013年第9期;许军珂:《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对法院适用国际条约的影响》,发表于《法学》,2014年第2期;刘益灯,陈璐:《论非国内规则在国际商事合同中的适用》,发表于《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① 例如,在中国刚加入WTO时,曾有众多学者认为WTO规则应在中国法院直接适用,甚至最高人民法院在多种场合也作出如此表态。对于该问题的详细介绍与探讨,参见车丕照:《“入世”后我国政府履行世界贸易组织条约义务的若干问题——对我国目前的一些流行观点的质疑》,发表于《国际经济法论丛》, 2002年第2期。
② 就私法自治与法律推理“三段论”的关系,学界曾有一定的探讨。有学者认为,私法自治与“三段论”是相矛盾的,也有学者对该观点进行了重新梳理。前者观点详见朱庆育:《意思表示解释理论——精神科学视域中的司法推理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后者观点详见姜强:《三段论、私法自治与哲学诠释学——对朱庆育博士的一个反驳》,发表于《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3期。以上两论著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由于笔者无意于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文中“三段论”为最基础的逻辑演绎推理方式,具体指在当事人合同依法成立的情况下,法官如何进行法律推理。
① 为便于讨论,下文表述均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其一,不论是契约自由的实现,还是意思自治的实现,当事人均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且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其二,在契约自由路径下的准据法为中国法律。不考虑对于涉外合同依据《法律适用法》指定其他国家法律为准据法的情况。
② 例如《法律适用法解释》第4条即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选择无效。”
③ 《法律适用法》第10条第1款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查明。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
④ 中国国际私法学界与民法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缔结的商事条约应成为中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详见陈治东,吴佳华:《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中国的适用——兼评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发表于《法学》,2004年第10期;李巍:《论中国撤回对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条b项的保留》,发表于《法学家》,2012年第5期;韩世远:《CISG在中国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发表于《中国法学》,2016年第5期;李旺:《论国际民商事条约的适用——以国际民商事条约与国际私法的关系为视角》,发表于《法学家》,2017年第4期。
① 《广东高院指导意见》第36条规定:“……在下列情况,法院应依职权查明域外法:1.涉外争议的准据法是我国缔结或参加的某一国际条约或经某一国际组织整理总结的国际惯例;……”
② 例如,CISG第7条第1款即规定了公约的解释方式:“在解释本公约时,应考虑到本公约的国际性质和促进其适用的统一以及在国际贸易上遵守诚信的需要。”一般而言,条约自身的解释规则较为笼统,多强调条约的国际性和自洽性。
③ 《民法典》第142条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不能完全拘泥于所使用的词句,而应当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行为人的真实意思。”
① 因约不必充分原则是英美法系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指当事人有自主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合同内容完全由当事人自愿约定,哪怕当事人订立的合同有失公允,只要不是出于胁迫、欺诈等原因,就应当得到认可。
② 参见《法律适用法》第1条。
③ 参见《法律适用法解释》第1条。
④ 《法律适用法解释》第7条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援引尚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的国际条约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该国际条约的内容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除外。”
⑤ 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人曾在就《法律适用法解释》答记者问时表示,《法律适用法解释》关于当事人选择对中国未生效的条约的处理问题上采用如下观点:把这类条约视为构成当事人之间合同的组成部分,据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更为合理,这样也可以解决由当事人援引一些不具有约束力的国际示范法、统一规则等引发的问题。
⑥ CISG第2条规定:“本公约并不适用于以下的销售:(a)购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的销售,除非卖方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不知道而且没有理由知道这些货物是购供任何这种使用;……”
⑦ 《广东高院指导意见》亦采用该观点,其第42条规定:“当事人选择某一国际公约作为准据法,但案件争议不在该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内的,不应适用该公约,而应根据我国的冲突规范确定适用的法律。”
① 《民法典》第543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② 《民法典》第544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
① 《联邦德国关于改革国际私法的立法》第27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可随时商定契约应当适用的其他法律,以代替根据以前的法律选择或根据本法的其他规定确定的对它曾适用的法律。……”
② 《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16条第3款规定:“对法律的选择可在任何时候作出或修改。……”
③ 《罗马公约》第3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得在任何时候以协议变更其合同所适用的法律,无论以前适用的法律系根据本条选择的结果或是依本公约其他规定的结果。”
④ 《罗马I规则》第3条第2款規定:“当事人可以随时依先前按照本条而做出的选择或依本规则的其他规定约定:合同适用它原先所适用的法律体系以外的另一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