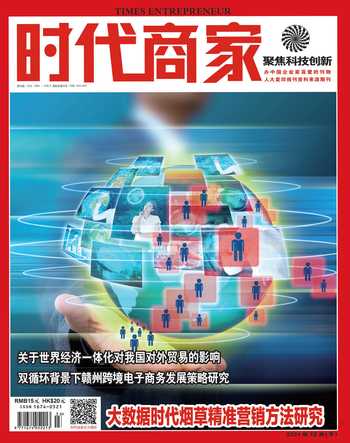我国股份回购制度的完善
游少媚
摘要:股份回购“原则禁止,例外允许”的基本原则不变,公司法142条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和“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两种情形,决策程序和处置期限等方面也有所放宽,但是删除了回购资金来源的限制。对现有两种立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我国股份回购制度的完善还可从信息披露以及法律责任机制方面着手。
关键词:股份回购;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法律责任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修正,其中为迎合公司治理需要,重点对股份回购制度作了相应修改。后上市公司回购操作明显增加,涉及股份数量、金额巨大,实施回购操作的公司多称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激励、优化公司股权架构,股份回购事实上逐渐成为公司治理及战略调整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立法部门、监管部门以及社会的深切关注。因而本文试图探究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比较分析域外两种立法模式以及我国本土制度经验,探索我国股份回购制度的完善之路。
一、域外实践与本土经验
(一)域外立法的基本模式
股份回购制度是公司治理的基本制度之一,逐渐形成了“原则允许,例外禁止”和“原则禁止,例外允许”两种立法模式。
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原则允许,例外禁止”模式,原则上允许公司回购自己的股份,但有限列举禁止回购的例外情形。若公司按比例回购股东股份,从结果上看相当于分配股东红利。在此基本原则上,各州公司法为规范回购行为作出相应限制,特别是资金来源、决策程序、回购数量以及程序等方面,如一些州明确规定仅允许使用营业盈余或资本盈余回购作为资金来源。在美国的制度体系下,回购的股份不再是公司的资产,一般有两种处置方式:一是注销,公司资本减少;二是以库存股的形式留存,一种介于发行与被取消的中间地位,因此在一些情形也需要对股份回购进行一定的限制,例如回购资金的来源限制。另外,在证券法上还设置了“安全港”规则,即只要满足SEC确立的1982年SEC Rule 10b-18和2000年的Rule 10b5-1规则中的交易条件,被认定违法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特别是操纵市场的证券违法行为,为上市公司回购股份提供“避风港”。公司回购股份应当按照公司法和证券法规定规范操作。否则,将构成违法回购,相关董事将被追究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二是“原则禁止,例外允许”模式,基于资本维持原则,原则上禁止公司回购已发行股份,仅限公司法明文规定的例外情形可适用。以欧盟践行该立法模式,并以指令来协调法律——第二号指令第18条明确规定公司不得认缴本公司股份,仅在例外情形下可以回购。除此之外,第二号指令还对回购股份的处置、回购资金来源等作出严格限制,要求董事会必须限制回购行为,在回购股票数量、价格、许可有效期等方面设置具体的限制标准。另外,尽管已经明显放宽条件,欧盟仍禁止使用银行贷款作为回购资金(指令第23条),旨在维护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和维护公司债权人利益[1]。
(二)我国的股份回购制度
我国股份回购制度的构建吸收了域外的立法经验。在建设公司制度及证券市场规范制度的过程中,对于股份回购,从严格禁止到逐步放宽适用条件,从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至逐渐建立有效监管机制[2],也是公司制度发展和证券市场完善的发展过程,开始正视股份回购可能发挥的巨大制度價值。
1993年我国《公司法》149条首次写入股份回购制度,但对于回购资金来源、程序、数量未有限制。随后1999年和2004年两次修正未有改动。
2005年《公司法》对股份回购制度在实体和程序层面都进行了适度补充。具体体现为:一是增加两种例外情形——“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以及“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二在程序方面,前三项情形明确要求经股东大会决议,第四种情形因属于股东权利,无需经股东大会决议,补充回购股份的决策程序要求。同时,对回购股份处置时间的限制有所放松,除减资情形仍需在十日内注销外,其他三种情形在六个月内转让或注销即可。三是关于回购股份数量和资金,要求回购数量不得超过已发行股份的5%,且应使用税后利润实施回购。这是我国公司法首次对回购数量、资金来源作出的明确限制。
2018年《公司法》迎合公司治理实践对股份回购规则作了较大的改动。修改要点有:一是在现有四种例外情形之上,增加“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和“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两种情形。二是降低回购决策程序要求,赋予董事会一定决策权。其中减资与合并两种情形仍需经股东大会决议,另三种情形可按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大会授权,由董事会决议通过即可,决定权由股东大会部分下移至董事会,体现了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由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过渡的整体发展趋势[[]]。另外,这三项情形回购股份的处置期限放宽至三年,适当降低要求,满足公司长期激励员工需求而设置较长处置期限,迎合公司治理的需求。三是对于股份回购的数量限制条件也进一步放宽,对于第(三)项、第(五)项以及第(六)项情形,由原来的5%上限放宽至10%。四是增加上市股份回购操作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五是删除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要求。《公司法修正案(草案)》说明提到是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删去该规定,但具体因何情况并未明确指出。
二、制度隐忧与功能重构
(一)制度隐忧
股份回购使用公司资金购买本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本质上是公司资产向部分股东转移,直接结果是公司资产减少,公司的偿债能力减弱,可能违背资本维持原则和股东平等原则,并对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与此关联的概念是“抽逃出资”,股东在履行出资义务后将已成为公司资产的资本金抽回,我国严禁股东抽逃出资。从我国股份回购的实践来看,即使上市公司“合规”进行回购操作,事实上也仍存在着“操纵”空间,甚至存在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证券违法行为,因而需警惕股份回购制度成为证券市场利益输送和市场操纵的温床。特别是“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情形,“必需”标准难以用客观、清晰的标准加以衡量。
(二)功能重构
作为公司法的一项基本制度,股份回购行为同时具备对内和对外的法律效果。对内,回购行为本质上是公司意思形成机关作出的决策行为,是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作出的决策,对公司内部成员具有约束力。当公司开始实施回购行为时,内部决策行为外部化,即对公司外部人员也产生了法律影响,如债权人等。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股份回购越发成为公司治理战略决策的重要手段。主要体现在:一是根据公司发展情况调整股份结构,或减少公司资本,或为激励公司员工;二是防止恶意收购,在特殊情况下捍卫公司的管理控制权;三是维护公司价值,在公司股价被严重低估时进行护盘式回购,公司通过回购股份向市场传递积极信息,力图将股价提高至正常市值。
三、完善的具体路径
(一)细化信息披露要求
《公司法》第142条明确要求上市公司依照《证券法》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要求的对象仅为股份有限公司中的上市公司,是否应当扩大为所有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回购行为均应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交所和深交所发布《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下称“两个《实施细则》”)强调要细化信息披露要求。但在《公司法》视角下,是否应当另行规定股份回购所要达到的信息披露要求?《证券法》以及两个《实施细则》要求上市公司应当披露董事会决议时间及会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实施回购的原因和目的,回购数量、资金来源、价格区间等重要信息。
另外,除了投资者进行充分披露外,还应当向全体股东、债权人披露回购事项的具体信息。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下,董事会享有部分权限可对回购事项进行决策,即使是减资或合并事项中经由股东会进行决议,也无法确保所有股东明确知悉回购股份事项,存在小股东知情权受损的情形。再者,公司债权人对于公司来说是外部人员,公司的内部决策根本无从知悉,直接或间接的对债权人利益有所波及。因此,实有必要完善142条,要求公司就回购事项公开进行公告,对全体股东、债权人、投资者进行充分披露回购具体事项,细化披露的内容要求,要求实质性披露,必要时应当充分征求全体股东的意见和建议。
(二)明确违法回購的法律责任
一般来说,公司法中有一类规则是强制性规则,各方主体除了遵循之外无其他选择。公司法第142条是强制性规则,违反则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但现有《公司法》及以往版本涉及法律责任的条文较少,规制违法回购行为的法律责任更是空白。为规范股份回购操作,证监会等部门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发布《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也未对违法回购设置法律责任。两个《实施细则》细化股份回购的操作规则,首次规定了违法回购的后果,但这仅仅属于自律性规范,尚未上升为法律责任。对于违反细则规定实施股份回购将视情节轻重对上市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施以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涉嫌违反法律及证监会规定的上报证监会进行查处,对于法律责任制度的建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二者比较,法律法规的缺失才是最根本原因所在。加之2018年《公司法》修订,股份回购的实体和程序要求均有所放宽,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操作显著增多,回购股份涉及的数量、金额也大大增加,对回购行为的监管也成为证券监管重点,法律责任制度也必不可少。
四、结束语
即使立法模式不一,各国针对违法回购行为却都设置了严格的法律责任规范公司回购股份行为。我国可在吸收、借鉴域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本国实践,对违法回购的具体情形进行区分,明确责任形式、责任主体以及责任分配原则等,明确违法回购的法律责任,加强对违法回购行为的实质监管。
参考文献:
[1]赵旭东.公司法修订中的公司治理制度革新[J].中国法律评论,2020(03):119-130.
[2]叶林.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的规则评析[J].法律适用,2019(01):5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