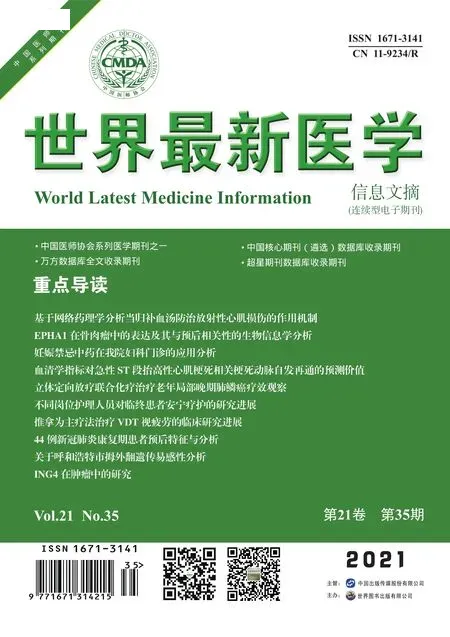瑞芬太尼在全麻拔管期预防呛咳反应的研究进展
李祺,钟海燕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0 引言
拔管后的即刻被认为是患者最关键和最脆弱的时期,正如英国皇家麻醉师学院最近的第四次国家审计项目(NAP4)所表明,气道管理的主要并发症中有三分之一发生在拔管或恢复室,死亡率为5%[1],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强烈建议麻醉医生在此时期有一个预先计划好的策略,来管理拔管时及拔管后的潜在问题[2]。目前在气管拔管过程中,有多种方法可以减少苏醒期各种并发症的发生,这些措施包括:①患者在深度麻醉下拔管;②局部麻醉药的使用;③各种药物的输注,如右美托咪啶、短效阿片类药物和血管扩张剂。
其中瑞芬太尼是一种即时起效、消除迅速的阿片类药物,不受年龄或肝肾功能的影响,不论连续输注多长时间,停药后10分钟内也会被迅速代谢,逐渐被推荐为减轻麻醉中血流动力学和呼吸并发症的一种最佳药物。然而,应该提醒临床医生,瑞芬太尼的最佳剂量可以根据手术的特点和麻醉方案的不同而有所改变。
1 瑞芬太尼预防呛咳的作用机制以及不同性别之间瑞芬太尼预防呛咳所需剂量有所差异的原因
在全麻苏醒期,患者的各种反射随着麻醉的减浅逐渐恢复,气管导管等机械刺激激活咳嗽受体并产生冲动,冲动通过迷走神经传入纤维到达延髓,终止于延髓咳嗽中枢孤束核(NTs),二阶神经元将信息传递给呼吸模式生成器,呼吸模式生成器激活呼吸运动神经元的活动并传至相应效应器,引起呛咳反射[3]。与呛咳反射相关的是脑干中的阿片受体μ和κ受体,它们参与呛咳反射的形成,而瑞芬太尼正是通过作用于脑干中的μ受体,抑制脑干咳嗽中枢,从而起到中枢性的镇咳作用[4]。
然而,尽管瑞芬太尼对这种呛咳反射有抑制作用,但根据以往的报道其有效值不尽相同。除手术类型的区别外,性别的差异更是影响瑞芬太尼用量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有研究称,若想利用瑞芬太尼获得同样满意的镇咳效果,男性患者所需效应点浓度可能高于女性[5]。Soh 等[6]将接受甲状腺切除术的患者按性别不同分为两组,分别测得全麻苏醒期靶控输注(TCI)瑞芬太尼预防呛咳的有效浓度,结果显示男性所需的瑞芬太尼剂量明显高于女性。这可能是由于女性的μ-型阿片受体可用性较高[7],因而造成女性对瑞芬太尼等内源性阿片类物质镇痛反应性高这一现象。
2 瑞芬太尼在几种特殊手术类型中预防呛咳的剂量差异
2.1 鼻咽部手术
鼻咽部手术后,在拔管期抑制呛咳是避免手术部位出血的实用方法,咽喉部的出血和分泌物以及鼻腔填塞,要求在拔管期做到平稳拔管、完全苏醒而不剧烈呛咳,这是麻醉医生面临的挑战。我们已知,应激时产生的组胺等物质对鼻黏膜的化学刺激可以增强呛咳反应,同时鼻黏膜中也存在丰富的与呛咳反应相关的传入神经末梢[8],因此,鼻咽部以及行鼻插管的手术可能需要较其他类型手术更多剂量的瑞芬太尼,来达到令人满意的镇咳效果。先前已有研究表明[9],在全麻下行鼻内镜手术术毕时,维持瑞芬太尼输注直至拔管与术毕即刻停止输注所有麻醉维持药物相比,前者可以减少气管拔管时的血流动力学改变和呛咳反应。后来Choi等[10]的研究发现,在复合七氟醚的全身麻醉下,瑞芬太尼预防患者鼻部手术后呛咳的EC95值为2.94 ng/mL。在Kim[11]等人的研究中,在复合丙泊酚全麻时瑞芬太尼预防拔管期呛咳的EC95值为2.92 mmol ng/mL。但是在一些文献的报道中显示[12],当血浆靶浓度≥2.0 ng/ml的瑞芬太尼可对一些老年患者产生呼吸抑制作用。这给与我们的临床启示是,我们在应用瑞芬太尼预防呛咳的过程中要加强对患者呼吸的管理。因此,是否有一种剂量或方法,既能够有效的预防呛咳和血流动力学紊乱的发生,又可使瑞芬太尼的这种副作用降到最低,这是我们今后的研究中应关注的方向。
2.2 甲状腺手术
近年来,甲状腺疾病的发病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甲状腺手术由于其手术部位特殊,术中操作和出血会对气管造成压迫和刺激,这无疑增加了拔管期各种并发症的发生率,拔管期的呛咳反应更可能会导致术后出血和潜在的致命的颈部血肿,使切口裂开、出血和水肿,因此平稳度过此时期显得尤为重要。那么,通过靶控输注瑞芬太尼,可以在可预测的效应部位浓度下有效地减轻呛咳。瑞芬太尼在甲状腺手术中预防咳嗽的EC50和EC95值分别为1.46和2.14 ng/mL[9]。对于持续静脉输注方式而言,陈宏志等人[13]的研究表明,甲状腺手术全麻术后静脉持续输注0.03μg/(kg·min)的瑞芬太尼可有效抑制苏醒期循环波动及呛咳反应,并且不造成苏醒延迟和减少不良反应发生率,是一种安全、可控、行之有效的麻醉与镇痛方法。
2.3 神经外科手术
神经外科手术由于其手术的特殊性,强调实现无呛咳的全麻后平稳苏醒,避免呛咳带来的颅内压升高和血流动力学剧烈波动等不必要的并发症,防止增加颅内出血和动脉瘤破裂的风险。首先,经股动脉插管血管内介入治疗的患者,瑞芬太尼预防七氟醚麻醉苏醒期间呛咳的EC50和EC95分别为1.42 ng/mL和1.70 ng/mL,血流动力学方面,虽无统计学差异,但相比对照组MAP和HR有降低的趋势[14]。同时,由于开颅手术对患者的刺激更强,麻醉用药的剂量会相应增加,一项对行幕上开颅肿瘤切除术患者的研究表明,与对照组相比,拔管期2.0 ng/mL的瑞芬太尼具有较好的抑制呛咳的作用[15]。但目前已发表的文献中,对开颅手术患者通过序贯法测得的拔管期瑞芬太尼抑制呛咳的EC50和EC95鲜有报道,尤其是脑膜瘤、动脉瘤等手术,为避免呛咳和血流动力学波动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应就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做深一步的思考。
3 瑞芬太尼在行双腔管插管手术中预防呛咳的应用
胸外科手术因为术中需要单肺通气,常需要双腔气管导管进行机械通气,双腔气管导管因其特殊的管体结构,拔管期对气道的刺激较大,且导管的支气管端直接压迫摩擦神经分布相对密集的气管隆突部位,呛咳和血流动力学紊乱更易发生。行胸科手术的患者因本身具有肺部疾病、肺功能不良、气道高反应性等特点,拔管期更应采取适当措施避免呛咳等不良反应的发生。Lee等[16]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复合七氟醚时行胸科手术并插双腔气管导管的女性患者瑞芬太尼抑制咳嗽的EC(50)为1.670 ng/mL,EC(95)为2.275 ng/mL。麻醉维持用药和性别都可能影响阿片效应,如男性对阿片类药物的敏感性低于女性,老年患者反而相对于女性更敏感。因此对于瑞芬太尼在双腔管插管的手术中的个体化应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4 特殊人群拔管期瑞芬太尼预防呛咳的研究进展
4.1 小儿患者人群
扁桃体切除术和腺样体切除术是儿科患者最常见的两种手术,拔管期切口出血、分泌物等和气管导管会刺激气道,呛咳反射可能会加重术后出血和喉痉挛等并发症的发生。Park等人[17]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瑞芬太尼预防小儿患者在地氟醚麻醉下行扁桃体切除术拔管期呛咳的EC95为 0.06μg/kg/min。
4.2 老年患者人群
老年患者自主神经功能减退,对呛咳引起的血流动力学变化调节功能较差,围术期发生心脑血管等意外的风险高于青壮年人群,因此拔管期应采取适当措施尽量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根据吉晓丽等人[12,18]的研究结果表明,老年患者短小咽喉部手术苏醒期TCI瑞芬太尼抑制呛咳反应的半数有效血浆靶浓度为1.76 ng/ml,而对于行胆囊切除术的老年患者,测得血浆靶浓度为1.5 ng/ml为气管拔管反应的适宜浓度。可以看出,对于同一人群,手术部位的不同,抑制呛咳所需瑞芬太尼的剂量也相应不同。
5 瑞芬太尼与其他抑制呛咳的药物或方法的效果比较
5.1 右美托咪定
作为一种高选择性α2受体激动剂,右美托咪定具有镇痛作用而不产生呼吸抑制。有研究表明[19],手术结束前静滴和泵注右美托咪定,可有效的抑制拔管期的呛咳反射,并可维持拔管后呼吸循环稳定。王海丽[15]等人的实验结果显示,右美托咪定更有助于维持苏醒期呼吸及循环稳定,而且具有一定的脑保护作用,就预防拔管期呛咳反射的作用而言,瑞芬太尼抑制效果更好。且在李伟萍[20]等人的实验中,相比瑞芬太尼组,右美托咪定组Ricker镇静-躁动评分显著小于瑞芬太尼,且患者表现为对言语指令迟钝。然而,在拔管期使用小剂量的右美托咪定复合瑞芬太尼用来减轻拔管并发症,此类研究国内已有不少文献发表,但两种药物具体的最佳剂量目前仍鲜有报道,这指导我们就这一方向进一步研究。
5.2 利多卡因
一项研究结果显示[21],行甲状腺手术的女性患者,相比较静脉推注利多卡因,靶控输注瑞芬太尼更能有效降低全麻苏醒期间对气管导管的反应性,这可能是因为利多卡因是钠通道阻滞剂,它通过特定的浓度来抑制气管处咳嗽受体上的动作电位的形成来抑制呛咳。超过3mg/kg的血清利多卡因浓度可以完全抑制咳嗽[22],但这一相对较高的浓度很难通过单次静脉注射来及时实现。
5.3 经皮电穴位刺激
近年来,针灸辅助麻醉和经皮穴位电刺激(TEA)被认为是治疗疼痛药物的替代方法。TEA是一种将经皮神经电刺激疗法与传统穴位疗法相结合的互补替代治疗方法,是一种具有镇痛作用的新针灸模式,具有无创、操作简便、患者接受度高等特点。刺激不同的穴位可以产生不同的疗效,我们一般选择与合谷、内关、足三里等痛症相关的穴位。TEA不仅可以诱导多种中枢神经递质和内源性阿片类药物的释放,而且可以减少应激反应和阿片类药物的消耗。根据文献报道[23],TEA可增强瑞芬太尼对患者气管拔管反应的抑制作用,其瑞芬太尼用量的EC50为1.20 ng/mL,较对照组降低约27%。
6 其他影响瑞芬太尼抑制呛咳作用的因素
6.1 给药方式
我们知道,瑞芬太尼在术必时的输注方式有三种:单次静脉给药、持续静脉输注、以及靶控输注(TCI)。有研究采用术毕单次推注0.2μg/kg的瑞芬太尼,对患者苏醒期的心血管反应有影响,但是对呛咳的抑制没有作用[24],这可能与单次给药难以维持抑制呛咳的有效血药浓度有关。与其相比,持续静脉泵注和TCI效果更好,瑞芬太尼特殊的药代动力学更适合TCI,但TCI技术主要根据外国人体设计,应用于国人时其精确度会有所差异,而持续静脉泵注的效应点浓度可能难以准确预测,但由于临床麻醉中此方法应用更为广泛,因而今后我们应着重关注各种手术人群中,瑞芬太尼持续泵注的剂量研究,为指导临床提供更加实用有效的依据。
6.2 复合用药
静吸复合麻醉和全凭静脉麻醉都是术中常用的麻醉方式,两者各有优缺点。尤其是对于神经外科的手术而言,复合七氟醚的全身麻醉得到广泛好评,这可能是因为七氟醚的血/气分配系数低,使得麻醉更易调控,且对脑血管扩张和颅内压变化的影响更加轻微。但丙泊酚能降低颅内压,相比七氟醚更能加快患者术必苏醒时间,且术中及术后应激反应的程度也有所减小。由于药物之间的协同作用,瑞芬太尼复合不同麻醉维持药物时,其抑制呛咳的剂量也相应不同。根据Lee[25]的实验,瑞芬太尼抑制呛咳的EC50 丙泊酚组为1.60 ng/mL,明显低于七氟醚组1.96 ng/mL和地氟醚组1.75 ng/mL。我们得出结论:瑞芬太尼在苏醒时的镇咳作用应根据麻醉复合药物的不同种类做出相应调整。
7 小结
曾有文献报道,全身麻醉苏醒期呛咳的发生率高达76%[26]。瑞芬太尼作为一种超短效的阿片类镇痛药,通过作用于中枢部位起到镇咳作用,且因为其效果在停止输注后能迅速、可预测地消失,而不会延迟麻醉恢复,使这种药物越来越得到临床麻醉医生的关注。由于术中各种影响因素的存在,随时调整拔管期瑞芬太尼的具体剂量是必要的,这也能使得我们的麻醉用药更加个体化。然而,阿片类药物的呼吸抑制作用,术毕大量静脉输注瑞芬太尼可能使患者清醒时间和拔管时间延长,或出现呼吸频率减慢及潮气量不足的情况,因此需临床麻醉医生根据人群和手术类型的不同掌握好给药剂量与停药时间,随时密切监测各项呼吸功能指标,观察是否有遗忘呼吸,避免严重低氧血症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