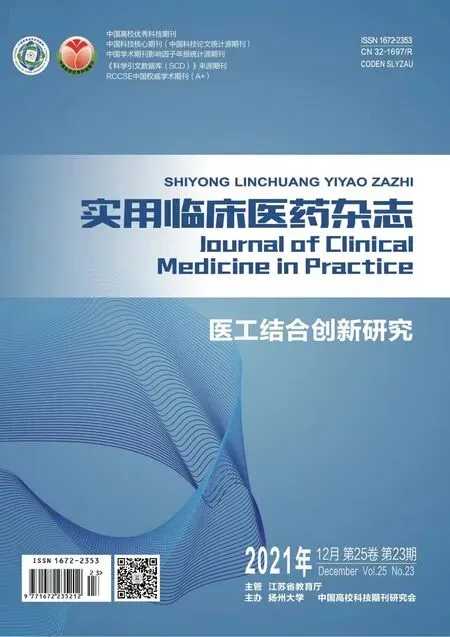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血清生物标记物的研究进展
刘久江, 林 华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江苏 扬州, 225001)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一种严重的急性炎症性肺损伤,患者病死率为27%~45%[1]。相关研究[2]报道, ARDS是重症监护病房(ICU)常见的临床综合征, ARDS患者占所有ICU患者的10.4%, 占需机械通气患者的23.4%。然而,仅51.3%~78.5%的ARDS病例能被临床医生识别,这表明临床医生治疗患者时往往忽视了ARDS的诊断[2]。因此,只有小部分患者可接受ARDS治疗措施干预,如小潮气量通气、高呼气末正压(PEEP)通气、神经肌肉阻滞剂和俯卧位干预[2]。ARDS诊断与治疗的主要挑战之一是缺乏简单的诊断测试,导致其诊断依赖于定义,但该定义无法鉴别ARDS的临床和病理生理异质性[3]。生物标志物的应用可为ARDS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提供重要依据,且有助于诊断、风险分层和确定候选治疗靶标[4], 现将ARDS生物标志物的临床应用进展综述如下。
1 诊断ARDS的生物标志物
目前,临床已发现许多生物标志物与ARDS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可帮助诊断ARDS。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可溶性受体(sRAGE)是其中之一,为肺泡1型细胞上表达的多配体受体的胞外结构域,是肺上皮损伤的标志物[5]。ARDS患者的血浆sRAGE水平升高,并与肺损伤的严重程度和肺泡液清除机制的损害程度有关[6]。发展为ARDS的创伤患者血浆sRAGE水平也会升高[7], 并与ARDS发生风险增加显著相关[4]。一项荟萃分析[8]评估了几种生物标志物与ARDS诊断和病死率的相关性,也发现血浆sRAGE水平与ARDS诊断的OR值为3.48。另一种用于诊断ARDS的生物标志物是血管生成素-2(Ang-2), 其可导致肺内皮屏障功能受损,是肺内皮损伤的标志物[9], 对于机械通气[10]或因创伤入院[7]的ICU患者ARDS的发展具有预测价值。研究[10]还发现,与单独使用任一组分相比,将Ang-2添加到急性肺损伤预测评分(LIPS)生成组合模型提高了诊断区分度,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4(95%CI为0.78~0.91)。表面活性蛋白-D(SP-D)主要在肺泡2型细胞中合成,被认为是肺上皮损伤和炎症的标志物,与无ARDS的对照组相比,ARDS患者血浆SP-D水平更高[11]。其他具有ARDS诊断潜力的血浆生物标志物包括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内皮损伤的另一种标志物)和促炎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IL)-6、IL-8[8]。相关研究[7]发现,由sRAGE、前胶原肽Ⅲ、脑钠肽、Ang-2、IL-8、IL-10和TNF-α组成的一组生物标记物区分ALI组和对照组的AUC为0.86(95%CI为0.82~0.92), 具有较高的诊断准确率。微小RNA(miRNAs)在炎症和感染中发挥重要作用,有研究[12]报道ARDS患者炎症反应标志物miR-181a、miR-92a水平显著升高,而肺动脉内皮细胞抗炎标志物miR-424水平显著降低。
2 ARDS患者预后或风险分层的生物标志物
血浆SP-D[13]、vWF[14]、可溶性肿瘤坏死因子受体(sTNFr)1、sTNFr2[15]、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sICAM-1)[16]和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PAI-1)[17]均与ARDS患者预后相关。CALFEE C S等[18]报道, sRAGE水平越高,急性肺损伤的严重程度越高,患者病死率越高。其他与死亡相关的ARDS生物标志物有Ang-2、IL-6、IL-8、IL-4、IL-2[19]。内源性抗凝蛋白C含量低也与病死率增高和无呼吸机时间减少有关[17]。TSENG J S等[20]研究发现,血浆降钙素原水平升高与严重社区获得性肺炎引起的ARDS病死率增高相关。WANG Q Q等[21]发现, miR-103、miR-107是脓毒症患者ARDS发生风险和28 d病死率的预测生物标志物。一项关于内源性碳氧血红蛋白(COHb)水平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临床病程和预后关系的研究[22]发现,ARDS患者和死亡患者治疗第5天的COHb水平显著升高(P=0.001)。血清半乳糖凝集素-3(Galectin-3)是一种结合β-半乳糖苷的凝集素,在免疫炎症反应中具有多种作用。PORTACCI A等[23]报告, Galectin-3水平高于35.3 ng/mL的患者病死率升高,入住ICU和发展为ARDS的风险增加。由于这种预测ARDS预后的潜在效用,生物标志物也被结合现有的临床预测模型进行研究,以提高性能。一项汉族患者群体研究[24]发现, Ang-2水平和LIPS联用比单独预测急性肺损伤的AUC更大。结合2个临床变量(年龄、APACHE Ⅱ评分)和2个生物标志物(SP-D、IL-8)的简化模型也具有良好的性能,且已在ARDS患者中得到验证[25]。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与现有ARDS临床预测模型相结合,生物标记物都可能在ARDS的预测和风险分层中发挥作用。
3 ARDS表型鉴定的生物标记物
ARDS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一种异质性综合征,其特征是亚表型具有不同的临床、影像学、生物学差异和不同的结局、对治疗的潜在不同反应。ARDS的直接和间接肺损伤的病因导致不同的肺损伤机制和不同的临床表型[3]。ARDS的放射学表型是根据胸部影像学上弥漫性与局灶性浸润模式描述的。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利用血浆生物标记物、遗传学标记物等来识别生物亚型或类型。
相关研究[13]发现,较高的SP-D水平与脓毒症和肺炎患者的死亡风险密切相关,且与创伤患者的死亡风险较低相关。临床研究[26]显示,与间接肺损伤所致ARDS患者比较,直接肺损伤所致ARDS患者有较重的肺上皮损伤(通过血浆sRAGE、SP-D评估)和较轻的肺内皮损伤(通过血浆Ang-2评估)、炎症(通过血浆vWF、IL-6、IL-8评估)。经典ARDS患者的RAGE、P-选择素水平高于COVID-19相关ARDS, Ang-2、ICAM-1和E-选择素水平低于COVID-19相关ARDS, COVID-19 ARDS和经典ARDS出现不同的生物标志物表达,表明两者有不同的病理途径[27]。
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队列研究[28]表明,与局灶性ARDS相比,非局灶性ARDS患者血浆sRAGE、PAI-1水平显著更高。Ang-2是最有希望用于ARDS类型鉴定的血浆生物标志物之一。血浆Ang-2是内皮细胞活化和通透性的一种生物标志物和介质,与ARDS风险和预后密切相关[10]。Ang-2基因(ANGPT2)的遗传变异与ARDS风险相关[29], 外源性给予Ang-2可加重啮齿动物模型的肺损伤[30]。孟德尔随机化分析[31]表明,血浆Ang-2与ARDS有因果关系,应优先用于药物开发。血浆Ang-2升高所定义的ARDS类型可能是对Ang-2靶向治疗最有反应的人群。因此,生物标记物可能有助于区分ARDS的不同表型,并有可能识别ARDS的各种病理生理机制,这些机制可作为未来治疗的靶点。
4 研究前景
此前大多数研究集中在ARDS的诊断和预后方面,关于生物标志物在ARDS治疗及临床分型方面应用的研究则相对缺乏,亟需开展更多的研究。首先,生物标志物或可用于监测ARDS的进展或对治疗干预的反应。研究[32]发现,采用低潮气量肺保护策略通气的ARDS患者,随着时间推移,血浆SP-D水平升高幅度较小。由此表明,生物标记物可用于监测肺损伤的进展或修复以及ARDS的治疗反应。其次,生物标志物对于鉴定具有共同生物学特征的患者亚群(或表型)至关重要,也有助于人们对ARDS病理生理异质性进行理解。ARDS治疗失败的原因之一是ARDS的病理生理异质性,生物标记物可能有助于克服这一问题。采用两种水平PEEP治疗ARDS的研究[33]发现,高PEEP组与低PEEP组相比,高炎症表型组患者的90 d病死率降低(从50%降至40%), 相比之下,低炎症表型患者使用更高水平的PEEP时病死率更高。在ARDS的液体和导管治疗试验(FACTT)中,采用自由而非保守的液体治疗策略时,高炎症表型的ARDS病死率较低[34], 而最初的试验发现液体治疗策略对病死率和保守液体治疗策略的无呼吸机时间没有影响[35]。关于辛伐他汀治疗ARDS试验的二次分析[36]发现,辛伐他汀也有类似的显著作用,最初的试验发现辛伐他汀和安慰剂的临床结果没有差异,但高炎症表型患者使用辛伐他汀的生存率更高,而低炎症表型患者的治疗反应没有差异。最后,生物标记物的一个主要潜在用法是在未来的介入试验中识别靶向生物通路[3]。例如,检测血浆sRAGE有助于选择肺上皮损伤加重的患者,这些患者可能受益于上皮靶向治疗,如β受体激动剂、角质形成细胞生长因子或抗RAGE治疗,以预防或治疗ARDS[37-39]。相反,具有明显肺内皮损伤的ARDS患者可能从靶向内皮细胞的重组Ang-1治疗中获益更多[26]。生物标记物可能有助于人们提高对不同ARDS表型机制的理解,并开发一个分类系统,从而帮助选择最有可能受益于针对特定生物或分子途径的新疗法的患者[3]。这些进步可成为精准医学在ARDS管理中应用的重要一步。
5 限制和挑战
虽然上述研究已证明生物标志物在ARDS诊断、分类和预后中的潜在效用,但目前生物标志物在ARDS临床管理中的应用和实施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没有单一的生物标志物能够可靠地预测ARDS的诊断或相关结果[19]。本文讨论的许多研究在招募的患者群体、测试的生物标志物、生物标志物测量的时间与方法以及关注的终点或结果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且许多研究受到回顾性研究和/或小样本量的限制。这些因素使得ARDS临床治疗中生物标志物的最佳应用方法难以确定。其次, ARDS生物标志物的检测仍有一些实际问题需在未来的研究中解决。理想的生物标志物应该具有高度的敏感性、特异性和成本效益,并且易于以时间敏感的方式进行检测,从而有助于ARDS的治疗[3]。因此,未来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确定哪种生物标记物(或一组生物标记物)在ARDS诊断或预后预测方面具有最佳的实用性、准确性。最后, ARDS生物标志物的最佳采样部位尚存争议,而本文只关注了目前研究最多的血浆蛋白生物标记物。肺泡腔中生物标记物的测试[19]以及代谢组学[40]的研究,对于应对ARDS精准医学的挑战也可能非常重要。支气管肺泡灌洗液被认为能更好地反映肺损伤期间的局部肺环境,并能捕获肺外部位可能不存在的生物标记物,但需要有创性的采样程序[41]。检查呼出的气体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可作为ARDS生物标记物[42]。此外,从机械通气患者热湿交换过滤器收集的液体中寻找生物标记物是有希望的[43]。STRINGER K A等[44]利用核磁共振(NMR)光谱对血浆样本进行初步研究发现,与健康志愿者相比,脓毒症诱导的急性肺损伤患者的总谷胱甘肽、腺苷和磷脂酰丝氨酸水平较高,而鞘磷脂水平较低。VISWAN A等[45]研究了ARDS患者肺泡灌洗液的NMR波谱,并鉴定了29种代谢物,以其中6种代谢物(脯氨酸、赖氨酸、精氨酸、牛磺酸、苏氨酸、谷氨酸)构建一个预测模型,用于区分轻度和中度/重度ARDS。然而,这些方法及其在ARDS管理中的潜在价值还需要进一步评估。
6 小 结
目前,许多生物标志物已被用于ARDS的诊断、分类和预测中,生物标志物的研究有望阐明急性肺损伤和修复的病理生理机制。但由于正在测试的生物标记物数量众多,且测量方法和测量时间具有广泛的可变性,目前生物标记物的临床应用仍会受到限制。未来,研究人员还需进一步确定哪些生物标记物在ARDS的诊断或预后预测中具有良好的临床实用性、成本效益,且需不断规范生物标记物的测量方法,前瞻性地验证其在ARDS临床治疗中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