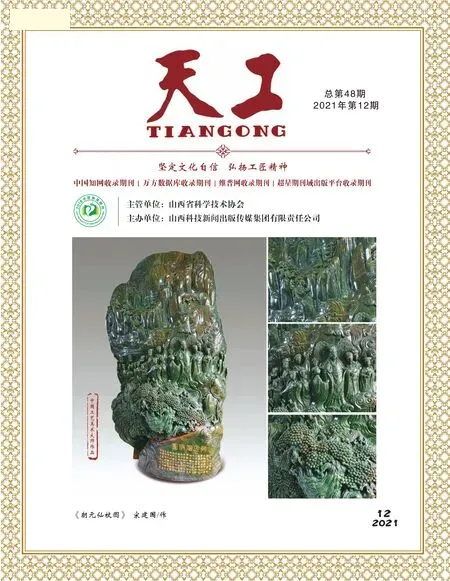艺术人类学视角下贺州瑶族服饰“图像艺术”研究
陆俞志 贺州学院设计学院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注:“衣,依也。”①莫碧琳:《象征之美——简析黄洞瑶族服饰刺绣中的象征符号》,《艺术评论》2009年第6期,第87-89页。俗话说:“衣食住行。”排首位的是“衣”。可见其与人类的密切关系,体现着服饰具有遮体与美化的双重作用。而服饰图像除了审美功能外,同时具有更深远的文化功能。瑶族文化中包含了大量的“图像艺术”,瑶族人民最早的图形纹样是为了记录生活的事件和保留其民族的文化。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观察,完成这些“图像艺术”功能,基本上得益于“艺术”的本来特征,如狩猎、生产、敬神、祈祷、战争等的记录。由于瑶族人民的生活环境比较封闭,所以瑶族纹样的传承比较完整。人们通过积极有效和最有力的方式,以产生强烈的情感经历。而艺术恰好是形成此类情感经历的文化活动。
一、从艺术人类学视角观察瑶族服饰中的图像起源
从艺术人类学角度来看,每个民族的“图像艺术”极有可能表现为其文化的外部符号,包含公共的或传统的意义,特别是对于部分没有文字的民族,此类功能通常体现得更为突出。“艺术”只是现代语义下的界定,而服饰里的图像直接体现了所有民族的自然环境、文化背景、传统理念等。它除了美化、保暖等功能之外,同时还承载着该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审美等许多因素。贺州瑶族服饰中的“图像艺术”也具备了上述特质,蕴含着瑶族民族或族群特有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认同,或者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本能。
二、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分析瑶族服饰图像的特征
博厄斯说:“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众多民族的艺术品,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单纯的形式装饰,而实际上却同某些含义相关联,并且能够被人所理解。”②石丽芳、方李莉:《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新艺术史观——以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为例》,《民族艺术》2013年第3期,第52-64页。可以看出这些图像纹样除了装饰作用外,更体现着该地域意义重大的文化符号。可见,艺术在不同时代体现着当时人类活动的重要特征,体现着当时人们的信仰与劳动成果,这也是区别于当代社会文明的功能的表现。传统服饰图像是由处于该环境下的人们所创作的,也正体现着当时社会环境中的事和物,同时也被注入了创作者的感情和审美意识。最初的瑶族没有记事的文字,但却可以创造出艺术特征显著、文化底蕴丰富的图像符号,并不断与其他文化交融,形成了体现自身文化的独具特色的造型符号,也成了瑶族文化的主要特征。贺州瑶族的服饰样式丰富,也造就了其多姿的服饰图像。据统计,贺州瑶族服饰多达几十种图像样式,基本来源于生活。经过瑶民们的精心创造,自然界的各类飞禽走兽与奇花异草都以简化的图案展现,如图腾纹、动植物纹等,这些元素代表着瑶族服饰的文化符号。最居中的是瑶族始祖“盘王印章”形纹,传说将盘王印章纹样绣在衣服或者配饰上面,穿戴者外出探亲访友,有保佑平安的含义。这些图纹装饰性极强,在视觉上给人以色彩鲜明、线条简练、庄重大方的感觉,体现了瑶族服饰文化元素的广泛性和丰富性,也表达了该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与精神。
瑶族刺绣俗称“五色绣”,而服饰则称“五色衣”。目前贺州瑶绣图像形制庞杂,不能详列,只能记述其中使用量较大且传承时间较久的部分。瑶绣常用的图像有两大类:一是抽象的几何纹,如曲折纹、锯齿纹、波浪纹、人字纹、十字纹、米字纹、万字纹等。①刘沁楚:《畲瑶文化在环境景观中的应用研究:以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为例》,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二是具象的写实纹,以人形纹、神仙纹、太阳纹、动植物纹为主,具体有八角花纹、枹桐花纹、梓桐花纹、鸟纹、盘王殿纹、鬼仔纹、五彩河纹、狗头纹、龙角纹、云雷纹、太阳纹、虹纹、盘王印纹、连鱼纹、山形纹、松枝纹、牛铃纹、波浪开光纹等。
上述图像大多以组合或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形式出现,搭配的纹样主要有八角花、龙角纹和菱形纹等。八角花纹是过山瑶服装中最常见的瑶绣图像,常与十五结、十一结等纹饰图像组合。狗头纹由狗耳、狗额、狗目和狗嘴四个部分组成,在服饰图像中常用白色绣线,而绑腿则用深蓝色绣线。不同支系所绣的图形也稍有变化,如西山瑶的狗头纹较瘦长些,东山瑶则偏宽,图形会更形象些。狗头纹常与波浪纹一起组合成狗头波浪纹。五彩河纹一般是用白、红、黄、绿四色以三角形波浪的连续形状拼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河面的图像。而虹纹是用这四色以直线并排的样式连接成虹的图像。连鱼纹一般以“十”字的形状出现,横竖各四个类似鱼的形状连接而成,每一条鱼主体由内外两个菱形组成,颜色多以红+白或红+草绿等为主,四周空白处配以八角花纹。因为是鱼与鱼相连,所以有年年有余的寓意。一些图像只出现在特定的位置,如连鱼纹主要用于尖头瑶传统挎包上。枹桐花松枝纹多见于开山瑶与石门瑶的服饰上。盘王印纹多饰于婚装头巾正中,或男装后背正中。贺州瑶族服装上的许多服饰图像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与期盼。注重“有图必有意,有意必是吉”。传统的瑶族刺绣形纹图像体现了瑶族传统文化的内涵,也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对生产生活的忠实记录。如在瑶族女书中表达吉祥如意的纹样有万字纹和太阳纹,在男、女上衣的胸前和头巾上就饰有众多的太阳纹。但绝不会在裤筒、衣袖口等部位出现。所以,我们由此能看到瑶族服饰图像具有装饰与表意的双重功能,这些保存和发展下来的传统服饰图像起到了传承民族文化与精神的重要作用。
不同支系的绣品图像各不相同,工艺也有差异。过山瑶与当地土瑶的最大区别在于,过山瑶服饰以复杂的绣饰见长,女性服饰的袖口、领口、围裙均绣上繁杂的华丽图像。平地瑶与汉族人民混居后服饰已基本汉化,男装为唐装,他们的服饰最大特征是几乎没有刺绣,只有帽子上的毛巾和内裤的裤脚边上可以看到刺绣图像,如男子裹头用白色毛巾。有些头巾绣变形女书“吉祥平安”四字;女装只束一条有小面积图像的彩色腰带或围裙,在花带下缝有红、黄、绿三色绒线线穗,这些五彩绒线也是土瑶民族的身份象征符号。唯一能看出刺绣图像的是女子穿的绣花鞋。瑶族服饰中体现艺术性纹样的这些符号,是最有效、也是最有力地抒发瑶族人民感情的方式。瑶族服饰中的“图像艺术”也因此获得了充分的展示空间,并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性特征。
三、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认识瑶族服饰中图像的文化内涵
“图案的起源和文字的起源是同步的,这些服饰上的图案可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符号的遗存。”②张犇、张曦元:《羌族释比服饰中“图像艺术”特色的艺术人类学阐释》,《民族艺术研究》2015年第5期,第147-153页。以瑶族服饰为例,能成为瑶族视觉符号的一种文化的一定是这些历经千百年凝练而成的诸多“图像艺术”。总结起来包括民俗生活的影响、图腾崇拜的影响和宗教崇拜的影响这三个方面。
(一)民俗生活对贺州瑶绣“图像艺术”的影响
贺州瑶族的先民曾经历过采集、渔猎和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其后过渡到犁耕农业、林业生产。③潘涛:《桂东瑶族服饰图案花纹的宗教文化意义》,《民族艺术》1994年第4期,第184-192页。以动物为题材是原始社会初期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服饰图像所体现的原始性,也恰好说明了动物与原始先民的生活状况、生产活动紧密相关,而渔猎则是他们的主要生产活动之一。贺州瑶族瑶绣图像的题材涉及面很广,包括人物、动物、植物和几何四种纹样。如体现瑶族先民从渔猎走向农耕的过程,可以从诸多的植物纹与动物纹中呈现;而对瑶族影响深远的佛道文化与原始宗教崇拜,则通过许多的人形纹和特殊字纹来体现。
(二)图腾崇拜对贺州瑶绣“图像艺术”的影响
图腾盘抓(盘王)是瑶族人民崇拜的主要对象。史籍载云:瑶“女,垂一绣袋,祖批高辛氏女配盘抓,著独立衣,以囊盛盘瓤足与合,故至今仍其制云。”①张有隽:《瑶族宗教信仰史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第110-114页。图腾崇拜对瑶绣图像纹样的影响基本体现在服饰上。据当地一些长者介绍,在以前的瑶绣中,盘王印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花纹;而绣一个完整的盘王印图案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盘王印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内涵,瑶族人民相信绣上盘王印,把盘王印放在胸前可得到盘王的保佑。有的瑶族人民除了在中间绣一个大的盘王印,两边还会绣6个小的盘王印,同时会在衣领、袖口、衣服前后摆绣上或拉长或缩小的盘王印。而现在真正从事这种手工艺的瑶族人民极少,所以很少有人再绣这类复杂的且耗时长的图案,笔者也只是在资料图案中看到此类图像。但在日常生活中,如婚嫁、节庆等情况下都会在他们的服饰上绣上相关的图案以有所区分,而且不管是日常生活、节日或是红白喜事中呈现出的那些图案纹样都可以看到图腾崇拜。
(三)宗教崇拜对贺州瑶绣图像纹样的影响
宗教崇拜对贺州瑶族服饰纹样有很大的影响。度戒是瑶族男子的成人礼仪式,也是宗教的一种仪式。瑶族度戒礼服受我国道教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影响非常大。他们在度戒中戴着道士帽,礼服的前襟下摆、后背、领子上全绣着“万”字图像。在佛教文化中,“万”字图像经常用在佛寺建筑与佛陀物品之中,传达出佛教的“永生”“轮回”理念。在瑶绣的图像中也能看到汉族宗教里的象形花纹万字花。这些纹样主要绣在女装的重要位置,如头部、胸前、背心等。
贺州瑶族宗教专职人员产生的标志是瑶绣“人仔花”图像的出现。②陆俞志:《论桂东瑶族服饰纹样的人文魅力》,《艺术科技》2015年第6期,第115页。即做法事的师公也就是图像中巫师的形象,而“行呈花”则是“人仔花”的另一名称。酷似人形的“人仔花”共有两种图像,都是采用白色的丝线绣成。头上戴帽是其一,双手双脚同时伸展张开,其二被认为是女性形象,头上有束发的双角,双手弯曲向上,双脚张开半蹲。以上两种图案以二方连续的牵手人形舞蹈的形式呈现,给人营造出气势与神秘的氛围。它们主要装饰巫师礼服的前胸、头部与袖的上方,体现巫师的重要地位和职能。
此外,瑶族人民认为虹象征着龙的形象,瑶话把虹称为“公柄”,是“龙花”的意思,也出现在很多瑶绣图像中。绣品采用红、黄、绿、白四种颜色,它们的排列顺序从上往下为红、黄、绿、黄、红,边缘均以白色勾边,整个色调既突出又和谐,同时直线和波纹形的运用形成了极富韵律感的图形。虹的图像主要绣在男、女装的胸前扣前后下摆以及头饰上,表达了瑶族人求雨祈丰收与祝福族群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望。②在平地瑶的纹样绣品中,他们会把一些祝福的语言绣进锦面图像里,寄托了瑶族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同时也促进了瑶锦图像的新发展。
四、结语
常说的意义符号化是通过艺术系统进行的,而贺州瑶族服饰中的“图像艺术”正是最好的诠释。虽然这些造型、形式、纹样更多的是属于瑶族人民无意识的“艺术行为”,但确确实实地与瑶族社会文化、族群的变迁进程和自然生态联系在一起。③张有隽:《瑶族宗教信仰史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第110-114页。如今,贺州地方政府、高校、民间三大力量都在努力保护与传承非遗瑶族服饰文化,同时反思其保护、传承中所面临的问题,并用艺术人类学所积极践行与倡导的这种认识和研究的方法,不断地丰富着民间艺术的“艺术知识”。正如格罗塞所言:“任何时代,任何民族,艺术都是一种社会的表现,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地把它当成个体的现象,就立刻会不能了解它原来的性质和意义”④[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39-40页。“我们将要专门研究艺术创造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我们要把那些原始民族的艺术当作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机能。”④格罗塞所论述的观点也正体现在瑶族服饰“图像艺术”的发展规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