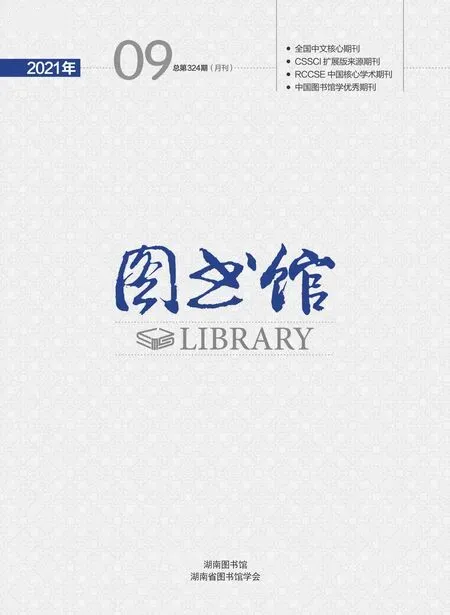文化自信视阈下宋代群体阅读意识、阅读行为与阅读文化探究*
华小琴 郎杰斌
(中国计量大学图书馆 杭州 310018)
1 引言
阅读是最普遍的文化现象之一,人们通过阅读获取信息、拓展思维、认识世界并获得审美体验。群体阅读意识则是由群体内部通过共同活动表现出来的群体成员共有的阅读行为特征或心理追求。阅读风气的形成、阅读行为的培育与阅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作用,群体阅读意识则是促进阅读兴盛的最直接因素之一。
近年来,我国倡导文化自信,明确指出文化自信源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阅读为培育和践行民族价值观发挥着强劲的文化力量,挖掘优秀传统阅读文化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充分信任与积极传承,也是巩固文化自信的“基底石”之一。我国对阅读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王余光等人的推动下,阅读文化研究开始成为文化学、教育学、图书馆学等领域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对重建阅读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学者们纷纷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传统阅读与数字阅读、中外阅读比较、内容建设、阅读疗法、阅读推广与阅读服务等研究尤为兴盛,但仍缺乏具有鲜明时代性、民族性、群体性等特征的优秀传统阅读文化研究,缺乏对某一时期群体共同形成并享有的阅读理念和阅读行为的深入探索,对作为人类阅读实践产物的历史阅读文化遗存的研究相对较少,从传统优秀文化的视角去解读阅读文化方面仍付之阙如。
宋代被公认为文人的黄金时代,在宋人的群体意识中,阅读是群体成员共同具有的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以阅读作为共同价值观的认定和核心内容,是群体实践的结果,也是群体理念的集中反映。本研究探讨宋代版印昌盛环境下的群体阅读意识与行为,了解社会各阶层的阅读价值取向以及不同群体的阅读习性等,有助于更好地汲取传统阅读文化中的中国经验,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中坚定文化自信。
2 宋代版印昌盛格局的形成与阅读普及
“文化之于根据,犹精神之于形骸。典籍者,又文化所赖以传焉者也”,宋代版印的繁盛和图书普及,是宋代群体阅读意识的觉醒和阅读文化发展最基本的条件。宋代版印机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广前所未有,形成了政府、私家、书坊、书院、寺院等多重出版系统,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一套集创作、出版、阅读为一体的完整版印产业链,全国自上而下、由公到私都风行版印图书事业,图书出版业进入全面发展时期。由于版印传媒具有价格低廉、传播迅捷、便于携带等优势,印本图书成为一种普通商品进入消费市场,“家至户到”“即日传播”等现象司空见惯。宋版图书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门类,不论是旧学商量还是新知培养都能自得其乐,满足了不同社会群体的阅读需求和乐趣,也使阅读多元化和主体多元化成为宋代阅读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宋代阅读文化的力量在于“百姓日用而不知”,阅读的浸润在于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堪称古代阅读文化昌盛的典型。大学士汪洙在《神童诗》开篇就提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处州(今浙江丽水)“家习儒业,声声弦诵半儒家”[1],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2]。晁冲之在《夜行》中提到“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夜深人静路过孤村,看到灯火首先想到的是主人在读书而非其他,可见整个社会浓郁的阅读氛围。
宋代是写本时代向印本时代转变的重要时期,雕版印刷的普及和图书出版的空前繁荣,加上右文崇儒的政策和科举制度的强势助推,使阅读成为宋代一种普遍的群体活动。版印传媒作为宋代最先进的传播媒介,降低了信息传播和流转的门槛,扩充了书籍阅读的容量,扩大了社会的阅读人数,刺激了阅读活动的开展,也引发了阅读观念的嬗变。文学创作与阅读接受周期大幅度缩短,昔日被供奉于“精英”“贵族”神坛之上的阅读文化,不再为豪门望族和通都大邑文人墨客所垄断,开始浸润到普罗大众的生活中,成为宋人的群体权利,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和群体自觉阅读意识得到开发,阅读群体急剧壮大,阅读向往加速扩张。
3 宋代群体阅读意识与阅读行为
3.1 不同阶层群体对阅读的倡导与实践
宋代读书人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上到帝王将相、士人学者,下到平民百姓,从通都大邑到广大农村乃至穷乡僻壤,倡导阅读成为宋人普遍的自觉意识,“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3]“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亦吟咏不辍”[4]等现象随处可见,整个社会书香弥漫,阅读普及率远高于前代。宋代出现许多名垂千古的全才型人物,与这种浓厚的阅读文化氛围不无关系。
宋代阅读之风的盛行始于统治者阶层,得益于历代帝王的垂范。《续资治通鉴长编》曾记载宋太祖行军时也经常手不释卷,称帝后多次提倡“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认为宰相必须由读书人担任。宋太宗无所爱,但喜读书,认为书籍是“教化之原,治乱之本”,“听政之暇,唯务观书”,留下了“开卷有益”的佳话。宋真宗倡导“五经勤向窗前读”,作诗“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宋仁宗诏令范仲淹等人多次掀起全国性大规模的兴学热潮等。宋代皇帝还经常“视学”,巡幸秘阁鼓励文教,极大地振奋了读书人的精神。宋朝历代帝王亲身示范,营造了浓郁的阅读氛围,朝野上下读书蔚然成风,有宋一朝历代帝王喜好读书,文化修养也普遍高于其他朝代,这在中国历朝历代帝王群体中也是比较罕见的。
流风所及,上行下效,士大夫们也纷纷以劝学阅读为重。司马光以“此趣人谁识,长吟窗日斜”表达对阅读的喜爱;欧阳修认为“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黄庭坚曾教育他人“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常作灾”;郑刚中认为阅读是“此殆有至乐,难今俗子知”;王安石在任明州知县时,推崇兴学阅读,当地文风大振;滕子京任湖州知县时,当地“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尤袤提出“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等;苏轼从年少时就“立志读尽人间书”;家颐《教子语》提到“人生至乐,无如读书”;朱熹提倡“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陆游更是写下了大量与阅读有关的诗句,表达自己终身阅读的乐趣。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劝勉自己、他人、后人阅读的现象屡见不鲜,阅读成为一种群体追求,直接丰富了宋代阅读文化的内涵。
在版印繁盛的背景下,在统治阶层的带动下,在科举制度的刺激下,整个社会开始倾向于鼓励更广泛阶层和地域的群体,自觉投入社会阅读风气的优化中,直接推动了平民百姓们也投身阅读,读书人队伍迅速壮大,出现了阅读的民众化倾向。叶适在《汉阳军新修学记》提到“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吴郡“师儒之说,始于邦,达于乡,至于室,莫不有学”,福建永福“家尽弦诵……工农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饣盍 妇,亦能口诵古人语言”,绍兴地区“弦诵之声,比屋相闻”,群体自觉阅读意识及阅读普及程度可见一斑。
伴随着社会普遍倡导女性知书达理,女性群体阅读意识也迅速觉醒,尤其是士大夫家庭中的女性更多承担着教养子女的重任,女性阅读形象更为鲜明。已有部分学者对宋代女性阅读活动进行探索,表明宋代女性阅读涉猎范围广,涵盖儒佛道经典、女教典籍、家训、史书、诗词、音乐、诸子百家、方技小说、天文、医药等各方面[5]。宋代女性的阅读对象随着时间、身份、境遇的变化而变化,幼年时多习读儒家和女教经典,嫁为人妇后以课伴后辈阅读为主,晚年则较多阅读篇幅较短、通俗易懂的佛道典籍[6]。有宋一代阅读在女性群体中盛行且多才女,《宋诗纪事》记录在案的女诗人就达百余人,《全宋词》中收录了百余名女词人的作品。这些女性群体阅读量巨大且阶层跨度极大,上至后宫佳丽,下到婢妾娼妓,其中不乏像李清照、朱淑真这样的历史名人。《李清照集校注》和《朱淑真集》共引用魏晋六朝诗文典故多达70余处,可见其阅读面之广。宋代女性群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宋代群体阅读意识增强与阅读文化普及的直接表现。
3.2 群体意识与集会阅读
宋代文人具有较强的结社、结派与结盟的意识,读书人的集会活动就是文人群体儒雅化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以日常交游、诗酒酬唱为纽带,不同层次的文人群体逐渐形成不同形式的集会活动。宋代文人集会活动的规模与频率也远超前代,且不再以皇宫为中心,而是蔓延至都市、乡村各个地方,集会活动的主体涵盖了官僚大臣到举子书生等各个层面,成为宋代读书人的一种普遍活动方式和生活组成。文学阅读与创作向来与读书人集会活动密切相关,《读李益诗》中提到“与彭城诗社诸君分阅唐诸家诗,采其平生,人赋一章,以姓为韵”,文人在集会时通过赋诗、传阅、品评、文艺创作、相互唱和、切磋互补,加强了群体联系与认同。著名的有欧阳修、苏轼、钱惟演三代文坛盟主发起的众多文人集会活动,开拓了新的阅读体验与活动空间。熙丰时期司马光、程颢、程颐、邵雍等人所形成的文化群落和文人群体,通过频繁的结社、鉴赏与唱和,成为当时洛阳的学术文化中心,新变派、元体、江西派等文人群体集会唱酬也都被传为美谈[7]。
宋室南渡后伴随新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形成,人口流动变得频繁,文人群体开始分裂与重组,具有地域依赖性的文人群体词学唱和活动重新活络,著名的有周密、施岳等人结成的西湖吟社,淮西王之道、张文伯等人的集会唱和,临安词人群体、台州词人群体、湖州词人群体等,在结社聚唱间研磨交流、创作赏析、商榷填词、赠书借书,多种门类艺术的交融也促生了诗、词、书、画珠联璧合的艺术创作,加强了文人群体内部的联系[8]。他们通过各自不同的阅读理解与文学表达,使阅读与创作从个人活动转向群体活动,并在群体中逐渐形成一致的文化审美与追求。宋代众多文学流派的形成也是群体自觉意识觉醒和集会风尚的有力佐证,是宋代文化区别于前代的显著特征,读书人集会作为宋代阅读文化的一种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极大提升了宋代阅读文化发展的高度。
此外,宋代“曝书会”发展成为常态性的图书展览会。曝书起源初衷在于曝晒图书防止蠹虫霉变,至宋代逐渐成为具有官方和群体性质的阅读盛会。专门论述宋朝馆阁制度的《蓬山志》中提到“秘省所藏书画,岁一曝之,自五月一日始,至八月罢”,《神宗正史 ·职官志》记述馆阁“岁于仲夏暴(曝)书”,《南宋馆阁录》也对绍兴十六年到开禧元年举办的24次曝书会进行了详细记载,可见曝书会是宋代一年一度、具有图书展览性质的文化“年会”。除个别年份因政局动荡等特殊情况不能举办外,曝书会几乎年年举办,每次持续两三月之久,使许多珍藏于室的作品得以重见天日,允许许多非馆阁成员入内观赏阅读并赠送《太平广记》《春秋左氏传》各一部,极大地带动了官僚士大夫群体对“书展”阅读的兴致,叶梦得、梅尧臣、苏轼等人都曾因在曝书会上得见珍稀藏书而兴奋不已,写下相关诗文作品。宋代民间私人曝书会也比较常见,如藏书家宋敏求多次举办曝书会,以书会友,观者如云。《宋史》记载:“敏求家藏书三万卷,皆略诵习,熟于朝廷典故,士大夫疑义,必就正焉,著述甚多,学者多咨之。”许多读书人为方便向其借阅图书,纷纷在宋家附近居住,使得附近的租金都涨了许多。虽然宋代文人群体集会形式繁多,但最具有书卷气息的还是以观摩探讨交流为主旨的曝书会,这也最符合读书人群体的身份追求和气质,充分体现了宋代对图书发展事业的重视与对文人群体的尊重。曝书会上文人群体观鉴揣摩、考较才学、切磋问学,为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交往游从创造了机会,也激发了彼此的鉴赏情趣和创作灵感,文人之间的集团性与群体性也得到加强。
3.3 藏书活动的兴旺与藏书家的藏书理念
藏书是阅读活动的对象,藏书的目的是阅读和研究,积书而读、丹铅治学是宋代藏书文化的优良传统,藏而能读、书尽其用是宋人阅读的普遍心态。宋代藏书机构众多,官府藏书、书院藏书、寺院藏书和私人藏书等系统均发展完备,单是官方主要图书机构就曾有秘书省、崇文院、史馆、国史院、政典局、提举所、秘阁、校勘所、编校所、补写所、著作局、书版库等,反映了统治阶级对藏书的重视。两宋的私人藏书活动也异常活跃,据《中国私家藏书史》统计,两宋藏书家达700余人,是千年来藏书家总和的近三倍,其中藏书万卷以上200多人,数量超过了许多官方藏书,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藏书家,如司马光、宋绶、曾巩、叶梦得、欧阳修、宋敏求等。藏书作为一种普遍活动和大众意识,折射出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与重视。持续不断的读书生活及阅读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促使宋人产生自觉、强烈的藏书意识,丰富的藏书也为他们阅读、著述、学习、研究提供了便利,进一步推动阅读热和藏书热。
宋代藏书家非常提倡藏书交流,例如欧阳修、刘恕、王安石等都曾长期向宋敏求借阅图书,李清照夫妇均喜好藏书、借书、抄书,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刻印了许多质量上乘的图书。藏书家们相互借阅、传抄、刊刻,就是读物的一次次迁徙和阅读的拓展。宋代藏书家几乎每一位都是文献学家[9],他们坚持藏校并举,收藏图书的同时加以校雠,著名藏书家宋绶、史学家郑樵、南宋方崧卿等均有亲自校雠的美谈流传,校雠的过程就是熟读书籍的过程。许多藏书家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进行著书立说等学术活动,著述与阅读相辅相成,私家庋藏蔚然成风,著述活动兴盛,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群体阅读共识的达成。藏书家们不仅利用藏书满足自身阅读和治学的需要,还将藏书看作是为子孙后代观书治学或读书科举的基石,更是泽及子孙后代的启蒙教育和成才教育的养分,是藏书家们普遍怀揣的藏书理念。尽管世家大族是家庭藏书事业的主体,但普通士大夫及寻常人家,只要稍有能力都会尽己所能丰富家庭藏书,苏轼曾描述当时人们“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读书人迫切渴求阅读及藏书的形象跃然纸上。宋人将藏书看作是将家庭优秀素质传承下去的重要媒介,除去阅读应试和家产遗后的藏书心态之外,阅读更被认为是普通百姓自身素质、人格品位及社会地位的体现,藏书群体相当庞大,阅读氛围浓厚。
4 宋代群体阅读习性与阅读文化的发展
4.1 群体阅读导向与书商图书刻印
宋代以科举考试作为官僚进用的主要途径,使部分应举入仕的读书人在阅读目的与动力上带有强烈的现实需求,其中尤以平民群体的功利性阅读较为突出。阅读仕进的模式为他们提供了垂直向上流动的阶梯,研习经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宋代士人群体最深沉的情怀,赵普入相前曾说“吾本书生,偶逢昌运,受宠逾分,固当以身许国”[10],范仲淹也曾慨叹“自省寒士,遭逢至此,得选善藩以自处,何以报国厚恩”[11]。希望依靠教育和科举实现阶级跃进的新兴士人群体,将“仕以行道”发展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士为知己者用”的感恩心态,激发了整个群体对“致君尧舜”和自我价值的强烈渴求,也直接影响了群体的阅读选择,追求发奋研读的同时强调经世致用,将阅读所得社会化,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作为科举最重要的科教书籍,四书五经在阅读的先后顺序上长期占据首位,这其中固然有传统的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但也是士人群体对儒学价值的普遍信仰与认同。“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六经》不可一日去手”“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也”等被奉为金科玉律,先儒家经典后百家,阅读主次之分相当明显。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士大夫,从书房走向上流社会,阅读已成为该群体最习惯的休闲方式[12],此时的士大夫群体阅读更加追求世俗乐趣,“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便是许多士大夫阅读生活的写照。
为满足广大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宋代书商在版印图书的选择上也遵循“市场规律”,呈现书商群体独有的判断性和指向性。例如,优先售卖科举考试用书、经典著作,生活类书籍如医书、农书等因其受众目标较广,也成为书商选题出版的方向。此外,书商抓住士大夫喜好阅读鬼神志怪和猎奇的心理,将洪迈所编鬼神怪异之事的《夷坚志》印成书册,果然成畅销之书,“士大夫或传之,今镂板于闽、于蜀、于婺、于临安,盖家有其书”[13],可见书商对群体阅读的理解和把握,是阅读市场的一个重要风向标。从更大的市场来说,书商巧妙地迎合了各阶层群体的阅读期待,将读者的阅读需求反馈给作者,以图书种类、内容、版本、数量等回应读者的阅读需求,将阅读需求、创作导向和出版传播联系起来,成为引导群体阅读走向的重要力量。考虑到不同群体阅读旨趣与理解能力的不同,书商也有区别化的方案。例如针对农夫“辄抄《要术》之浅近者摹印”,将农学名著《齐民要术》中较为浅显易懂的内容选择性刊印出售,诸如此类例子甚多,书商以此提高市场占有率,也极大地推动了“全民阅读”。值得一提的是,宋代书商在刊印书籍时,开创性地在书后附上相同系列书籍或即将刊印的新书。如南宋《后汉书》记载“今求到刘博士《东汉刊误》,续此书后印行”[14],这种类似新书推介的“广告”也起到了吸引读者阅读的作用,读者可根据推荐目录和相似图书进行拓展阅读。
4.2 群体阅读感受与方法论
宋代文人群体的共同理念中,阅读被视作一种美好享受,普遍体现出对书斋生活的热爱与追求[15]。他们从阅读中汲取知识的养分,获取无尽乐趣,书写阅读生活、表达阅读之乐的作品更是浩如烟海。司马光《书楼》写道“使君有书癖,记览浩无涯……此趣人谁识,长吟窗日斜”;郑刚中《书斋夏日》写道“文书任讨探,风静香如丝。此殆有至乐,难今俗子知”;叶采《暮春即事》写道“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翁森《四时读书乐》将春夏秋冬不同时节阅读的情趣诉诸笔端,至今仍被视作情致高尚的劝学诗;尤袤写道“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欧阳修感慨“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并在《学书为乐》中提到“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16]。与“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这种丧失读书乐趣的苦读相比,宋代士大夫不是以勉强的态度去阅读,更多像如今我们所提倡的“悦读”,对书斋生活的沉溺,对阅读的美好体验与追求,都彰显了士大夫群体积极的、持久的阅读感受。
如果说宋代文人群体对阅读是“心之所向,身之所往”,那么由此衍生的阅读方法论则是阅读生活自然而然的产物。士大夫对于阅读方法的见解大有异曲同工之势,例如张载主张阅读“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黄庭坚认为“泛滥百书,不若精于一也”,陆九渊也主张“读书最以精读为贵”等,都在强调“精读精思”的要义。在此基础上分专题阅读和反复阅读的观念也被提出,如苏轼主张“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因此他在阅读时“盖数过而始尽之……每过博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而精读往往是在“慢阅读”过程中完成的,程颢主张的“读书要玩味”,陆九渊主张的阅读“须是平平淡淡地去看,仔细玩味,不可草草”等,都在强调“慢工”的理念。文人群体的阅读经验与方法集大成于朱熹,他总结了阅读的“两心三到”,即“为学读书,须是耐心,细意去理会,切不可粗心”“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并将熟读精思、读思反复、细嚼玩味、知行合一等为众人所认同的阅读理念进行系统性论述,其中许多阅读方法对当时乃至后世的读书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4.3 市民群体阅读呈现“雅俗共赏”倾向
随着市民经济的发展、社会观念与风气的转变,市民个体逐渐向群体转变的过程中,形成了超越身份和职业差别的文化趋同意识和阅读价值倾向,推动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组,“至北宋而达于顶点的城市革命”直接促成市民阶层群体的兴起和壮大。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也使士人文化开始走向普罗大众,促成了通俗诗词、话本等新文学形式的盛行,与此同时,原本流行于底层群体的说唱、戏剧等民间文化开始跻身主流文化队伍。日益壮大的市民群体,和不断成熟的市民阅读载体,也意味着作者群体和阅读群体的集体下沉,形成了雅俗共体、雅俗共赏的独特局面。阅读存在于大众活动与大众传播之中,并为市民群体所共有,满足了不同身份、职业、年龄、性别群体所构成的市民阶层多元化的心理需求和价值认同,形成了以不学无术为耻的社会风气。
市民的阅读情趣开始向日常生活倾斜,许多文学作品便取材于市井细民的生活、情感、思想愿望等,“接地气”的作品受到大家的普遍追捧,也因此促成了通俗文学的流行。尤其在国家承平日久的时期,休闲娱乐的阅读倾向更加明显,词的兴起就是适应市民群体的精神需求。“盖长短句宜歌而不宜诵,非朱唇皓齿,无以发其要妙之声”[17],作为一种咏唱艺术,词曲可以说是以视听的形式来阅读作品。伴随着都市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出现了许多歌楼酒馆、勾栏瓦肆,市民们迎来送往之时都有唱曲助兴,很多时候市民为了遣兴娱情,创作一些集表演性、音乐性为一体的词作,以求更高的“乐”读感召力。市民自发自主形成的会社组织也开始大量涌现,文会、诗社、词社遍地开花,形成新的创作和阅读风潮,极大地增强了市民群体阅读的生命力。
宋代版印传媒的繁荣为话本小说的兴起和“说话素材”的积累创造了条件,也相应地产生了“说话人”职业。据统计,宋代仅汴梁和临安两个都市,有文献可考的“说话人”就达124人[18]。《清明上河图》中多处展示了宋代东京街市上民众聚集听说书的画面。一批批高素质的“说话人”,将小说、史书、公案、战事、佛书等,以街头讲述的形式承接了市民的阅读需求。人们冲破了以往忌俗尚雅的阅读取向,欣然接纳了新的文学形式和阅读趣味。市民群体的需求使优秀的说话作品有了被保存和继续阅读的价值,书商们为利益所驱动,完成整理刊印、公开发售、供人阅读的过程,并在加工过程中使描写更加细腻,以迎合读者的阅读感受[19]。“说话人”需要丰厚的艺术积累和宽广的认知,所掌握的大量知识来自丰富的阅读,话本作为“说话人”表演所用底本,以其独特的表演艺术吸引市民群体的争相“悦”读。此外民间戏曲、平话、弹词等通俗文学成为市民群体自我叙事和自我审视的有效途径,体现了市民群体对都市阅读文化的一种集体认同,是不同于士大夫群体的新的理解追求与愿望表达。代表文化身份和审美品位的士大夫阅读行为,和代表市民群体文化诉求的阅读活动,都是宋代阅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5 结语
宋代雕版印刷的发展促成了图书信息量空前的盛况,改变了社会的阅读环境与阅读习惯,各个社会层次的群体阅读想象与文学创作产生了交织与重叠,呈现出阅读文化的丰富性与多层次性,形成浓厚的读书风尚。现今我们同处知识传媒变革时期,开展宋代阅读文化研究与经验总结,具有鉴古知今的现实意义。宋代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顶峰”,恰恰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经验最重要的内核之一。增强文化自信就要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开发,推广全民阅读就要思考传统阅读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宋人群体所秉承的“修齐治平”的阅读志向、知行合一的阅读观念、融会贯通的阅读方法以及终身学习的阅读情怀,传承至今的文学价值、治史崇文等思想理念,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宝贵经验。赋予优秀阅读文化新的内涵和表达方法,挖掘其中蕴含的提升文化自信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和独特的精神气质,有助于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为培养良好的阅读风尚、净化社会风气、提高民众素质、坚定文化自信提供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