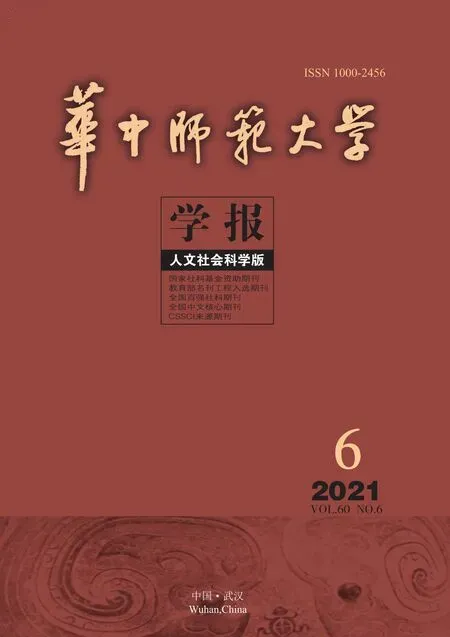清代漕河中的百万“衣食者”
——兼论清代漕运对运河大众生计的影响
吴 琦 李 想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清代漕运是京城不可或缺的粮食保障和朝廷政局稳定的重要物质基础,关系国计民生,因而备受清廷重视。同时,清代漕运也是朝廷在地方社会运行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所涉区域最集中的一项国家事务,尤其是对于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方面,有着直接的、长期的、深层的影响。
清代漕运催生了一批以漕运或漕运衍生行业为生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不仅各有分工而且数量庞大,文献记载:“漕河全盛时,粮船之水手,河岸之纤夫,集镇之穷黎,藉此为衣食者不啻数百万人。”①漕运和运河成为大众维持生计、获取利益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场域,依漕为生的社会群体融入这个场域,既是这一生存环境的营造者,也是“藉此为衣食者”。对此,学术界从不同角度予以了关注和研究②,主要针对部分与漕运相关群体,如漕运水手、纤夫、河工等进行了梳理,并一定程度探讨了这些群体与区域社会变动的关系。但以往的研究缺乏对依漕为生群体的系统性和全面性考察,对于漕运与这些群体关联与互动的剖析也明显不足。本文考察清代依漕为生的运丁和水手、纤夫和脚夫、浅夫和泉夫、商人和贩夫等主要群体,并揭示清代漕运对于区域社会的影响。
一、运丁和水手
运丁和水手是清代漕运的直接参与者,有运输漕粮之责,也是最显著的藉漕为生的“衣食者”,两者合计达十余万人,以至于康熙年间有“通漕旗丁、水手十万家”之说③。清初沿明旧制,以运军承担漕运,只改明代卫所为屯卫,改卫军为旗丁,亦称为运丁。按清代军运方式,原本每艘漕船上的劳力都是运丁,但在实际运行中无法实现,变通的方法是以一到两名运丁负责领运,其他劳力全部通过雇募的方式按额募集,雇募的劳力称为漕运水手。行之既久,清政府认可了漕运雇募水手的合法性。于是,运丁和水手一起承担每年的巨额漕粮运输任务,以此获得安身立命的钱粮,同时他们在漕运过程中进行广泛的私货贸易,为沿运区域带来巨量的商货,极大地改变了沿运区域的商业环境。
清代的屯卫是政府管辖下专责漕运的军事组织,运丁属于屯卫的军籍,不得改投别差,违者严肃处理。因此,运丁运输漕粮成为一种父子相承的世业。根据光绪《钦定户部漕运全书》的记载,清代全国的额定运丁总人数为六万五千四百余人④,而每年在运河上直接参与漕粮运输的运丁有一万余人⑤。为保障漕运的平稳运行,清廷给予运丁诸多方面的报酬和待遇,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月粮、行粮、赠贴等报酬。月粮是按月发给运丁的粮饷,保证运丁及其家庭的日常所需;行粮是运丁出运之年,官府给予他们运输途中食用和花销的粮饷。二者数目各省不一⑥。每名运丁每年所得行、月二粮,合计在十二石至十四石左右。行、月二粮的发放方式,清初之时主要折银支给,其后逐渐形成本折各半的定例,即一半给本色粮米,一半给折银,每石本色米可换算银一两四钱⑦。清廷对行、月二粮如数发放的管理十分严格,“务同漕粮并兑”,如果漕粮兑完而行、月二粮未完,要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⑧。此外,清政府为保运丁每年能完成粮运工作,还给予一定的赠贴。此项津贴在各地的称谓有所差异,光绪《钦定户部漕运全书》记载,江南称为“漕赠”,浙江称为“漕截”,山东、河南称为“润耗”,江西、湖广称为“贴运”;支给数额各省也不同,如“江安山东河南每米百石征银十两、米五石;苏松常镇四府每米百石征银十两、米五石;浙江每石征漕截银三钱四分七厘;江西每石赠银三分、赠米三升,又征给副耗米一斗三升;湖广无加赠银米,康熙十年,题准于四耗之外加耗二斗,随粮征给”⑨。另外,运漕之年,如遇闰年和闰月,也均有补贴。
第二,耕种屯田的收入。清廷沿袭明制,分派屯田给运丁及其家庭耕种,屯田的产出以资赡运。有漕八省运丁的屯田共68361.75顷⑩。针对各屯卫屯田多寡不同的情况,清廷实行统一的屯田贴补制度,屯田不足的屯卫则发给等价的赡运银,每艘漕船约可得到150亩屯田收入的贴补。
第三,土宜货物的贸易获利。清政府允许运丁在漕运途中携带一定数量的免税土宜,交易后的利润归运丁支配,以此贴补运费。从清初开始,政府允许每艘漕船携带的土宜数量不断增加,从60石到100石、126石、150石,最终在道光七年(1827)增加至180石。漕船回空时还可携带60石的免税土宜,嘉庆五年(1800)又增加到84石。清代漕船重运北上和回空南下所载土宜总量巨大,据张照东先生统计,清代内河漕运最兴盛时期,每年通过漕船附带并流通的南北商货,平均达四百万石以上。这个数额还只是清政府允许的合法携带量,如果包括实际运行中违规夹带和违法揽载的商货,这个数量还要大大增加。据李文治、江太新估算,每年漕船所带的各种商货,“可能到600~700万石乃至800~900万石”。如此巨量的商货在运河沿线周转贸易,所得利润不但为运丁提供了必要的收入,而且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沿运区域商业的繁盛和城镇的繁荣。
第四,其他临时性奖赏。例如,运丁提前按额完成粮运任务,清廷还会给予临时性奖赏,以资鼓励。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山东、河南等省的漕船提前数十天完成当年的漕运任务,乾隆皇帝下旨加赏,“每正丁一名,给银一两”。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清廷为保障漕运顺利运转,给予运丁多种报酬和补贴,然而在实际漕运中,由于物价上涨、屯田丧失、易遭勒索以及肩负巨大的赔补责任等多种原因,大多数运丁的生活入不敷出,处境窘迫,“所得津贴不敷沿途闸坝起拨、盘粮交仓之费,倾覆身家,十丁而六”。针对运丁这种窘迫的生存境况,清朝历代统治者也采取了一系列优恤措施,如借银救济、清理屯田等,但效果甚微,运丁的贫困问题一直延续至漕运废止。
水手是在船舶上从事操舵、划桨、撑篙、升降船帆、装卸货物等工作的劳动者的统称。在清代漕运的绝大部分时间中,雇募的水手成为漕运劳力的主体,这在康熙中后期已经显现。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廷对每艘漕船应雇募水手的人数定规:“漕船出运,原系佥丁一名,雇募水手九名。今以数军朋管一船,易致推诿。应仍照旧例,每船佥选正身殷丁一名,其余名数总以身有家属、撑驾谙练之人充当。”这一规定说明在康熙三十五年之前,已经普遍存在每艘出运漕船除一名运丁外其余九名均为雇募水手的现象。上述规定只是重申旧例而已。据此,康熙中后期的漕运水手已占到漕运劳动者人数的90%左右,成为漕粮运输的主力。按每艘漕船九名雇募水手计算,每年从事漕运的水手约有6万人。
清代漕运水手大多来源于沿运地区的流民,他们身处社会底层,缺少其他谋生的手段,极度依漕为生。康熙二年(1662),漕运总督林起龙在奏疏中提及当时的漕运水手多是“赤贫穷汉”,在漕船上辛苦一年,“每名止得身银六两”。此价格并不是清初雇募水手的固定标准,水手被雇佣后为了多获雇值,经常与运丁发生纠纷,“加添名色,聚众打抢,扰害官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漕运的正常运行。为减少纠纷,维护漕运的稳定运转,雍正元年(1723),清廷将各省各帮雇佣的各色水手工价开列,形成定规,绝大部分普通水手往返一次的雇值在三两至六两之间,远少于运丁的各种报酬。事实上,雍正以后,就连这样低标准的收入也难以保证。嘉庆年间,漕运水手的实际收入远低于额定标准,生计窘迫,漕运总督铁保奏请“加头舵各工一千文,水手身工五百文”。道光时期,水手工价又一度回落,“水手雇值,向例不过一两二钱”。
咸丰之后,运河漕废,数万漕运水手失去赖以为生的工作,大多成为无业流民,极其贫困。他们有的被迫参加农民起义,有的参加清军,更多人渗入沿运地区,组成盐枭、青帮等社会组织,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
窘迫的生存状况下,运丁和水手通常会纠合在一起,组成利益共同体,最大限度利用朝廷的政策规定,在出运过程中大肆进行贩私活动,以至于贩运私货成为运丁和水手的重要副业,这是其依漕而生的重要途径。当然,与运丁相比,水手群体人数更多,境况更困窘,加之其受雇的特殊身份,会表现出更强烈的趋利冲动。另外,运丁和水手还在漕粮兑、运的过程中,极尽所能地勒索州县、敲诈商船、偷盗漕粮等。他们围绕生存、生计的所有活动不断地影响运河区域社会,并融入运河沿岸的社会经济生活之中。所以,漕运运丁和水手既是有漕区域尤其是运河区域社会生活环境的营造者,又是其中的“衣食者”。
二、纤夫和脚夫
清代的大运河干道为南北向,北高南低,重运漕船由南而北,逆水而上,途经闸坝、险溜等复杂地形,或遇到干旱、泥沙淤积等导致运河淤浅等状况,皆需人力牵挽才能前行。同时,清代运河两岸商业繁荣,众多民船穿梭其中。因此,在运河沿线形成了数量庞大的纤夫群体。
清代运河纤夫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来自于沿运州县承担拉纤差役的民户,主要为官船拉纤。如乾隆年间,英马戛尔尼使团访清时,看到运河边的纤夫就是官派纤夫:“他们大多是老弱病残,有的瘦里巴干、面带病容、衣着褴褛,一群人看来应上医院就医,而不应去干苦活。我们的同伴解释说,租种河流或运河畔公家土地的农民,在租种期间都要在需要时刻出人力给政府的船只拉纤。”另一种是专门以拉纤为生的人,通常被称为“短纤”。这些人多为流民或者生活贫困的百姓,他们聚集在运河沿线,等待漕船运丁的雇用,以此获得勉强糊口的酬金物资。运河沿线以拉短纤为生的群体数量巨大,《湖海文传》记载:“国家漕东南之粟,上输神仓,联巨舰以载……艘入运河,沿河左右待募牵缆之夫亦不下数万人。”
清代,运河纤夫的工作量大,非常艰辛。如从淮安清口至徐州张庄一段运河,长仅二百里,但一路逆水溯黄而上,一艘漕船需要纤夫二三十人才能牵拉,每日只能前行几里,大约两个月才能完全通过:“自清口以达张庄运口,河道尚长二百里,重运溯黄而上,雇觅纤夫,艘不下二三十辈。蚁行蚊负,日不过数里。……迟者或至两月有奇,方能进口。”山东运河沿线的百姓亦认为在诸多差事中,“最苦者无如纤夫”。清初诗人梁清标曾亲眼见到运河纤夫拉纤,并作《挽船曲》一诗,感叹纤夫之苦:“穷民袒臂身无粮,挽船数日犹空肠,霜飚烈日任吹炙,皮穿骨折委道傍。”
清代的运河纤夫劳苦万分,但出卖的只是廉价劳动力,所获十分微薄。清初,漕船重运北上,遇闸坝险溜处,由该船的运丁负责酌情雇募纤夫,船只过后即解除雇用,所以沿途短纤并无定价。行之既久,弊端丛生,运丁和短纤之间纠纷不断。运丁方面想压低雇值或以货物充当脚价;纤夫方面或串通沿河官兵勒索运丁,“倍出工价”,或在漕船航行至险要处乘机索要加价,“不遂则哄而散”。为稳定沿河秩序,清廷在乾隆五年(1740)制定了统一的短纤脚价标准:“短纤每夫每里给钱一文,打闸每夫给钱一文,如闸坝水急,夫役守候,临时酌增。”乾隆三十年(1765),对运河各段的短纤雇价重新定规:“乾隆三十年,经漕臣咨准,以水势顺逆,酌给短纤每夫每里制钱一文半至三文不等。又北河自杨村至通州,每夫每里给制钱二文,如遇大雨路泞、纤夫短少之时,仍听该帮弁丁等自行酌量加增,亦不得过每里四文之数。”嘉庆时期,朝廷又重申乾隆时的雇价旧制。可见,清代官方规定的沿途短纤雇价,每夫每里一文至四文不等,价格可谓低廉。
脚夫是从事货物搬运、以体力劳动换取报酬的从业人员的泛称。脚夫早已有之,在全国各地均有分布。至清代,脚夫数量在运河沿线增长迅速,是沿运城镇最常见的群体之一。究其原因,一是清代漕运的兴盛和运河的畅通带动了沿运区域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南来北往的巨额商货在沿运区域频繁交易,需要大量搬运货物的脚夫。从众多相关的文献记载来看,脚夫聚集、活跃的地方,多为商业繁荣、市场兴盛的市镇。二是随着沿运区域商业化城镇的发展繁荣,附近农村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有所提高,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渐减,农业领域的多余劳动力流向可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城镇,其中很大一部分加入到职业门槛较低的脚夫行业。
脚夫群体在沿运城镇中广泛集聚。如苏州府城“地方冲要桥梁,向被脚夫恃强霸踞”;淮安府城西北的河下镇为沿运重镇,很多附近的农民从事搬运工作,“食力之家不下数千户”;通州运往京师的漕粮在经过通惠河上的五闸时,需要数量众多的脚夫搬卸过闸,这五闸的脚夫归就近的闸官管辖。
脚夫有固定工和临时工之分。固定工多为城镇内的贫苦民众,“日则聚集桥顶,夜则各归其家”。有的父子相承,几代都做脚夫。临时工多为近郊的农民,或外地到城里谋生的人。他们农闲时进城挣钱,农忙时回家种田,流动性很大,就像放鸭子一样,吃饱就走,故名“放鸭子的”。清代,由于脚夫群体的发展壮大,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脚夫组成的行业工会——脚班。脚班根据所装卸货物的不同又分为粮食班、杂货班、陶瓷班、皮货班、煤炭班、药材班和竹木器班等。脚夫主要活动在沿运城镇的码头、商业街市、货栈等处,他们坐地待雇,有人雇募时即商谈脚价,谈妥后即搬卸货物,赚取雇值。运河沿线区域脚班的生活主要依靠着大运河,正如歌谣《济宁州·赛银窝》:“老运河,南北长,水流济宁到苏杭。交通方便行商多,南门枕着运粮河。船只不来货不多,扛大个的都闲着。船一靠岸就卸货,脚班搬运忙得多。”
脚夫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受雇获得的脚价,脚价多寡又与扛搬的货物及路程远近相关。史料对脚夫脚价记载不多,且与其他费用混在一起,难以精确统计。道光年间,户部尚书英和提及漕粮过坝脚费,“自清江高坂头起卸,至黄河水口受载,雇佣小船、小车、扛夫等脚费每石需银二分八厘”,具体到每名脚夫,所得雇值更加微薄。总的来说,由于脚夫群体出卖的是廉价劳动力,且同行间竞争激烈,所获收入“常不足糊口,加以晴雨无时,道途羁滞,彼为脚夫者,无以赡其家室”。
纤夫和脚夫属于典型的社会底层的“衣食者”,大多是来自于运河沿线的穷苦农民或流民,依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挣取养家费用。然而,这是运河上每年数千艘漕船及其他各类船只频繁往来而促成的一种社会生活场域,在清代漕运大规模运行及运河物资交流繁荣的环境下,纤夫和脚夫群体应运而生并发展壮大,成为清代运河全盛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浅夫和泉夫
运河开凿之后,由于自然原因,经过一定时间便会出现泥沙淤积而致使河道变浅的问题,易造成漕船阻滞难行或搁浅,影响漕运的运行。淤浅之处必须开挖疏浚,漕船方能通行。这些挖浅的人夫称为“浅夫”。
浅夫最早出现于明代,清代为维持运道畅通,也在运河沿线设置浅夫。浅夫的来源有军、民之分。清初的民浅夫主要在沿河州县中佥派,但由于工作繁重,所得工食银较少,不足糊口,佥派而来的浅夫多有逃亡。因此,康熙初年之后,民浅夫逐渐改为雇募:“康熙十二年,议准停止河南佥派河夫,如遇岁修,准动河道钱粮雇募,每夫一名月给银二两;十三年,覆准江南河夫停止佥派,准动河银召募,每夫一名月给银一两二钱;十六年,题准河南河夫照江南例,每日给银四分。”雇募浅夫的工食银最高时达到每名每月二两,后来雇值降低,每名浅夫每年能获得雇银五六两至十二两不等:“黄、运两河各有额设夫役以供修浚,而各夫工食每岁每名或十二两,或十两八钱,或七两二钱,或五六两不等,其坐支于河库者,详明批给。”乾隆十一年(1746),户部议准在北运河“长设浅夫三百名,每月各给工食银一两二钱”,此雇值应为乾隆时期雇募浅夫的普遍身价。浅夫的工食银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在雇募所在地的州县地丁银内拨补,一是在修河的河库银中动支。
除民浅夫外,清初还设有军浅夫,即以卫所军士充任浅夫,但由于清代卫所的大量撤废,军浅夫制度逐渐改为河兵制度。康熙至乾隆晚期,民浅夫与河兵并存,一同负责疏浚淤塞,保运道畅通,但总的趋势是民浅夫数量益少而河兵数量益增。大致在乾隆晚期之后,河兵取代民浅夫成为河工最主要的力量。
泉夫也起源于明代,主要集中于大运河的会通河段,负责疏浚会通河附近的泉源和泉道,使泉水流入运河,补给枯水期的运河水量,以维持漕运的畅通。入清之后,会通河段以泉济运仍是济运保漕之必需,关系国家大政,即“东南岁漕数百万藉以达京师者,惟运河一线,而运河之得以不匮,惟泉源是赖”。为保障运河的畅通和漕运的正常运行,清代在山东会通河沿线的州县设置泉夫,负责对泉源和泉道的维护,以泉济运。泉夫因此成为清代重要的济运保漕群体之一。
清代泉夫分为佥派和雇募两种。佥派泉夫主要在清初实行,清廷通过强制手段征派泉源附近的农民充当泉夫,尽可能快地疏浚泉源和泉道,以泉济运。佥派之法虽在短时期内易取得成效,但弊端明显,对佥派的百姓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导致百姓纷纷逃避差役。因此,雇募的方式逐渐兴起。康熙九年(1670),工部认为佥派民夫不便,应先尽力雇募,倘若无人应募,再就近佥派。此后,以银雇募泉夫成为泉夫群体最主要的来源。
清代泉夫的数量在不同时期略有增减,但总体变化不大,保持在大约七八百名。康熙十五年(1676)以前共有754名泉夫,雍正年间为784名,乾隆时期泉夫总数为788名。泉夫来自于会通河沿线有泉地区的十七个州县,即莱芜县、新泰县、泰安县、蒙阴县、肥城县、平阴县、东平州、汶上县、泗水县、曲阜县、邹县、滋阳县、宁阳县、济宁州、鱼台县、滕县、峄县。
泉夫的收入主要为工食银。康熙初年以后,不论佥派泉夫还是雇募泉夫,皆可得到工食银两。康熙中期,泉夫所得工食银颇高,达到每年十二两:“峄县现役泉夫十名,每名十二两,共银一百二十两。”至雍正十三年(1735),清廷统一泉夫的工食银标准,“每名岁给银十两”,数额较之前减少了二两。乾隆年间,雍正时制定的工食银标准也不能达到,新泰县“现役泉夫99名,连闰征银九百一十八两八钱四分”,每名泉夫每年所得工食银只有九两余。 泉夫工食银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由所在州县的官府从地丁银中加征,一种从修河钱粮中动支。除工食银外,清廷还对浚泉有功的泉夫采取奖励政策,以提高其积极性。雍正三年(1725),蒋廷锡奏请“应立法劝泉夫浚出新泉,优赉银米,岁终册报,即为州县课最”。雍正四年(1726)规定,“有能浚出新泉者,酌给银米,以示奖励”。
浅夫和泉夫是清政府为保障漕运这一国家大政在沿运区域佥派和招募的济运群体,人数虽然不多,但在保障运道畅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也以此获得了维持生计的钱粮,是依漕为生的“衣食者”。
四、商人与贩夫
清代运河的贯通和漕运的兴盛为沿运区域带来了便捷的交通和巨额的商货,如重运漕船经过淮安,“自江广附带竹木板片、钉铁、油蔴糖、籘绳、磁器等货,沿途下卸”;山东的临清“每届漕运时期,帆樯如林,百货山积”;南方漕船经过天津的杨柳青,运丁水手们将随船携带南方土产在此销售,被当地人称为“粮船蛮子”或“南货蛮子”。这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运河沿线及南北间的商贸往来与发展,由此商贸成为与漕运紧密相关的一大产业。繁荣的商业环境吸引了形形色色的商人在沿运城镇从事各种活动,包括各大商帮组织、往来各地的行销商人、就地经营的商铺商人以及从事各种商业经营与服务业活动的民众。
活跃在运河区域的商人、可分为坐贾与行商。坐贾又称铺户,即坐地经商的商人,一般在沿运各城镇开设固定的商铺或货栈,进行货物的批发或零售。运河沿线的坐贾经营的商品门类繁多,很多都是由漕船北上携带的外埠商品。如清代济宁的杂货业繁盛,鼎盛时期有120多家,经营的商品主要是来自外埠的红白糖、江大米、纸张、海味、调料及祭祀品等,其中很多商品种类都和漕船附载的商货种类相同。清代长江以北地区多不产竹,因此南方漕船北上时竹子是最常附载的货物之一,大量竹子因漕运转销北方。运河沿线的诸多长江以北城市,如淮安、济宁、聊城、临清、德州、天津、北京等地,都有商人开设的竹器铺。繁盛的竹器制作与售卖业对当地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淮安、济宁和临清等沿运城镇都有竹竿巷的地名,实际上就是当地经营竹器店铺的专业市场。粮食也是经运河贩运贸易的大宗商品之一。商人们从粮食盛产地收购粮食,再经运河转贩到其他地方以粮行的方式销售,很多运河城镇都有为数甚多的粮行,如天津“城西北沿河一带,旧有杂粮店,商贾贩粮百万……河东新创杂粮店,商贾贩粮通济河东一带村庄”。漕船运输的漕粮和运丁的行粮、月粮等通过一定的渠道流入沿运商品市场,成为粮食市场的重要来源之一。
运河沿线还有为数众多的行商,行商流动性强,并不固处一地,他们通过运河往返贩运,赚取利润。行商通过运河贩卖商品,常与同在河上运粮的运丁水手发生矛盾。运丁水手经常依势刁难商民,“拦江索费,夺船毁器,患苦商民”。针对这一弊病,清政府数次下令,严禁漕船扰害商船,骚扰商民的正常商贸活动。统治者认为,“漕运所经河道,固以通国廪之输,亦以便商民之利涉”,对于运丁与商民,“自应一视同仁,无容偏护而偏累也”。
运河的畅通以及官方的鼓励,使得行商在运河沿线的贩卖活动非常兴盛。食盐是清代行商利用运河行销最大宗的商品之一。徽州商人、山西和陕西商人皆以贩盐为主。清初盛产海盐的淮扬地区就有众多徽州盐商寓居,从事贩盐活动。盐商当中,不少都有世代贩盐的传统,比如寓居扬州的徽州商人吴尊德“世业盐法”,徽州黟县的汪方锡在浙江贩盐,“经营十年,积巨赀”。运河流经的天津、河北一带产盐,多有山西商人转运销售。山西浮山县人张午阳因科举屡试不中,弃文从商,在天津从事盐业:“弱冠屡应童子试不售,改业为商贾,游于直隶天津府襄理鹾务。”山东海滨历来盛产海盐,山西商人赴山东业盐者不少,乾隆年间有山西洪洞人刘克昌,因家庭变故来山东贩盐,发展成巨商:“克昌赴东省业鹾务,有才智,尤善居积,数十年成巨富。”茶叶也是行商们在运河沿线运贩的主要商品之一。临清作为北方茶叶转销中心,有众多商人来此经营茶叶转运贸易。他们从安徽、浙江、江苏、福建等地收来各类茶叶,然后经运河北上运至临清,除一部分本地销售外,大部分分销外地,“或更舟而北,或舍舟而陆,总以输运西边,西边之人仰赖惟殷”。此外,纺织品也是清代行商在运河沿线运销的重要商品。徽州商人和山西商人经常在江南地区收购棉布、丝绸等纺织品,经运河北上,或直接在运河沿线销售,或经临清、天津等转销码头运往陕西、辽东等地。
行商在运河上贩运活动的兴盛还反映在运河关税的收入上。明清时期,政府在运河上设置了七个钞关,负责对运河上流转的商货课税,从北至南依次为:崇文门、河西务(清时移至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北新。从明万历年间至清中叶,七关商税从30余万两增至150万两,足见民间商人在运河沿线商业贸易的繁荣。
清代运河商业贸易的繁荣吸引了国内各大商帮的涌入,抢占商机,分攫市利,其中以徽商和晋商最为突出。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后,徽商即沿运河开展贸易活动。入清以后,徽商依旧是运河沿线城镇当中最为活跃的商人群体。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寓居于运河沿线的商业城市中:“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清代的淮扬地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盐业中心,徽商是在此业盐的最大商帮,史载:“在昔盐业尤兴盛焉,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淮安府城北的河下镇是运河沿线著名的淮盐集散地,吸引了众多徽商到此经商居住。河下镇由此发展成为徽商在淮扬的主要聚居区之一,街衢巷陌繁密,商店鳞次栉比。豪奢的徽商们在小小的河下镇修建的园林就达70多座。苏州吴江的盛泽镇是江南丝织业中心,虽弹丸之地,却商贾辐辏,徽商多来此集聚经商:“皖省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多有,而盛镇尤汇集之处。”赚取了大量财富的徽商们还在盛泽营建了徽宁会馆。在浙江杭州经商的徽州商人也不少,徽商沿运河南下抵达钱塘江边的登陆之处即被人们称为“徽州塘”。
清代晋商实力雄厚,不仅称雄北方,还活跃于大运河上,是运河城乡社会重要的商人群体。清代,晋商势力由于地缘关系在北运河沿线发展很快。如早在康熙十年(1671),北京通州张家湾就有不少山西商人在此经商,并修复当地的大王庙。晋商在天津从事烟草、食盐、杂货等各种商品贸易。财力雄厚的晋商还营建了两座山西会馆,锅店街的会馆“栋宇巍焕,局面堂皇,内祀关圣帝君”,“该馆存项甚巨,皆本省人捐纳”。 清中晚期,晋商在山东运河沿线势力较大,如聊城,“殷商大贾,晋省人为最多”;冠县“全城商号籍隶本境者仅十分之二,外来者占十分之八,山西人多钱善贾,占大多数”。位于大运河中段的扬州亦有众多晋商在此业盐,“两淮课甲天下,国计所关……且淮商半系晋人,情形尤悉”。有清一代,晋商在苏杭一带也非常活跃。在清前期,晋商已成为苏杭沿运地区最重要的商人群体,康熙帝南巡时指出:“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乾隆年间,晋商云集苏州,共同捐资营建了山西会馆、翼城会馆、全晋会馆等晋商会所,其中,为山西会馆捐资的商号超过80家,为全晋会馆捐资的商号更超过百家,日章号、三立号两家商号捐资超过1000两。可见晋商在苏州的商铺之多,财力之雄厚。
运河沿线城镇繁荣的商业环境和巨大的消费力市场,还为大量小商小贩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时人评价:“南漕由江淮达运,连樯北上,岁踰千艘,江南、山东之民,舟佣食及随漕逐末者极众。”“随漕逐末者”即从事与漕运相关的商业活动者,其中大部分应是普通的小商小贩。他们有的靠贩卖漕运带来的商货谋生,如山东峄县紧邻运河,南来漕船带来的“奇物珍货衍溢”,当地居民“皆仰之以赡身家”;有的为漕粮运输者和过往商人群体提供生活所需物资以补贴日用,如清人文康在《儿女英雄传》中说:“那运河沿河的风气,但是官船靠住,便有些村庄妇女赶到岸边,提个篮儿,装些零星东西来卖,如麻绳、棉线、零布、带子,以至鸡蛋、烧酒、豆腐干、小鱼子之类都有,也为图些微利。”类似的小本生意在运河沿线非常普遍,同时也反映了运河区域商业氛围的浓厚及民众的重商重利之风。
结语
清代“衣食”漕事者甚众,除了以上论述的直接参与漕运的运丁和水手,辅助漕粮运输的纤夫和脚夫,为保漕济运对运河进行日常维护的浅夫和泉夫,以及围绕漕事逐利的商贩等之外,还有管理漕运和修河的各级官员、剥船船户、闸夫、漕船修造工匠、粮仓建造工匠和粮仓看守等。此外,其他手工业者和服务业者甚至盗匪人群,也无不与漕事活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漕运成为运河沿岸乃至于更大区域的社会各阶层谋生牟利、特别是底层群众维持生计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场域,由此,运河沿线各城镇、码头尽皆分布着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极大地增加了沿运区域的人口基数。
清代漕河中的“衣食者”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类型多样、来源复杂。这些以漕运及其衍生行业为生的各类社会群体,从不同地方的传统生活秩序中“溢出”并结成新的生活共同体。他们聚集在运河沿线,为漕运和运河提供巨大的人力支持,既依漕河为生,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运河区域消费市场和商业环境的繁荣。
漕运的重要特性之一,在于其巨大的流动性。漕船的流动带来物资的流动和人口的流动。清代漕河中的百万“衣食者”,在运河沿线的经济结构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他们的地域性空间流动,不仅成为漕粮运输的主力军,也是运河商品流通、城镇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以南北大运河为主干,运河区域不断影响更大的空间,连接更多的区域、市镇,吸引更丰富的商品、行业与人群,形成相对成体系的、流动状态的、具有发散与辐射作用的运河经济带。
清代,漕河上的“衣食者”具有很大的流动性,流民类人群十分庞大。从社会变迁与官府治理的角度而言,这些社会群体皆属区域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是潜在的社会破坏力量,当然也是社会治理的难点所在。道光年间,清廷实施漕粮海运;咸丰年间,运道淤阻,运河漕运逐渐走向衰落并最终废止,近百万依漕为生人员的失业与安置遂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这其中的部分人在巨大社会变动中结成盐枭、青帮等社会寄生组织,对沿运区域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持续的影响。
注释
①丁显:《河运刍言》,见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7《户政十九·漕运上》,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湖北省图书馆藏。
②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彭云鹤:《明清漕运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吴欣:《明清京杭运河河工组织研究》,《史林》2010年第2期;戴鞍钢:《清代漕运盛衰与漕船水手纤夫》,《安徽史学》2012年第6期;曹金娜:《清代漕运水手研究》,南开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沈胜群:《清代漕运旗丁研究》,吉林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吴欣:《京杭大运河纤夫的生计与制度》,《学海》2020年第5期等。
④根据光绪《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卷28至卷30《卫帮额支》相关内容统计。
⑤清代,在实际运输过程中,逐渐形成每艘漕船由一名运丁领运,其余运丁出银帮贴济运的规则。漕船上其余的劳力由雇募的水手承担。康熙五十一年(1712)后,又规定每船再添设一名副丁协助驾运漕船。因此,每船出运时有正副丁各一名,其余为雇募的水手。
⑥江南运丁每名支行粮二石四斗至二石八斗,月粮八石至十二石。浙江、江西、湖广行粮三石,月粮九石六斗。山东行粮二石四斗,月粮九石六斗。其通、津等卫协运河南漕船运丁行、月之数,与山东同。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122《食货志三·漕运》,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588页。
⑨光绪《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卷9《征收事例·随漕杂款》,见《续修四库全书》(第83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5页。
⑩光绪《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卷35《计屯起运·屯田坐落》,见《续修四库全书》(第83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