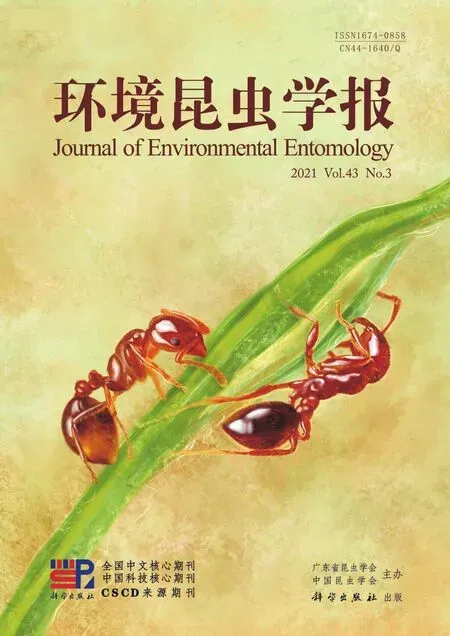植食性昆虫的嗅觉选食过程及其机制研究进展
王 鹏,张 龙
(1. 青岛农业大学植物医学学院,山东青岛 266109;2. 中国农业大学草业科学与技术学院,北京 100193)
1 引言
嗅觉在植食性昆虫的选食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前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寄主和非寄主植物挥发物的释放和散布特征;相关化合物的种类、组合、比例和浓度变化;昆虫的嗅觉器官功能及其上分布的嗅觉感受相关蛋白等,共同影响了其从远距离定位追踪到近距离选择取食的整个嗅觉选食过程。本文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综述,系统分析和讨论了影响该过程的相关因素,相关内容可为今后深入研究植食性昆虫的嗅觉选食机制提供理论指导。
2 植食性昆虫选食行为及其感受植物信息途径
据统计,全世界的昆虫种类超过1千万种,而以活的植物组织为食的植食性昆虫至少占了其中的一半以上(Gullan and Cranston, 2005; Speightetal., 2008)。现今已有包括直翅目(蝗虫等)、缨翅目(蓟马)、半翅目(叶蝉、蚜虫等)、鞘翅目(甲虫)、膜翅目(树蜂、叶蜂等)、鳞翅目(蝶类和蛾类)、双翅目(蝇类)等都有植食性昆虫种类,这还不包括一些以死亡植物组织为食物的昆虫(Priceetal., 2011)。植食性昆虫的选食行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温湿度等物理因素、其自身的感觉行为和营养代谢等遗传特征,以及寄主植物的营养水平和次级代谢产物等(钦俊德, 1980)。不同的植食性昆虫取食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不同,根据其寄主植物的范围,可分为单食性、寡食性和多食性(Johnson and Lyon, 1991; Bernays and Chapman, 1994)。其中单食性昆虫的食谱单一,仅取食某一种植物,如三化螟Tryporyzaincertulas仅对水稻造成危害(李云瑞, 2002);相比之下,寡食性昆虫可取食属于同一个科或几个近似科的多种植物:如飞蝗Locustamigratoria就表现出嗜食禾本科Gramineae和莎草科Cyperaceae植物的特性(Bernaysetal., 1976; Bernays and Chapman, 1977),这其中包括了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如小麦、水稻、玉米等;又如小菜蛾PlutellaxylostellaL.主要取食以油菜、甘蓝、白菜等为代表十字花科的植物;而多食性昆虫的寄主范围极广,能够广泛危害不同科属的植物,如棉铃虫Helicoverpaarmigera能够取食包括茄科、豆科、禾本科等超过30个科的200多种植物(郭予元, 1998)。实际上,大多数植食性昆虫属于单食性种类,因而其特异选择寄主植物的行为是植食性昆虫中普遍存在的行为(Dixon, 1986; Janzetal., 2001)。
植食性昆虫的选食行为大致分为两个过程:一个是远距离寻找适宜寄主植物的过程,即昆虫通过视觉和嗅觉获得植物信息,产生定向反应来缩短与植物的距离,最终与植物接触。如苹果实蝇Rhagoletispomonella、温室白粉虱Trialeurodesvaporariorum、桃蚜Myzuspersicae等在较远距离上主要通过视觉对植物进行定向(Moerickeetal., 1975; Vaishampayanetal., 1975; Kennedy, 1976)。另一个是对植物进行试探取食的过程,即昆虫通过嗅觉、味觉和触觉近距离对植物进行比较以确定该植物是否能满足自身的需要(Visser, 1986; 钦俊德, 2003)。在整个选食过程中,昆虫充分利用多种感觉模式协同感知植物的理化性质(Miller and Stricker, 1984),但其利用的感觉方式及先后次序不尽相同(赵冬香等, 2004),例如玉米黄翅叶蝉Dalbulusmaidis在经过视觉刺激后才会表现出对寄主植物气味的趋向反应(Toddetal., 1990)。
更多研究结果表明,嗅觉在昆虫远距离定位和选择食物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Bruceetal., 2005; Bruce and Pickett, 2011)。Tortoetal.(1996)发现嗅觉在沙漠蝗Schistocercagregaria行为中起重要作用,如己醛、辛醛、壬醛、癸醛、己酸、辛酸、壬酸和癸酸等(其中的部分化合物为植物挥发物)能明显吸引蝗蝻,而愈创木酚和苯酚能显著增强这种作用(Tortoetal., 1994)。沙漠蝗和马铃薯甲虫Leptinotarsadecemlineata均可以在距气味源较远的地方通过触角感器感知寄主植物的气味,并通过顶风追踪到达气味源(Haskell and Shoophvoen, 1969; de Wilde, 1974)。在追踪气味源的过程中,昆虫一般按“之”字形的折线运行轨迹穿梭于不同浓度和成分化合物的气缕中,在这个过程中昆虫逐渐趋向高等级(high rank)气味线索,而忽略质量不高的气缕(Beyaert and Hilker, 2014)。烟草天蛾Manducasexta的研究发现,相关气味在散布过程中的频率和浓度是其能准确定位曼陀罗花香气的最主要因素(Riffelletal., 2014)。Finch和Collier(2007)认为在昆虫搜寻寄主植物的过程中,植物挥发物的最主要作用是刺激昆虫在有寄主植物的区域里产生更频繁的降落行为。当昆虫在植物上降落后,它们还可以在短距离上通过口器上的嗅觉感受通路对食物的质量进行评价,如黑腹果蝇Drosophilamelanogaster下颚须上的嗅觉感器能够在短距离内有效判断食物信息的特异性(Dwecketal., 2016)。
3 植物挥发物结构和散布特征
植物释放的挥发性化合物在昆虫定位寄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Hopkins and Young, 1990; Szentesietal., 1996),它们可以在较远距离为昆虫提供潜在食物源的信息,并帮助它们迈出觅食过程的第一步(Kang and Hopkins, 2004; Vickersetal., 2000)。因此,植食性昆虫的嗅觉选食与植物组织释放的挥发物及其性质直接相关。
植物挥发物属于植物的次级代谢产物,由植物表面释放。目前,世界上已知的大约90个科的植物释放了总计超过1 700种的化合物(Dudarevaetal., 2006; Laothawornkitkuletal., 2009),多是分子质量为100~200 u的烃、醇、醛、酮、酯和萜烯类等。而植食性昆虫对其中六碳醇、醛和衍生物酯类等普遍存在于植物中的挥发物有较为强烈的趋向性反应(Whitman and Eller, 1992; Paréetal., 2000)。实际上,这些挥发物被释放后并非一直稳定存在于大气中,其中某些气味在空气中极易被O3、-OH、NO3氧化(Holopainen, 2004),同时在风的作用下,这些挥发物会以气缕的形式自气味源顺风扩散,其浓度会不断降低并形成变化梯度(闫凤鸣, 2003)。以绿叶挥发物中的顺-3-己烯醛为例,该化合物在空气中的残留期只有2 h(高宇等,2012)。据Falletal.(1999)报道的数据显示,该化合物在植物叶片经过受伤处理后1~2 s之内就由α-亚麻酸分解出来并迅速释放,在5 min之内含量即到达顶点,然后迅速下降,在二十多分钟时就接近并趋近于零值。在这个过程中,顺-3-己烯醛被逐步衍生成反-2-己烯醛和顺-3-己烯基乙酸酯等化合物,而这2种化合物也分别会在十几或几十分钟时含量到达最高点并逐步下降。此外,植物中另一种普遍存在的挥发物苯甲醛在空气中也极易被氧化成苯甲酸和苯甲醇。相比之下,2-苯乙醇则能够在较低空间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Wangetal.(2019)的风洞试验也表明,不同植物挥发物在相同释放距离上,其相对浓度的变化差异各不相同。
植物挥发物能否远距离传播,除了与其本身的稳定性相关,也与风速、温度、湿度、辐射等环境因素有关。植物气味分子在空气中的散布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气味分子的随机运动使它们彼此缓慢分离;紧接着包含有这些分子的气团会被空气湍流打乱而迅速散布开来,这两个过程的时空特征完全不同(Murlis, 1992)。整体来看,气缕从气味源处散发后,随着距离的增加其结构尺寸在增大而气味的浓度在降低(Voskampetal., 1998; Murlisetal., 2000; Dekkeretal., 2005)。然而,气缕结构的变化极为复杂,包括不同化合物流动速度、不同时间内化合物的结构变化、因化合物的带电特征而重新组合与成团等。挥发物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化,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昆虫在较远距离对植物信息指示性气味的识别方式。在这个过程中,风和风速发挥到了关键的作用(Smith, 1990)。实际上,昆虫常常表现出一种趋风性的行为特征:即使在没有气味刺激的情况下,仅凭机械感受就会往逆风向运动(Bell, 1984)。在一定距离的范围里,昆虫通过嗅觉器官感知上风向气缕中浓度达到一定阈值水平的化合物组成所代表的植物信息,并据此将行进目标准确指向气味源(Davidetal., 1982; Geieretal., 1999; Beyaert and Hilker, 2014)。
随着植物挥发物释放距离的增大,不同植物释放的气缕相互交错,相关化合物组合彼此混合,在大气中形成了一个对于植食性昆虫而言复杂且处于动态变化的嗅觉感受环境,对其定位寄主植物产生重要影响(Atema, 1996;Randlkofer, 2010; Riffelletal., 2014)。在这种复杂的化学信息背景下,植食性昆虫可能会因为寄主植物指示性挥发物的浓度因距离和其它气味的稀释,而降低了其对寄主植物的定向效率(Voskamp, 1998; Murlisetal., 2000)。举例来说,马铃薯甲虫对寄主植物马铃薯叶片气味的趋性,会因为非寄主植物野生番茄或甘蓝气味的混入而降低(Thiery and Visser, 1987);黑豆蚜Aphisfabae则会被其非寄主植物(薄荷和艾菊等)的挥发物所驱避(Nottinghametal., 1991)。因此,对植物挥发物在释放后形成的多维时空动态特征的研究,即挥发物各种类浓度、比例和组合方式等随时间、空间的动态变化规律,可作为未来理解昆虫嗅觉选食过程机制的重要途径。
4 植食性昆虫嗅觉感受特征
嗅觉在植食性昆虫从较远距离搜寻寄主植物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作用机制。早期观点认为,昆虫对远距离植物的定向常缺乏种类的特异性,由于寄主植物或非寄主植物共有的绿叶挥发物的释放量要远远高于它们特异挥发物的释放量,昆虫首先感受到的应是以绿叶挥发物为主的背景气味(Shorey, 1973; Kennedy, 1977; Chapman, 1982)。Bruceetal.(2005)对前人文献的研究发现,一些常见的绿叶植物挥发物普遍会对不同种类的植食性昆虫产生强烈的电生理反应,如己醇、己醛、反-2-己烯醛、顺-3-己烯醇、2-庚酮和1-辛烯-3-醇等。这些绿叶挥发物通常会在植物遭受到外界压力的胁迫时被大量释放,如被植食性昆虫咬食、被植物病原菌侵染以及受到机械伤害等(Agelopoulosetal., 1999; Falletal., 1999; Matsuietal., 2000)。而作为很多绿色植物共同释放的化合物,绿叶挥发物可能本身并不具备特异性,或者仅有较弱的吸引能力,甚至对某些植食性昆虫有降低取食或者引起拒食的特征(Heil, 2004; Brilli, 2009; 高宇等, 2012)。但是,这些普遍存在的挥发物可以给植食性昆虫乃至捕食性天敌以初步的指示,即这里可能存在食物源,且这些背景气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锐化昆虫对于低浓度的真正寄主植物“资源指示气味”的感受,这种增强效应会使昆虫定位寄主的镜像变得更加清晰,使之在下一阶段可以顺利找到寄主植物(Schroeder and Hilker, 2008)。但是,一个具有大量绿叶挥发物背景气味的环境同样意味着这里存在更多的取食竞争者(Ballhornetal., 2013)。而相同种类的昆虫因其发育阶段和性别对植物挥发物反应方式和强度也会有差异,例如雌虫因自身生殖的营养需求以及后代生长所需食料可能更多关注食物的状态,因而对绿叶挥发物的识别和反应较雄虫更敏感,雄虫则会优先考虑更多的配偶和交配机会,这种性别差异在鳞翅目、鞘翅目、双翅目和半翅目等植食性昆虫上均有报道(Fernandez and Hilker, 2007; Ballhornetal., 2013)。
要更准确识别适宜的寄主植物,需要下一阶段更为精确的感觉机制。有研究认为,由于代表寄主和非寄主植物各自特征的特异化合物释放量极低,使得能够被昆虫识别的有效距离限制在十几乃至几十厘米的范围里(Finch and Skinner, 1982; Schoonhovenetal., 2005),近来的观点认为这一距离通常不超过5 m(Finch and Collier, 2000; 2012)。例如,印度棉叶蝉Empoascadevastans等对寄主植物气味仅在较短距离内会引起定向反应(Saxena and Saxena, 1975)。这或许说明,能够指示特定植物种类的信息,如特异的挥发物种类或气味比例(Clifford and Riffell, 2013),仅仅在较近距离时才会被昆虫感受到并识别出来。但是,从植食性昆虫嗅觉器官及其化学感受功能的角度来看,仍可能存在某些具有远距离传播能力的特异植物挥发物对其远距离定向发挥重要作用。近年的研究发现,昆虫的触角和口器触须在识别植物气味信息中存在较为明显的功能差异:例如飞蝗在较远距离上能够仅通过触角感受植物气味并产生趋近的行为,但却无法仅通过口器触须实现这一点(Zhangetal., 2017)。而作为除触角以外的最重要的嗅觉感器,口器触须在昆虫嗅觉选食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近距离探测和分辨寄主和非寄主植物的气味上(Blaneyetal., 1973; Blaney, 1975; Chapman and Sword, 1993)。飞蝗在近距离上利用口器触须的触诊行为对食物进行初步判断,在这一个过程中可以观察到一系列触诊动作(Blaney and Chapman, 1970; Blaneyetal., 1971)。该动作贯穿于从开始试探到最后取食的整个选食过程,通过这种行为可以使昆虫的化学感受器官与植物化合物进行充分接触,从而有效地感受近距离上植物释放的气味以及植物表面化合物的组成(Renwick and Chew, 1994; Blaney, 1981)。
关于植食性昆虫通过嗅觉识别寄主植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假说:一种是昆虫通过识别并对寄主植物释放的某一种或数种特异化合物表现出吸引性趋向行为(该化合物在其他物种上不存在或者存在量很少),但这类案例相对较少,如蚜虫对十字花科植物的识别主要依靠异硫氰酸酯类化合物(Bruceetal., 2005);再如洋葱释放的挥发物丙硫醇二硫物和丙基二硫能够对葱蝇HylemyaantiquaMeigen产生强烈的吸引行为(Pierceetal., 1978; Ishikawa, 1988)。多数昆虫则是通过感受和识别寄主植物释放的具有特定浓度和配比的普通化合物组合(Milet-Pinheiro, 2013),如Feinetal.(1982)报道了苹果实蝇在风洞实验中对由苹果释放的特定比例的7种活性成分产生吸引降落的行为,且在人工合成的混合物测试中也得到了相似的效果;再如马铃薯甲虫可以被马铃薯叶片释放的气味混合物所吸引,而对其中单一化合物无明显吸引反应,这同样说明特定剂量的挥发物组合在其感受植物气味时发挥的重要作用(Visser and Ave, 1978)。通过多种化合物组合的方式,昆虫中央神经系统也可以根据外缘嗅觉感受神经元在不同时间同时感受的化合物种类,来对由植物释放的气缕的来源形成判断。之所以以气味组合的形式,Bruceetal.(2005)认为是由于这几种气味在被植食性昆虫的嗅觉器官同时探测到时,其上的嗅觉感受神经元释放的电信号在神经系统传导过程中形成同步,从而使昆虫获得了相比单一化合物更高的时空分辨率(Martinetal., 2011)。因此,昆虫对来自寄主植物的化合物组合的感受相对于单一化合物的感受会更加敏感(Riffelletal., 2009; Websteretal., 2010)。Bruce和Pickett(2011)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昆虫通过嗅觉识别某种植物可以只依据该植物的挥发物成分中的3~10余种特征化合物,且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不可替代。通过对这一些特征化合物进行识别,昆虫可以拥有灵活和高效的感受寄主植物信息的能力,而且这种编码方式也更利于昆虫适应环境条件的变化。这些化合物在挥发物气团中的比例和浓度特征,则是影响昆虫对寄主植物识别的最主要因素(Riffelletal., 2013)。此外,昆虫对非寄主植物释放的挥发性化合物的拒绝反应,也可能是基于由非寄主植物释放的化合物的刺激带来的排斥作用,这同样在昆虫对寄主和非寄主植物的识别和选择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Zhang and Schlyter, 2004)。如Chapman在1990年出版的《Biology of Grasshopper》一书中就提出了蝗虫对食物的选择可能是因为非寄主植物释放的化合物不为蝗虫所接受,从而选择其他可取食的植物的观点。
5 昆虫嗅觉选食行为分子基础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气味分子受体蛋白(Odorant Receptors, ORs)基因和气味分子结合蛋白的发现(Odorant binding proteins, OBPs)(Vogt, 1981; Buck and Axel, 1991),使嗅觉与动物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进入了分子时代。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在化学感受中ORs起决定性作用,是探讨行为嗅觉分子机制的关键,特别是相关受体组合可能联合参与了对某种(些)气味的识别过程(Bruceetal., 2005)。目前已经明确昆虫的ORs具有7个跨膜区,一般有370~400个氨基酸(Vosshall, 2003)。通过基因组测序和生物信息学、分子生物学技术鉴定出多种类昆虫的ORs基因:鳞翅目的烟蚜夜蛾Heliothisvirescens(Kriegeretal., 2004)、家蚕Bombyxmori中鉴定出66个ORs(Sakuraietal., 2004; Nakagawaetal., 2005)、膜翅目的蜜蜂Apismellifera中鉴定出163个 ORs(Robertson and Wanner, 2006)、直翅目的飞蝗中约140余个ORs(Wangetal., 2015; Lietal., 2018)。昆虫会在感受到食物源释放的气味后发生趋向性行为,而当其嗅觉通路中的某些(类)关键的化学感受蛋白被干扰后,就会丧失这种趋向行为。在黑腹果蝇的研究中发现,敲除了Orco后其对多种食物的挥发物丧失了电生理和行为学活性,经过补救实验恢复该受体的表达,对相关化合物的反应活性也得以恢复(Larssonetal., 2004)。同样,降低气味分子结合蛋白OBPs在昆虫嗅觉感器内的表达,也能够减弱昆虫感受寄主释放的气味分子的能力,具体表现触角电位反应活性的减弱和其吸引的趋向行为的丧失等(Lietal., 2016)。这些研究为解释植食性昆虫对寄主植物的识别和选择分子机制提供了重要基础和依据,此外,Zhangetal.(2017)报道了植物重要的挥发物己醛,具有激活飞蝗口器触须上的两类嗅觉受体通路(LmigOrco和LmigIR8a),增强神经信号传播强度和调控嗅觉选食的能力;而大量表达在触须上的OR12,也被证明与植物释放的几种醛类物质的识别相关(Lietal., 2018)。
研究发现单一气味分子受体或结合蛋白的表达,可以影响昆虫嗅觉选食过程中对多个气味的感受;而单一的挥发物也可以被多个气味分子受体或结合蛋白所感受,其引起的行为反应也会因多个蛋白的干扰而发生改变。这表明许多气味会激活不同的ORs组合,形成独特的“编码”(Hallem and Carlson, 2006; Wilson and Mainen, 2006),并在初级嗅觉中枢形成编码(Chouetal., 2010)。例如黑腹果蝇对16种气味的行为学反应表明OBPs以组合编码的方式来介导嗅觉行为反应(Swarupetal., 2011)。而OR对气味分子的编码特征有3个重要原则:(1)组合式编码,即每种气味分子可以激活多个OR,每个OR也可以被多种气味分子所激活;(2)OR决定了嗅觉神经元的反应模式是兴奋还是抑制;(3)不同OR对气味种类的反应范围不同,有的宽,有的窄,例如果蝇Or82a只能被乙酸香叶酯强烈激活,是典型的窄调节受体,而Or67a可以被大多数气味强烈激活,是典型的宽调节受体(Hallemetal., 2004; Careyetal., 2010; Carey and Carlson, 2011)。
值得注意的是,昆虫不同的嗅觉器官因其上分布的嗅觉感受相关基因数量和表达量存在差异,导致其在选食过程中承担的功能有所不同。Wangetal.(2019)报道了东亚飞蝗通过触角和口器触须两种嗅觉器官,对不同距离上的植物挥发物刺激产生不同的行为反应。这种功能性差异应与这两类器官上的嗅觉感器和化学感受相关蛋白的种类、数目、表达量及其气味配体的差异有关(Lietal., 2018)。在果蝇中,仅有极少量的嗅觉感受神经元分布在下颚须上,且这些少数的神经元仅存在于一种锥形感器中(de Bruyneetal., 1999)。飞蝗的转录组数据发现,触角相较于触须拥有更多的化学感受相关蛋白乃至更高的表达量,仅少数几种嗅觉受体基因在触须上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其在触角上的表达水平(Wangetal., 2015; Lietal., 2018)。通过触角与口器触须相比,推测触角应具有对来自植物的挥发性化合物更广的反应谱以及相应更高的敏感性,而这种感受差异可能直接导致昆虫在不同距离上识别寄主植物信息能力的差异(Wangetal., 2019)。
6 展望
关于植食性昆虫利用嗅觉识别植物过程的机制研究,是从化学信息流的方面探讨昆虫与植物的协同进化、生物群落的演替规律,属于化学生态学的重要内容。植食性昆虫利用嗅觉识别寄主的过程极其复杂,这个过程不但与昆虫个体的生理、行为有关,同时这种识别过程也受到同种个体、甚至相关其他种类等的影响,更受植物种类、品系、个体和群体的生长发育阶段、状态和周边植物的存在方式影响,也受其它物理环境,如光、气温、风速和风向等影响。尽管也有大量的研究,但多是在实验室或者相对简单的环境下的研究结果,限制了揭示实际环境中的植食性昆虫嗅觉识别寄主植物的机理。今后的研究至少需要更加重视植食性昆虫在自然环境或接近自然环境条件下利用植物气味识别植物的机理。而其中难度最大的是如何研究在实际环境中植物挥发物在释放后形成的多维时空动态特征,包括挥发物各种类浓度、比例和组合方式等随时间、空间的动态变化规律,可作为未来理解昆虫嗅觉选食机制的重要途径。此外,同种群体的个体间相互作用对于利用植物气味识别寄主植物的影响是未来研究一个重要方面。而对于植食性昆虫嗅觉识别寄主植物气味的分子机制仍处于初级阶段。对植食性昆虫的嗅觉相关蛋白或基因的鉴定、以及确定编码植物挥发物的基因或蛋白,是从分子层面解析植食性昆虫嗅觉选食过程机制的重要途径。随着越来越多的昆虫种类的基因组测定,以及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相信对于植食性昆虫嗅觉选食过程的分子机理的理解也会越来越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