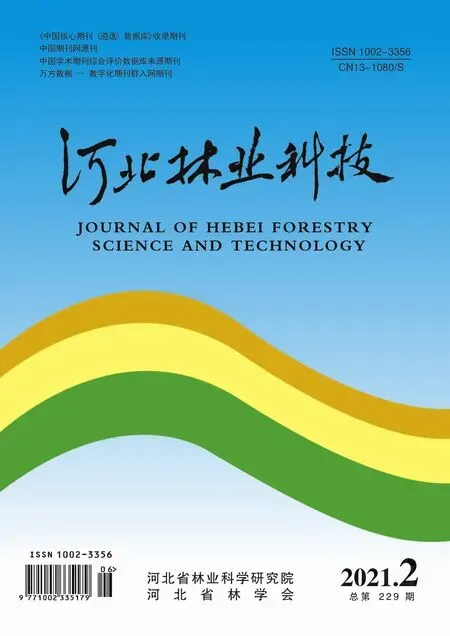松材线虫病防治方法研究进展
朱云倩,黄维燕,谢伟龙,冯 莹,温秀军,王 军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 广州510642)
松材线虫病(Bursaphelenchus xylophilus)是松树萎蔫病的俗称。这种系统侵染性病害主要侵染松树,破坏维管系统从而使松树无法疏导水分,导致松树迅速萎蔫死亡[1]。1971年,确定是松材线虫造成松树萎蔫,此后,松树萎蔫病就被称为松材线虫病[2]。
1 松材线虫的起源与现状
截止目前,世界上至少有8个国家发生过松材线虫病,如北美洲的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亚洲的中国,日本和韩国,欧洲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等[3],尤其在亚洲格外严重流行,对生态造成巨大破坏,在未来可能引起巨大生态灾难。
1934年,Steiner等在报道中指出有松材线虫出现在美国蓝变的松木中[4]。1979年,松材线虫病致死欧洲黑松(Pinus nigra),引起美国重视,后被发现松材线虫还分布在美国超过36个州,感染且致死外来松,如:日本赤松(P.densiflora)、日本黑松(P.thunbergii)等。同时也发现,火炬松(P.taeda)、长叶松(P.palustris)、班克松(P.banksiana)、沙松(P.clausa)等美国乡土松不仅很少感染这一病害,而且大多数有抗病性。国际上普遍认为松材线虫与美国本土松树经过漫长时间的互作适应,可以抵抗松材线虫侵染且不会死亡,等松树逐渐存活下来,其抗性基因不断遗传给后代。这种长达数百年基因筛选,最终使得美国本土松种的自然群体具有高度抗病性[5]。
松材线虫病对日本林业的打击是巨大的。1905年,日本九州岛的长崎县县志曾记载有松树大量死亡,之后的几十年间,松材线虫病由南向北在日本不断蔓延。1979年,日本发病松林面积达到67万hm2,木材损失达240万m3。在1971年,清原友也和德重阳山第一次证明正是由于松材线虫导致松树萎蔫死亡。有研究表明日本发生的松材线虫病最初应该是来源于北美洲且更大可能是来源于美国[6-7]。
1988年,松材线虫病首次被发现存在于韩国釜山的赤松和黑松林中,且到1997年病害都一直被控制在100hm2的范围内[8]。此后,疫情范围不断扩大,基本覆盖所有县市郡。这一病害的来源被认为是由日本九州传入[9-10]。
目前受到松材线虫病危害最严重的国家就是中国。根据孙永春等研究可知,在1982年,江苏南京中山陵中山墓后面的黑松受到松材线虫侵害,病死植株达256株[11-12]。随后,松材线虫病传播到南京周边,逐步扩大范围,出现在安徽、广东深圳、山东烟台、浙江象山等地[13-16]。特别是1991年在浙江发生的松材线虫病,造成大面积马尾松受害[17]。
马尾松大面积分布在南方15个省区,面积达到2000万hm2,且马尾松十分易感病[18-19]。研究发现,中国的松材线虫由日本传入[20]。这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松材线虫刚开始发生在南京时对日本黑松和日本赤松危害最大,对中国乡土松种马尾松危害较小。曾有研究表明:马尾松对松材线虫具有抗病性[21],5~10a后,随着松材线虫群体的组成结构对寄生的适应和选择发生很大变化,马尾松也就由抗病变成易感染病树种。松材线虫入侵我国30多年以来,已经致死松树达数十亿株,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上千亿元,这一病害成为我国近30a来灾难性的病害。
松材线虫对中国或亚洲的乡土松种都有很强的致死性,且在多数松树上呈现出典型的病源主导性病害特征,即病害的流行取决于松材线虫能否传播到该区域松树[22]。松材线虫病作为一种病原主导性病害,病原物在病害的发生、发展中具有主导地位[23]。只要松树感染了松材线虫,哪怕生长健康,依然会发病死亡,且该区域中生长势最好的松树会首先被感染。这就表明,松材线虫对松林的威胁是极大的。
我国目前有超过6000万hm2松林,到2020年底,疫情涉及18个省区市,共有726个县级发生区,发生面积180.9万hm2,同时,健康松林依然面临着松材线虫病的严重威胁。随着疫情寄主植物、传播媒介和分布界限不断发生变化,全国所有松树种类都可能染疫,所有松林分布区都是松材线虫适生区。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工作。2020年以来,林草部门摸清了松材线虫病发生底数,首次将疫情落到森林小班并实现精细化管理;采取“揭榜挂帅”方式推进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科技攻关,将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纳入“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专项;近期,还将印发《关于科学防控松材线虫病疫情的指导意见》,组织开展疫情防控五年攻坚行动。下一步将开展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五年攻坚行动,力争到2025年,全国疫情发生面积和乡(镇)疫点数量实现双下降、县级疫区数量控制在2020年水平以下,使疫情快速扩散态势得到有效遏制。
2 松材线虫病的防治
过去30a来,我国对松材线虫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有了深入认识,也在病害致病机制、流行规律、防治技术等方面获得较大突破,在防治工作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当然,在实践中,中国对松材线虫的防治缺失了很多机会,有过十分惨痛的教训,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仍有一些误区和盲区。面对松材线虫巨大的威胁,除不断解决防治体系、防治机制等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外,还要不断从过去的防治中总结经验,进行科学防治,不断深入学习病害防治的关键环节、核心措施、辅助方法和长期战略等。
针对松材线虫病侵染循环规律和病原主导性病害特点,目前的防控主要从病害检疫和疫情监测、疫木除治、媒介昆虫防治这3个关键点进行。当然,还有树干注射等主动预防措施。
2.1 疫情监测和疫木监管
在尚未出现松材线虫的非疫区,尤其需要进行病害检疫和疫情监测。松材线虫传播主要通过人为传播和自然传播。人为传播的区域较大,主要是受感染松木被人带进非疫区,其中的媒介昆虫将疫木内的松材线虫带出传播到该区域健康松树从而出现病害。自然传播因主要靠媒介昆虫的传播因而传播范围一般在几千米内。我国松材线虫病发生区域75%以上都是因为人为传播,因此对疫木和带疫制品需要进行严格地检疫和监测,从而防止人为传播。外检中各口岸要对从国外特别是从美国、加拿大、日本输入的松材原木、松材加工制品、包装材料以及松科的观赏树种等应实施严格检疫,检疫工作做得好,可以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松材线虫病的发生,避免染病疫木木极其制品在我国大量扩散。
当然,对疫木和带疫制品的监测需要先进的技术。2006年以前,因缺乏相应的技术,就造成我国疫区有超过75%是由人为传播造成。随着松材线虫分子检测技术的成功应用以及推广实践,无人机监测也开始大量应用于松材线虫的疫情监测中,我国松材线虫病检疫和监测过程中出现的鉴定技术难题得以解决[24]。
2.2 疫木除治
在发现疫情后,疫木的除治十分重要。只有彻底干净消灭疫木中的天牛和线虫,病害才可以得到防治。相比较于除治疫木或带疫制品中的天牛和线虫,如何应对较大林间发生的疫情则会有较大难度。病死树清理彻底的程度决定着第二年病害再度发生的程度。从理论上讲,如果病死树清理干净,第2年新发感染的情况就不会出现,除非存在当年感染要越年才死亡的情况。
2008年前,主要采用2种方式对疫木进行除治:一是将疫木清理下山后通过熏蒸、干燥、碎片、制板处理等除疫处理后加以利用[25-27]。在疫木下山的过车中,难免会因为监管不力,疫木数量较大等问题,一些疫木处理不彻底甚至遗漏,从而造成人为传播。二是疫木不下山。通过塑料薄膜牢牢包裹疫木材料,使得天牛羽化后不能飞出疫木[28]。这一方法在理论上可行,但在实际中很难牢牢包裹疫木,且对森林造成一定污染。除两种方法之外,也发现有部分地区通过大面积砍伐疫木区域来除治松材线虫。这一方法往往造成更大的疫区,且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2018年国家修订《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中,对这一方法进行了一定限制。择伐的病死树和濒死树在山上或山下需要就地尽快粉碎或烧毁[29]。
2.3 媒介昆虫防治
杀灭媒介昆虫是松材线虫病防治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松材线虫病的传播主要依赖媒介昆虫松墨天牛。根据杨宝君等的研究发现,在我国松墨天牛等是主要的传病媒介昆虫[30-33]。天牛羽化后将携带附着在其体表的松材线虫到健康树上,从而传播松材线虫。防治天牛主要有化学防治,引诱剂诱杀以及生物防治这3种方法。
2.3.1 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是较普遍的消灭媒介昆虫的手段[34-35]。在天牛成虫补充营养期和交配产卵期,地面树冠喷雾或飞机空中喷雾,从而杀死天牛成虫。然而化学喷雾方法又受限于2个主要因素:一是喷雾药效时间有限;二是天牛羽化时间不一致,且历时较长。如果在大面积范围内喷洒药雾就需要多次,这就浪费较多人力物力,且对生态环境有一定影响。因此小范围内可以通过这一方法来保护松林。
2.3.2 引诱剂诱杀 在防治实践中,使用诱捕器诱杀松墨天牛也较为常见。天牛羽化后补充营养要趋向健康大树,产卵要趋向衰弱木或濒死树。掌握了这2个时期的化学信号物质,从而开发出相应的引诱剂和诱捕器。在防治实践中,对引诱剂的使用也要科学,要注意不同区域,不同时间。有时也因为不清楚天牛的密度而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2.3.3 生物防治 松材线虫防治研究中的热点一直以来都是生物防治。在保护环境和不污染环境的前提下,有效防治松材线虫的同时又能够保证森林健康成长,生物防治是最佳选择。
生物防治是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中原有的有益的生态因子“天敌”来控制有害的生态因子“病虫害”,通过调节森林生态系统中的益害平衡而达到抑制病虫害发生,使其无法成灾,森林达到和恢复生态平衡状态,达到“健康”水平。
目前较为有效的的生物防治手段一是利用白僵菌(Beauveria bassiana)等虫生菌来防治天牛成虫或幼虫[36-37],二是寄生性天敌寄生于天牛幼虫,主要是肿腿蜂(Scleroderma guani)[38-39]和花绒寄甲(Dastarcus helophoroides)。杨忠岐等曾利用花绒寄甲[40-42]成功控制了松材线虫病的传播,其中花绒寄甲对松褐天牛的最高寄生率达96.0%,平均为88.6%。
除研究寄生于松褐天牛的天敌外,也有一系列研究关注松材线虫的内寄生真菌,如伊式线虫菌。如今,通过伊氏线虫菌对松材线虫病防治也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最早对该菌的报道见于Liou等[39]的研究。当时,Liou等在疫木上发现寄生于松材线虫的新属新种真菌,并将其命名为Esteya vermicola,菌株号为ATCC74485,为模式种。伊氏线虫菌真菌来自于自然界,不对环境造成污染,其靶目标为松材线虫,可从根源上防治松材线虫病,是一种十分具有潜力的生物手段[40-41]。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对该菌的发现、形态学、培养、侵染机制、分子层面研究和生物防治应用等方面有较系统全面地介绍[42]。虽然伊氏线虫菌的防治效果没有比之前报道过的节丛孢属菌(Arthrobotryssp).高,但由于其独特的特性,作为一种生物方法控制松材线虫仍然很有潜力[43-44]。
2.4 树干注射
除以上的几种防治方法外,也有树干注射这种主动预防措施。针对重要生态区和古树名木,有各种各样的树干注射保护剂。随着对保护剂的不断研发,这项技术的保护作用也越来越明显。目前应用效果比较好的保护剂有效成分主要是甲维盐或阿维菌素,根据松树大小不同注射不同的剂量,施药一次可以保护松树2~3a不被感染[45-47]。
3 展望
对松材线虫病的防治依然是十分漫长的。我国松材线虫病防控侧重于“应急性”、“单项技术”和“传统技术”,因此亟待融合现代科技进行创新,防控技术与产品不仅要注重环境友好型和可持续性,而且要注重标准化与规范化。目前我国在马尾松抗松材线虫病的选择育种方面初步积累了一定的抗性资源和培育技术[48-51],在引进抗病黑松和赤松资源并进一步开展抗性评价和利用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42-55]。对松材线虫病而言,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都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劣势,而生物防治对环境更加友好且有一定成效。除此之外,仍需对具有抗病性的松种进行选育。为保护人类重要的林业生态资源,应该采用各地区适宜的方式方法,始终坚持科学防治,绿色防治。随着松材线虫病防控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松材线虫病的防控即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由粗放、低质量的管控向集约、高质量的全程防控方向转变,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有待做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