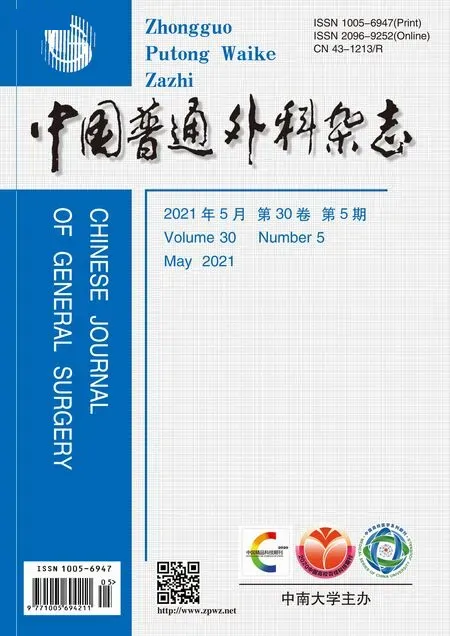三阴性乳腺癌治疗进展
吴松阳,江一舟,邵志敏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乳腺外科/复旦大学乳腺癌研究所,上海 200032)
乳腺癌在女性恶性肿瘤中发病率最高、病死率排名第二,且近年来发病率逐年上涨,根据最新研究统计,乳腺癌新发病例占所有女性新发肿瘤的近30%[1-3]。目前临床上使用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表达对乳腺癌进行分子分型,可以根据表达谱分为腔面型、HER-2过表达型、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4],根据不同分子分型分类而治极大地改善了乳腺癌患者的预后[5-6]。
TNBC占整体乳腺癌的10%~20%,在临床上定义为缺乏ER、PR表达,并且没有HER-2扩增,因而缺乏相应治疗靶点,目前化疗仍是主要的系统治疗方案[7-8]。相比于其他亚型,TNBC侵袭性较强,术后2年内容易早期复发,并且相较于其他亚型乳腺癌更易发生远处转移,复发转移患者的的总体生存(overall survival,OS)仅为13~18个月[9]。近年来,随着以基因组、转录组为代表的多组学技术快速发展,研究者们发现TNBC内部同样存在异质性,可以被分为不同亚型,并基于此提出基于分子分型的精准治疗方案,同时根据TNBC的分子生物学特征开发新型靶点,在多项临床试验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未来值得投入更多的精力对基于分子分型的靶向治疗方案进行深入探索。
1 TNBC 的标准治疗方案
目前,化疗、手术治疗仍然是TNBC的标准治疗方案,相比于其他乳腺癌类型,TNBC生物学行为更加恶性、预后更差,但对化疗的反应性相对较好。对于局部病灶,手术是首选的治疗方案,部分患者,尤其是肿瘤负荷较大者,考虑在术前接受新辅助治疗。TNBC患者的新辅助治疗以化疗为主,主要终点为达到病理完全缓解状态(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对于高风险的早期TNBC患者,pCR往往与更好的OS相关[10],同时研究者们也在多项临床试验中不断探索新辅助放疗的使用指征,但目前尚无可靠证据。在辅助治疗阶段,对于进行保乳手术,或伴有腋下淋巴结阳性的患者,多数都会接受辅助放疗,而化疗仍是首选的全身治疗方案。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不断提出更多有效的药物组合、给药方案,并逐渐将其拓展至后线治疗阶段,即使是对无法手术的转移性TNBC(mTNBC),化疗也有独到的作用。
目前TNBC 患者临床上最常用的是蒽环类(anthracycline,A)、紫杉类(taxane,T)药物,CAGLB9344研究发现在辅助治疗中,相比于仅使用蒽环类药物,蒽环序贯紫衫类药物可以减少约1/3 的复发与转移风险[11],并且剂量密集方案会带来更好的预后[12]。与外科手术从尽可能扩大范围全切到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减小手术范围、保证患者生活质量的发展历程相同,目前临床医生也尝试使用序贯给药等方式代替以往的治疗方案,BCIRG-005研究提示,辅助阶段相比于同时使用多西他赛、蒽环类药物、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CTX)的TAC方案,AC-T方案对患者带来的获益相似,10年OS(79.9%vs.89.9%,P=0.506)与无病生存(disease-free survival,DFS)(66.5%vs.66.3%,P=0.749)均无统计学差异,并且具有更低风险的血液学毒性[13-14],更进一步,INTENS研究提示相比于TAC方案,在新辅助治疗阶段对TNBC患者使用AC-T方案更容易达到pCR,5年DFS约增加10%[15],为后续临床试验指明了方向,在保证疗效的基础上使用具有更好耐受性的治疗方案。
近年来,在传统蒽环、紫杉类药物的基础上,研究者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以铂类、吉西他滨、长春瑞滨、卡培他滨为代表的新型化疗药物逐渐得到重视,同时在此基础上尝试使用新的给药方式以提高患者疗效,在新辅助、辅助,及后线治疗中均取得进展。在III期CBCSG006研究中,使用顺铂+吉西他滨(GP)相比于紫杉+吉西他滨明显延长mTNBC患者DFS,并且安全性较好[16],最近发布的GAP研究中,白蛋白紫杉醇+顺铂(AP)相比于GP方案的客观有效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明显升高,PFS明显延长,但具有较强的神经毒性,经过改良后有望成为mTNBC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一项Meta分析也发现,即使对于BRCA没有突变的患者,在新辅助治疗中加用铂类药物能够明显提高pCR,但同时会伴随更加明显的血液学毒性[17],而在辅助治疗中,PATTERN临床试验比较了单周紫杉醇+卡铂方案(PCb)与FEC-T标准方案,发现PCb方案能够明显提高5年DFS(86.5%vs.80.3%,P=0.03),而对于携带同源重组修复相关基因突变的患者,其获益更加明显(HR=0.39,P=0.04)[18]。而相比于传统的静脉化疗,以卡培他滨为代表的口服化疗药物安全性较好,使用较为便捷,近期得到广泛关注,CREATE-X临床试验发现,针对TNBC新辅助治疗患者,如未达到pCR,可通过卡培他滨强化辅助治疗改善OS、DFS[19],同样,在CBCSG010研究中,对于术后的早期TNBC患者,在标准方案FEC-T加用卡培他滨组方案(XEC-XT)能够明显提高5年DFS,并且耐受性良好,没有增加相关不良反应[20],后期也有荟萃分析提示,在原有的TNBC辅助方案中加入卡培他滨显著改善OS与DFS,提示在蒽环和紫衫类药物的基础上加用卡培他滨具有很强的应用前景,这也奠定了卡培他滨在辅助化疗中的地位。更进一步,调整其给药方式能为患者带来更大的获益,SYSUCC-001研究发现,对于术后的早期TNBC患者,在标准辅助治疗方案上加用低剂量高频率卡培他滨的“节拍治疗”明显提高5年DFS,并且安全性良好[21]。
同样,我们也不能忽视TNBC是一组异质性非常强的疾病,化疗的反应性在不同的TNBC患者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Lehmann等[22]提出的VICC(Vanderbilt-Ingram Cancer Centre)分型中,虽然总体pCR率为44.7%,BL1型患者的pCR率可以达到65.5%,而在LAR型中则只有21.4%[23],提示我们除了针对总体患者改进化疗药物与用药方案,在具体方案的制定中需要依据患者的特征量体裁衣。并且,基于现有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传统化疗药物的使用已经进入瓶颈,未来,研究者需要基于TNBC不同于其他亚型乳腺癌的独特分子生物学特征,例如极高的基因组不稳定性、更多的PIK3CA突变等,探索更多适用于TNBC患者的新型治疗靶点,并根据其内部异质性的理论基础,对不同分子分型患者给予相应的靶向治疗方案,基于精准治疗理念设计转化性临床试验进行深入探讨。
2 TNBC 的分子分型与分类而治
TNBC是一类有着极强异质性的疾病类型,随着以基因组、转录组为代表的多组学技术高速发展,研究者对于TNBC的研究逐渐深入,从多维度探索其生物学本质,基于组学数据将TNBC分为不同亚型,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VICC 分型、Baylor分型和复旦大学上海癌症中心(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re,FUSCC)分型,在阐述各种亚型分子生物学特征的同时,基于亚型特点提出基于分子分型的靶向治疗方案,值得提到的是,FUSCC团队进一步提出伞型临床试验进行后续验证得到较好成果,具有潜在的临床转化价值。
2.1 VICC 分型
2011年,来自VICC 的Lehmann等[22]收集21 个公共数据库共587 例TNBC 患者的信息,首次基于基因表达谱提出了TNBC 的六分型,包括基底样1型(basal like 1,BL1)、BL2、免疫调节型(immunoregulatory,IM)、间质型(mesenchymal,M)、间充质样细胞型(mesenchymal stem-like,MSL)、腔面雄激素受体型(luminal androgen receptor),其中BL1、BL2两型呈现更高的细胞周期与DNA损伤相关基因表达,并且高表达Ki67,更易从基于铂类的化疗方案获益,IM亚型表达更多的免疫相关分子,可能尝试免疫治疗,M、MSL亚型富集上皮-间质转换(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和生长因子相关途径,可能从PI3K-mTOR抑制剂获益,而LAR亚型中高表达雄激素受体(androgen receptor,AR),抗AR 治疗,例如恩杂鲁胺(enzalutamide)、比卡鲁胺(bicalutamide)等药物可能对此亚型患者有效。后续研究也发现该分型具有较强的临床应用价值,对于新辅助治疗阶段,BL1 亚型p CR 率最高(52%),而BL2 亚型几乎没有患者达到pCR,LAR亚型同样较低,并且该分型可以作为pCR的独立预测因素[24]。在2016年,该团队进一步使用组织病理学定量和激光捕获显微切割重新更新了分型系统,发现IM和MSL的转录物分别来源于微环境中的淋巴细胞与间质细胞,因此将IM和MSL亚型融入M亚型,从而定义新的TNBC四分型,包括BL1、BL2、M、LAR,同时在临床病理学层面对4个亚型进行对比,发现在预后、确诊年龄、肿瘤分级、淋巴结阳性率、局部和远处复发转移和组织病理学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25],目前有部分研究尝试提出基于VICC分型的治疗方案,并进行回顾性分析,但尚无针对性的前瞻性临床试验进行后续验证 。
2.2 Baylor 分型
在VICC 分型的基础上,大批学者投身到TNBC的继续分型与验证,并基于分型提出相应的治疗方案。2015年,来自Baylor医学院的Burstein等[26]通过分析198例TNBC组织的DNA和RNA表达谱,将TNBC重新分为4个亚型,分别为LAR、间质型(mesenchymal,MES)、基底样免疫抑制型(basal-like immunosuppressed,BLIS)、基底样免疫激活型(basal-like immune-activated,BLIA),并使用外部队列进行验证。其中,BLIS预后最差,而BLIA预后最好,提示免疫微环境在TNBC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且通过寻找每个分型的分子生物学特征,从而提出了基于分子分型的靶向治疗方案,在LAR亚型中,AR和细胞表面黏蛋白1可以作为特异性靶点,MES亚型中富集生长因子受体相关蛋白,而BLIS与BLIA则是在免疫相关分子表达存在明显特征,BLIS中高表达免疫抑制性分子VTCN1,BLIA中STAT信号转导分子和细胞因子均呈现富集状态。相比于前者,Baylor分型在深化分型体系,发现其与临床病理学指标相关的同时,基于每个分型进一步提出了相对应的治疗靶点,为TNBC基于分子分型的精准治疗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2.3 FUSCC 分型
基于前人的基础与该团队在2016年的发现[27],来自FUSCC的学者纳入465例TNBC患者,绘制了全球最大的TNBC多组学图谱,并基于转录组数据将TNBC分为4个亚型,分别为基底样免疫抑制型(BLIS)、腔面雄激素受体型(LAR)、免疫调节型(IM)、间质型(MES),并通过解析每个分型的不同分子生物学、临床病理学特征,提出了基于FUSCC分型的潜在治疗靶点[7]。IM亚型中存在大量淋巴细胞浸润与免疫相关通路富集,可能对免疫治疗更加敏感,而LAR亚型存在细胞周期与AR相关分子的过表达,提示CDK4/6抑制剂与AR抑制剂是可能的治疗靶点,同时存在更高频的HER-2突变,可以尝试抗HER-2靶向治疗。虽然BLIS预后较差,但研究者进一步发现,根据同源重组修复缺陷(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deficiency,HRD)评分,BLIS可继续细分为高HRD 与低HRD 亚型,其中高HRD 亚型患者更有可能从铂类化疗药物中获益。而MES亚型中则相对富集肿瘤干细胞与JAK/STAT3相关通路基因,STAT3抑制剂可能用于该亚型患者的治疗[7]。
由于高通量测序结果对检测平台、费用、需要的时间,以及后续的数据解读能力要求较高,VICC、Baylor分型仍处于研究阶段,探索TNBC内部异质性与相应靶点,仅有回顾性研究证据,尚未直接用于临床决策。基于此,FUSCC 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使用免疫组化进行替代,基于本中心平台筛选出4个临床上常用的分子,包括AR、FOXC1、CD8、DCLK1,并进行外部验证,发现能够快速便捷地在TNBC患者中复现FUSCC四分型的结果,与通过基因检测结果得出的分型高度一致,目前大部分中心对高通量测序的分析流程尚不成熟,因而该分型具有很强的临床推广价值[28]。后续,该团队秉承基于分子分型的精准治疗理念,开展Ib/II期FUTURE伞型临床试验(NCT03805399),共纳入69例多线治疗耐药的TNBC患者,结合分子分型与基因检测结果,开展精准治疗,共分为7个治疗臂,人群总体的ORR达到29%,尤其针对IM亚型患者,联合使用白蛋白紫杉醇与卡瑞利珠单抗的ORR达到52.6%,而对于LAR亚型中存在HER-2激活突变的患者,即使临床上判断HER-2表达阴性,吡咯替尼联合卡培他滨仍然具有较好的疗效,为TNBC患者的后线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29],后续该团队正进一步开展以FUTURE-SUPER为代表的系列临床试验,尝试将该治疗方案推向一线,甚至辅助治疗阶段,为TNBC患者目前以化疗为主的一致性治疗方案提供新的选择。
未来还需要研究者不断挖掘更大样本的多中心队列以及更多维度,例如表观修饰组、蛋白组、代谢组等在内的多组学数据,从而对TNBC进行更加系统性的描述,在四分型的基础上对TNBC进行更加准确的分型与更加系统的解读,根据不同亚型的特点开发相应的药物靶点,真正实现基于分子分型的靶向治疗[30]。同时,随着以单细胞测序[31-32]、空间组学测序[33-34]为代表的高精度测序技术不断成熟,研究者能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对TNBC的分子生物学本质进行深入探索,但由于成本、样本保存、技术限制等原因,目前多为小样本研究,基于临床试验的微观队列仍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3 TNBC 的精准治疗靶点
目前,针对TNBC的内部异质性有了奠基性的多项研究,而随着对其生物学本质的了解不断深入,以及基于大队列多组学研究的持续展开,结合越加成熟的分型系统,TNBC精准靶点的开发同样呈现高速发展的趋势。针对TNBC的分子生物学特征,例如增殖指数更高、存在较高的基因组不稳定性、PIK3CA突变频率较高,同时针对TNBC各亚型的特点,例如部分TNBC具有更高的突变负荷与杀伤性T细胞浸润,或存在特征性的AR高表达,进行相应抑制剂的的开发与靶向治疗的尝试,在多项临床试验中均取得较好结果,部分已经写入临床指南,有望真正应用于临床实践。
3.1 PARP 抑制剂
TNBC 基因组不稳定性较高,随着对TNBC细胞在DNA同源重组修复机制的研究不断深入,HRD逐渐被发现是TNBC的重要分子生物学事件,导致DNA双链结构难以修复。研究发现,TNBC中胚系BRCA1/2突变率约为15%,远远高于其他亚型乳腺癌,并且在FUSCC四分型中,BLIS亚型中存在一部分患者HRD评分远远高于其他亚型,可能作为该群患者的靶向治疗方案。PARP是一种DNA修复酶,对于保持基因组稳定性有着重要作用,而PARP抑制剂可以通过抑制PARP的活性,抑制DNA损伤修复,通过合成致死的机制导致细胞凋亡。目前临床上常用的PARP抑制剂包括奥拉帕尼(olaparib)、维拉帕尼(veliparib)等,2009年Paczulla等[35]在I期临床试验中将奥拉帕尼应用于胚系BRCA1/2突变的晚期肿瘤患者,总体临床获益率为63%,其中包含9例乳腺癌患者,并且相比于传统化疗方案,除了轻度的消化系统不良反应外并无其他明显的副作用。I-SPY2临床试验发现在TNBC新辅助治疗标准方案的基础上加用维拉帕尼和卡铂可以明显提高pCR率[36],III期临床试验OlympiA(NCT02032823)尝试评估奥拉帕尼在存在胚系BRCA1/2突变的高危患者辅助阶段的应用,相应研究仍在进行。同样,研究者们发现联合使用其他药物,例如DNA甲基化酶抑制剂[37]、β-拉帕醌[38],可以增敏PARP抑制剂,并且最新研究发现,包括RAD51D胚系突变在内的指标可以用于指导PARP抑制剂的使用[39]。而对于不存在胚系突变的患者,只要HRD相关指标较高,奥拉帕尼同样能获得较好的疗效[40],但在部分研究中仍观察到存在PARP抑制剂耐药,可能是DNA通过单链退火修复等途径进行代偿修复,未来还需要对其耐药机制,以及相应的疗效预测生物标记物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3.2 PI3K-mTOR 通路抑制剂
PI3K-Akt-mTOR通路的激活对于肿瘤细胞的增殖有着重要的作用,TNBC中PI3KCA的突变频率约为10%,相关通路的激活在LAR、MES亚型中更为常见[7]。一项I期研究提示,对于存在PI3KAkt-mTOR通路激活的晚期TNBC患者,在化疗的基础上加用PI3K-Akt-mTOR通路抑制剂能够显著延长PFS[41],同样,对于存在PIK3CA-Akt1-PTEN通路激活的mTNBC 患者,一线治疗紫杉方案中加用Akt的抑制剂capivasertib可以明显延长OS、PFS[42],在艾日布林治疗的基础上加用mTOR抑制剂依维莫司(everolimus)同样具有很好的安全效果[43]。而对于早期TNBC患者,FAIRLANE研究提示,在基于紫杉醇的新辅助方案加用PI3K/Akt通路抑制剂ipatasertib并不能提高pCR率,提示该类药物的使用还需要更加精确的指导[44]。联合用药可能为其提供更广阔的前景,在移植瘤模型中,抑制PI3K可以通过减少BRCA1/2表达,造成类似于BRCA1/2突变的效果,从而导致更高的HRD水平[45],提示PARP抑制剂与PI3K-Akt-mTOR制剂的可能前景,在一项Ib临床研究中,联用奥拉帕尼与阿培利司(alpelisib)安全性良好[46],并且该通路的新型抑制剂,例如MK-2206也在进一步研究中,具有很大的临床应用前景[47]。
3.3 内分泌治疗
和腔面型乳腺癌高表达ER、PR相似,部分TNBC存在明显的AR表达,而以往研究发现AR高表达和患者不良预后相关[48],提示靶向AR可能是TNBC,尤其LAR亚型患者的潜在治疗手段。比卡鲁胺、恩杂鲁胺是目前较为常用的抗AR药物,一项II期单臂研究发现对于AR阳性、ER阴性的晚期乳腺癌患者,比卡鲁胺可以提供19%的临床获益率[49]。在体外,LAR亚型的肿瘤细胞通常存在更加活跃的细胞周期相关基因表达,因此联用细胞周期相关药物可能具有很大的潜力,同时该亚型通常携带更多的PI3K突变,对恩杂鲁胺耐药的LAR型患者可能从PI3K-mTOR抑制剂中获益[50],提示其与PI3K-mTOR通路抑制剂联用可能是未来的应用方向。在体外,同时抑制AR与PI3K-mTOR通路能够对AR阳性的TNBC细胞有明显的协同作用,在Ib/II期TBCRC032临床研究中,蒽杂鲁胺联用PI3K抑制剂Taselisib可以明显提高AR阳性TNBC患者的临床获益率,尤其在LAR亚型患者中更加有效,同时伴随可耐受的高血糖以及皮疹;以往研究多使用AR的表达情况来定义AR抑制剂的获益人群,但TBCRC032研究表明该指标并不能真正反映AR抑制剂的有效情况,FGFR2融合基因和AR剪接体变异可能具有更强的预测能力[51]。虽然AR抑制剂显示了相当大的潜力,但在多线治疗失败的患者中并没有表现出很好的获益[29],提示我们不能片面看待AR在TNBC中发挥的作用,同时需要寻找更好的在临床上定义AR的方式,也许只有AR强阳性的患者才能从中获益,并且基于研究结果,AR可能只是TNBC恶行生物学反应的表型,而不是驱动原因,需要从更加综合的角度审视,寻找AR上下游的靶点开发新型抑制剂可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3.4 免疫治疗
近期,肿瘤免疫微环境得到了深入研究,而与之相对应的免疫治疗也成为肿瘤治疗中的新兴疗法,在多项临床试验中得到了很好的结果。相比于其他类型乳腺癌,TNBC突变负荷较高、免疫原性更强,同时存在更多的免疫细胞浸润[52],使得TNBC成为免疫治疗的可能获益人群。IM亚型约占整体TNBC 的24%[7],并且相比于其他亚型有着较好的预后,虽然在该亚型中没有突出的基因组、转录组特征,但存在明显的免疫富集,更有可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近年来,免疫中和(immune normalization)的概念也不断得到深化[53],在不增加不良反应的同时,重塑肿瘤诱导的抑制性微环境,以此为代表的便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ICB),尤其是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及其受体PD-L1单抗,在TNBC治疗中大放异彩,同时有研究提示传统化疗可以导致肿瘤细胞表面表达CD47、CD73、PD-L1[54],从而逃避肿瘤细胞杀伤能力,因此在化疗的基础上联用免疫治疗大有前景。
IMpassion130发现对于mTNBC 患者,在白蛋白紫杉醇的基础上使用阿特丽珠单抗(atezolizumab)明显延长总体,尤其是PD-L1阳性亚组患者的PFS,揭开了TNBC 免疫治疗的新篇章[55],同时,针对PD-1的药物,例如纳武单抗(nivolumab)、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德瓦鲁单抗(durvalumab)[56-57],以及针对PD-L1 的药物,例如阿维单抗(avelumab)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55,58-59]。既往研究多采用免疫细胞PD-L1表达水平预测PD-L1单抗疗效[55,60],而近期研究[61]发现,不仅是在总体免疫细胞,肿瘤细胞中表达的PD-L1同样与德瓦鲁单抗新辅助治疗的获益有关。近期公布的III期KEYNOTE-355研究[62]发现,在未经治疗的PD-L1高表达的mTNBC患者化疗方案中加入帕博利珠单抗可以明显提高PFS,为mTNBC一线免疫治疗应用提供了最新的证据。而对于早期TNBC,IMpassion031研究[63]发现在新辅助化疗标准方案加用阿特丽珠单抗明显提高pCR率,并且具有良好的安全反应。对于多线耐药的TNBC患者,在卡培他滨的基础上加用帕博利珠单抗不能延长PFS[64],同样,KEYNOTE-119研究提示帕博利珠单抗单药使用相比化疗不能带来疗效获益[65],而在FUTURE临床试验中,研究者精准定义出的IM 亚群患者(CD8≥20%),卡瑞丽珠单抗(camrelizumab)与白蛋白紫杉醇联合治疗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ORR=52.6%),并且没有严重的药物相关不良反应[29],提示未来免疫治疗也需要向精准方向发展,寻找更有可能获益的患者人群。
免疫治疗无疑是TNBC未来有望的发展方向,还需要不断发现新的靶点,例如CTLA-4、TIM-3、IDO1,以及充分应用药物联用以逆转耐药,并且根据基础免疫理论尝试新型免疫治疗方式,例如细胞过继疗法、CAR-T等TNBC中的应用,形成优势互补,进行深入探究。
3.5 细胞周期疗法
细胞无限增殖是肿瘤细胞区别于正常细胞的重要特点[66],而TNBC相较于其他亚型乳腺癌存在更强的增殖、侵袭能力。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cyclin-dependent kinase,CDK)4/6是细胞周期的关键调节因子,与细胞周期蛋白D(cyclinD)磷酸化RB 蛋白,触发细胞周期从G1期进入S期,CDK4/6抑制剂,尤其是哌柏西利(palbociclib)、瑞博西林(ribociclib)相关的临床试验在ER 阳性乳腺癌中取得了很好的结果[67-68],TNBC也常伴有CDK家族蛋白的过度表达,以此为靶点的CDK4/6抑制剂在TNBC治疗同样具有很好的前景。
在临床前研究中,RB基因高表达的TNBC细胞对哌柏西利更加敏感,AR/RB双阳性的细胞系,恩杂鲁胺、哌柏西利联用的效果也更加明显[69],而在TNBC患者中,AR与RB表达常呈现正相关,因此AR阳性的TNBC患者,尤其是LAR患者更可能从CDK4/6抑制剂中获益[70]。同时,在LAR亚型中,不仅高表达AR,细胞周期相关通路也呈现高度激活的状态,因此以往研究多考虑联用两种药物,并且体内体外实验都发现其对于CDK4/6抑制剂敏感,值得在后期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31,71]。除了传统的哌柏西利与瑞博西林,也有新的药物正在开发,在一项II期研究中,对于mTNBC患者,在化疗的基础上加用短效CDK4/6抑制剂trilaciclib明显延长PFS[72],可能与该药物保护免疫细胞免受化疗损伤有关,近期也有多项研究发现CDK4/6抑制剂可以激活免疫反应,例如增强杀伤性T细胞的功能[73],在小鼠体内移植瘤模型中,联用CDK4/6抑制剂和PD-L1单抗可以抑制肿瘤生长[74-75],因此,未来联用CDK4/6抑制剂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能是新的方向,相关的临床试验也正在进行[76]。
3.6 血管生成抑制药物
相比于正常组织与其他亚型乳腺癌,TNBC表现出更强的增殖活性,而肿瘤新生血管的大量形成为肿瘤生长提供大量的营养物质[77],参与其发生发展、侵袭转移的生物学过程,因此靶向血管生成可能是TNBC的治疗方向。
目前研究较多的抗血管药物主要包括单克隆抗体以及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CALGB40603研究发现在II~III期TNBC患者标准新辅助化疗方案中加入贝伐珠单抗(bevacizumab)可以明显提高pCR率[78],同样,RIBBON-1研究发现在一线治疗的标准方案中加入贝伐珠单抗可以明显延长PFS,并且没有增加毒副反应[79],后续临床研究也对其进行了验证[80],并且在二线治疗中该药物组合同样具有很好的效果[81],IMELDA研究的亚组分析提示,贝伐珠单抗联合卡培他滨可以带来OS、PFS的获益[82]。并且,在GeparSixto研究中,对于存在胚系BRCA1/2突变的TNBC患者,在贝伐珠单抗的基础上加用卡铂可以提高pCR率[83-84],这也与CALGB40603研究结果相互佐证。并且,近期有研究[85]报道联用抗血管生成药物可以明显增强PD-1单抗的疗效,为后续药物联用提供了方向。
相比于单克隆抗体,TKI相关的研究较少,一项II期研究发现针对晚期TNBC患者,相比于单药,联用阿帕替尼(apatinib)和卡瑞利珠单抗可以明显提高ORR[86]。虽然多项研究发现贝伐珠单抗可以明显延长PFS,但目前并没有足够强力的证据表明可以带来OS获益,并且对于早期TNBC而言,贝伐珠单抗在辅助阶段并不能在生存上带来获益[87],未来还需要更多的基础与研究,并且探究合理的联合用药方案,例如与化疗、免疫治疗,以取得更好的疗效[88-90]。
除了上述提到的几类药物,也有新型药物正在不断得到研究,例如针对TNBC高表达细胞表面糖蛋白TROP-2,研究者将靶向TROP-2抗原的人源化IgG1抗体与化疗药物伊立替康的代谢活性产物SN-38偶联形成新型药物sacituzumab,最近发表的临床研究提示该药物可以作为mTNBC的治疗方案,中位PFS为5.6个月[91-92],并得到FDA批准。未来需要基于高通量的方式对TNBC特异性表达的分子展开更多研究,筛选出类似HER-2的驱动分子,并针对性地开发特异性靶向药物,并尝试更多的药物联用方案,在提高疗效的同时降低患者的药物相关不良反应。
近10年,分类而治和精准治疗已经成为TNBC治疗的主要发展方向,在各项临床试验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基于分子分型的靶向治疗方案有望在未来成为TNBC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未来还需要对TNBC的微观本质有更深入的了解,例如代谢领域、肿瘤共生菌群领域,不断开发新型靶点,并且通过合理的药物联用来达到更好的疗效,克服现有药物的耐药,同时,精准定义适用于已有靶点药物治疗的人群也是重要的发展方向,例如在MES亚型患者中使用抗血管生成药物,在LAR患者中联用AR抑制剂与PI3K-mTOR通路抑制剂。另一个需要重视的点是整合现有的多维度组学数据,将TNBC进行更加准确的划分,寻找每个亚型的特点,并使用临床可及的技术,例如免疫组化、精准检测来复现已有分型,实现精准的个体化治疗,真正在临床上得到应用。
虽然目前对于TNBC的内在分子生物学特征,以及其与微环境间质细胞的动态联系已经得到了较为深入的探索,但由于TNBC存在极强的异质性,未来还需要对其本质有更深的探索。随着对其分子特征、微环境结构等认识的加深,以及新型检测手段的诞生,会出现更多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并通过基于精准治疗理念设计的转化性临床研究加以验证,有望为患者带来更佳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