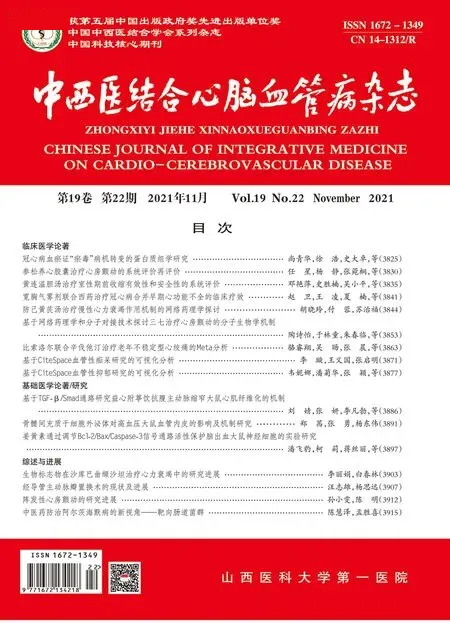基于阴阳理论探究自噬在高血压中的作用
方俊锋,金 政,吴 伟
高血压是一种进行性“心血管综合征”,其特征是动脉血压持续升高[1]。高血压容易损伤病人心脏、脑和肾等靶器官,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健康问题[2]。虽然现代医学在高血压治疗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其发病率、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尚未出现转折点[3-4]。因此,寻找有效的干预靶点已成为治疗高血压的新方向。自噬是细胞的自我保护措施,便于应对各种情况的发生,具有调节组织稳态的作用,在心血管疾病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5]。
中医阴阳学说是用以阐述“天人合一”整体观以及“恒动”理念的中医理论体系。所谓“天人合一”,即将大自然、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生命与疾病的生、发、传、变都是阴阳之间微妙的变动产生的结果。另外,《素问·天元纪大论》有云:“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由变而生也”。此与阴阳转化、对立、消长的恒动过程相似,人体的生理病理发生也在不断变化。自噬的促进与抑制双重作用及维持动态平衡过程是中医阴阳对立制约、互根互用的体现。机体达到“阴平阳秘”为中医防治疾病的最终目的,故阴阳的失衡在高血压的发生发展中具有关键意义。因此,从中医阴阳理论出发探索自噬在高血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1 中医阴阳理论
阴阳理论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中医哲学唯物辨证法的核心内容,是基于自然观察而对天地、昼夜、向阳与背阳事实和规律的认识和总结。目前所出现最早记载“阳”字的文物为商代甲骨文,“阴”字出现在周代的金文中,从春秋时期开始出现了“阴阳”两字联用,此时的阴阳概念指的是自然地理方位,而阴阳哲学概念的出现始于《太一生水》。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道家与儒家、法家、各家等各派交流融合,阴阳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归纳、升华、抽象为标示对立属性的概念。《周易系辞上》将“阴阳”推向了哲学本体论的层面,并明确提出了“一阴一阳”,此时的阴阳理论解释了宇宙的起源,阴阳结合起来产生了一切;与此同时《易传》认为,万物的形成和变化都是由阴阳对立的变化引起的。阴阳的提升是两个方面,代表着相互关联的事物或同一事物的内在矛盾,使得阴阳观念更为系统化、理论化,逐渐发展成相对完善的一种思维体系。阴阳理论渗透到医学中主要体现在《黄帝内经》中,其明确指出阴阳是物质运动的驱动力,包括对立统一,交感相错;互根互用,胜复转化;动静升降,消长平衡。其后,中医的阴阳学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进一步发展为以下几个方面:人与自然的阴阳,即人与天的关系,人与自然统一的阴阳规律;人体本身的阴阳,即人的生命运动的阴阳特性和规律;阴阳病的病变,即阴阳特征和人类健康与疾病发展变化的规律;防治阴阳,即病变表现于临床的阴阳,以及对其进行防治的规律;方药阴阳,即方药、针灸等防治手段的阴阳特性和规律。综上可知,阴阳理论对中医临床医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 高血压与阴阳的相关性
古代文献中并无高血压病名的相关记录,然而根据病人症状表现,高血压属于中医学“眩晕”范畴。“眩晕”的解释分为“眩”与“晕”,统称为“眩晕”。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记载:“头眩虽属上虚,然不能无涉于下。盖上虚者,阳中之阳虚也;下虚者,阴中之阳虚也”及“阳失阴而离者,不补阴何以收散亡之阳;水失火而败者,不补火何以延垂寂之阴?此又阴阳相济之妙用也”,提示阴阳的变化与眩晕病密切相关,阴阳平衡是维持血压正常的必要条件。
中医学认为,阴阳为万物对立统一之根本所在,阴阳合和交感,而生万物。正如“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寒极生热,寒气生浊,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月真胀。此阴阳反作,病之从逆也”,所谓“和”,指的是阴与阳相互顺接,阴平阳秘,使整个人体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相反,如若阴与阳不能互为依托、衔接顺畅,则出现阴阳失衡的局面,百病由生。阴阳偏盛偏衰是疾病产生的物质基础,阴阳失衡百病始生,正如《景岳全书·阴阳篇》所云:“凡诊病施治必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眩晕的辨证应以阴阳为纲,阴阳失衡、脏腑功能失调乃眩晕病机关键,高血压发病与肾、肝、脾密切相关,发于肾则阴虚阳浮,虚阳外越,发于肝则肝阳过亢,阳损及阴,发于脾则阳虚水停,聚而为痰饮。故治疗高血压根本在调整人体内在气血阴阳,以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治以燮理阴阳为本,辅以损其有余,补其不足,以恢复阴阳平衡。因此,阴阳的失衡及调整与高血压的发生和论治密切相关。
3 自噬对高血压的作用
原发性高血压的早期预防和及时干预,对控制其发病率和缓解病人的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表明,血管结构和功能的异常是高血压发生的早期病理机制,其中血管内皮细胞损伤主导的血管功能改变在高血压发生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6-8],而自噬在血管内皮细胞凋亡的调控中可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是血管壁的主要成分,在阻力血管中有助于维持血管张力,从而调节血压以及氧气和营养物质向周围组织的分布,高血压病变中的反应性物质、生长因子、细胞因子等促使VSMC激活自噬,因此,VSMC中自噬的调控可能具有重要的治疗意义[9]。而过度自噬会清除必需的细胞因子,可能引起细胞死亡并导致高血压性心脏病[10]。
迄今为止,高血压发生的具体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从细胞自噬角度探讨高血压的潜在机制,已成为研究高血压的热点领域,目前已有相关研究提示,细胞自噬水平与高血压的发生发展具有一定的关联。其中miRNA得到了广泛研究,其参与调控细胞增殖、分化、衰老、凋亡等过程,在高血压的发展过程中多个miRNA分子的表达发生变化,在心脑血管损伤中具有临床诊断价值[11]。研究发现外周血中miR-199a-5p的表达与高血压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K)信号通路的激活可引起UNC-51样激酶1(ULK1)的磷酸化和自噬的激活[12],miR-199a-5p通过下调AMPK/ULK1信号通路的活性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的自噬,促进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凋亡,加重血管内皮损伤[13]。一项涉及高血压病人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显示,与高血压相关的损伤调控自噬调节基因存在一个常见变异[14]。有临床试验表明,自噬活性的缺陷或自噬反应的过度激活都可以导致细胞稳态的紊乱和凋亡过程的启动[15]。
以往的体内外研究表明,保持在生理水平上的自噬是维持心肌细胞内稳态所必需的。心肌的自噬反应在生理和病理过程中可能具有双重作用[16]。不受控制或过度活动的自噬可能导致必要细胞成分损伤,最终导致心肌细胞的程序性死亡[17],因此,对心肌自噬活性的调控成为另外一个防治心肌肥厚和心力衰竭的新靶点,研究表明,肾脏去神经支配(RD)是治疗顽固性高血压的一种新的治疗策略,肾去神经支配可能通过减弱过度激活的细胞自噬反应减轻高血压所致的左室肥厚[18-21],但RD对心肌自噬反应调解作用的信号通路尚需进一步研究。另有研究表明,高血压前期自发性高血压大鼠肠系膜内皮功能障碍至少部分归因于血管组织的过度自噬。中药何首乌中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的白藜芦醇类似物四羟基二苯乙烯苷(TSG)通过激活蛋白激酶B(Akt)/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信号通路抑制自噬,从而部分修复微血管内皮功能障碍,提示TSG可能用于保护血管功能免受高血压前期亚临床改变的影响[22]。还有研究表明自发性高血压大鼠脑内自噬被激活,而血管紧张素-(1-7)处理4周后自噬活性明显减弱,提示血管紧张素-(1-7)的慢性治疗可能有助于预防高血压引起的脑内过度自噬激活[23]。相对地,自噬在高血压引起的心肌肥厚中被激活[24-25],自噬可能具有心脏保护作用,在衰竭的心脏中激活自噬可能是一种适应性反应,若自噬不足则使心脏对心肌病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26-27]。有研究发现,阿托伐他汀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左室功能和结构的改善可能部分通过调节Akt/mTOR信号通路增强心脏自噬而实现[28]。另有研究表明,缬沙坦在调节肾血管性高血压所致高血压心脏病的心肌自噬和线粒体转换方面具有新的潜在作用,研究发现缬沙坦改善左心室肥厚和心肌微循环与恢复自噬活性有关[29]。
4 基于阴阳理论探讨细胞自噬
自噬是细胞降解自身“毒物”的过程,将“消化”的物质转为能量,维持机体内环境稳态,适应各种因素导致的恶劣环境[30]。其不同于一般形式的细胞死亡模式,是受上游靶基因调控的程序性“自食”过程。大多数组织中都存在基础水平的自噬发生,其基本作用是允许细胞质组成成分的基本周转,但是,也可以感受环境压力相关的信号,如营养不足、缺氧或氧化损伤等,使养分再利用和能量生成,从而在不利条件下也能维持细胞生存能力。除了细胞应激外,基本的自噬也可被特定的药物增强[31],提示自噬是不同疾病的一个潜在的治疗目标。
在机体生理与病理情况下,细胞自噬都参与调控体内阴阳平衡。从自噬本身微观层面来讲,细胞通过调控自噬水平,降解多余的代谢产物(阴),从而产生新的能量物质以实现能量和物质的更新(阳)。从中医学角度来看,降解多余的代谢产物为“体”,产生新的能量物质为“用”,体为阴,用为阳,自噬通过“阴”和“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使机体维持“阴平阳秘”状态。而自噬如果不及或过度,都会导致阴阳失衡。分解过多代谢产物,使机体“阴”象削弱过度,呈现“阳”象亢奋,出现“阴虚阳亢”状态;反之,细胞自噬能力不足,分解代谢产物能力下降,使代谢产物堆积,能量产生过程减弱及受限,呈现“阳虚阴泛”状态。故在能量产生的同时,将消耗掉精微物质,前者为阴长阳消过程,后者为阳长阴消过程,二者相互作用,此消彼长,细胞自噬的微观动态平衡才可得到较好的维持。由此可见,细胞自噬导致的“阴虚阳亢”和“阳虚阴泛”与高血压的中医病因病机相似。阴虚日久,抑制、凉润、宁静作用减弱,机体表现阳亢状态,导致细胞自噬水平过强;同理,阳虚持续不改善,兴奋、温煦、推动作用降低,细胞自噬不及。
5 调整阴阳指导高血压的治疗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可见,调整阴阳的平衡对疾病的防治意义重大。现今西医治疗高血压不良反应较多、副作用多、禁忌证多、药物联合使用条件受限、病人依从性较差,中医药注重调节机体整体平衡,其作用的多效性、多靶点性、增效减毒性、稳定持久性等方面有独特的优势[32-35]。阴阳的失衡是导致高血压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调整机体阴阳来调节细胞自噬维持在适度的水平是干预高血压的新思路。当机体出现阴虚阳亢即自噬过强的状态时,可通过“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取滋阴降火之法来抑制自噬水平;而当机体出现阳虚阴泛时即自噬不足的状态时,可通过“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取益气助阳来激活自噬。因此,调节机体阴阳平衡,调控自噬水平,是防治高血压的重要思路。
自噬通过适应性和非适应性调节在高血压中发挥重要作用[36]。自噬主要受两种复合物的调节,即Beclin-1复合物和mTOR复合物[37]:Beclin-1复合物可以促进自噬的发生,而mTOR途径的激活抑制自噬的发生。它们与上游和下游信号传导途径一起形成了一个调节自噬的复杂信号调节网络。研究提示,炎性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可促进细胞自噬增加,而mTOR的抑制剂Rapamycin可进一步促进TNF-α介导的自噬发生;相反,自噬减弱了促炎因子白细胞介素-6(IL-6)和白细胞介素-1β(IL-1β)的表达以及NOD样受体蛋白3(NLRP3)炎症体的活化,从而加剧了高血压的发生。故自噬的过度或不及参与高血压的发生发展[38-39],而中医通过调整阴阳的平衡使得细胞自噬处于适当水平,进而调控高血压,具有重要意义。
6 小 结
高血压与阴阳失衡密切相关。自噬水平上调与下调的双重调节功能,受到全世界医学家的关注,而自噬的过度或不及,都可能引起机体的阴阳失衡。从中医“整体观”调节平调阴阳角度把握自噬在高血压疾病中宏观作用机制来调控自噬功能,并且以“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为宗旨,是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理论互为契合治疗心血管疾病之切入点。然而迄今为止有关自噬与高血压的发病机制尚未阐明,药物的靶向细胞自噬机制仍在进一步深入与探索,研究前景广阔,是本课题组今后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