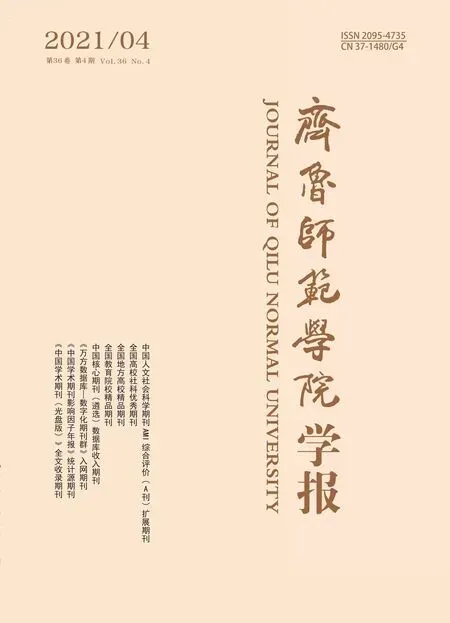郑文焯评柳永词“骨气高健”说探论
张宇辰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在各代词论家的期待视野中,“婉约派”“俗文学”已成为柳永词作的代名词,对其解读也不脱“屯田家法”“雅俗之辨”“音律词调”等范畴。近代以来,学者们对柳词的关注视角日益丰富,对柳永其人其词的研究也愈加深入,然而在对柳永传统解读的思维惯性引导下,对柳永及其词作的认识仍存在不够全面客观、单一固化的倾向。与文学史对柳永的主流评价不同,作为晚清四大家之一的郑文焯针对柳永词所提出的“骨气高健”说,具有独特的词学价值。本文着眼于郑文焯对柳永词的评价,探究其“骨气高健”说的内涵、原因及影响,以期为发现柳永词的新特点、新侧面提供一些启示。
一、郑文焯“骨气高健”说的提出
郑文焯是著名词学家,被誉为晚清词坛四大家之一,其对词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均有深入研究。郑氏曾说:“周、柳、姜、吴为两宋词坛巨子,来哲之楷素,乐祖之渊源。……今之学者,当用力于此四家,熟读深思。”[1]34将柳永与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并举,视其为词坛之楷模,可见推崇之意。今存郑文焯关于柳永词的著述有《手批石莲庵刻本乐章集》,另外,还有在其致友人的论词书札中关于柳永词的不少论述。他在深入研究柳永词作的基础上,对柳词风格特征的论断独具特色,即指出了柳词“骨气高健”的特点。现将原文摘录如下:
耆卿词以属景切情,绸缪宛转,百变不穷,自是北宋倚声家妍手。其骨气高健,神韵疏宕,实惟清真能与颉颃。盖自南唐二主及正中后,得词体之正者,独《乐章集》可谓专诣已。以前作者,所谓长短句,皆属小令。至柳三变乃演赞其未备,而曲尽其变。距得以工为俳体而少之?尝论乐府原于燕乐,故词者,声之文也,情之华也,非娴于声,深于情,其文必不足以达之,三者具而后可以言工,不其难乎?求之两宋,清真外微耆卿其谁欤?[1]40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郑文焯一方面承续前人之见,指出柳词写景之铺叙渲染、抒情之婉转多变、创制慢词长调、声律谐婉深情的特点,充分肯定其在宋词发展史上的贡献;另一方面自立新警之论,将“骨气高健”等风格属之柳词。无独有偶,郑文焯在批校《乐章集》时说:“学者能见柳之骨,始能通周之神,不徒高健可以气取,淡苦可以言工,深华可以意胜,哀艳可以情切也。”[1]18在这里他将柳永的骨气与周邦彦的神韵并举,认为“柳之骨”与“周之神”之间具有承续的关系,并同时提出自己的词学主张:在气韵方面追求高健,在语言方面追求简洁锤炼,在意境方面追求深邃,在情感方面追求悲壮深婉。此外,郑氏在给友人张尔田的信中亦有类似看法:“屯田则宋专家,其高浑处不减清真,长调尤能以沉雄之魄,清劲之气,写奇丽之情,作挥绰之声,犹唐诗之家,有盛晚之别。”[1]219这些评价不但别出心裁,而且有悖于古代文人对柳永的主流看法。
从宋代到清末,文学史上的柳永很少远离评论家们的视线。古人对柳永人生之争论、对其作品之阐释批评、对其文学史地位之评价,向来褒贬不一。宋陈振孙言柳词“音律谐婉,语意妥帖,承平气象,形容曲尽”[2]616,明王世贞亦褒其为“词之正宗”[3]385。而批评者又以之为俚俗的典型,以“言多近俗”“词语尘下”加以批评,自宋代起,不喜柳词者多加转用,讥其词品卑下,将其斥于雅词阵营之外。金元二代,曲代词兴,柳永词鲜有人道,对其人其词的研析逐渐消歇。降及明清,随着词学的中兴,柳永词的传播又逐渐复苏,受到文学家们的广泛关注。无论词学史上对柳永作何评价,在各代词论家的期待视野中,“婉约派”“俗文学”已成为柳永词作的代名词,对其解读也不脱“屯田家法”“雅俗之辨”“音律词调”等范畴。在这些褒贬不一的争论之中,郑文焯的评价展现出与前人不同的独特见解。由上引郑氏的评论可以看出,他力图阐明以婉约为主导风格的柳词亦不乏“骨气”,这一论断无疑是针对前人指斥柳词之“俗”而发,对人们重新认识柳词,重塑柳永的文学史地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骨气”的传统意涵与郑文焯的词学主张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语境中,“骨气”这一审美概念具有丰富的含义。“骨”的概念最早见于《老子》:“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4]86可见在先秦时期道家哲学观念里,“骨”与人之生命相联系,蕴含着对生命力量的隐性表达。“气”则与自然万物相通,《说文解字》云:“气,云气也。……凡气之属皆为气。”又有《广雅·释言》云:“风,气也。”可见“气”又与“风”相关。从文化层面来讲,“风”源于儒家诗教,《毛诗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5]6其后孟子又提出“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风”与“气”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性作用及人的内在品格,后世文人受传统儒学观念的影响,常将“骨气”“风骨”用于论人论文。发展到魏晋时期,文人在文学评论及人物品评之中开始频频使用“骨”“气”二字,如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6]312葛洪《抱朴子》:“属家之笔,亦各有病……其浅者,则患乎妍而无据,证援不给,皮肤鲜直而骨鲠迥弱也。”[7]199可以说是首次将“气”“骨”引入文学批评之中。其后又有钟嵘评曹植“骨气奇高,辞采华茂”[8]39,这里的“骨气”是针对曹植五言诗的审美特质来说的,强调了建安文学所具有的充沛情感和慷慨悲凉的美感力量。刘勰《文心雕龙》亦专设《风骨》一篇,力图调和文学创作过程中辞采与内容的关系,系统地提出了“风骨”理论,是文学批评领域的一大进步。沿袭六朝的文学理论传统,初唐的陈子昂、四杰也高举“风骨”大旗,唐以后以“骨气”“风骨”评论文学、书法、绘画作品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可以说,“骨气”已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种美学标准,凝聚为中国文人统一的艺术追求。
明确了“骨气”的传统意涵,郑文焯所说的“骨气”是否具有相同的文化表意呢?通过考察郑氏对各家词籍的评点,可以发现在他的词学批评体系中,“骨气”是常用概念。单以“骨”“气”二字评价柳词,就有多处。如郑氏在评点柳永《抛球乐》(晓来天气浓淡)时说其语意“有掉入苍茫之概,骨气雄逸,徒与写景物情事意境不同”[1]32,评《夜半乐》(冻云黯淡天气)时说“其气骨更雄杰也”[1]35,评《安公子》(梦觉清宵半)等词作中亦提到了“骨”“气”二字。此外,在对其他词人的词籍批校中亦可见类似的评价,如郑文焯在点评温庭筠《杨柳枝》(宜春苑外最长条)时指出“唐人以余力为词,而骨气奇高,文藻温丽”[1]1;评韦庄《浣溪沙》(夜夜相思更漏残)时指出其“善为淡语,气骨使然”[1]2;在评价吴文英词时说“至人谓其词为涩体,不知其行气清空,正如朱霞白鹤,飞荡云表”[1]15;评价二晏、周、秦词时说“其骨气高深处,亦不减韦、薛风流”[1]3;评价苏轼《八声甘州》(寄参寥子)时说“是何气象雄且杰。妙在无一字豪宕,无一语险怪,又出以闲逸感喟之情,所谓骨重神寒,不食人间烟火者,词境至此观止矣”[1]53;评价周邦彦词“清真长调骨气奇高,其雄浑处全在连用三字”[1]56;又言“清真风骨,原唐诗人刘梦得、韩致光,与屯田所作异曲同工”[1]57;评吴文英词“其行气存神之妙,不得徒于迹象求之”[1]118;又言“其实梦窗清空在骨气,非雕琢薄辞,徒以文掩义也”;评价《声声慢》(夏景)时说“此调清健在骨,是北宋风格,其高迥不减清真”[1]155。在《与张尔田书》中,郑文焯对“骨气”二字做出更加明确的解释:“所贵清空者,曰骨气而已。”[1]220综上所引,可以看出郑文焯所说的“骨气”,在继承先秦汉魏以来的文化意涵的基础上,主要是针对词这一文学体裁提出的,其所指更为具体,至少包括四个方面:首先,在风格方面,骨气与“高健”“清空”“雄浑”相联系,与作品所要表达的精神内容密切相关;其次,在语言方面,追求恬淡清丽、流畅连贯的字句,反对雕琢薄辞;第三,在情感方面,传情达意富有感染力,写景摹人能够“生出无限情思”;第四,郑文焯所说的“骨气”代表了北宋的文学创作风貌,并与唐代文学风格有契合之处。
三、柳词特质与“骨气高健”的具体表现
经过上面的梳理,可以廓清郑文焯“骨气”说的含义,那么,郑文焯对柳永词作出的“骨气高健”的评价是否恰切呢?需要我们做进一步分析。
首先,就内容而言,柳词确有风格“高健”“清空”的一面,这集中体现在他以典故传情的词作中。郑文焯曾言:“其实经史百家,悉在熔炼中,而出以高澹,故能骚雅,渊渊乎文有其质。”[3]4331如果能将典故与所要表现的内容熔炼在一起,那么词作就会显得雅正高澹而有内容。其实,在柳永词中不乏用典之作。据笔者统计,在薛瑞生先生校注的《乐章集》中,涉及到使用典故的词作大概有70首,单首用典最多的达12处。内容涵盖《庄子》《左传》《史记》《三国志》《晋书》《世说新语》等典籍,其中对宋玉之事典的化用最多,此前已有诸多学者论及,因此不赘。关于柳词中语典的使用,则多是化用六朝诗人的作品,如《荔枝香》(甚处寻芳赏翠)上片“缓步罗袜生尘”化用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笛家弄》(花发西园)上片“草薰南阳”化用江淹《别赋》“陌上草薰”,《八声甘州》(对潇潇)下片“天际识归舟”化用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倾杯乐》(楼琐轻烟)下片“看朱成碧”化用王僧孺《夜愁示诸宾》“谁知眼乱,看朱忽成碧”,等等。这些典故的使用,一方面延续了前代作家本身具有的文学意蕴,将宋玉、曹植等高健之气化于自身词作之中,另一方面使词意更加委婉含蓄,将浓烈的情感藏于典雅的文字之间。同时,这种通过典故的运用展示画面、表达情感的手法,实现了贵神情、重内涵而遗迹象的表达效果,营造出引人想象的清空之境。柳永的这些作品用典虽多但并不粘滞,反而为全词添上了清疏幽远的色彩,这无疑契合了郑文焯“词意固宜清空,而举典尤忌冷僻”的词学主张[3]4335。
事实上,郑文焯对“清空”的重视是由他早年推崇姜夔开始的,他曾自述说“为词实自丙戌岁始,入手即爱白石骚雅”[1]217,又言“近拟专意柳之疏奡,周之高健,虽神韵骨气不能遽得其妙处,尚不失白石之清空、骚雅”[1]283。另外,在郑文焯之前亦有不少词论家提出“清空”这一概念,如张炎《词源》曰:“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9]49清代沈祥龙《论词随笔》亦言:“词宜清空,……清者,不染尘埃之谓;空者,不著色相之谓。清则丽,空则灵,如月之曙,如气之秋。”[10]216郑文焯的词学观点与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对柳永词的评价中,将“骨气”与“清空”两种审美类型相互融合,其所言“所贵清空者,曰骨气而已”[1]220,即是认为清空在于骨气而非字面。相较于前代对“清空”或“骨气”的单一倡导,郑文焯在追求高健劲峭的内在骨气的同时,亦准确把握艺术层面的神韵清空,力求达到“高健在骨,空灵在神”的审美境界。这无疑有益于词作情致、文辞之生气的展现,对词学创作及“骨气”说的发展颇有贡献。
其次,就语言运用而言,前人对柳词的看法存在颇多争议。贬之者如王灼《碧鸡漫志》言柳词“浅近卑俗”,“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3]67褒之者如宋翔凤在《乐府余论》中言:“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虽多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3]2493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亦言:“耆卿为世訾久矣!然其铺叙委婉,言近意远,森秀幽淡之趣在骨。”[3]1627毋庸讳言,柳词中确存在少数较为露骨的艳情词,但这类词在《乐章集》中占比很少,何况同时期的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等均有类似艳情词作,故评价柳永不能仅以这类词为依据,而忽略了其他词作的价值。事实上,柳词中有较多清丽浑健之作,最为典型的当属《八声甘州》(对潇潇)中的“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11]101,被苏轼评为“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11]103;又如《卜算子慢》“江枫渐老,汀蕙半凋,满目半红衰翠”[11]201写羁旅行役途中的秋景,工巧清劲,蔡嵩云由是有“柳词胜处,在气骨,不在字面”[11]265的评价;再有《夜半乐》“凝泪眼,杳杳神京路。断鸿声远长天暮”[11]46,《雪梅香》“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应同”[11]265,《诉衷情近》“暮云过了,秋光老尽,故人千里。尽日空凝睇”[11]400等,这类词大多以萧瑟之言写羁旅行役,意境苍凉寥阔,感情凄婉沉郁,郑文焯评柳词“长调尤能以沉雄之魄,清劲之气,写奇丽之情,作挥绰之声”[1]27,殆指此类。
第三,在情感表达方面,宋人叶梦得曾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之论,这在反映柳词俚俗化、市井化的同时,亦可见出柳词表情达意之感染力,因此具有广泛传播的力量。柳永常将内心的愁苦悲情融于词中,通过一系列特殊的字词、意象、句式及叙事手法表达出来,这种凄美深情的情感诉说亦是其“骨气”之体现。比如《竹马子》(登孤垒荒凉)上片写初秋雨后词人登高临远,追忆从前的帝京生活,其中“孤垒”“烟渚”“雌霓”“雄风”这一组意象,将雄浑苍凉的艺术境界全然烘托出来,用词雅致考究。接下来由“一叶惊秋”四字感慨时光的流逝,引出时序变换中词人的悲秋情绪,“览景想前欢”将全词由写景向抒情过渡,为进一步的抒情打下前奏。下片写自己登高凝伫,感慨“新愁易积,故人难聚”,充分流露出对朋友诚挚深刻的思念,紧跟的“销魂无语”四字形象地表现出离愁无法排遣的精神状态。接下来词人将霁霭、归鸦、角声、残阳等景象融合一气,以情景交融的方式来烘托和强化离情别绪。最后以“南楼画角,又送残阳去”结尾,更是意味深长,将离别之苦、思念之情发挥到极致。除以上所举的登临羁旅之作外,柳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富于变化的情感表现方式,在其市井风情词、相思怀人词、咏物抒怀词中均有充分体现,这种雅俗互融、独具匠心的抒情艺术展现了其骨气高健的一面,极具典型化意义。因此,郑文焯评柳词“浑妙深美处,全在景中人,人中意,而往复回应,又能寄托清远”[1]41,他正是从这种情感意绪的升华角度,看到了柳词浑妙深美的“骨气”所在。
另外,就艺术风貌而言,郑文焯常将柳词与唐人气韵相联系,他曾引用张端义“诗当学杜,词当学柳”的评价,将杜诗柳词并举,肯定柳词写景状物的真实豪宕;在评价《少年游》(长安古道马迟迟)时,亦点出上片意境雄浑辽阔,“晚唐诗中无此俊句”[1]32的风格特色。所谓的“唐人高处”,即是渗透在唐诗字里行间的清俊恢弘气象,如杜甫《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王维《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李白《越女词》“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无论是状辽阔之景、绘清幽之境,还是摹婉丽之情,都蕴含深远清绝的审美意趣。柳词在此方面与唐人风骨有相通之处,如他的《曲玉管》“陇首云飞,江边日晚,烟波满目凭栏久。一望关河萧索,千里清秋,忍凝眸”[11]247,《雪梅香》“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应同”[11]265,《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凭栏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11]436等等。叶嘉莹先生认为柳永“能写悲秋兴象妍”,就是注意到了在柳永的作品中,蕴含着能感发人之自然情感的兴象,这种兴象的使用,已不同于晚唐时期温庭筠、韦庄、二李、冯延巳等词人单一的客观景物描写,而是将词人本身作为抒情主体。可以说,柳词中兴象与抒情主体的建构,既继承了中盛唐时期写景抒情的真实可感,又凸显了词作当中隐含作者的存在,消解了词人与词中抒情主人公的疏离之感,是对晚唐五代词单一写景抒情模式的突破。这一艺术效果方向的拓展,有利于在“无我之境”中抒发“闲逸感喟之情”,从而达到郑文焯所说的“不得徒于迹象求之”的骨气清空的境界。
综上所述,柳永词的“骨气”体现在内容、语言、情感、格调及艺术表现诸多方面,虽不同于魏晋时期的慷慨任气,也不似盛唐时期的兴寄放达,但柳永的部分词作,不以一字一句的雕炼争巧斗奇,而是以真挚疏宕贯彻全词,保持了抒情的形象性、思路的完整性,达到高健情怀与清空的艺术风貌浑然一体的境界。从这一角度来看,郑文焯所言柳词“骨气雄逸,与徒写景物情事意境不同”[1]31-32,不可谓不恰切。
四、郑文焯对柳词作出“骨气高健”评价的原因
通过考察郑氏对柳永词的批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柳词中“高健”“沉雄”“清劲”的内容非常关注。经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印证柳词确有“骨气高健”的一面,而这一独具创见观点的提出,得益于郑文焯对柳永词的深入研读,那么郑文焯对柳永高度关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首先,郑文焯对柳永词作的高度评价来源于他们相似的人生经历,以及对柳永其人的同情与欣赏。郑文焯与柳永一样,均出身官宦世家,濡染家学,少时聪颖,有功名用世之志,但柳永至暮年才应“恩科”而及第,官至屯田员外郎而卒。郑文焯亦曾七次赴京,两度应恩科会试,皆不售。他在致朱祖谋的信中曾言:“《避暑语录》云:‘柳永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词人固甘于寂寞,而身后至无以归骨,亦可哀也已。”[1]42郑文焯面临同样屡试不第、晚景困窘的坎坷遭际,自然生出同病相怜之感,这是其推举柳永的情感基础。其次,郑文焯与柳永秉持相似的词学主张。两人均通晓音律精研乐理,柳词不事雕饰,情感真挚,表现手法疏宕流畅,这与郑文焯所处时期词坛的晦涩之风恰恰相反。在当时词坛“宁晦无浅,宁涩无滑,宁生硬无甜熟,炼字炼句,迥不犹人”[3]4625的创作观念下,郑氏意图通过对柳永的推崇,纠正浙西词派流于空洞和浮滑的弊病,实现“以空灵救晦涩”的词学理想。另外,郑文焯自身的文学观点与创作并不局限于一家一派,他曾在致张尔田的书信中提出“凡为文章,无论词赋诗文,不可立宗派”[1]217,并指出各派之间存在党同伐异、相互排斥的眼界狭隘问题。事实上,郑文焯始终秉持转益多师的词学主张,他在推举柳永的同时,亦给予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词人较高评价,这种涉猎广泛、超越立场局限的词学态度,无疑赋予了郑文焯更高的眼界,使他能够从词人词作本身的特点出发,对各家词人进行全面且精当的评价。
总体观之,一些词论家以“俚俗”“市井”评柳永词,其得在于指出了柳永词语言生活化、抒情直白化的特点,而其失在于将其词的俗与雅完全对立,是此而非彼。郑文焯对柳永词“骨气高健”的评价,向我们揭示了以“婉约”为代表的柳词,未尝不能具有峭健遒劲的骨架、冷峻秀拔的内在筋脉。“俗体”也可“高雅疏宕”,也可“清空劲健”,即二者是一对矛盾,却也可以统一。而二者统一的内在条件在于柳词的意趣、境界、手法之妙,在于其“如怨如慕,可兴可观”[1]26,即以情感和文化内核来驾驭字面,这样“直白之语”也可蕴含清高劲健的力量,这是认识柳永词的关键。
综上,郑文焯以“骨气高健”为标准来评价柳永词,是“骨气”这一文学批评范畴在晚清的丰富和发展,突破了宋代以来对柳词的传统认识,赋予了其新的内涵。从郑氏所论可知,其主张的“骨气”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文人所标榜的“骨气”,他强调词作的“清空疏宕”“形气存神”“切情附物”,即是把“骨气”与使事用典、情感表达、写景状物融合起来。他对柳永词的认识没有受到派别与传统成说的拘囿,而是融合了浙、常两派的精髓,融入了自己的思悟,其所论的深刻之处,对后世研究柳永词无疑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