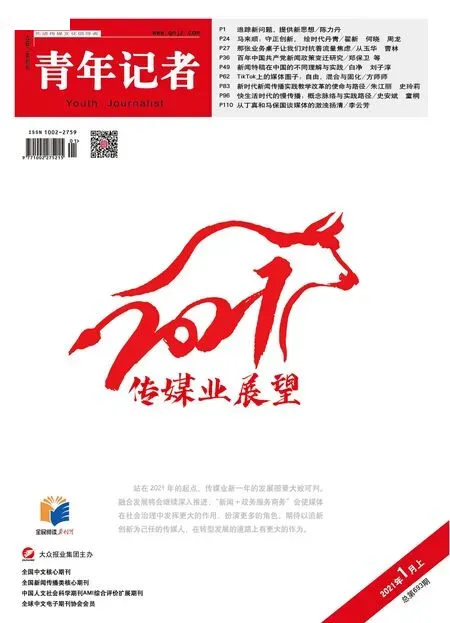那张业务桌子让我们对抗着流量焦虑
——访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从玉华
曹 林
《冰点周刊》是中国青年报的王牌周刊,成就了几代名记者名编辑,堪称新闻界的传奇。特有的选题关怀、标题质感和写作风格,能让读者从新闻信息海洋中一眼找到“冰点”特稿。作为“冰点”基因的“老汤的味道”,到底是怎样的味道?这种基因在代际传承中有哪些“守”哪些“破”?这个新闻精英群体拿什么面对流量的冲击?中国青年报编委、高级编辑曹林本期“茶座”邀请了《冰点周刊》主编从玉华,聊聊“冰点故事”和“冰点人”的写作方法论。
曹林:从老师是从驻站记者开始做新闻的,中国青年报不少名记者名编辑的新闻从业生涯都是从驻站开始的,比如现在的张坤书记、毛浩总编辑、刘健社长,退休的李大同老师、谢湘老师,等等,形成了传统。您觉得驻站经历对您现在的新闻观、采访和写作有哪些影响?
从玉华:我刚刚入职的时候,报社要求每一个新人到地方记者站锻炼一年,这个制度很好,真是冰与火的历练。我在广西和湖北驻过站,刚驻站时,像掉进了信息的汪洋大海:新闻太多了。在武汉,我有两个小灵通和一个手机,有时三个同时响起来,我都不知道该接哪一个,太忙了。北京的电话也不断,报社的经济、教育、法制版都找你写稿,好像千线万线都从自己这个小针孔穿过的感觉。
只能判断什么是最重要的选题,我的优先级是什么,对新闻公共性的理解就慢慢建立了。比如,在广西这样一个号称中国最“甜”的地方,我关注甘蔗糖业亏损、荔枝大丰收农民却在田里哭这些“甜”背后“苦”的问题。像筛子一样筛选新闻,慢慢练基本功。
刚入行,会有让世界更美好的“无冕之王”的感觉,然后很快发现报道几乎不能改变什么。当时采访也不职业,我犯过不少错,比如莫名地仇富仇官,人家说什么,都要怀疑三分,天然地同情弱者,弱者说什么都相信,采访起来哭得比对方还凶。后来年头长了,明白新闻是灰色的,人物是复杂的,有时候需要“上帝视角”、零度情感、人在现场的“现场抽离”,采访姿态要平视,你大我大,你小我小。对弱者廉价的同情,是对对方的二次伤害。
现在,我越来越感恩采访对象,他凭什么“赐予”你他的故事,为什么他要把“伤疤”揭开给你看,我真正开始懂得“尊重”。受访人原则成了我的第一原则。
曹林:武汉大学的新闻教育对您有什么影响?哪些老师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悔学新闻吗?现在流行其他专业背景的人做新闻,好像更有专业优势,新闻科班出身却常常成为劣势。
从玉华:武汉大学的樊凡老师,我印象很深刻。他治学严谨,又很和蔼,我记得有一次写武汉码头文化的小论文,樊老师把我叫到他家,和我说这篇论文怎样写才能更深入。他家很简朴,讲着讲着,天花板上掉下一小块墙皮,一会儿又掉一块,他讲得很投入,一副对“毛毛雨”不在乎的样子,又迂又真。后来,他去世了。我很后悔毕业了再没去看过他。
我喜欢新闻,一直都喜欢。以前我的同事说在中青报工作“一个月每天都很开心,只有发工资那天不开心”,差不多吧。今天早上,孩子出门,我在孩子的物理卷子上签字,写下:“不要太在乎分数,物理很美很阔,近之,习之,乐之,足矣。”我想,这里,物理换成新闻两个字,也是成立的。
干新闻真的感觉让人多活了五百年。每次听采访对象讲到深处,那种忘掉了自己四肢的存在,似乎只有自己踩踏进的“无人之境”的美好,让自己瞬间觉得又赚了十年。
新闻可以说是浅学,也可以说是深学,入门浅,但是越走到后面越觉得难。好的作品是一个人知识结构、性格、认知、调查事实内核能力等的总和,所以一流的作品是结晶物,但溶质析出的过程漫长而又痛苦。
现在有的高校取消了新闻本科教育,专注研究生教育,我认为有合理性。大学里,用专业打底,再收口新闻,这样编的筐肚子大,业界很欢迎学者型记者。就像关羽是铁匠,他打过各种武器,才能“青龙刀盖世无双”。
曹林:《冰点周刊》的版面人格被概括为“矜持态度、精致阅读”,可否解释一下“精致”与“矜持”?我记得,您在一篇演讲中提到过,“冰点”要做香奈尔一样的报道,而不是班尼路。“冰点”作为一个现象级的、符号般的传统新闻作坊,经历了很多,几任主编的专业气质也不一样。作为“冰点”现任主编,您怎么看待这种风格的变化?坚持了哪些作为“冰点”基因的品质?从李大同、卢跃刚、杜涌涛那里继承了哪些、改变了什么?
从玉华:“矜持态度、精致阅读”是“冰点”的前辈杜涌涛老师提出来的,我个人理解,“矜持”可能指对新闻不偏不倚、温和克制的态度,“精致”指文本的精致。好的新闻的审美要求是很高的,它不是易碎品,生命不止一天,它是历史的底稿,是要留一百年的。即使我们死了,它还在,当然要好好待它。
“冰点”的前辈李大同、卢跃刚、杜涌涛,在我心里都是高峰一样的存在。他们是“冰点”的脊骨。我不过是“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更像是“守夜人”吧。
这些年,尽管有人说“冰点”“软”了,变味了,但我们觉得传统的基因,那锅“老汤的味道”还在,“冰点”的人文气质、公民公心公益的大公精神、对丛林法则之外的叙述,在我们的作品里从来都一以贯之。我们在不放弃社会“焦点”“热点”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尚不那么显著的人群和事物,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想法,更多地发表一些人所未知的真知灼见。
“冰点”很像我成长的鱼米之乡,那种原始的生命力绵延不绝,在它面前,我就是庄稼人。
当然,我理解,“冰点”最大的挑战不是“守”,而是“破”,改革,坚韧地成长、保持团队可持续的生产力是我们的眼前事。我很怕自己是新时代的旧人,可我有时候就是。
曹林:常常有人觉得“‘冰点’胆子很大”,很多别人不敢碰的题材“冰点”敢碰,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同行评价和读者期待”的?
从玉华:讲“胆子大不大”显然不是当下很理性的表达,我们鼓励记者每接到一个选题都用尽全力,你是不是实现了最大半径的闭环采访,你有没有在通往事实内核的隧道里再多铲一铲子,你是不是读完了相关主题的几十万字论文,你是不是为这篇稿子搭了最大面积的龙骨架……稿子深、阔、硬,文本优,是我理解的“胆”。
同行评价和读者期待对我们很重要,但不是我们的“指南针”,他们会微调我们的“针”。
曹林:焦虑和转型似乎是当下传统媒体人的主流心态,流量似乎成为评价很多作品成功与否的核心标准,“冰点”有流量焦虑吗?“冰点”不缺高流量的作品,比如《我站立的地方》《湍流卷不走的先生》《无声的世界杯》《永不抵达的列车》等,在“冰点”编辑部,流量算老几?
从玉华:有啊,尤其是开始很焦虑,万分恐惧成了“十万分恐惧”,怕落后,怕变成“老家伙”。不过经过这几年新媒体的冲击,我们越来越有做深度内容的定力了,我们发现好内容,尤其是万字八千的长文,不在乎什么平台、什么排版样式,只要它足够好,就能破圈,就能被看到。
说实在的,我们有时候也判断不好什么稿子会成为流量王,比如《那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我们报纸发了一两天后才推送公号,没料到会成为现象级作品;《湍流卷不走的先生》也是,一个静态的人物稿,丝毫没有爆款元素;《我站立的地方》,在公号上2万多字……慢、静、长都是公号爆款指南提醒避险的“雷”。我们就是日复一日的庄稼人,每周都在发稿,很难说哪颗豆子会长得最大。
前几年,人员流动大,新媒体很热,我们还在海运仓的老楼办公,我们把会议室那张油漆斑驳、腿都不齐的老桌子称作“新闻业务漂流桌”,每周大家在这里尖锐地批评、自由地讨论业务,互撕头花。不过,离开桌子,大家就闷头抢吃火锅,肉还是红的就被夹走了……在最难的那几年,那张业务桌子让我们对抗了些许流量焦虑。以至于好几年我们的部门工作群叫“最纯净的冰点进行时”,真是矫情啊,后来终于被一个忍无可忍的直男同事把“最纯净”几个字删了。
现在我们搬到了新楼,桌子很新,阳光房的会议室很美,叫“光合空间”,工资仍然不高,有人走有人来,每周开会,我们会提到流量,但我们更在乎这个桌子边的人怎样评价。
曹林:“冰点”选题很有特点,从热事件中找冷视角,“冰点”标题很有特点,外界评价称有一种“性冷淡风格”,高冷。比如《湍流卷不走的先生》《永不抵达的列车》《回家》《拐点》,不像很多标题党那样充满狰狞的欲望,《湍流卷不走的先生》在转载时就被改成了艳俗的“她是中科院最美的玫瑰,是中关村的明灯;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您能否分享一下“冰点”的标题观?
从玉华:“冰点”的稿子在报纸上的标题确实比较“性冷风”,一篇长文,我们取标题时,总希望有一种抽离,这种抽离多数不是信息,而可能是意象、态度、双关词等,总之,我们努力把思考塞在标题里,不那么让你一眼看到底。
比方说,《永不抵达的列车》,永不抵达是一种抽象;《湍流卷不走的先生》,湍流是一种意象;《回家》,回家是一个具体的个体的回家,也是当时整个国家的情绪:关注灾区每个人回家,“回家”就是当时的最强音。
最近我们写了一个长得像马云、名叫范小勤的孩子,从8岁开始被经纪公司带到外地,上直播做各种活动,两个学期没上学。从定下选题,我就想好了标题,“我是范小勤”或者“寻找范小勤”,把范小勤这个完全不知名的名字放进标题,表达我们的立场:请尊重这个孩子。
做公号标题,大家一致认为要把小马云加上,还是得“蹭”。在纠结中,我们做了“我叫范小勤,不叫小马云”。我承认,我是两栖动物。
有时公号标题很好,报纸标题寡淡,比如《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是公号题,报纸题是《教育的水平线》,两个题看一眼就高下立判,命运、改变、屏幕,这样的词显然更有吸引力。所以,我们的标题不故意冷,也不故意热,还是看平台读者的属性,看我们最想传递什么。
曹林:您曾在演讲中谈到过,一个再广大的悲伤,比不上一个小人物具体的悲伤。“冰点”在操作时怎么避免“具体”变成一种“琐碎”,从而让“具体”与“广大”产生勾连,与公共情感产生巨大的共鸣,成为记录某个事件或某种现象的现象级作品?
从玉华:在选题层面,我们会判断这个“具体”是不是“琐碎”,这个“小”背后有没有“大”。每周选题会上,我们反复讨论一个题的角度,延展度,有没有大空间,这个新闻的贴合面,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人,怎么让新闻的这个“点”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在社会坐标里,这个“具体”有没有“路标”意义。
比如,范小勤是个“具体”的人,但他背后有时代的各种大浪:流量、中国最富的人、最底层的残疾家庭、未成年人保护……这些大浪要不动声色地表达,克制地记录,只述不评,“呈现、呈现,还是呈现”。我们看起来在写这个孩子,其实在写成年人,我们看起来在写近景,其实是在写远景……它像油画一样,人物身后有一层层的底色。
我尊敬的前辈卢跃刚曾说:“所有的写作都是在写背景。”那时我不懂,现在我渐渐开始懂了。
谷雨写过一篇《一个名字叫“喂”的女人》,讲一个不会说汉语的布依族女人寻亲回家的故事,当时我们也谈论过这个题,觉得太“个案”了,寻亲故事太多,她的事情不新奇,布依族语言和多少读者贴合呢?好像太冷。后来,记者张月表示,她领下这个无人认领的题,是因为她在国外待过,那种语言不通造成的隔膜感、疏离感,她深有体会,她想去写。当我听到张月说隔膜感时,一下子就击穿了我,是啊,这是人人都有的“病”,是时代病。
曹林:“冰点”编辑部中的人员多是名校毕业,出现了很多名记名编。近年来人才流动好像比较大,您怎么看待媒体的人才流动?进入“冰点”编辑部是一种职业荣耀,上“大冰”才能完成一个“冰点”记者的成名想象,“冰点”对记者有什么标准或门槛?
从玉华:也许现在不是成就名记者最好的时代,但确实有年轻记者因为一两篇现象级作品被圈内外看到。我们也总是开会时敲打,“记者的名字永远在新闻作品的后面”,写作不要功利,要沉下去,不要抱着成名成家的想法去写稿,也不要有偶像包袱,写完了,写下一篇,再下一篇。
记者的成就感哪里来?还是得自洽。钱少活儿苦,外面的诱惑还那么多。流动性大再正常不过了。但正是这种来来往往,把真正喜欢新闻写作的人筛出来了。留下来的人在一起,不说新闻理想了,还经常自黑,像共有了一个密码,不说自明,一种土嗨。
我们招记者没有什么量化的标准,人是多神奇的生物啊,三观大概合,能写好故事就可以了。
曹林:作为名编您的选题判断很厉害,作为名记您常能写出“深度好文”。2020年武汉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后,您写的那篇《高高低低的肩头撑着城》,感动了很多人,成为一些中学生的必读文章并进入考题。您在武汉生活过很多年,能否分享一下这篇佳作的写作心路和心得?
从玉华:您过奖了。相比前方武汉一线记者的报道,《高高低低的肩头撑着城》只是我在后方编辑部的一些感慨,实在算不了什么,一线的新闻报道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我可能作为湖北人,对武汉那座城市,那里的人,个人情感更饱满一些,下笔有情吧。其实,我害怕煽情、滥情。
曹林:“冰点”也在转型,拍电影,做短视频,与新媒体平台合作,您觉得转型成功吗?有哪些转型经验值得与同行分享,尤其是传统媒体做深度报道的同行。
从玉华:我们的转型还远远谈不上成功,还在笨拙地跑。
我本人不是很锐利、极富创新精神的人,把我踩在泥巴里,我会长出来,这我不怕,但长成很高的树,看到很远的风景,我担心力所不逮。我很怕我个人的原因影响了品牌的转型,所以我尽可能鼓励年轻人去做,掉下来我这个胖子当肉垫,鼓励大家尝试新的写作,打破固有的文本习惯,不要被“老汤的味道”所限,也鼓励新团队做纪录片,有的尝试还不错,也得过一些奖。
不过确实谈不上什么经验,各种被锤,正酸爽呢。不过韧性很重要,就像小说《白鲸》里一条带着标枪和脓疮的白鲸,在大海里生活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