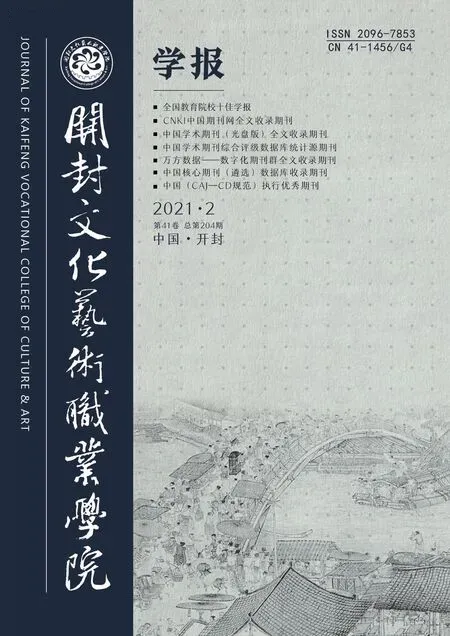失败的自我救赎:空间批评视角下的《疾病解说者》
穆 歌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疾病解说者》是美国印裔女作家裘帕·拉希莉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一经出版就颇受好评,并荣获了2000 年的普利策奖。小说集包含9 个故事,每一篇都堪称精品,本文选取了其中的同名小说《疾病解说者》作为研究对象。这篇小说讲述了达斯太太在旅行途中偶然得知导游卡帕西的工作是疾病译解后,向其倾诉了不幸的生活以及隐藏多年的秘密的故事。
“空间就是产品”[1]26是列斐伏尔在其专著《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其强调了空间是可以被生产的以及空间具有极大的社会属性。生产的空间“是思想和行动的工具;除了作为生产手段之外,它也是一种控制的手段,因此也是一种支配权力的手段”[1]26。
自我在哲学中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体验说”。亚里士多德认为,自我是在个人体验基础上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救赎。随着文艺复兴的发展,人逐渐成为世界的中心。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将自我定义为会以意识思考的东西,能感觉到快乐或痛苦,是一种与物质相对的精神实体。在心理学上,弗洛伊德提出自我(ego)是人格结构中的行为主宰者“我”,由本我发展而来,受超我的监督,具有协调人格结构各部分关系的功能。但也有心理学家认为,弗洛伊德的自我(ego)并非完全的自我(self)。荣格认为,自我(self)是个性的全部,包含自我(ego)。威廉·詹姆斯认为自我(self)包括“物质我”“社会我”“精神我”以及“纯粹的自我(ego)”[2]。综上,自我(self)是包含所有个性在内的精神实体。
本文将从空间理论切入,探究达斯太太在家庭空间中被压抑的自我、文化空间中扭曲的自我以及社会空间中的自我救赎。
一、家庭空间中被压抑的自我
“家庭首先总是以一种空间的形式出现”[3],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家庭空间与公共空间不同,是个人私人空间的一部分。因而家庭空间相对较为封闭,人在家庭中不断接受着父母、伴侣和孩子带来的幸福或痛苦。在拉希莉的作品中,“家庭既是与个人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单元,也是心理层面的归属感”[4]。家庭空间作为一种权力统治手段,控制着达斯太太的思想和行为。她在家庭空间中遭受着父母的权威话语、丈夫的精神压迫以及生养孩子带来的肉体负担。
达斯太太是在父母从印度移民美国之后出生的,二代移民的身份使得父母成为其最信任和依赖的人,但她“从没跟他们十分贴心过”[5]66。谈到离世的父母,达斯太太并没有多少怀念,反而在潜意识中强调父母的权威,如从年少起父母就为自己安排好了和拉兹的婚事,自己也从了父母,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父母对子女在话语上的权威。
达斯太太在婚前被父母所束缚,在婚后则为两性关系所统治。达斯太太和拉兹结婚时还不满20岁,过早的婚姻生活让她“整日疲累不堪”[5]66。婚前在大学里,她把时间都花在了拉兹身上,因此交心的朋友没有多少;婚后的生活充满了争吵和矛盾,她找不到人倾诉,更不用说开导和安慰了。而拉兹却只顾着教课,没有多余的心思放在她身上,达斯太太陷入了婚后焦虑,“拉兹倒觉得没什么”[5]66。八年来,她每天都承受着因丈夫的冷漠和无视而带来的无尽的痛苦,挣扎着在家庭中存活,压抑着内心真实的感受。或许是想要逃离封闭的家庭空间的束缚,“仿佛她一生都在马不停蹄地旅行着”[5]49,借此机会让自己暂时得到一丝喘息。
此外,孩子也是在家庭空间中控制和束缚达斯太太的工具。罗尼出生后,玩具扔得乱七八糟,“走路须踮着脚尖,坐一坐都得小心扎着”[5]66;达斯太太耳边从早到晚充斥着孩子“挣扎着想从学步车里爬出来的哭闹声”,每天照顾孩子忙得四脚朝天,她逐渐“变得烦躁、焦虑,人也长胖了”[5]66。其间她还婉拒了大学同学约她去逛街的邀请,“以至于后来人家再也不来找她了”[5]66。达斯太太的人际关系因为孩子断得一干二净,整天被束缚在家庭中。拉兹“倒还是和从前一样”,回到家“一边看电视一边把罗尼抱在腿上颠着玩”[5]67,沉浸在工作和孩子的喜悦中,却从未给予达斯太太一丝关怀。
家庭空间“既是家庭的宅所,也是家庭的枷锁。它既让家庭成员陷入绝望的漫漫黑夜,也让家庭成员被狂喜所汹涌地撞击”[3]。达斯太太在家庭空间中遭受的疲累和烦躁没有地方发泄,只能被压抑着的痛苦所蚕食。父母去世,没人帮忙分担照看孩子的压力;生活的无望没有贴心的朋友可以倾诉;丈夫也没有给予应有的体贴和关注,导致夫妻之间越来越冷漠和疏远。对于达斯太太来说,家庭像是一个枷锁,使之陷入绝望,但出于责任又不能抛弃家庭,只能在自我压抑中等待救赎。
二、文化空间下扭曲的自我
文化空间是不同文化之间交流、冲突、融合的空间。米歇尔·福柯将其视为“多层次历时性的积淀”;杰克·格林认为文化空间是一种物质空间或社会空间,由拥有这一空间的特定群体的一整套相关行为和生活模式来定义;罗伯特·杨认为文化空间是一种文化能够习得并得以传承的框架[6]。文化作为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其产品本身具有空间性,文化空间强调发展演变的历时性。
达斯太太作为美国印裔的第二代移民,在美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对抗冲突中挣扎,想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却始终未能逃离传统的处于边缘地位的印度文化。印度文化主导了达斯太太的前半生,等待救赎的自我逐渐变得扭曲。
卡帕西在旅行途中看到达斯夫妇间的不和,认为他们可能是“很糟糕的一对儿”[5]56。卡帕西是土生土长的印度人,其婚姻也是父母包办的,儿子的意外去世使得夫妻间的感情日渐冷淡,“吵嘴、冷漠、长时间无话可说”[5]56,种种迹象此时正发生在达斯夫妇身上。在印度,大多数婚姻都是父母一手包办的,这是当地一种传统的婚姻制度和风俗习惯。但是,在美国出生、接受美国文化熏陶的达斯夫妇也未能建构自由的婚恋观,最终接受了父母对其婚姻的包办。拉兹和达斯太太一样,也是印裔美国人,相同的文化身份唤起了双方父母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因此,有意撮合各自的孩子。达斯太太现在想来“总觉得多少是有点像是安排好的”[5]66。父母传统的早婚观念以及双方相同的文化身份使得达斯太太过早地进入婚姻生活,焦躁和不安笼罩着她,精神压力无处发泄。
印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在当时美国主流文化中属于由社会建构起来的边缘群体,地位较低,相互抱团取暖是一种寻求自我以及群体安全感的最佳方式。因此,拉兹在得知一位来自旁遮普的朋友要到美国参加工作面试时,跟达斯太太说想留他在家中暂住一周,而“她一下子肺都气炸了”[5]67。达斯太太不仅忍受着因拉兹文化身份认同带来的不便,而且承受着男权主义对女性的压迫。男尊女卑的文化环境剥夺了夫妻之间的平等交流,达斯太太也同时失去了拒绝的权力,只得默默接受拉兹的提议。也正是朋友的到来使得达斯太太在家庭空间的重压下找到了发泄口,对家庭的失望使得达斯太太对于朋友的挑逗行为“没有任何反抗,他们手脚利索、默然不语地做爱”[5]67。私生子波比的降生并未让拉兹对孩子的身份有丝毫怀疑,达斯太太把这个秘密隐藏了整整八年。朋友后来结了婚,两对夫妇每年都会互寄贺卡并附上一家人的照片。“他不知道自己是波比的父亲,一辈子也不会知道的。”[5]67达斯太太独自一人背负着秘密,“被它折磨得痛苦不堪”[5]68,逐渐产生了可怕的冲动和想要“把一切都抛掉”[5]68的病态心理。旅途中,达斯太太在向卡帕西倾诉之后询问自己是不是病态,并希望他为自己诊断、治病,她内心知道自己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并等待着某个人把自己拉入正常的生活轨道。
达斯太太的父母遵循传统对其婚姻的包办是导致其自我压抑和扭曲的直接原因;而达斯夫妇移民的文化身份使得拉兹邀请朋友暂住家中,则直接导致了达斯太太和朋友的偶发性出轨行为,这使得其内心的压抑情感爆发,并形成了想要把一切抛弃进而获得解脱的扭曲心理。印度的传统文化禁锢、束缚着达斯太太,虽然其接受了美国的教育和主流思想,也没能改变父辈和自己骨子里对印度文化的认同感。
三、社会空间下的自我救赎
社会空间是指“社会的空间,社会生活的空间”[1]35。社会空间是由人的日常生活行动建构起来的,它的本质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互动关系,空间的生产就是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7]。
达斯太太和卡帕西的互动与交流是其在社会空间中寻求救赎的表现。达斯太太在与卡帕西交流的过程中得知他除了导游外还有另一职业,即疾病译解,因为当地的医生不会讲古加拉提语,所以请他过去帮病人做翻译。达斯太太对其做译解的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他可以治疗自己的病态心理。一个“连三十岁都不到,就已经不爱丈夫和孩子,失去了对生活的眷恋和热爱”[5]68的女人向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倾诉了自己痛苦的婚姻生活以及隐瞒多年的秘密——波比不是拉兹的亲生儿子,而是她出轨后的私生子,并希望从卡帕西那里获得理解和安慰,从而走向自我救赎。
“八年了,八年来我一直在忍受煎熬。我盼着你能让我感觉好点,讲一些宽慰我的话。”[5]68当达斯太太向卡帕西诉说深藏多年的秘密时,卡帕西先生心情沉重,尤其是当他想到拉兹时,“这种沉重感就格外加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5]69。卡帕西的反应表现出他对拉兹的深切同情而无视达斯太太的感受。他站在男性的立场上心疼拉兹,妻子出轨还生下了私生子,被蒙骗了八年,一无所知。他认为达斯太太与其他来到诊所就医的患者不同,没有“目光呆滞神情绝望”的样子,她多年的煎熬只是“普普通通、鸡毛蒜皮的小秘密”,为她疏解痛苦“像是受到了侮辱”[5]69。
在卡帕西听到达斯太太用“浪漫”一词来形容他的译解工作时,他感觉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重视,获得了巨大的存在感,并被达斯太太所吸引,一直寻找机会要和其独处。但是,终究达斯太太对于卡帕西来说只是性的吸引而非心灵上的交流,像是利用达斯太太来疏解妻子对自己的冷淡,因此两人沟通的失败有其必然性。
达斯太太和卡帕西先生属于社会性别中的两个对立面。性别的不同导致双方难以站到彼此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因此,当卡帕西听到达斯太太的秘密时,体会不到其多年的痛苦,只是从男性的视角上问达斯太太“所感到的,真的是痛苦吗?还是心有愧疚?”[5]69卡帕西在其潜意识中认为男性在社会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女性是男性的附属物,女性做错事情之后只能对对方怀有愧疚感而不能有其他的想法。达斯太太听到卡帕西的回答,“转过头来,眼含怒意”,之后却“停嘴不说了,她打开车门,顺着山路就往上走”[5]69。两人交流的失败意味着达斯太太寻求救赎的希望已然不复存在,她只得重新回归家庭,继续压抑自我。
小说讲述了两对不幸的夫妻,而作者在小说结尾选择让两对夫妻中的一男(卡帕西)一女(达斯太太)尝试进行交流,是想要把夫妻间的隔阂代入陌生关系,观察是否随着关系的改变,两者之间的交流可以顺利进行,但最后沟通的失败凸显了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状态,而男性总习惯于把女性看作附属物,两性关系的不对等是二者交流失败的根源。
达斯太太自我救赎的失败是其在家庭空间、文化空间以及社会空间中相互作用的结果。家庭空间中父母的话语权威、丈夫的冷漠以及生养孩子的艰难使得达斯太太产生了自我压抑的心理状态;文化空间中二代移民的文化身份和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让达斯太太从自我压抑走向自我扭曲的病态心理;社会空间中与卡帕西的沟通障碍导致了达斯太太渴望得到自我救赎的失败,最后只得重新回归家庭,继续压抑和隐忍。因此,女性如何消解心理疾病,寻求真我和自我救赎应该重新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