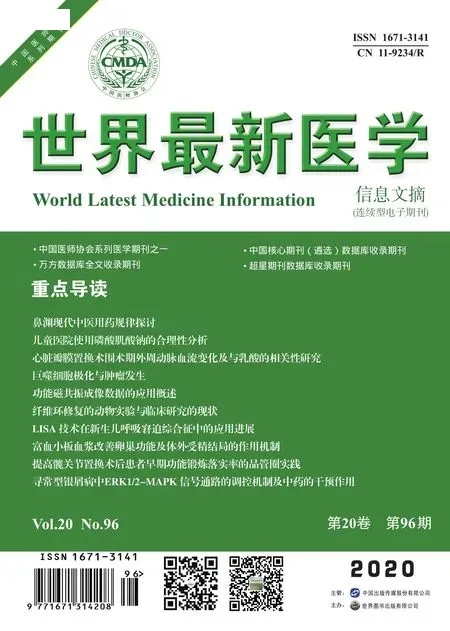余尚贞异病同治乌梅丸
向蕾,黄卓,周小琼,林东桥,练景灏,余尚贞
(1.暨南大学,广东 广州;2.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3.暨南大学附属医院江门市五邑中医院,广东 江门)
1 异病同治
“异病同治”是祖国医学所特有的临床思维模式,首见于清代医家程文囿的《医述》:“┈┈有时同病须异治,有时异病须同治,而同一病的各个阶段治法又不同。”但这一独创性的临床思维模式早在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已经充分展现。吴氏[1]等为研究“异病同治”的适用条件,将《伤寒论》中同一方用于治疗不同疾病的条文进行总结分析,得出的结论为不同的疾病,若其核心病机相同,则治法相同;若其病因、病位或者脉象相同,治法也相同。临证中如何灵活应用“异病同治”?董氏等[3]指出,只有“异病同证”才可同治,“异病同治”的基础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辨病是前提,辨证是核心。只有首先辨清疾病才能知道疾病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确定该病的基本治法;只有辨证准确才能抓住疾病现阶段的核心病机,随证治之;两者相结合才能取得良好的疗效。“异病同治”对当代医家诊治疾病有什么实际意义呢?陈可冀[4]院士认为当代临床实践中应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提出了“病证结合”的学术思想。临床上有很多西医诊断明确的疑难杂症,而现代医学无治疗手段,或疗效不明显。中医治疗则不拘泥于一病用一方,一方治一病,不同的疾病即便症状迥异,只要现阶段的核心病机与经方的病机一致,便可用该方治疗,中医临证更灵活,往往能取得西医无法达到的疗效,中西医结合“异病同治”是一大趋势,能让中西方医学发挥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优势互补,更有利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2 乌梅丸
《伤寒论》:“┈┈蛔厥者,乌梅丸主之;又主久痢。”乌梅丸最初用来治疗蛔厥和久痢。而柯琴认为:“乌梅丸为厥阴病之主方,非只为蛔厥之剂也。”陈修园在《金匮要略浅注》中说:“肝病治法,悉备于乌梅丸之中也。其味备酸甘焦苦,性兼调补助益,统厥阴体用而并治之。”指明乌梅丸亦为厥阴病主方。清代叶天士将乌梅丸用于治疗痉厥、中风、暑病、虚劳等多种疾病,为后世乌梅丸“异病同治”提供了实践依据。现代医家更是扩大了乌梅丸的临床适用范围,将乌梅丸用于治疗脾胃病、胸痹、失眠、痛经、皮肤病等疾病[5],刘芳[6]等将CNKI数据库中所收录的乌梅丸用于治疗的临床疾病种类及中医症候进行频数分析,该研究表明乌梅丸治疗的西医病种达70余种,涉及各个系统,最多见的是消化系统疾病,如慢性肠炎和胆道蛔虫病;该研究涉及的中医病名达50余种,其中泄泻、痢疾、头痛、胃痛、蛔厥等出现频率最高;该研究表明乌梅丸现代临床中涉及的中医症候频率最高的为寒热错杂证(61.59%),其次分别是脾胃(肾)虚寒证(6.22%)和肝脾(胃)不和证(6.21%)。龙砂医学流派传承人顾植山教授认为,自然界中阴阳两气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且是有盛衰变化的规律性运动,这种规律性表现为周期性的“离合”运动,形成“开、阖、枢”三种状态,阴阳各有“开、阖、枢”,因此产生了三阴三阳六气[7]。《素问·阴阳离合论》:“三阴之离合,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说文》:“阖,门扇也。阴尽阳生之厥阴,如门户关闭。”厥阴为阴之“阖”,即是阴尽之时,由阴出阳,为阳之初生,如若阴尽阳生失常,阴阳转换不利,则会阴阳失调,出现寒热错杂等症候。由此可知,厥阴病病机为枢机不利,阴阳两气不相顺接,病象为寒热错杂。故临床上凡见以厥阴病寒热错杂为主证的病人,皆可选用乌梅丸。
3 厥阴欲解时
“欲解时”这一概念首见于《伤寒论》的六经病,其与时辰的对应关系是以《黄帝内经》中天人相应和昼夜更替、阴阳消长的理论为依据的。六经各自有其所对应的时间区间,在此时间区间内,本经经气相对旺盛,功能活动增强,抗邪能力增强,易于祛除病邪,则疾病易解,或者因经气旺盛,正邪斗争激烈而表现为症状加重。在临床上,大多医家更注重辩证、方证对应的研究和使用,往往忽视“欲解时”在临证中的作用。《伤寒论》中云:“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即是说凌晨1到7时为厥阴病欲解时所对应的时间区间,在临床上看到这个时段出现明显的证候或原有症候加重或减轻,可按厥阴病论治。故在临床上,但见在凌晨1-7时出现相关症状或原有症状明显加重的疾病,皆可选择厥阴病主方乌梅丸。
4 余尚贞主任医师运用乌梅丸临床思路
国医大师梅国强曾说“复用经方,便是新法”,经方的“异病同治”大大地扩宽了其临床应用范围,余尚贞主任医师师承梅老,深受其熏陶,以经方配伍严谨的特点,灵活掌握病机,辩证准确而择其方,异病同治,以精简之药物以达病处,故疗效显著。同时余尚贞主任医师近年来亦师承于顾植山教授,深受顾植山教授“五运六气”学术思想的影响,在临证中,注重抓住核心病机,辩证准确的同时,强调中医治病应重视天人合一,应注意及时观察气候变化及患者症状出现、加重、改变的相关时辰,将“六经病欲解时”灵活应用于临床上指导疾病的诊治。在临床上余尚贞主任医师常用乌梅丸,结合患者核心病机为寒热错杂及厥阴病欲解时(1-7时)发病或原有症状加重的特点,选用乌梅丸加减,在治疗失眠、胸痹、眩晕、腹痛腹泻、头痛、皮肤瘙痒及高血压病等多种疾病上疗效显著。现举余尚贞主任医师基于“寒热错杂”的核心病机及“厥阴病欲解时”理论临床上应用乌梅丸的验案3则,以为佐证。
4.1 失眠案
梁某,男,43岁,主诉:眠差3年余。患者3年前出现多梦,每于凌晨1-3时醒来,醒后难再入睡,伴有少许口干口苦,舌红苔薄白,脉沉。夜尿1-2次,有长期便秘病史。平素晨起时觉肩部寒冷。中医诊断:不寐(寒热错杂)。西医诊断:非器质性失眠。处方:乌梅丸加减,方药:生白术40g乌梅30g 干姜6g花椒5g当归12g黄连8g桂枝10g黄柏6g太子参30g淡附片10g(先煎)细辛3g。5剂,日1剂,分两次温服。二诊患者诉睡眠明显改善,偶尔仍凌晨1-3时醒来,醒后能入睡,守前方5剂巩固疗效。
按:本案患者每于凌晨1~3时(丑时)醒来,醒后难入睡,即是厥阴阴尽阳生之时功能失常,阴阳两气不相顺接,故患者还表现为口干口苦、肩部寒冷、舌红苔薄白,脉沉等寒热错杂之象。本病与乌梅丸证病机相符,且每于丑时易醒,符合“厥阴病欲解时”所对应时间段内发病的特点,故选方乌梅丸。
4.2 胸痹案
陈某,女,68岁。因“胸闷、心悸2周”来诊,2周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胸闷、心悸,常于夜间发作,烦躁焦虑,入睡困难,下半夜易醒,醒后胸闷加重,舌暗红苔薄黄,脉沉。平素手冷,汗多。既往有反复心悸病史30余年,2016年于我院住院,完善动态心电图等检查未见明显异常,诊断为“心神经官能症”、“焦虑状态”。中医诊断:胸痹(寒热错杂)。西医诊断:心神经官能症。处方:乌梅丸加味,方药:麦冬50g乌梅50g干姜6g黄柏10g 细辛3g黄连15g当归12g花椒5g桂枝10g太子参25g淡附片10g(先煎)。5剂,日1剂,分两次温服。二诊患者胸闷、心悸、睡眠有所改善,仍入睡困难,易醒,汗多,大便偏烂,舌仍暗红,脉沉。患者舌象提示火象明显,结合当年运气,戊戌年为岁运太火,故在前方基础上麦冬、乌梅加至60g,黄连加量至18g,桂枝减量至8g,干姜、附子减半。三诊时所有症状减轻,无明显不适。
按:本案患者胸闷、心悸,睡眠不佳,烦躁焦虑,病位在厥阴心包及厥阴肝二脏。且胸闷、心悸等症状常于下半夜发作,早醒,见入睡困难、多汗、手冷、舌暗红苔薄黄,脉沉等寒热错杂的特点,故余师抓住此病象,按厥阴病论治,方选乌梅丸,但由于患者火象较为突出,兼有阳不入阴入睡困难之象,除考虑“厥阴欲解时”的疾病日之节律,还应考虑自然界年节律及四季节律的影响,结合五运六气辨证施治,因而调整方中寒凉药与温热药的用量比例,灵活加减运用经方,辨证准确,故而取效。
4.3 眩晕案
焦某,男性,46岁(1971年12月出生)。主诉:反复眩晕1年余,再发伴眠差1月。患者近1年来反复出现头晕,伴有视物旋转、行走欠稳,无恶心呕吐,无耳鸣,无肢体乏力等,近1月来眩晕再发,伴有夜寐差,易醒,以凌晨零时许至2时多见,醒后难再入睡,精神倦,偶有心悸,双目发胀感。夜尿3次。次于外院及我院门诊就诊,给予营养神经药物治疗效果欠佳,今到工作室门诊求诊。刻诊见患者眩晕发作,舌红苔黄厚,脉沉弦。中医辨证:眩晕(寒热错杂)。西医诊断:眩晕查因。处方:乌梅丸,方药:乌梅40g淡附片5g(先煎)黄柏10g花椒5g干姜8g黄连16g当归12g桂枝8g 党参15g细辛3g。5剂,日1剂,分两次温服。二诊诉服药5剂后眩晕发作频率减少,夜寐较前稍好转,每于凌晨4时醒,醒后能再次入睡,精神好转,继守原方。三诊诉眩晕未发作,早晨6时左右自然醒,调上方用量善其后。
按:《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病机十九条“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患者眩晕伴双目发胀感,符合肝开窍于目,病位在厥阴肝,根据患者临床表现,也符合厥阴病寒热错杂的核心病机。每于丑时醒,而丑时正好是厥阴欲解时,给予乌梅丸治疗。服用乌梅丸后患者症状好转,早醒时间推迟到寅时,复诊续服原方3剂,头晕消失,早晨6时左右自然醒(卯时)。从该病例能看出余尚贞主任医师在六经辨证基础上运用五运六气,从《伤寒论》六经欲解时入手,拓展了经方运用途径。
5 总结
在临床上,余尚贞主任医师使用经方乌梅丸可谓是得心应手,认为乌梅丸可治疗具有“厥阴阖不利、阴阳两气不相顺接,寒热错杂、上热下寒,或症状在下半夜出现或加重”等特点的各种疾病,为进一步扩大乌梅丸临床使用范围提供了实践经验。余尚贞主任医师常说中医临床要回归经典,要上升到“道”的水平,道就是规律,只有掌握了这个“道”,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就如前文中的医案,在应用经方乌梅丸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应用中医独特的原创思维“异病同治”理论,不拘泥于乌梅丸为治蛔厥专方,掌握每个疾病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抓住疾病现阶段的核心病机“寒热错杂”,灵活应用“厥阴病欲解时”的疾病相关时理论,严谨选方,精准用药,直达病所,故而疗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