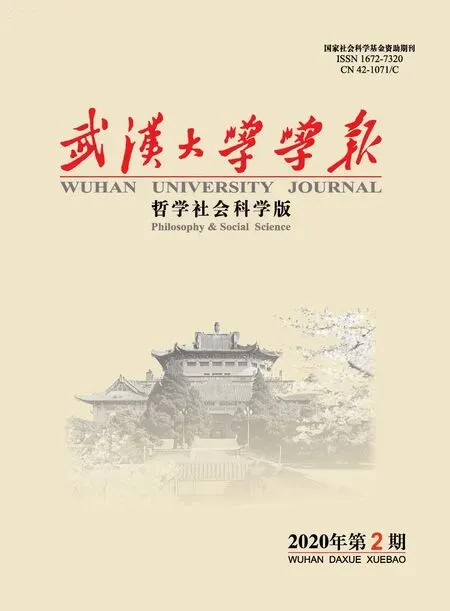楚辞与汉代骚体赋流变
易闻晓
对于辞、赋的关系、不必拘于《楚辞章句》以书定名及《文心雕龙》《文选》文体分类之囿,而当回归辞、赋合一的原初实情。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应当出脱《诗》学经义的立场。讨论楚辞和汉代骚体赋,必须确认《诗》《骚》异体与《骚》、赋源流,并就体制、篇章、句式、名物、语词等多方面展开整体性和历时性的考察。
一、楚辞与骚体赋
楚辞本是汉人对楚国屈原、宋玉等作品的通称,或以《离骚》代之,“及宋陈说之更定(《楚辞》)旧次,晁补之重编《楚辞》,皆以屈子首篇曰《离骚》,乃谓以下各篇为骚,而‘骚’之一名,遂由局而通”[1](P1)。宋黄伯思《校定楚词序》更泛称“屈宋诸《骚》”,谓“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2](P311),是仍汉人所称,屈宋不然。《史记·酷吏列传》言武帝时“(朱)买臣以楚辞与(庄)助俱幸”[3](P3143),《汉书·朱买臣传》亦谓买臣能言楚词[4](P2791),同书《王褒传》又言宣帝时九江被公能诵楚辞[4](P2821),虽不必屈宋之作,但必为楚产。及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以书定名,首题刘向所集,然向子歆奏进《七略》,只言屈原赋二十五篇,《汉书·艺文志》仍之[4](P1747)。刘氏父子与班固都视所集为赋,作者亦然,如汉初贾谊作《弔屈原赋》《鵩鸟赋》全拟屈辞而命名为赋,辞、赋为一,骚、赋无间,是谓“骚体赋”,迄清如戴震《屈原赋注》、马其昶《屈赋微》、现代姜亮夫《屈原赋校注》、沈祖绵《屈原赋证辨》、刘永济《屈赋通笺》都是如此。汉人论赋,亦辞、赋不分。《汉书·艺文志》以“不歌而诵谓之赋”,即诸侯卿大夫问对称诗,谓屈原作赋亦犹诵诗,但“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4](P1755-1756),屈、宋楚辞被确指为汉赋的源头。《离骚》长篇巨制,怨怼激发,广托名物,宋玉承之,而弃情叙物,由《骚》变赋,《高唐》等篇[5](P477)[6](P100-102),虽不定自题为赋,然其假设问对、散语铺陈、名物形容等方面都为汉大赋所本。屈辞则流为汉代骚体赋。
自王逸《楚辞章句》直到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以《辩骚》《诠赋》分论、萧统《文选》骚、赋别类,后二书在“文章”的总体系统中分类愈细,在下级的文体分类系统中,辞、赋或《骚》、赋固可分别,实惟分类层级所致。实际上辞、赋或《骚》、赋本来为一,这是讨论辞、赋或《骚》、赋关系问题的原点。回到这一原点,“楚辞”作为汉人对楚人诸作之称,刘永济谓“初非指曰文体之名”[1](P1),但楚辞产生之初,即以散语长篇而具“楚语、楚声、楚地、楚物”,迥异《诗》四言重章叠句的咏唱,不待汉人拟造,即已显示不同于《诗》的文体特性。惟以《诗》的形式限制不堪怨怼激发的情感抒发、不克长篇巨制的尽情铺陈,只能在体制的限定中“怨而不怒”[7](P15)“哀而不伤”[8](P2468),或者说如此淡定的“悠婉”[9](P1402)和欲言又止的“主文谲谏”[10](P271),适需重章叠句的咏唱。反之,则《离骚》等也惟以长篇巨制、散语繁复、名物众多、语词繁难适合怨怼激发的情感表现。
楚辞诸篇显见异于《诗》之内容和形式的鲜明特征,但并非遵循统一的定式。从情感特点来看,《离骚》《九章·远游》等篇怨怼激发的主体情感与《九歌》情爱代言的凄迷哀婉、《天问》带着理性的穷极追问、《招魂》极其险恶的环境铺陈不尽相同,《九章·橘颂》则非怨怒;从篇章结构来看,复杂无伦、重三倒四而非汉代拟作的整饬有序不同,《离骚》《招魂》《天问》长篇与《九章》《九歌》《卜居》《渔父》短制有异,《离骚》等多以主体情感抒发为主线,《卜居》《渔父》则以问答构篇;从句式结构看,《离骚》等以散语长句为主,《天问》《橘颂》等则多短句,《九歌》长短参差,各篇固有句式对举,但并不着意,总体上较为随意,本质上是散语入韵;从语词运用和铺陈来看,也有复沓繁难和简明流畅之别,前者如《离骚》,后者如《九歌》和九章中的《橘颂》;从名物铺陈看,则《离骚》等长篇名物为多,《九歌》《卜居》《渔父》及《九章》中的短篇名物为寡。凡此都是楚辞研究应当深入的方面,汉魏乃至其后的骚体拟作所取不同,或合而拟之。
“楚辞”除汉人之作外,不尽屈原所作,有的归属不明。《九章》诸篇,王逸注谓“屈原之所作也”[11](P120),但宋洪兴祖已疑《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非屈原所作[11](P181)[4](P3515),明许学夷《诗源辩体》疑《惜往日》《悲回风》为屈原后楚国唐勒、景差等人之作[12](P36)。《远游》王注亦谓屈作[11](P163),但清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凡例》谓此篇“杂引王乔、赤松,且及秦始皇时之方士韩众,则明系汉人所作”[13](P2)。按《史记·秦始皇本纪》,韩众为始皇时人[3](P258),或证《远游》中韩众非秦人[14],然“杂引王乔、赤松”并神仙道家之语,确实不类屈辞诸篇。又司马相如《大人赋》与《远游》大同小异,故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后记》疑《远游》为《大人赋》初稿[15](P380),然《大人赋》字词繁难,与《子虚》《上林》相似,而《远游》字词较《骚》亦属简易,当在相如之前,摹拟屈、宋所作,《大人赋》递相拟之。《渔父》一篇,《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用其文[3](P2486),并《卜居》一篇,王逸认为屈原所作[11](P176,179),但今代疑之,以二篇都为对话叙事体,与屈原他篇不类。《渔父》“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荀子》亦见[16](P28),当作于《荀子》之前;或疑宋玉所作,与旧题宋玉其他诸篇共为假设问对。《九辩》王注宋玉作[11](P182),今代多从。《招魂》一篇,王逸谓宋玉之作[11](P182),而司马迁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3](P2503),学界不能取决。又《大招》一篇,王注“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10](P216)。凡此疑义,都无确证,要之汉以前之作,不害汉人取效。
二、理想精神与乡风别调
汉人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扬抑不一,但都本于儒门经义。在此,区分孔学尤其是经学与“前儒学”是十分必要的,孔子“从周”述礼,其学至汉始为专尊。《诗》学经义也待汉儒训传,不必以后律前。屈原的人格理想维系于“帝高阳之苗裔”(《离骚》)的血脉和贵族精神,很难证实受到孔学影响,也以楚国乡风保持了不同于《诗》的“楚辞”特点。以此考察汉人对于屈原的评价,当有是非然否的大义判断。
班固《离骚序》引“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1](P49)。《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用其文[3](P2482)。班固则以“斯论似过其真”,谓“今若屈原,露才扬己,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11](P49-50)。刘、班扬抑不同,对于《离骚》的评价却都立足于《诗》学本位,然而出于经义的贬抑却正好显示屈原人格精神及其作品异于经义,为其附会经义的褒扬提供了相反的证明。按照汉儒的理解,屈原“露才扬己”,是为不谦;“忿怼不容”,情同犯上;“沉江而死”,不谓明哲。也许儒学的经学化不尽“原始儒家”的本义,但“独尊儒术”确是汉代君主的策略,而屈原以帝胄自许,以高洁自任,焉如陋儒谨守?披发而狂,长歌当哭,安如“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国家既没,宗庙不存,又何堪忍辱苟活,独善其身?其高洁纯粹而系于理想的人格精神岂以经学之义可以方之?以此度彼,诚“无异妾妇儿童之见”[11](P51)。屈原仿佛从远古三代走来,带着纯粹高洁的人格精神,亦如“老、庄、孟子所以大过人者”[11](P50),这正是执于经学化思想的后儒所不乐认同的,何况楚狂气性,异于鲁地崇礼,诚如洪兴祖所谓“士见危知命,况同性,兼恩与义,而可以不死乎”[11](P50),对于屈原来说,不是汉儒所谨守的君臣之义,而是宗庙社稷之于自身的帝胄贵族任持,正是死得其所。不必揣度屈原受到孔孟思想的影响,毋宁说战国时代的屈原具有老、庄、孟那样“大过人”的理想精神。
刘永济考《离骚》《九辩》《九章》称引尧舜禹汤,曰“美、善、修、仁、义、礼、忠、祇敬、中正、耿介、谅直、谨厚”,又考《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国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证明“上世帝王遗书,已流入楚域”,又子革能诵《祈招》逸诗,“可证《诗》《书》之教,传至于楚久矣”;又《国语·楚语》申叔时对楚王问,“教之春秋”“教之诗”“教之礼”“教之乐”“教之训典”云云[1](P9)。凡此“皆足为楚被六义之教之证”,而“屈子生战国之末季,涵濡文武周工之教已深”[1](P9)。这只是猜测,即使楚国可能受到“文武周工之教”的影响,但至少不是教化的中心区域,这种教化影响必不甚深,而且“文武周工之教”虽为孔教所取的资源,却尚未经过后者的规范化,可以归为“前儒学”的范围,汉儒则通过既有典籍的经学化,将远古以来的历史和相关资源据为己有,“六经皆史”[17](P1)实际上就是史皆六经,在被经学占有和改造的三代文化中,屈原的人格精神当然就被塑造和追认为经义的表现。
尤其是《诗》学的影响,无论是刘安《骚》兼风雅、班固“恻隐古诗”之说,还是王逸以至南朝刘勰对于屈原作品的褒贬,都是本于《诗》学经义的立场。《汉书·艺文志》谓屈原和荀子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4](P1755-1756)。王逸更称《离骚》为经,指其“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以乘鹥”,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11](P49)。不用说这都是漫无根据的比附,《诗·大雅·生民》记述周人始祖后稷的传说,屈原则只是自陈世系;乘龙遨游乃是上古人们共有的想象,佩饰则人之同尚;陈词重华情同梦呓,不过牢骚无极的陈诉,《虞书·皋陶谟》则是传说的君臣对话;“潜龙勿用”只是索隐的解释,与屈语无与;而“登昆仑而涉流沙”的“远游”设想,竟被附会于《禹贡》之事。所有这些都是上古文化的遗响,屈原的理想精神由此而来,然为汉儒据为经典,于是依经立义,就形成话语的垄断,汉儒所取用的资源在此,但反过来追认为儒学的经义,就从鲜活的理想精神变成了经学的说教。
历史或传说经典化的话语垄断在阐释学中形成了顽强的传统。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承接刘安、班固、王逸的经学立场对《离骚》进行了同样的评价:“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祇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谕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擿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18](P46-47)尧舜禹汤之陈,桀纣羿浇之讥,自是远古以迄三代文化的传存,不必附会“典诰之体”和《诗》之比兴,后者只是一种表现手法,《诗》可用之,何独屈辞不能?不必指为“同于风雅”。至于“托云龙,说迂怪”等四事,也明白显示《离骚》等篇“异乎经典”的独绝之性,都是来自遥邈的传说,惟以未受经学影响的原生形态,连通楚人的精神,成为《离骚》等篇浪漫铺陈的不尽资源,光怪陆离,不可方物,倘若擿而去之,全同风雅,何复《离骚》之存?洪兴祖驳之曰:“《骚经》《天问》多用《山海经》,而刘勰《辨骚》以康回倾地、夷羿弊日为谲怪之谈,异乎经典。如高宗梦得说、姜嫄履帝敏之类,皆见于《诗》《书》,岂诬也哉!”[11](P21)《骚》取于“谲怪之谈”,不必受《诗》《书》影响,《诗》《骚》共取于悠久的传说,显现“文学创作”的特质,却总被经义障蔽。
在某个角度上说,文学创制的形式和语言是决定性的,对于屈辞而言,文本几乎是唯一可资阐论的资源,尽管《离骚》总被附会风雅,但没有人能够在屈原诸作中找到《诗》的形式影迹甚至片言祖述。刘勰《文心雕龙·事类》谓“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18](P615),屈、宋自己何曾“号依诗人”?其引“古事”是在三代乃至以前,而一无取于《诗》者,这是确凿的事实,却在经学的独断中恒被遮蔽久远,视若当然。只有跳出经学的藩篱,才能说出原本简单的事实。晚清姚华《论文后编》云:
楚隔中原,未亲风雅,故屈原之作,独守乡风,不受桎梏,自成闳肆,于《诗》为别调,于赋为滥觞。[19](P29-30)
同步教学的产生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对个别教学方式的否定,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教学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我们从我国近代语文教育发展的两个方面的分析中可见一斑。
这是至为确切的论断,从屈原诸作的所有语句文词来看,确实“未亲风雅”,倘使“同于风雅”,则如同“桎梏”,安能尽情抒发怨怼激发?正是长篇巨制、散语长句乃至“江离、辟芷、申椒、菌桂、蕙茞”之楚物、“中洲、江皋、极浦、澧浦”之楚地,以及“顑颔、缤纷、婵媛、犹豫、容与”之楚语,凡此各个方面都以迥异于《诗》之形制、篇章、造句、名物、语词显示“未亲风雅”、出脱《诗》之“桎梏”而“独守乡风”、“自成闳肆”的“别调”异彩,经由宋玉弃情叙物的辞、赋转换,终成一代文学之盛,同时屈、宋之辞也在汉代以降“骚体赋”的摹拟流变中获得了久远的传承。
三、情理事与骚体分途
屈辞为抒情之作,宋玉作品除后人明标为赋者外亦然。情感的抒发是根本性的,其中所涉理、事被激越的情感驱使裹挟,篇章结构都随情感的抒发展开,往往杂乱无序,重三倒四。《离骚》或训“离忧”“遭忧”“离愁”,王逸谓“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衺,忧心烦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骚经》”[11](P2),或以屈原被谗放逐后作。清刘熙载《艺概·赋概》谓“《离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20](P88),其所“不变者”,就是情感的激荡,惟以“忧心烦乱”,不堪着意安排使然。清王邦采《离骚汇订·自序》说:“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屈子之情生于文也;忽起忽伏,忽断忽续,屈子之文生于情也。”[21]张永鑫谓王氏“指出了《离骚》的结构同屈原感情的激动跌宕是密切相关的”[22](P438-439),情文合一,不可端倪。倪晋波《论〈天问〉的“叙问”特征和抒情结构》,说《天问》对宇宙、天地、人事的170 个追问也是错杂无序,如在宇宙的追问中忽然插入鲧、禹治水之事,叙述周继商起,不按世系,而是从武王说起,推动其追问思维的“流动性”和“跳跃性”,也是“诗人去国怀忧状态下奔腾流泻的内心情感”。《九章》则王逸谓“屈原放于江南之壄,思君念国,忧心罔极”而作[11](P120),朱熹谓“非必出于一时之言”[23](P72),其中“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涉江》和《哀郢》有大致的行路叙述,后者尤然,但纪行不是主要的,而是一路悲歌,且行且怨,《哀郢》从“发郢都而去闾”,依次叙述“过夏首而西浮”“上洞庭而下江”之后,却又反过来“哀故都之日远”、悲“郢路之辽远”,惟以悲愤的情感驱动一步一顾的故国思恋;《抽思》题名取于篇中“与美人抽思兮,并日夜而无正”,《章句》作“抽怨”,王注“拔恨意也”[11](P139),虽亦放逐途中所作,但无纪行,而是“反复其词,以泄忧思”[11](P141),情感的抒发并不在于后世所谓篇章的结构,只有清晰的写作思维才斤斤讲究“谋篇”的章法。《九章》其他篇章也大抵如此。
《九歌》原是远古之乐,《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王逸注谓启为禹子,《九辩》《九歌》为禹乐[11](P21),洪兴祖注引《山海经》“夏后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11](P21),楚人传之,以为祭神,王逸谓沅、湘之间,其俗信鬼好祠,歌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作此[11](P55)。现代学者多认为屈原作于放逐之前,用供祭祀。《九歌》中除《国殇》祭祀楚国阵亡将士外,都写神恋,愁怨惆怅,营造水湄山中的凄迷场景,多在情景交融,可称意境。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谓,“蒙叟《逍遥》,屈子《远游》,旷荡虚无,绝去笔墨畦径,百代诗赋源流,实兆端此。”[24](P126)实际上《九歌》尤然,不仅与屈原其他诸作一起直开赋体,也可能演变为诗。现代学者多从“兮”字脱落着眼,其实情景、意境为要,固当识取大者。《九辩》为宋玉所作,当代多无疑义,与《九歌》同为远古之乐,王逸注谓“九”为阳数之极,取为歌名[11](P55),然《九歌》为短歌之集,《九辩》单篇敷陈,借景抒情,融情于景,抒发“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非如后世枚乘《七发》、东方朔《七谏》分为七事构篇。《招魂》王注“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11](P197)所作,在极度散乱的精神状态中,何堪着意构结?也是语无伦次。《远游》取效屈宋,“悲时俗之迫阨”“怊惝恍而乖怀”,虽涉神仙道家之事,仍然以情为主,通篇杂沓有之。外此者较为特殊的是《卜居》《渔父》问答构篇,议论有之,不涉儒、道之理。凡此屈宋等“楚辞”与汉代拟作不同,后者虽亦抒情,但以明显作意构篇而或取于儒、道,理性为本,或以事构篇,次序井然。
汉代骚体赋对于屈宋等“楚辞”的传承,根本上就是抒情,与汉大赋承接宋玉赋叙物,并为两大主线。汉代骚体赋因其所祖不同,厥分四途:
一是弔悼屈子,或以自悼,如贾谊《弔屈原赋》、扬雄《反离骚》取效《离骚》,《鵩鸟赋》句式为短,有类《九章·怀沙》,《惜誓》则祖《九章·惜诵》,王褒《九怀》、王逸《九思》则拟《九辩》《九歌》,凡此亦参屈、宋其他诸篇。《弔屈原赋》共三段,首段同序,次段为正文,概括屈原行事遭遇,抒情为主,末段为“讯”,议论为主,刘勰《文心雕龙·哀弔》谓“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18](P241),迥异《离骚》怨怼激发、重沓繁复,而以事、理为主,明孙月峰谓“视《鵩赋》较有骚人之致……第述意太分明,便觉近今”[25](P12)。扬雄《反离骚》名虽为反,却是哀弔,希望屈原能留住有用之身,以孔子“终回复于旧都”,悲其“弃由、老聃之所珍,蹠彭咸之所遗”,抒情虽近于《骚》,但通篇贯穿了清醒的思理,结构转为谨严,篇幅去《骚》甚短。《鵩鸟赋》有序,交代缘由,则一篇思路构结已定,自是理路较然,多用老庄之义,这是汉初尚黄老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庄子》“荒唐谬悠”也许与屈辞“旷荡虚无”同有南方文化的浪漫特质,前者较诸经学与后者的结合尤为适应,刘师培即指屈辞“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26](P81)。《惜誓》自抒己意,不似代屈所为,篇中不仅如《远游》言“赤松、王乔”而念“长生久仙”,且陈“比干忠谏”“仁人尽节”,反映儒家忠节仁义,与《九章·惜诵》之言“五帝”“六神”不同,远古之神已降为世俗所羡之仙,三代理想已经降为儒门经义,而且从《惜诵》抒情为本变为议论为主。至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追思屈原,固以抒情为主,然其鸿篇巨制,出于精心构架,每章各主一义,述旨分明,已较屈原《离骚》和宋玉《九辩》出于情感复沓铺陈尤其是屈辞生命精神的熔铸不同,且《九辩》取于阳数命名,至此则变为篇章结构之数,在其精心结撰之中,作者变为一个清醒的叙述者,理性的反思隐然其中,也是全篇构思之本。又东汉梁竦《悼骚赋》历述孔子、重耳、乐毅、项羽、范增,抒发对于历史人事的感慨,只是体制拟《骚》而已。
二是《太玄》《思玄》之制。除汉初尚黄老的短暂时期之外,汉代思想基本以经学为尊,反映于骚体赋的创作,但在贾谊《鵩鸟赋》之后,也有扬雄《太玄赋》和张衡《思玄赋》等,清陈螺渚谓“汉儒者不傍老庄门户”[25](P11),贾谊《鵩鸟》仅为例外,却不及扬、张二赋。《太玄赋》只是以骚体形式阐论玄理。张衡“常思……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4](P1914),为汉代骚体赋中可比大赋的鸿篇巨制,拟于《离骚》而述想象之游、玄远之思,一样是上天入地,漫无方的,但不是《离骚》以情为主的繁复迭出,而是谨于谋篇,“势虽宽而用意甚紧,此长篇能事”[25](P19)。
四是自述其志。屈辞多为第一人称的自我抒情,并兼述志,尤其《离骚》前半部分自述理想,《九章》中《惜诵》《哀郢》诸篇也有类似的表述,是为汉人祖述所本。董仲舒《士不遇赋》首段用《诗》四言,接着“重曰”第二、三段用楚辞体,都是感慨议论,以明其志,称述“圣贤”“圣人”“君子”之“道”而“正心”归“善”。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很短,几乎都是概念化的表述,不克铺陈,也不尽“兮”字句,且杂取四言,不类骚体,只是拟于董仲舒《士不遇赋》,可以视为骚体再变。王莽新朝时崔篆《慰志赋》追思以母兄受宠莽朝,“身丁汉世之中微”,耻事伪职,篇中称述《诗》之《大雅》《氓》及六经等,固以经义为本。班固《幽通赋》陈述家族盛衰,表达对宇宙、历史、人生的思考,亦称“系高顼之玄胄,氏中叶之炳灵”,盖班氏之先与楚同姓,陈其世系,亦若屈原帝胄自许、高洁其身之意,但与《离骚》激情喷发的繁复杂沓不同,在无尽兴感中伴随着理性之思、历史之鉴,写实而非“多称虚无”是其作为骚体赋演变的突出特点。
五是纪行之作。《离骚》与《九章》中的《涉江》《哀郢》《抽思》及《远游》《惜誓》,都见作者主体行游之迹,但除《涉江》《哀郢》尤其是后者具有纪实性外,大多都是假设陈词,如《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就重华而陈词”,即使在具纪实性的《涉江》中,如“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也都是基于远古神话的想象驰骋,这是屈、宋等楚辞“多称虚无”的“浪漫”特点,汉代骚体纪行赋递相拟之,但大抵由虚征实。刘歆以主《左传》列入学官被贬五原,从河内北上太行,经山西南北,作《遂初赋》纪行,历述纪传人事。班彪《北征赋》,以赤眉入关,杀更始,故远避凉州,乃发长安,至安定,作赋纪行,怀古伤今。东汉初冯衍《显志赋》述行显志,是一篇虚拟的述行赋,自论“上陇阪,陟高冈,游精宇宙,流目八纮,历观九州岛山川之体,追览上古得失之风,愍道陵迟”[31](P987),在想象中周游泛览,历述虞舜、皋陶、高阳、夏启、伯夷、务光、成康,扬朱、墨子、苏秦、张仪、李斯之事,不是屈辞那样以自我为中心驱遣神话传说以为想象,而是作为历史事实的追述,同时发表议论,抒发感慨。班昭《东征赋》,以从子曹成陈留赴任,写沿途观感,缅怀先贤,体恤民难,“乱词皆箴规语,畅言师古听命之义”,正是“儒者之言,不愧母师女士矣”[25](P20-21)。蔡邕《述行赋》作于延熹二年秋,以宦官徐璜遣陈留太守发邕诣朝鼓琴,“到偃师,病不前,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32](P911),写景抒情,感慨人事,也是纪实之作。此外,汉末建安阮瑀有《纪征赋》、徐幹有《序征赋》,并极短,粗呈梗概。建安王粲《登楼赋》述其登楼所见,形制有如述行,又作《浮淮赋》,极短不克铺陈。
六是楚辞变体,从抒情转为叙物,或与大赋相合。贾谊《旱云赋》援取骚体句式,却以“凭虚”夸饰的大赋手法极力铺写旱云形貌、大旱之烈,后半议论天地人事,归于寡德不仁。在此之前,已有传为宋玉《风赋》,此赋或有取效。王褒《洞箫赋》多用“兮”字句,间以四言,扬雄《甘泉赋》、傅毅《舞赋》亦然,其四字句一顺铺陈,同于相如《子虚》《上林》。东汉黄香《九宫赋》造语若加“兮”字,则与骚体无异,亦如大赋铺陈,也是骚体与大赋相合之制。东汉朱穆《郁金赋》、蔡邕《伤故栗赋》《霖雨赋》,又建安王粲、陈琳、应玚各作《迷迭赋》,应玚亦有《慜骥赋》,亦如《旱云》《洞箫》叙物,赋体益小,篇幅极短,铺陈殆亡。凡此或亦受到荀子五赋的影响,另当别论。
汉代骚体赋继承屈、宋等楚辞之制,最为根本的特点就是抒情,与汉大赋叙物判然为二。屈宋等楚辞抒情是主导性的,是为全篇结构之本,理、事则在其次,一唯抒情所需;屈辞的情感融合了源于三代的政治理想、身系社稷的贵胄情怀以及南国楚人的狂狷气性。汉代骚体赋主体情感则主要系于一己之进退、宠辱、生死,或作为臣子“心存魏阙”[18](P493)之维,而且情感本身为理性所节制,或起于情而止乎理,如贾谊《鵩鸟赋》、司马相如《长门赋》、班婕妤《自悼赋》及刘歆等述行诸赋,莫不如此。只是理有分殊,除了贾谊之作及扬、张二《玄》之外,汉代骚体赋所反映或依据之理就是儒家经义,从根本上说,经义乃是汉人思维的基本方式甚至心理定势,无论抒情、述志、纪行,最终都归于此,经义充当了情感的平衡。在屈宋等楚辞作品中,抒情统摄理、事,即使《九章·哀郢》呈现较为明晰的放逐程途,也非纪行为主,且行且叹就是愁懑的摅写。但在汉代纪行赋中,征途的形迹乃是作为全篇结构的主线,而且不同于屈辞远古三代神话传说及楚诡谲之事,率皆“多称虚无”,汉代骚体赋则由虚转实,取于经籍和自古至今的故实承载或引发主体的历史感慨,不用说出于主体的“学者”博识和严谨,如扬雄、班固、张衡诸作,然已丧失屈子之作的“旷荡虚无”,因而也就失去屈辞那种无所依凭的绝世精神和纯粹品质。在篇章结构上,则是由屈宋之作的繁复杂沓变为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而且汉代骚体赋取效屈宋等楚辞之作,篇幅长短不同。《离骚》《天问》《招魂》《九辩》本为巨制,拟之若无典事充实,则无所铺陈而变为短制,如贾谊诸作、梁竦《悼骚赋》、董仲舒《士不遇赋》为然,至建安诸人所作,则至简而卒无铺陈,即如王粲《登楼赋》取效楚辞而衍为短制,周平园谓“篇中无幽奥之词,刻镂之字,期于自摅胸臆……无取乎富丽”[25](P30),殊不知汉代骚体赋长篇,正是由于大赋巨制的影响才有所铺写。及建安抒情短赋不然,并非只是出于“自摅胸臆”。至于张衡《归田赋》抒情体物,情景交融,却去楚辞已远,固为骚体再变。而汉代骚体赋受到大赋影响,则于纪行诸赋长篇和张衡《思玄》见之,尤其后者巨制,若非参合大赋作法,断不可为。
四、句、物、词的演变
屈原《离骚》开启楚辞以及汉代骚体和大赋的传统,为《诗》之后的伟大创制,从此《诗》《骚》并峙,二者不同,根本在于体制之异。体制的形成,要在句式。《诗》以四言句式而成为四言体,其分章合乐、重章叠句乃至语词和用韵都以四言句式为基础。稳定的句式不仅是《诗》而且是后世五、七言体形成的先决条件。从这个角度比较屈原诸作,不是“诗”而是称“辞”即表明《诗》《骚》体制的根本区别。屈辞诸篇虽有大致相近的句式,但非整齐划一,而是长短参差,随意变换,这是区别于《诗》并后世诗语整齐句式的重要特征。以一篇之内《离骚》为例,“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两句长短不一;即使一篇中相近之句,如《九歌·湘君》“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短长相接,不求整饬。从屈宋诸篇来看,句式尤有不同,如《离骚》《九辩》及《九章》中的《惜诵》《涉江》句式较长,而《天问》《招魂》及《九章》《怀沙》《橘颂》句式为短,这是屈宋楚辞作品给予读者的直觉印象。
相对于《诗》四言的整齐划一而言,屈宋等楚辞本质上都为散语,这是重要的判断,惟此才能经由宋玉弃情叙物的转换而成为“散体大赋”,班固谓“赋者古诗之流”,却根本不可能给出散体赋演变于《诗》四言的证明。散语之于《诗》四言和后世诗语整饬的基本特征,就是不以句式之限而省略或压缩、颠倒“句法成分”,而是以相对的长句保留这些成分,即有省略颠倒,也较诗语如四言、五言具有更大的容纳空间。楚辞中《卜居》《渔父》叙述和对话,就是散文语。《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往见太卜郑詹尹曰:‘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曰:‘君将何以教之?’”是与《高唐赋》《风赋》散语一致,汉大赋假设问对的散语由此而来。举出此例是必要的,以此而视“赋者古诗之流”的言论,正如颠倒黑白;现代或有将楚辞视为诗歌者,当然也是黑白不分。实际上楚辞中的散语特征十分明显,略举最著者如《离骚》“余既不难夫离别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以标准的散文语法保留主、谓等语法成分;“虽萎绝其亦何伤兮”“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表现转折和条件的关系,前者则以一语构成复句。这些都是长句,短句则如《九章·怀沙》“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如果去掉“兮”字,与形式主义所谓“日常语法”略无不同。尤其《天问》基本上是四言短句,开头几句云:“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表面上与《诗》四言似乎不异,但后者是以四言限定而用虚字凑足,如《卫风·氓》“将子无怒”“载笑载言”“士也罔极”,“将”“载”“也”都在凑足四言,尤其“士也罔极”“其黄而陨”较诸日常语法的不顺,表明四言句式的严格限定。《天问》则是造语自然一顺,两两相接的四言排比形成一将滚出的无穷追问,对比一目了然。
散语偶句入韵,又以“兮”字单句拉长语气,形成楚辞可诵的独特体式,如《离骚》“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兮”字用以拉长语调,加强感叹的效果,正合诵的需要,去之则立即失去抒情的感染力。当代楚辞研究十分强调“兮”字在楚辞句式的重要性,认为是“楚辞体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其他任何韵文体式的标尺”[33](P4)。“兮”字或用于句中,间顿语气,更主要的是具有连词的结构作用,如《九歌·山鬼》“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九章·惜诵》“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与向服”,前例“兮”与后例“以”“与”造成句中停顿,又起到连接前后字句的结构作用,这种较为整饬的句式演变为东汉到魏晋六朝的骈语对举。重要的是楚辞散语的分析,尤能显示虚字的结构功能,如《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之”字形成一个主谓结构,充当“嫉”的宾语,如果没有下句末字入韵和上句末字之“兮”,就是散文语的通常表达,而“佩缤纷其繁饰兮”之“其”惟以语气连接前后字词,等同“心犹豫而狐疑兮”之“而”的连词之用,究与“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之“以”没有本质的区别,后者当然是典型的散文句式。而如《思美人》“芳与泽其杂糅兮”,尤以一句中“与”“其”二虚字相接,结构更为复杂,乃至《九辩》长句“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虚字连接字词而构成散语长句的功用尤为明显。凡此可见诸多句式之于楚辞体式的作用,不仅“兮”字句的简单指实,而且各种句式尤与楚辞诸篇不同的主题、体制乃至名物、描写的铺陈紧密相关。
汉代骚体赋的句式当然绝多末尾“兮”字,但后来拟作必不反证楚辞都是如此,《天问》《招魂》不然,只是汉代罕习而已。骚体赋对楚辞句式的模仿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取于整饬,以上七下六为常,如班婕妤《自悼赋》“承祖考之道德兮,何性命之淑灵”,本篇除重辞援《远游》之例有所变化外,其余都是上七下六,汉武帝《悼李夫人赋》除乱辞外也是如此。班彪《西征赋》等述行赋亦然,偶有其他字数长、短为句者,不为通例。最显著的是张衡《思玄赋》巨制,全篇除系词外都是这种句式,何焯评曰“仿古太似则不新……但其一往浩瀚之势,亦迥不可及也”[25](P23),“仿古太似”之于句式的整饬或可理解为句法摹拟的严谨,毕竟上七下六多见于屈宋等楚辞篇章,在汉代骚体赋中固定下来而表现为普遍化的倾向,这种格式化表明主体创作意识的执著,已经不是屈宋等辞惟以情感抒发的长短参差,变化随意。这种倾向是渐次形成的,在武帝之世若司马相如《哀二世赋》则以“汩淢噏习以水逝兮,注平皋之广衍”之长及“弥节容与兮,历吊二世”之短间破上七下六之式。尤其是《大人赋》如“驾应龙象舆之蠖略委丽兮,骖赤螭青虬之蚴蟉宛蜒”,其祖述的源头是在《离骚》尤其是《九辩》长句,更主要的是参合大赋造语的散行之句,后者可以变为“应龙象舆,赤螭青虬”的名物铺陈和“蠖略委丽,蚴蟉宛蜒”的形容堆砌,相符若契,比较扬雄《甘泉》大赋之制“腾清霄而轶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柅也”,从而上溯《离骚》“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及《九辩》“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漻兮收潦而水清”“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显然比后来骚体赋整齐划一的句式更为接近屈宋散语,而宋玉《九辩》语词也与《高唐赋》具有相近的特点,可当《高唐》宋作之证。一方面,在汉代骚体赋如马、扬句式的冗复繁难惟以散体大赋保留甚至增强屈宋之作句式的散语特征,也是覆掌可按。另一方面,汉代骚体赋的总体大势却是由繁复而整饬,由繁之简,不惟作意严谨,追求一致,更是造语用字渐趋贫乏的表现,及建安诸人所作短赋而不克铺陈,即是明证。句式的愈趋整饬最终导致句尾“兮”的脱落,如张衡《归田赋》“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变为轻松明快的惬意对举。
《离骚》以句中虚字连接更多的字词形成复杂结构的长句,并以句尾虚字加强情感的表达和咏叹的效果,实质上乃是借助虚字以使散语长句成为韵语,较之《诗》语四言的拘限具有情感表达和名物容纳的更大空间[34]。例如“杂申椒与菌桂兮”“畦留夷与揭车兮”,“与”字连接前后两个名物,在《离骚》长篇中,就十分适合名物的铺陈。屈宋等楚辞广托名物,所谓美人香草,正惟怨怼激发的抒发,若在《高唐赋》及汉大赋中,则可变为“申椒菌桂,留夷揭车……”四言一顺的直接铺陈,或为形容的堆砌,如“巌岖参差……窐寥窈冥”,谲诡奇伟,在《离骚》则以虚字连接为长句如“修姱以鞿羁”“犹豫而狐疑”,显见屈骚散语长句之于名物和语词铺陈的独特功能。
屈宋等楚辞的长篇巨制和散语长句较《诗》具有远为丰富的名物铺陈空间,古人“物事”“事物”相连,事亦物,楚物、楚事显示屈宋等楚辞之于《诗》的不同特点。屈辞称述远古三代之事而“多称虚无”,后者如宓妃、望舒、飞廉、鸾皇、雷师之类,而汉代骚体赋则多称周代以下及当代之事,即称远古三代之事,也是作为史实而基于经义,在汉人所取,远古三代之事就是经典所载。屈辞多述楚地,如沅、湘、澧、及江皋、中洲、北渚、西澨之类,贾谊《吊屈原赋》、司马相如《大人赋》力拟《远游》,地名也多取于楚辞。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追怀屈原,多仍楚辞风物,刘向编入一书,确有同然者在焉。但如司马相如《大人赋》“朅轻举而远游”,则已不限楚地。最显著的是纪行之作,如冯衍《显志赋》虚拟新丰、镐京、平阳、太行、壶口之游,蔡邕《述行赋》实写大梁、晋鄙、中牟、北境、荥阳、虎牢、太室、河洛之行,完全突破楚地之囿,风物亦自不同,不妨说为境域的拓展,但楚辞之所以引人入胜,南国楚地风物环境的幽美凄迷也是重要的原因。
屈辞名物,率多卉木,故谓“美人香草”,以为寄托,如江离、木兰、宿莽、申椒、菌桂、留夷、揭车、杜衡、芙蓉、薜荔之类,暗蔼芳馥,层出不穷,且为器用美称,如桂棹、兰枻,并神所居者如荪壁、荷屋之类。《九怀》《九叹》《九思》亦多取用,尤其汉大赋名物铺陈益广,如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取于屈辞者,草卉则芙蓉、芷若、揭车、留夷、杜衡、江蓠,射干、兰蕙、麋芜、青薠之类,木则橘柚、桂树之属,甚至《上林》写秦地而援楚物,左思《三都赋序》批评“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侈言无验,虽丽非经”[35](P74),正是“凭虚”[36]所致。名物而外,屈辞的铺陈也在形容描写尤其是重言和联绵字,所在为多,如《九歌》中《东皇太一》“琳琅、偃蹇、菲菲”,《云中君》“连蜷、昭昭、周章”,《湘君》《湘夫人》“夷犹、要眇、婵媛、浅浅、翩翩、眇眇、袅袅,潺湲、逍遥、容与”,《山鬼》“窈窕、容容、冥冥、磊磊、蔓蔓、填填、啾啾、飒飒、萧萧”,形容状物,多有佳致,字形美好,音声要妙,情意宛然,极尽委曲之致。汉人所取,多在大赋及骚体之近于大赋者如司马相如《大人赋》,以及骚体与大赋相合的变体如《甘泉赋》、傅毅《舞赋》等,形容描写的铺陈,倍于《离骚》,充塞巨篇,繁难复杂,令人炫目,而骚体外此者寡见。不妨取录冯衍《显志赋》一段以见其实:
陟雍畴而消摇兮,超略阳而不反。念生人之不再兮,悲六亲之日远。陟九嵕而临薛兮,听泾渭之波声。顾鸿门而歔欷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纯兮,信吾罪之所生。伤诚善之无辜兮,赍此恨而入冥。嗟我思之不远兮,岂败事之可悔?虽九死而不瞑兮,恐余殃之有再。泪汍澜而雨集兮,气滂渤而云披。心怫郁而纡结兮,意沉抑而内悲。[31](P987)
从抒情、篇幅、句式等方面来看,这是汉代骚体赋较为典型的文本,虽有《离骚》影迹,但更近《九章》的《哀郢》,在屈辞中,《哀郢》抒情而寡涉名物和形容铺陈,《九章》中如《涉江》不然,但明许学夷《诗源辩体》犹以二篇“文又甚显”,又谓《九章》不如《九歌》,而“《离骚》不易学也”[12](P36)。《九歌》则名物、形容众多,《离骚》尤甚。尽管如此,《哀郢》“怊荒忽其焉极”“楫齐扬以容与兮”“涕淫淫其若霰”“心婵媛而伤怀兮”“焉洋洋而为客”“忽翱翔之焉薄”“思蹇产而不释”“今逍遥而来东”诸语,也以重言或联绵字用为形容,爰使声气舒缓,一唱三叹,反复缠绵。冯作既以仿效《九章》而非《九歌》《离骚》,取法不可谓高,汉代纪行赋都是如此,大约纪行较为分明,不藉名物语词铺陈,拟之不难。《显志赋》此段则仅“歔欷、汍澜、滂渤”略为点缀,一段的造语都是直接抒情,实际上是带着感慨的议论,“诚善”“败事”的概念化以及“念生人之不再兮,悲六亲之日远”的浅直表白固然可以在屈辞诸篇找到祖述所本,但屈辞精义却不在此,而是名物、语词及其散语句法的叠复铺陈。汉代骚体赋尤其是纪行赋既以议论抒情,则于篇章谨于结构,句式归于整饬,名物比兴为寡,形容描写不盛,即如张衡《思玄》巨制亦然,不用怀疑同一作者所作《西京赋》名物语词铺陈的巨丽壮观,只是骚体赋抒情接续屈宋楚辞的流韵,却没有继承其“美人香草”和反复陈辞的形容描写,而屈宋楚辞的这种形容描写却在弃情叙物的汉大赋翻作波澜,汹涌滂㵒,澎濞沆瀣[3](P3017),显见屈辞经由宋赋直到汉赋的分途,只有大赋才是一代“辞章”之盛。
——评杜朝晖《敦煌文献名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