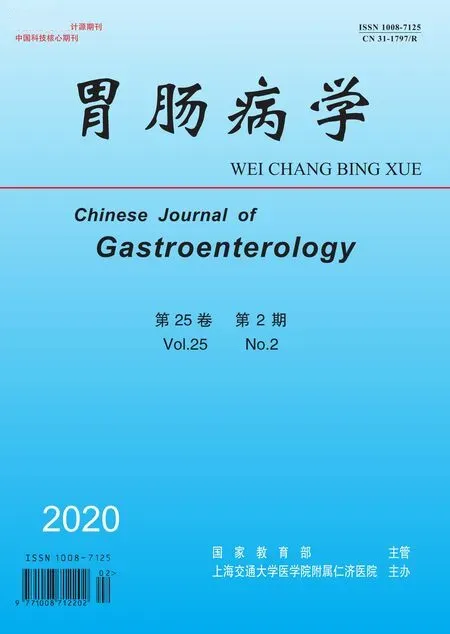肠道微生态与消化系统健康和疾病*
陈 烨 刘 乐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科(510515)
胃肠道中含有广泛多样、宿主特异性的微生物群,它们不仅适应了胃肠道中独特而多样的环境,而且能对外界各种变异原迅速作出反应,通过一系列生化信号与宿主相互作用,协调营养物质交换,调控免疫功能。宿主与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建立在内环境稳态的基础之上,菌群失调可参与或促进疾病的发生、发展。肠道菌群并没有所谓的最佳组成,群落平衡对人类健康至关重要。本文从微生态学角度研究肠道菌群与人类宿主的关系,对近年来发现的肠道微生态与消化系统疾病的关系进行总结。
一、肠道微生态的功能
肠上皮将肠腔细菌与黏膜固有层分隔,形成一道天然的物理屏障,允许有限分子的细胞侧转运,精确调节上皮细胞间紧密连接对于维持肠上皮完整性至关重要[1]。肠上皮表面覆盖着一层黏液,内层致密,外层松散,其高密度的特性可阻止大多数细菌移位。黏蛋白在个体间表现出高度保守性,在肠道细菌选择中起重要作用[2]。只有少数微生物能黏附于黏液之上并几乎完全附着于黏液外层,是否具有黏附能力取决于该细菌是否表达凝集素。正常人结肠中含有丰富的具有降解黏蛋白功能的阿克曼菌(Akkermansiamuciniphila),其在维持肠道完整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3]。
先天免疫系统(innate immune system)是抵御病原体感染的第一道防线。Nod样受体信号激活可诱导具有细胞保护作用的细胞因子、热休克蛋白以及抗菌肽表达,发挥宿主防御功能。固有淋巴细胞(innate lymphoid cells, ILCs)是肠道先天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Ⅲ型ILC的分化成熟受肠道微生物调控,其分泌的白细胞介素-22(IL-22)可促进肠上皮细胞和Paneth细胞合成、分泌抗菌肽,促进宿主防御,维持肠稳态[4]。肠道共生菌也参与调节黏膜固有层T细胞亚群的募集和分化。分节丝状菌(segmented filamentous bacteria)紧密黏附于小肠上皮细胞和集合淋巴结,诱导黏膜Th17细胞反应,促进肠道细菌与宿主之间的共生[5]。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fragilis)和梭菌可促进调节性T细胞分化、扩增,诱导肠道免疫耐受[6-7]。此外,B细胞来源的IgA分泌至肠腔中可与细菌抗原结合,阻止细菌移位,也是肠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8]。
肠道菌群与宿主能量代谢之间也有密切联系,部分细菌可直接合成激素或激素样化合物,也可通过调节肠道内分泌细胞的功能间接参与内环境稳态的调节。梭菌发酵膳食纤维的代谢物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 SCFAs)可作用于肠道内分泌细胞L细胞,调控胰高血糖素样肽-1(glucagon-like peptide-1, GLP-1)、酪酪肽、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的释放,调节机体胰岛素敏感性和能量代谢,也可促进肠嗜铬细胞合成、分泌5-羟色胺(5-HT),参与肠道运动、分泌反射以及血小板功能的调节[9]。此外,经肠道微生物转化而来的次级胆酸可结合L细胞上的法尼酯X受体(FXR),刺激GLP-1分泌,参与血糖平衡的调节[10]。
肠道共生菌还可通过多种机制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稳态,包括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神经免疫反应、神经元发育、迷走神经信号转导和血脑屏障的稳定性[11]。膳食纤维代谢物SCFAs不仅可调控肠道内分泌细胞合成、分泌5-HT,维持中枢神经系统和肠神经系统稳态,还可调节神经传递过程和血脑屏障的稳定性,从而影响情绪和行为。
二、肠道微生态与消化系统疾病
1.艰难梭菌感染(Clostridiumdifficileinfection, CDI):1935年Hall和O’Toole从健康新生儿粪便中成功分离出革兰阳性厌氧产芽孢杆菌艰难梭菌,其孢子广泛存在于外界环境中,对热、酸和多数抗菌药物耐受,通过粪-口途径传播[12]。约5%的成人和15%~70%的婴儿可发生CDI,住院患者和养老院老人的感染率则是前者的数倍。正常菌群的定植抗性是抑制病原体感染的主要生物屏障。一般情况下,初级胆酸通常可刺激艰难梭菌孢子萌发,经7α-去羟化肠道细菌转化而来的次级胆酸则抑制这一过程[13]。肠道菌群失衡后,艰难梭菌开始定植于并支配结肠,这可能是CDI发生的第一步。然而只有部分艰难梭菌定植患者会出现CDI症状。艰难梭菌在致病过程中主要产生肠毒素A和细胞毒素B,艰难梭菌转氨酶是部分艰难梭菌,包括流行的高毒力PCR-核糖体型027分泌的第三种毒素。这些毒素引起肠道黏膜损伤和炎症,导致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如不及时医治可发生严重的伪膜性肠炎和脓毒血症,病死率高达15%~24%[14]。几乎所有抗菌药物都会增加对CDI的易感性,特别是头孢菌素和氟喹诺酮类,克林霉素和青霉素类引发CDI的风险最高。在过去十年中,CDI已成为最重要的医院感染之一。接受抗菌药物治疗的老年住院患者CDI发生风险最高,粪菌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已成为复发性CDI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
2.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和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是IBD的两种主要类型,近十余年来,IBD患病率在全球范围内急剧上升,其病因目前尚不清楚,主要与遗传易感性、黏膜屏障受损、免疫紊乱、环境改变以及菌群失调等有关。IBD是最早对肠道菌群进行深入研究的疾病之一,相关研究揭示了IBD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和稳定性降低,具体表现为真杆菌、拟杆菌、梭菌减少,肠杆菌、梭形杆菌、肠球菌增加。同时,代谢组学研究显示SCFAs等有益的菌群产物减少,原代胆酸及其甘氨酸和牛磺酸结合物明显增加[15]。全基因组关联研究鉴定出163个与IBD相关的易感基因位点,先天免疫基因如NOD2、ATG16L1、IRGM等与CD发病显著相关[16]。然而,并非所有携带IBD易感基因变异体的个体都会发病,基因突变在IBD发病中仅起有始动作用。肿瘤坏死因子(TNF)ΔARE小鼠表现为主要累及回肠的CD样透壁性炎症,但Schaubeck等[17]的研究发现,TNFΔARE小鼠自发性肠炎的严重程度是微生物依赖性的,无菌TNFΔARE小鼠不发生肠道炎症,常规TNFΔARE小鼠经抗菌治疗后回肠炎症减轻;分别将炎症和非炎症TNFΔARE小鼠的粪便移植至无菌TNFΔARE小鼠体内,仅前者可成功诱导CD样回肠炎,证实肠道细菌是引发IBD炎症损伤的重要驱动因素。IBD药物治疗与肠道菌群也有一定关联。与未经治疗者相比,美沙拉嗪治疗可降低粪便细菌和黏膜黏附细菌浓度,在体外可以剂量依赖性的方式抑制鸟分枝杆菌副结核亚种生长,后者与CD病因密切相关[18];同时可抑制沙门菌的侵袭性和抗菌药物耐药性相关基因表达,抑制感染后IBD发生[19]。以抗TNF-α抗体诱导IBD缓解,应答者治疗前和治疗过程中的肠道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prausnitzii)丰度均显著高于无应答者[20]。如能利用粪便细菌作为生物学标志物,以非侵入性的方式预测IBD患者的治疗应答,临床医师将能更迅速地确定有效治疗方案,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3.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CRC是全球第三大常见恶性肿瘤,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CRC发病率增速最快,主要与西方化饮食的生活方式有关。从发病机制角度,肠上皮细胞恶性转化并进展至CRC至少包括三个主要步骤:Lgr5阳性肠干细胞发生致癌突变;Wnt/β-catenin信号改变;促炎信号的级联放大效应。肠道菌群紊乱是CRC病情进展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一项全基因组关联研究[21]证实,高比例的拟杆菌、梭形杆菌和肠杆菌与CRC局部炎症和肿瘤分期密切相关;与摄入水果和蔬菜相反,肉类饮食(红肉)可降低肠道产丁酸菌和胆汁酸代谢菌丰度,表明饮食方式在CRC发病中起重要作用。目前,已比较明确的是,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nucleatum)、产大肠菌素的大肠埃希菌(Escherichiacoli)和产毒素型脆弱拟杆菌与CRC进展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然而,目前对于靶向肠道细菌防治CRC的机制知之甚少。从机制角度看,肿瘤组织中大量富集的具核梭杆菌FadA黏附素是上皮细胞E-cadherin的配体,可激活下游β-catenin信号,引起肠上皮细胞生长失控、腺瘤样表型形成和细胞极性丧失,与微卫星不稳定型和BRAF基因突变型CRC密切相关[22]。此外,提示预后不良和肿瘤分期较差的肠黏膜大肠埃希菌多含有基因组聚酮合酶(polyketide synthase, PKS)毒力基因岛,编码基因毒素colibactin,能诱导哺乳动物上皮细胞DNA损伤和基因突变[23]。研究发现,细菌核苷酸代谢基因可影响5-氟尿嘧啶和喜树碱的抗肿瘤效应[24];由肠道菌群介导的免疫调节机制与机体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程序性死亡分子-1(programmed death-1, PD-1)/PD-1配体(PD-L1)单抗的免疫应答密切相关,如双歧杆菌可显著增强抗PD-L1治疗的疗效[25],PD-1单抗的疗效强烈依赖于阿克曼菌诱导的Th1型免疫反应[26]。具核梭杆菌可通过Toll样受体4信号通路和某些miRNAs激活自噬等复杂机制导致CRC对化疗耐药[27],抑制具核梭杆菌及其黏附受体可能阻止化疗耐药的产生。
4.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IBS是最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之一,其特征是慢性、复发性腹痛和排便习惯改变。目前IBS仍缺乏有效的诊断以及预测病情进展的生物学标志物,疾病的异质性使其管理差强人意。神经-免疫-内分泌系统在表观遗传学和性别上的差异、脑-肠轴、胆汁酸代谢以及遗传因素都可能涉及IBS发病的调控。IBS的遗传易感特质可与细菌感染、毒性物质、饮食方式、生活事件相关因素等共同作用,增加肠屏障通透性,最终引起黏膜免疫微炎症和局部微环境失调。研究发现急性胃肠炎后发生IBS的风险显著增加,其机制可能与感染触发物(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在易感个体中激活异常免疫反应有关,部分患者对菌群调节治疗策略有积极应答[28]。因此,菌群失调可能是IBS病理生理学机制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组学研究证实IBS患者肠道中肠杆菌等促炎细菌种类相对丰富,梭菌、双歧杆菌数量相应减少[29]。双歧杆菌可与其他细菌或宿主相互作用,分泌细菌素,对外来病原体有一定杀菌作用,也可刺激树突细胞调节宿主免疫系统功能。IBS患者中比例较低的双歧杆菌、梭菌、瘤胃球菌、韦荣球菌等均为产SCFAs菌,而SCFAs具有一定的抗炎和胃肠动力调节作用[30]。甲烷短杆菌是最常见的产甲烷菌,甲烷可抑制肠道转运,与便秘型IBS(IBS-D)的病情有一定关联[31]。此外,明确IBS病情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与肠道菌群组成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十分重要。一项基于正常人群的菌群研究[32]表明,性别与肠道微生态结构、多样性和功能单元丰度(同源集群)密切相关,女性相对于男性表现出更高的菌群功能单元丰度。然而在IBS菌群相关研究[33]中,尽管男、女性患者间各“肠型”(肠道微生物菌型)的分布比例存在一定差异,但并未发现整体菌群功能单元丰度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IBS患者的精神心理改变与肠道菌群失调也存在一定关联,将腹泻型IBS(IBS-D)患者的粪菌移植入无菌小鼠可使其产生焦虑样行为[34]。因此,性别和精神疾病可能是解释IBS特异性微生物变化的重要变量。
5.乳糜泻(celiac disease, CeD):CeD是一种由免疫失调介导的肠道疾病,独特之处在于已明确其具体触发因素为麸质蛋白。目前治疗主要采用无麸质饮食(gluten-free diet, GFD)。数项研究确定了CeD患者与健康人的差异菌群,表现为棒状细菌如拟杆菌、梭菌、大肠埃希菌丰度增加,双歧杆菌、链球菌、普氏菌、乳杆菌丰富降低[35]。然而这些研究大部分是描述性的,难以确定肠道菌群改变是CeD的原因还是后果。为了解CeD中肠道菌群的致病机制,分别将CeD患者和健康人的小肠细菌移植入无菌小鼠,结果显示乳杆菌具有保护作用,条件致病菌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aeruginosa)则与CeD发生相关[36]。铜绿假单胞菌可分泌纤维素酶LasB,该酶可破坏肠屏障并促进麦醇溶蛋白移位至黏膜固有层,激活黏膜免疫反应;相反,乳杆菌产生的蛋白酶可进一步分解人胃蛋白酶部分降解的麦醇溶蛋白肽或铜绿假单胞菌生成的免疫原性肽,有效降低这些多肽分子的免疫原性。益生菌被认为是可使肠道菌群恢复至抗炎状态的重要治疗手段,然而目前尚缺乏支持益生菌用于治疗CeD的数据。
三、结语
肠道生理微结构如黏液层厚度、肠上皮细胞密度和受体位点对微生物与宿主间的相互作用、肠屏障完整性的维持和免疫系统的调控都有一定影响,细菌与上皮细胞之间的正常通讯是维持内环境稳态的关键因素。肠道菌群不仅参与维持胃肠道健康,对疾病的发生、发展也起有重要作用。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多数研究都停留在关联分析阶段,缺乏特定细菌参与消化系统疾病发生的直接证据。然而,肠道菌群在宿主生理功能中的作用可能揭示了菌群失调与宿主功能紊乱之间的某种联系。益生菌可纠正肠道菌群的失衡状态,特别是益生菌的代谢物,如细菌素、抗菌肽以及SCFAs等,具有良好的抗炎作用。研究、开发与肠道其他微生物和谐共处的益生菌组合、促进内环境稳态是当前相关研究领域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