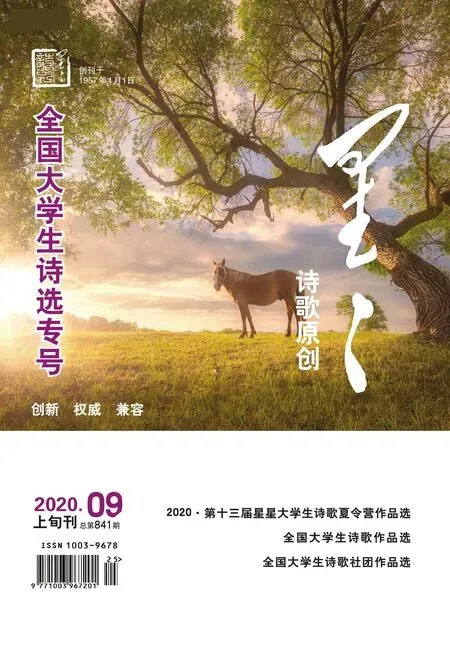雏菊(组诗)
同 频
喜欢就是原地不动,因为星河还在那里,
没有风。
松涛如沸,斗转星移,
相爱是这个庸碌人间配不上的另一种同频,
从拥挤的人潮中达成共识。
牧羊记
我梦到一片田野,我在田野里放羊。
羊在吃草,我躺在草垛上数羊,
羊群每少一只羊,
天上就多一朵发出“咩咩”声的白云。
我在河里挤了个橙子,一个黄昏从
下游的羊群远道而来,递给我火把与蝉鸣;
我接过火把,在蝉鸣上用力划擦。
借着光,我把羊赶回圈。
白亮的星辰漫天闪烁,月光给田野覆上
绵密的被子,唯独不见月亮。
在醒来的那一瞬间,
我正扬起鞭子,从羊圈里撵出一轮白月亮,
月亮把月光踩得咯吱咯吱响。
锁
“哥哥,你为什么要锁车子?”
“因为我怕把车子弄丢。”
“哥哥,那你为什么不把我也锁了?”
“因为我就是你的锁。”
“你是我的锁?那谁是我的钥匙?”
我不再言语,只是摸了摸你的小脑袋,
圆圆的,像星球在人间的投影。
小傻瓜,哪有什么钥匙,
只有新锁才能解开旧锁,
你的未来将会在锁与锁之间交接。
雏 菊
黄昏醉了酒,云色酡红,与秋千满撞入怀。
一只风铃撩拨雨后的禾束,湿漉漉的花架下
少女穿着水蓝的衣裙,乳房细小,踮起脚尖;
一朵雏菊模拟她的姿态,噘着小嘴,倾倾欲坠。
刹 那
白鹭捕鱼刹那,夕光正弹奏着湖泊的起伏,
俯身衔走了一小片柳色佐食;
彼时有风来过,枝条每一寸骨骼
都在噼啪作响,粉白的袈裟披在树的肩头,
那是三月在无声处奔腾。
遇见泡桐刹那,回眸顾盼啄破啤酒的气泡,
我本就不胜酒力;
此时有你来过,我体内每一块骨骼
都在噼啪作响,与鸟儿用啁啾擦亮期许一样,
都是为了被春天认领。
我欠母亲一把伞,在每一个雨季
二十一年前的照片,你刚好在我这个年纪。
路过雨季的野径,你曾身穿绿裙
扶着花苞的背脊静坐
若沾雨的梅子,只弯折了一根冷硬的枝条,
半个夏天就俯首称臣。
二十一年后的照片,我刚好在我这个年纪。
你扶着厨房的炊火,人到中年,言语肿胀,
喜欢打盹,喜欢照镜子里眼角的皱纹。
我说,“雉尾纹容纳着生活的引力。”你并不喜欢。
我又说,“雉尾纹是雨季遗赠给眼帘的彩虹桥,连通你我。”
你开始失神。
不得不说,母亲是一个笨手笨脚的女子,
还是那个雨季,你只顾收我的虎头鞋,
把年轻的自己晾在一边,这一晾
就是二十一年。
我欠母亲一把伞,在每一个雨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