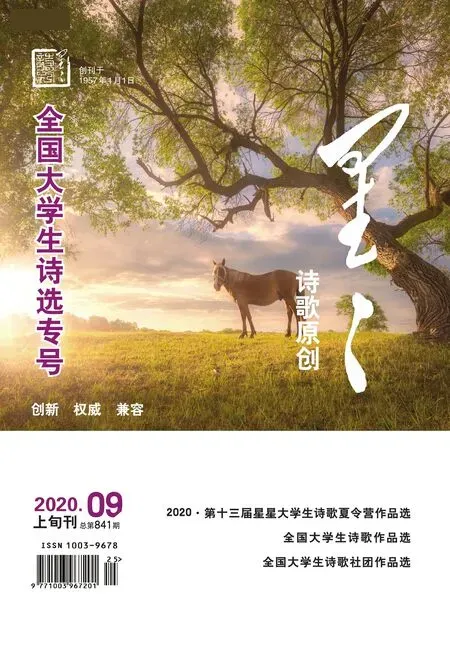宛如一丛构树(组诗)
小的恩赐
把苦难说得小点,说成蚊子的某次叮咬
把休假、落日和车票说小一点
说成:一座孤独的城,端坐在远方
把某次残疾说小一点
说成一不小心落下了点东西
把乌鸦的嘴说小一点,说成一根发针
把红绿灯说小一点,说成带色儿的灯泡
把救护车说小一点,小到玩具的模样
把住房贷款说小一点,就一个厕所钱
把呼吸说小一点,给口气就行
最后,把自己说小一点吧
小成一个袖珍娃娃,灿烂地舞蹈
一丛构树
母亲总像黑夜,降临
在我身后;宛如一丛构树。
她火急火燎闯进肃穆的庙宇,
说出粗劣的乡音,
祈望庇佑发生在多难的家中。
那时她就不管自己的叶子。
那锯状的三角冠叶,白净的绒布。
——小时候,我劈打构树,
作为我淘气的惩恶扬善的对象。
因为它遍地丛生,旺盛地活命。
像一朵朵绿色的火,
结满了诱人的红果。
在修复伤口后,它们没有退避。
挂着白色乳汁的枝条,
在那片旺盛的毛草地,在那片
只有母亲知道的我玩耍的地方。
水珠一颗
水珠一颗推动另一颗
蜣螂在推动粪球翻过沙丘
却反复失败;家燕企图飞越
石头和风蚀岩组成的撒哈拉
沙鸣声像海浪
沙丘的曲线如同海浪的波纹
——电视屏幕的闪动中
非洲如此贴近于我,斑马迷人的黑白条纹
从鼻子辐散到臀部
(打斗中,强健的雄性赢得芳心
获得交配权后,骑跃而上)
讲解词提到有关非洲的秘密
六千年前,雨带南移,稀林草原退除
而这都归根于地球的一次抖动
偏离了原有的自转轨道
在繁衍过程中
宇宙的神秘被我忽略了
以为自然的平衡就是宇宙的平衡
劳 动
接受命运折腾的父亲,
开始将自己拱手让人。
他发誓不能成为菩萨,
生活的茧铸他成一把生锈的利刃。
他一生都没有读完过一本书。
念及此处,我脑海里的风越吹越大。
太阳上也长满了风霜。
他拿单布衫裹紧自己。
在雪夜,在夏日,
摸黑才爬进家庭这个无底洞。
他像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一样,
抱着昏黑的信念:因为皮肉结实,
神的刀子会避开自己;
因自己汗涔涔地劳动,
神明或许会突然出现。
墙 壁
我忽略了墙壁的存在。
但它们没有忽略我。
在事情的再三督促下,我撞见了它。
冷峻的外表和灰冷的内心。
这多么像我。我埋头走路的时候,
谁也喊不回我。我只与自己为伍,
这叫爱我的人憎恨。
现在墙的存在让我憎恨,
因为我冒着热气,撞见了它,还是在
大庭广众之下。路人们有些讶异。
我流出了血迹,薄薄一层,贴在额头。
仿佛看见了墙体的灵魂,
在刹那间。因为我有些发晕,觉得
世界被撞静止了。这种感觉
就像一个壮汉遇见了另一个赤膊的壮汉。
因为庞大,而总是被忽略的墙壁,
它终于发声了;此时我不再
能轻易穿过它留给我的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