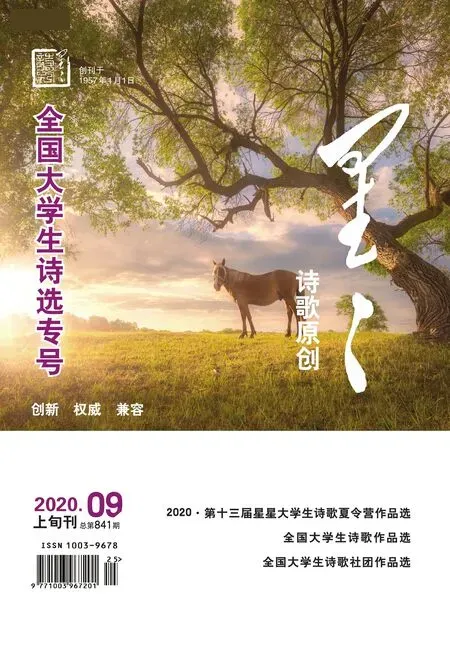1897,或毕业歌(外一首)
如果你生于1897,一个尚不存在我的母校的
空旷年代。比空旷更寂寥的,是你都不知道
这,也将是你的母校。王府遥映着荒草
我们的母校如蚕叶上的幽灵,拖着残阳的血渍
千疮百孔地游荡
一岁时你缩在乳母胸口,来到我错过四年的
蓝绿色地铁站。第一次目击鲜血的你
觉得它跟日落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向上,一个向下
一同降落的还有垂帘般的校门,如刽子手怀里
钝锉的断头台。你吮着笋尖一样细嫩的小手指
把肃杀秋声嚼得奶声奶气
1912年,我21岁的时候,你才15岁
与荡妇同名的双脚和书签似的短发,立在申报的
正反两面。战舰如海葬的鲸鱼,成群结队
破釜沉舟。你的小船刚刚挂起面朝着扶桑的帆
我的归舟却早已沉在浮梁水底
长江铮铮的珊瑚,每一朵都是我不得不爱的枯骨
低头,深深吻向襁褓中的牌坊
还君明珠,不如还君明月光:
孩子……哦,好吧,弟弟:你未来的母校里,依旧会有桃花
点缀于水榭高楼,像在谧谧夏夜里
躲手绢的萤火虫。月白色的衫子有什么难以忘怀?
只要走得够远,你甚至还会见到
月白色的眼睛
1936年,我18岁的时候,你39岁
红砖黛瓦的民国,师生恋像无数花径未扫里
丛生的鹅卵石。再多酒,再多桥,再多云
都与我们无关——先生,我们去看雪吧?
对,“何时杖尔看南雪”的那个雪
也是历史从今以后,最后一场地道的红楼飞雪
我在国文门学到的,全是天文知识:比如一千年
青天里的太阳和月亮,才会碰头一次
上回的是李杜,下一轮的金风玉露
用的是年号还是公元纪年?死神替我推着你的摇椅
告诉我: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阳关千叠
我要认不出你了。
先生,我再也不看文学史了
谁说死亡就比白头更迟?都是骗人的
我和梅花,都不相信
1952年,你55岁的时候,我19岁
沙暖睡着的鸳鸯被迁徙到清冷湖畔
喝着奶粉长大的我,直到骨质变成骨殖
也不懂猜忌与背叛,何以成了人类磨牙时的口粮
我法律上的“爱人”是你生死簿上的凶手
换句话说:我的丈夫,是你的儿子
历史出奇地讽刺:新文化的阵营,最终还是要归根
旧王朝的园林——这难道不是不伦?
楼船画桥早已葬身烈火
我脚下的石舫,是皇室最后一颗舍利
跳下去的那一刻,我迟疑了:不是怕水冷
而是怕湖底的旗头与花翎,仍要竖着吊梢眼
演绎阴间的“人言可畏”。于是,入水的时候我反复念诵
一个最暧昧的“殉道者”的自谓
我只能在心里记住,一个你都不知道的
殉情人的身份——千秋万载,都不会名正言顺
春草渌水,我赤脚踩在苔藓未干的额发上
提着两只温顺的白鸽子。远远看到你也光着脚
迎面走来,手上是两朵展翅的白玉兰
晚霞氤氲中,你我唯一信任的香气
只是洗发水潮湿的余韵,浑然不知什么叫
千古流芳。自由的单车从无数黑夜里喧嚣而过
只有我们的几位老师,还在固执地写竖排繁体
还在不懂事地,传授一些唐诗宋词里的春天
1984年,你20岁的时候,我也20岁
你低头对我说:
“等了你一百年,你终于来了。”
闲情赋
久候的茶杯垂钓出了
酒杯的感觉。碧螺敞开圆鼓鼓的胃口
迎送一尾尾的春如线
太五月。鱼的纲目都长成了藻类植物
瓷器的水底早已万事俱备,只欠一只寄居蟹
长久的居家开始现形:天长地久
原来是一只猫。我用分针的韵律开始摆弄这条
残雪压枝犹有橘的大尾巴
挠得时间开始发痒,挠得空气
也变得毛茸茸的——记住噢,两小时后
我的猫饼要翻面。白色偏多的这一面
得多涂些奶酪
直到我融化成外酥里嫩的阳光
床单已经兜不住我了。我像收网的四点半
一样蔓延,见到两只脚的一切
都想像尾生一样,抱住不放
或者说,“抱柱不放”
“你不可以言而无信的哦
……你若有心,吃我这半条儿小鱼干。”
拿鱼做相濡以沫的聘礼
是我们猫与猫之间才懂的黑话
一种奇异的依恋——想做你的猫
胜过做你的女儿。难怪陶渊明倾心于
当她的梳子,胜过当她的身体发肤
偏心穿过她肩上的垂柳,如折扇梳过歌声
我是在你每一寸无需裸露的肌肤上
都可以覆盖的身外之物
猫乃流体,随物赋形
我是你的遮遮掩掩,也可以是
你的青山遮不住
我像好奇一只蜻蜓一样好奇你
好奇心,让我提早捉光了今夏所有的蝉
旷日持久,听起来像旷古里
养了颗耳朵会动的毛线球
躺在你的床上看窗外,像一条鱼眺望大海
早知道,就应该在三月的时候
做你的一只石榴
只要我不开口,你永远不会猜到
我身体里还睡着那么多
从不会因天亮而苏醒的
蜜蜂最喜欢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