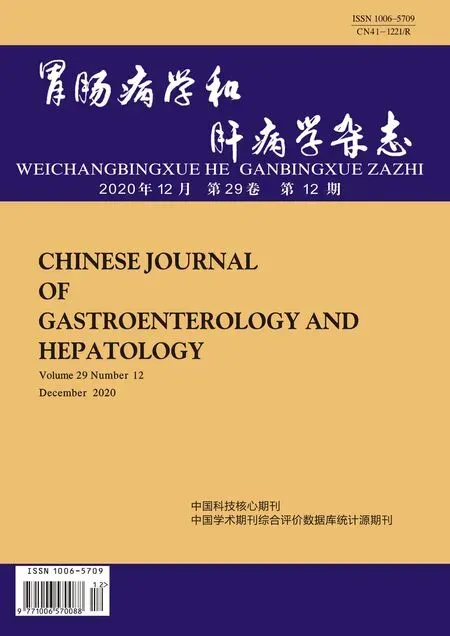精氨酸代琥珀酸合成酶1在肝细胞癌进展中的作用和潜在价值
罗 霞,史青苗,余祖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河南 郑州 450052
原发性肝癌是世界范围内第六大常见癌症,也是第四大癌症相关死亡原因,每年新增病例约84.1万例,年死亡病例约78.2万人[1],而我国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人数约占全球的一半[2]。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占原发性肝癌的75%~85%。手术切除是早期HCC治疗的首选方法及主要治疗方式,但多数患者在就诊时已经发生肝内和肝外转移,失去手术治疗机会。只有不到30%的患者适合采用手术切除、肝移植、动脉栓塞等治疗方案[3-4]。而目前获得批准的治疗HCC的一线分子靶向药物索拉非尼和仑伐替尼、二线药物瑞戈非尼以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虽为HCC患者带来了福音,但因不良反应大以及耐药问题等存在很多局限性[5-7]。因此,探讨HCC的发生、发展及其转移复发的分子机制,寻找潜在的特异性分子生物靶点对于HCC诊断治疗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尿素循环是将剧毒氨转化为尿素排出体外的氨解毒代谢途径[8-9]。通过同位素标记相对和绝对定量(isobaric tags for relative and absolute quantification,iTRAQ)技术以及Western blotting等技术对大血管侵犯肝癌患者的肿瘤组织及临近正常组织进行蛋白组学定量差异分析显示,尿素循环中的5种关键酶氨基甲酰磷酸合成酶1(carbamoyl phosphate synthetase 1,CPS-1)、鸟氨酸氨基甲酰转移酶(ornithine carbamoyl transferase,OCT)、精氨酸代琥珀酸合成酶1(argininosuccinate synthetase 1,ASS1)、精氨酸代琥珀酸裂解酶(argininosuccinate lyase,ASL)、精氨酸酶(arginase)在HCC组织中均异常下调,而尿素循环中关键酶的异常下调可通过促进HCC大血管的侵袭和转移而降低HCC患者的总体生存期[10]。其中,ASS1可催化天冬氨酸和瓜氨酸转化为精氨酸代琥珀酸,后在ASL的作用下裂解生成精氨酸。精氨酸是一种半必需氨基酸,是合成多种影响癌细胞生长、增殖、侵袭、免疫和转移的代谢物的底物。HCC患者由于ASS1低表达或表达缺失不能从头合成精氨酸,极度依赖外源性精氨酸维持必要的生物学过程,因此,HCC呈现出明显的精氨酸依赖现象。最近的研究证明,ASS1的过表达可明显抑制肝癌细胞的体外转移潜能和体内肺转移率,相反,敲除ASS1可显著提高体内外肝癌细胞的侵袭能力[11]。本文结合该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从ASS1的生化结构、功能调节及其在HCC进展中的作用和潜在价值,以期为HCC的精准治疗提供新的特异性分子治疗靶点及新的治疗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1 ASS1的生化结构及功能调节
ASS1是哺乳动物体内普遍存在的酶,主要在肾脏和肝脏门脉周围肝细胞和内皮细胞中表达,其表达水平因细胞的种类、分化程度和作用而异。ASS1也是一种高度保守的肝细胞胞浆酶,主要参与精氨酸的合成代谢。人类ASS1蛋白的生化结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核苷酸结合域、合成酶带和多聚螺旋C端,构成同源四聚体结构。ASS1基因位于人类第9号染色体上即9q34.11~9q34.12,有16个外显子和1 236个碱基对组成的开放阅读框。在ASS1的第1个内含子和启动子中有大量富含CpG的区域,通常不受甲基化保护的区域被称为“CpG岛”,在肿瘤发生过程中易发生高甲基化。在进行甲基化特异性PCR检测及甲基化测序时显示,肝癌组织中ASS1的甲基化水平明显高于正常肝组织和癌旁组织,同时存在很多从C到T的突变。肝癌组织中ASS1缺失的机制可能是DNA编码ASS1的甲基化所致,也导致了肿瘤对外源性精氨酸的依赖[12]。DNA甲基化模式的异常破坏与癌变发生有关,可能导致基因沉默和恶性细胞转化[13]。因此,通过利用甲基化抑制剂5-氮杂胞苷(5’AZA)逆转甲基化状态,使细胞重新表达ASS1。
ASS1表达的调控是复杂的、动态的。肝脏中的ASS基因高度表达,其中细胞外激素、营养物质如氨基酸、细胞因子和转录因子等主要在转录水平上调节ASS1基因表达,如(1)糖皮质激素、胰高血糖素和胰岛素,特别是在发育和成年期控制该基因的表达;(2)饮食蛋白摄入刺激ASS基因的表达,对谷氨酰胺等特定氨基酸具有特异性;(3)转录诱导因子,ASS1的基因表达是由结合在ASS1近端启动子上E-box的正性转录因子c-Myc与Sp4和负性转录因子HIF-1α交互作用调控的。(4)ASS1在缺氧和酸性状态下的表达下调,ASS1在肿瘤中的表达下调可能导致上游代谢物如谷氨酰胺和氨(来源于谷氨酰胺)的积累,这些代谢产物可以碱化肿瘤细胞内的pH,维持肿瘤细胞膜两侧pH的梯度,对肿瘤细胞的存活、侵袭和迁移至关重要,从而为肿瘤细胞提供了氧化还原和pH值的优势,提高了其存活率[14]。
2 ASS1在肿瘤中的作用
肿瘤细胞中尿素循环酶的表达下调导致了肿瘤中普遍存在尿素循环障碍,随后激活了CAD复合酶体(包括氨基甲酰磷酸合成酶Ⅱ、天门冬氨酸氨基甲酰转移酶和二氢乳清酸酶)的活性使氮源流倾向于嘧啶的合成,使细胞核中嘧啶与嘌呤的不平衡,增加了嘌呤突变为嘧啶的风险,这与肿瘤的发生密切相关[9]。CAD复合酶体是指位于同一条肽链的一种多功能复合酶,有利于以均匀的速度参与嘧啶核苷酸的合成。胞浆中的天冬氨酸不仅作为ASS1的底物提供氨基,同时也是CAD复合酶体的底物。在ASS1缺乏或低表达的肿瘤细胞中,胞浆中的天冬氨酸异常积累,导致CAD异常活化,同时增加了底物的可用性,促进了CAD催化嘧啶核苷酸的合成,为肿瘤细胞的增殖提供了原料[15]。因此,对于ASS1表达缺陷或低表达的肿瘤,尤其是那些对精氨酸降解酶产生耐药性的肿瘤,可将天冬氨酸剥夺作为一种额外的治疗干预策略。
随着对ASS1在肿瘤发生和发展中作用的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ASS1与肿瘤的增殖、侵袭、转移和预后密切相关。ASS1的低表达与骨肉瘤患者术后肺转移和不良临床结局显著相关,临床前试验中ASS1的过表达在体外抑制了肿瘤生长,因此,ASS1可能为骨肉瘤患者转移和不良反应的预测生物标志物[16];另外,ASS1作为黏液纤维肉瘤的抑癌基因,具有抗血管生成、抗增殖、抗氧化及抗侵袭的特性,与黏液纤维肉瘤的分级和分期的增加密切相关,并且可以独立的预测肿瘤的无转移生存期和疾病特异性生存期[17]。与这些结果一致,约51.6%(64/124)的鼻咽癌患者存在ASS1表达缺失,与晚期鼻咽癌分期、DNA甲基化和临床侵袭性相关,ASS1的表观失活与显著降低的总体生存期和无转移生存期相关,也表明该ASS1具有肿瘤抑制功能[18]。
然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不同类型的肿瘤中,ASS1在临床结果中的作用可能不同。已有研究表明,ASS1在胃癌中呈高表达,并与胃癌侵袭性及预后不良呈正相关[19]。另外,ASS1在结直肠肿瘤中也呈高表达,可以作为人类原发性结直肠肿瘤的上调靶点,应用ASS1抑制剂或敲除ASS1时会削弱结直肠肿瘤的致病性[20]。肿瘤细胞中ASS1的基础表达差异可能导致相反的临床结果。ASS1在肿瘤中的双重作用机制尚不清楚,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探索其潜在机制。
3 目前ASS1在HCC进展中的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肿瘤转移是癌细胞进入血管系统向远处器官转移和侵袭的复杂过程,是各种癌症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HCC转移定义为经门静脉播散的肝内转移,或肝外转移到其他器官,包括肺、淋巴结、骨骼和肾上腺。肝内和肝外转移发生在半数以上的HCC切除患者中,肝内转移更为常见。肿瘤转移是一个复杂的多步骤过程,包括原发肿瘤细胞的扩散和血管内灌注,循环肿瘤细胞的存活,新的微小转移瘤的形成,以及随后这些肿瘤细胞向临床可检测到的转移病灶的增殖,是由复杂的细胞内和细胞间信号传导网络级联调控的,因此,肿瘤转移仍是肿瘤进展机制中最不为人知的部分[21]。肝癌细胞的血管侵犯、转移和复发导致了患者的预后不良。HCC的侵袭转移发生机制复杂,多种信号通路参与其中。其中,上皮-间质转化(epith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是肿瘤侵袭过程中的关键事件,上皮细胞层失去极性和细胞间的相互作用导致细胞骨架重塑[22]。肿瘤细胞分泌的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s)是一类锌依赖性内源性蛋白酶,通过降解基底膜启动血管生成[23]。这改变了细胞与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了内皮细胞通过所形成的间隙向肿瘤细胞的聚集迁移,导致新血管的增殖和形成[24]。
在研究人类磷酸激酶阵列探索ASS1调控的蛋白磷酸化参与HCC的转移时,发现pSTAT3Ser727是ASS1调控的最特异的下游激酶。当敲除ASS1时,pSTAT3Ser727水平升高;当ASS1过表达时,pSTAT3Ser727水平下降,证明了STAT3蛋白表达与ASS1的表达有关。在HCC中,STAT3的缺失可能会显著损害通过下调ASS1而增加的转移能力,表明ASS1通过STAT3调节HCC的侵袭[11]。信号传导与转录激活因子3(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STAT3)因含有SH2和SH3结构域,故可与特定的含磷酸化酪氨酸的肽段结合。在丝氨酸蛋白激酶的作用下,位于丝氨酸(Serine,Ser)727位点的STAT3被磷酸化后形成pSTAT3Ser727,pSTAT3Ser727蛋白有三个方面作用:(1)可发生聚合成为同源或异源二聚体形式的活化转录激活因子,进入胞核内与靶基因启动子序列的特定位点结合,促进其转录;(2)pSTAT3Ser727蛋白可诱导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生成,促进血管生成;(3)激活MMPs等转移相关蛋白的表达,MMPs通过激活生长因子、抑制细胞凋亡、诱导血管生成、增强组织再生等多种途径促进肿瘤进展[25]。其中,MMP-9是STAT3通路激活后产生的下游蛋白因子,几乎能够降解基质中的各种蛋白质成分,破坏肿瘤细胞侵袭的组织学屏障,在肿瘤侵袭转移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
在进行全人类基因组微阵列分析时,发现STAT3信号通路中识别ASS1调控的差异基因的合适靶点是分化抑制蛋白-1(ID1)[11]。ID1又称DNA结合抑制因子,是一种螺旋—环—螺旋(HLH)结构的负性转录因子调控蛋白,这类蛋白不具有与特定DNA结合的能力,可与碱性HLH家族成员形成异二聚体,抑制转录因子的DNA结合和转录激活能力。ID1在人和小鼠肝脏肿瘤及HCC细胞系中均有较高表达,可通过MAPK/ERK通路在转录水平上调控ID1的表达。敲除ID1基因抑制了好氧糖酵解和谷氨酰胺分解,使代谢向有氧糖酵解方向转变,促进了HCC细胞的代谢重新编程[26]。而在敲除ASS1时,HCC细胞中的ID1水平升高;当ASS1过表达时,ID1水平下降[11]。而STAT3是ID1表达的又一重要调控因子[27],pSTAT3Ser727在HCC患者中表达与ID1呈正相关。因此,ASS1过表达可能通过抑制pSTAT3Ser727通路负向调控ID1表达,从而抑制HCC进展[11]。但ASS1调控HCC进展的具体分子机制仍需继续探讨。
4 ASS1在HCC进展中的潜在价值
大血管浸润(macrovascular infiltration,MVI)是HCC患者预后差的因素之一。MVI主要是指肿瘤侵犯门静脉或肝静脉主干或分支[28]。利用iTRAQ等技术对大血管侵犯HCC患者的肿瘤组织及邻近正常组织进行蛋白组学定量差异分析显示,尿素循环中的五种关键酶(CPS1、OTC、ASS1、ASL、ARG1)在大血管侵犯的HCC组织中均呈异常下调,尿素循环失调通过促进HCC大血管的侵袭和转移抑制HCC总生存率。尤其是尿素循环中的关键酶失调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大血管侵犯HCC患者的潜在治疗靶点[10]。在使用比较蛋白组学研究HCC患者转移复发的生物标志物时,发现三种生物标志物(HSP70、ASS1、UGP2)联合应用对HCC转移复发的预测比单独甲胎蛋白(AFP)具有更高的灵敏性和特异性,转移性复发性HCC组中ASS1的表达明显低于非复发性HCC组,亦表明ASS1可作为转移性复发性HCC的预测生物标志物[29]。最新的研究表明,ASS1的稳定沉默促进了HCC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而过表达则抑制了HCC细胞在体内和体外的转移[11]。
5 ASS1与HCC的治疗
HCC由于ASS1低表达或表达缺陷失去独立合成精氨酸的能力,只能利用细胞外精氨酸维持其生长代谢需要,因此,可通过剥夺细胞外精氨酸靶向杀伤这类肿瘤。癌症模型的临床前研究已经证明了精氨酸剥夺会导致线粒体功能障碍、活性氧积累、DNA和染色质损伤,最终导致癌细胞死亡[30]。精氨酸脱氨酶是催化精氨酸转化为瓜氨酸的酶,经聚乙二醇修饰的聚乙二醇化精氨酸脱亚胺酶(ADI-PEG 20)抗原性减弱、半衰期延长。之前的研究[31]证实了ADI-PEG 20在肝癌患者的Ⅰ/Ⅱ期临床试验中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最近的ADI-PEG 20应用于既往治疗失败的晚期肝癌患者中的Ⅲ期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结果显示,ADI-PEG 20单一疗法未显示出中位生存期的益处,但具有很好的耐受性,目前旨在延长精氨酸耗竭时间和协同ADI-PEG 20效应的策略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32]。
前文已经阐述了尿素循环障碍导致的嘧啶合成增加不仅会促进肿瘤增殖也会由于嘧啶与嘌呤比例失调而引起DNA、RNA甚至是蛋白水平的突变,使肿瘤细胞对免疫疗法更敏感[9],同时,使用ADI-PEG20治疗对正常细胞影响并不明显,因此,ADI-PEG20可以尝试与化疗或免疫疗法联合使用治疗HCC。近来的研究数据也已证实了ADI-PEG20与5-氟尿嘧啶(5-FU)的联合治疗比单一治疗更能导致ASS1阴性的肝癌细胞死亡[33]。另外,ADI-PEG 20和改良的FOLFOX6(mFOLFOX6)联合治疗难治性HCC和其他进展期胃肠道肿瘤的Ⅰ期临床试验显示出令人鼓舞的初步疗效,且是安全的、可耐受的,目前的Ⅱ期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亦正在进行中[34]。
6 未来展望
本文聚焦尿素循环关键限速酶ASS1在HCC中的进行情况,分析HCC患者中ASS1的异常表达对HCC恶性表型的调控机制及其在HCC进展中的作用和潜在价值,通过靶向肿瘤细胞的异常代谢为HCC临床的精准治疗提供新靶点及理论支持。但由于目前对ASS1如何具体调控HCC进展的分子机制尚不清楚,未来需结合基础生物学研究和大型临床试验进一步探讨ASS1调控HCC进展的具体分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