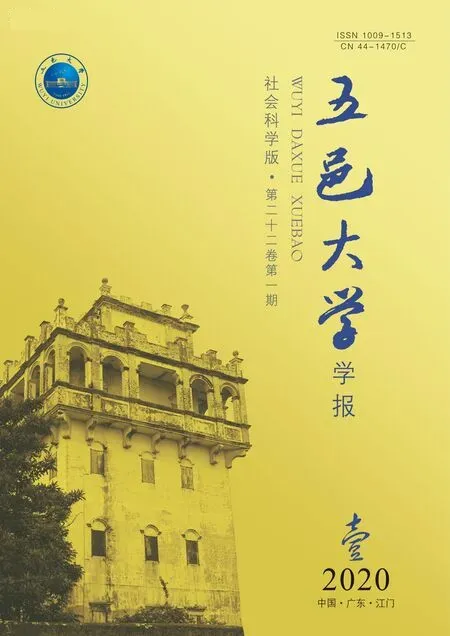论《荀子》对老庄的批评
庞光华,范思敏
(五邑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尸子·广泽》篇称:“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己皆弇于私也。”《尸子》说百家“己皆弇于私也”,这并非公论。百家争鸣都是为了救世,并非出于私心。但《尸子》说百家各有自己的根本主张以至相互批评,这却是事实。《吕氏春秋·不二》称:“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这些学术概括十分精准。荀子是我国文化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也是极其伟大的批评家。《荀子·尧问》:“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 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世不详察,云非圣人,奈何!天下不治,孙卿不遇时也。德若尧禹,世少知之;方术不用,为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为纪纲。呜呼!贤哉!宜为帝王。”《汉书·艺文志》称:“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整部《艺文志》称大儒的只有荀子一人。东汉徐干《中论·序》:“予以荀卿子、孟轲怀亚圣之才,著一家之法,继明圣人之业。”徐干已经以荀子为“亚圣”,并非专指孟子。《中论》卷上《贵言》:“仲尼、荀卿先后知之”,以荀子与孔子并称。《中论》卷下《审大臣》:“昔荀卿生乎战国之际而有睿哲之才,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明拨乱之道”,高度推崇荀子睿哲之才。《文心雕龙·才略》:“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称荀子为“学宗”。《颜氏家训·勉学》:“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称荀子为硕儒。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二十三《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称荀卿明王道。战国末期的儒家经典多由荀子学派所传。
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荀子》是非常重要的批评性巨著。《荀子》对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几乎都有精到的批评,只对少数几家(如《管子》、《商君书》)似乎没有提及。先秦学术只有《庄子·天下》篇对墨子等六家的评论可与《荀子》对诸子的批评媲美。《荀子》的评论名篇《非十二子》为学术界所熟知。本文专门讨论《荀子》对老子和庄子思想的批评。
一、 批评老子“有诎而无信”的思想
《吕氏春秋·不二》称:“老耽贵柔。”这是对《老子》思想最为精确的概括。《荀子·天论》对老子思想尖锐攻击:“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 则群众不化。”《荀子》用非常简洁明净的语言指出了慎子、老子、墨子、宋子各家的偏颇之处,尤其是批评了老子。
老子在先秦时代就非常著名,影响很大,思想家们对老子往往非常崇拜,很少批评。例如整部《庄子》对老子极为推崇。老子在《庄子·天下》篇中几乎没有缺点,被赞美为“古之博大真人”。《韩非子》《淮南子》《文子》《史记·老子列传》对老子也都极为推崇。再如《吕氏春秋·贵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将行,请所以治鲁,周公日:‘利而勿利也 。’荆人有遗弓者, 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 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 。’老聃闻之曰 :‘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孔子在先秦思想家中有“贵公”之评,考《尸子·广泽》篇称:“孔子贵公。”而《吕氏春秋》称老聃至公,超过孔子,可见对老子推崇备至。
《孟子》对杨朱学派和墨子学派猛烈攻击,但一字不提《老子》。笔者分析是因为《孟子》学派没有注意到《老子》一书,并非读过后置之不理。只有《荀子》能精辟地指出“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其中“诎”即“屈服”,“信”就是“伸”。只知道顺从屈服,不懂得抗争和奋斗、积极进取的价值,这是老子贵柔思想的缺陷。《荀子》并不完全否定柔顺,例如《修身》篇称:“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同时《荀子》也认可刚强的价值。但《荀子》认为二者都不能走极端。如《荀子·不苟》称:“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同篇又称:“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荀子·臣道》篇:“柔而不屈。”足见《荀子》有深刻的辩证法思想。《荀子》肯定“信(伸)”的价值,就是肯定儒家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人生精神。
然而,详考《老子》一书,论述“诎、屈”的地方很少,且并无褒赞之义。如第5章:“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第45章:“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今本《老子》和马王堆帛书本《老子》甲乙都没有出现“诎”字。郭店楚简本《老子》乙称:“大成若诎,大植(直)若屈。”今本《老子》的这两处“屈”和楚简《老子》的“诎”“屈”都没有特别的褒义或哲学上的含义,不能表现出《老子》特别崇尚“屈(诎)”的思想,因此《荀子》说“老子有见于诎”的“诎”就是相当于今本《老子》的“柔”,而不是今本《老子》的“屈”。考《老子》第10章:“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第36章:“柔弱胜刚强。”第43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52章:“守柔曰强。”第55章:“骨弱筋柔而握固。”第76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第78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这些都是《老子》一书对“柔”的崇尚。
要注意的是楚简本《老子》乙篇明显将“诎”与“屈”二字分用不混:“大成若诎,大植(直)若屈。”“诎”与“成”相对,“屈”与“直”相对。则简本《老子》的“诎”与“屈”不同,对应今本第45章:“大成若缺。”“诎”与“缺”古音相通,当训为“缺”。或“诎”训“折”,《广雅》:“诎,折也。”无论简本的“诎”训“缺”还是“折”,都不是《老子》所崇尚的。
因此,《吕氏春秋·不二》称:“老耽贵柔。”这表明《吕氏春秋》的作者所看到的《老子》与帛书本和今本很相似,与郭店楚简本《老子》不同,因为郭店楚简本《老子》没有“贵柔”的思想,甚至没有出现“柔”字。而《荀子》的作者所看到的《老子》却不是楚简本《老子》、帛书本《老子》或今本《老子》,因为三者并没有“有见于诎,无见于信”。“诎”“屈”的思想在各本《老子》中没有显著的位置。《庄子·天下》篇对关尹、老子的评论,也没有提到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的思想。《天下》篇所依据的《老子》应该与《荀子》所依据的《老子》是不同版本。
如果不存在独立于简本、帛书本和传世本之外的古本《老子》,那么可以认为《荀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的“诎”就是帛书本和今本《老子》的“柔”。只是《荀子》以“诎”来替换了“柔”。在《老子》中,“柔”与“刚”相对,而《荀子》将“刚柔”换成“诎信(伸)”,这要么有古本《老子》的根据,要么是《荀子》对《老子》做了自己的解读和概括。《荀子》的这种释读是非常重要的,与《老子》本身的思想实际上有所不同。因为依据《老子》的“刚柔”来立论,就不会得出“有柔而无刚,则贵贱不分”的逻辑结论;必须是“有诎而无信”,才会有“贵贱不分”的结论。“信(伸)”的意思是成功而得志,大致就是世俗常说的获得荣华富贵。如果人人都不去追求荣华富贵,全部都淡泊无为、安于贫苦,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出现“贵贱不分”的状况。当然,也可能是《荀子》对《老子》的整体思想归结为“有见于诎,无见于信”,而不仅仅是对“刚柔”的替换。《荀子》的批评确实击中了老子学术的要害,至今有重大价值。
二、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的思想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荀子曾批评庄子:“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这个批评十分尖锐,是儒家学派对庄子学派的第一次反击,但还停留在单纯的谴责上。而《荀子·解蔽》对诸子有精辟的批判:“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埶而不知智。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欲谓之道,尽嗛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埶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也。”这一段对六家的批判极其敏锐精湛,尤其是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由天谓之道,尽因矣”,寥寥数语抓住了庄子学术的主要弊病,非常精警。
荀子的学生李斯有一段话可以理解为对庄子学派的抨击,考《史记·李斯列传》:“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这段话分明是批判当时流行的庄子学派的“非世而恶利,自讬于无为”,认为这违反人性,即“非士之情也”。这是对战国后期流行的老庄学派倡导的无为主义的尖锐抨击。李斯的这段精彩言论遥承《论语·微子》孔子传授给子路的话:“不仕无义。”李斯对庄子学派的批评,是属于荀子学派的立场,只是二者角度稍有不同:荀子批评庄学只知道顺从自然、因循无为,而不知道创造;李斯批评庄学安于贫贱,不肯有所作为。但这两种批评其实出发点是一致的。《吕氏春秋·论威》:“人情欲生而恶死,欲荣而恶辱。”可见《吕氏春秋》也认为“人情欲荣而恶辱”犹如“欲生而恶死”,教人完全安于贫贱是不可能的。《吕氏春秋·情欲》《吕氏春秋·适音》亦有类似表述。《韩非子·难三》:“人情皆喜贵而恶贱。”人有情欲是不可避免的,是无法完全消灭的。这可以看作是庄子学派的批评①。儒家经典《尚书·仲虺之诰》:“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尚书·泰誓上》:“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都肯定人民天生有欲望。因此,老庄否定欲望,就是违反人情,甚至违反人性。
《荀子·天论》关于“天人之分”的论述非常精辟,强调了“天”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存在,与人间的治乱祸福无关。《天论》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同篇又曰:“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这些论述表明天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并不介入人间的治乱祸福。这是对先秦早已存在的“天人感应”观的批判。《荣辱》篇、《法行》篇亦有类似表述。此可比较《庄子》关于“至人”的说法。考《庄子·逍遥游》:“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田子方》:“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田子方》又曰:“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田子方》引老聃曰:“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离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庄子·知北游》:“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达生》:“子列子问关尹曰:至人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
《庄子》提及“至人”的地方很多,都是指能够体达天地之德并顺应天地之自然的人,这样的至人无为无己。这显然与《荀子·天论》的“至人”大异其趣。《荀子·天论》的“至人”正是要“明于天人之分”,也就是要懂得天地自然与人类的不同之处,天道与人道不同。《荀子·儒效》说得最分明:“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足见天道地道与人道不同,不能用天道地道来规范人道。这固然是对《庄子》顺天乐天思想的批判,也是对先秦就有的“天人合一”观念的否定②,是《荀子》很伟大的思想。天道是不变的,与人间祸福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天论》称:“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这里明确指出天道无形而难知。既然天道无形,难以窥测,所以圣人并不希望能够理解天道,只可专注于人为的努力。春秋时代郑国的执政大臣子产早有过类似的见解。考《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子产认为“天道”与“人道”不相关联,且“天道”难以理解。子产关于“天道”“人道”的观点是《荀子》的先驱。更早的《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明确指出“下民之孽”是人祸,不是天灾。《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闵子马见之,曰:‘子无然!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无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奸回不轨,祸倍下民可也’。”鲁国的闵子马所称“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奸回不轨,祸倍下民”都是说祸福都是人为,非关天道③。西汉前期的《淮南子·人间》:“夫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这也是反对天道祸福的迷信。实则,庄子学派十分崇拜的《老子》已经说过天道与人道不同。考《老子》第77章:“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这种思想已经看到了天道与人道的区别。但是《老子》认为“天道”高于“人道”,只有圣人才能达到“天道”,《老子》同章称:“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这分明是说只有圣人才能遵循天道,而不会顺从一般的人道。因此《老子》的“天道人道”观与《荀子》不同,《荀子》认为天道、地道、人道是平等的,只有性质的不同,没有高低的不同。《淮南子·氾论》称:“故苌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主术》:“偏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人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行,则有以任于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则无以与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则无以与道游。”这些思想都是强调天道与人道有别,同于《荀子》而异于《庄子》④。
《庄子》一味追求顺从天道、自然无为,轻视人为的努力。在《荀子》看来,《庄子》将“天”当作“道”,就会一切都顺从天地之自然,不会去努力创造,所以《荀子》批判庄子“尽因也”。“因”就是“因袭、顺从”而不加改造,也就是“述而不作”。《天论》对“天”的态度正相反:“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这里鲜明地表现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强调了人为的努力,而不是一味顺天或应天。“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也是强调人为努力的极端重要性。《荀子》对庄子的批判真可说是一针见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从此可见荀子素来对庄子不满。庄子这位杰出的思想家在荀子学派眼中,只是“猾稽乱俗”。言虽过当,未为无故。
《韩诗外传》卷四承袭《荀子·非十二子》的观点,称庄周等十家也属于“夫当世之愚,饰邪说,文奸言,以乱天下,欺惑愚众,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是“顺非而泽,闻见杂博,然而不师上古,不法先王,按往旧造说,务自为工,道无所遇而人相从,故曰十子者之工说,说皆不足以合大道,美风俗,治纲纪,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愚众,交乱朴鄙,则是十子之罪也”。《非十二子》并没有包括庄子,但《韩诗外传》按照儒家的思想传统,认为庄子也应在批判之列。
实则,孔子就曾对隐逸思想有所批评。《论语·微子》对长沮、桀溺的批评,也可以看做是儒家对老子、庄子的批评。孔子说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其积极的救世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对后世的知识精英的人生态度有很大的影响。《微子》篇孔子教子路对一位隐士说:“子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这段话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隐士最集中的批评。《微子》称:“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可以说老子、庄子都是“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孔子对此采取了不同的人生态度⑤。杨雄《法言·问道》篇称:“或曰:庄周有取乎?曰:少欲。至周罔君臣之义。”《法言》批评庄子“罔君臣之义”,这完全是承袭了孔子对隐士的批评。《荀子》对老庄之学的批判,与孔子对隐逸思想的批判有所不同,更加具有哲学性,而不仅仅是一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唐代的韩愈《送陆歙州诗序》称:“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韩愈认为《庄子》一书的思想是“以其荒唐之辞”对周代末世的批评,这就仅仅看到了《庄子》思想的社会性,而没有看到其哲学性,谈不上是对《庄子》有深度的批评。
三、结 语
《荀子》一书对诸子百家的批判固然十分深刻精湛,但一般只是批评各家的种种弊端,没有赞美各家的优长。而《庄子·天下》、《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汉书·班固传》所载班彪《史论》、班固《汉书·艺文志》、刘勰《文心雕龙》、刘昼《刘子·九流》、刘知几《史通》以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这些批评性名著都能够在其批评中优劣并举,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这是我国一个优良的学术传统。《荀子》批判百家确实尖锐深邃,但对百家之善绝口不提,似稍逊恕道。宋朝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杨倞注荀子二十卷》对《荀子》颇有微词,固然不无偏见,但也代表了学术界的一种意见。
注释:
① 例如《庄子·列御寇》曹商使秦的故事、《庄子·秋水》楚国有神龟的故事和惠子相梁的故事,都体现出《庄子》有蔑视荣华富贵的思想。荀子学派和《吕氏春秋》认为这违反人情,不可能做到。
②例如《尚书》《左传》就有某地发生了自然灾害就意味着国家的政治腐败、有冤假错案。如有凤凰来临、黄龙出现,就意味着国家有吉祥的事情发生;天上的一个明星突然黯淡,就意味着人间某伟人要死去。这就是“天人感应”的观念。
③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见《嘉定钱大昕全集》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卷三《天道》条称:“古书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祸福而言。”举《古文尚书》《易传》《春秋传》《国语》《老子》《孟子》为例。
④《淮南子》的某些思想明显与《荀子》相通。例如《荀子·不苟》称:君子“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而《淮南子·氾论》称:“故圣人论事之局曲直,与之屈伸偃仰,无常仪表,时屈时伸。卑弱柔如蒲苇,非摄夺也;刚强猛毅,志厉青云,非本矜也,以乘时应变也。”两相比照,《淮南子》明显参考过《荀子》。又如《荀子·劝学》:“螾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而《淮南子·说山》:“蚓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饮黄泉,用心一也。”《淮南子》显然依据了《荀子》。
⑤孔子并不完全否定隐逸文化,《微子》中他对伯夷叔齐有较高的评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