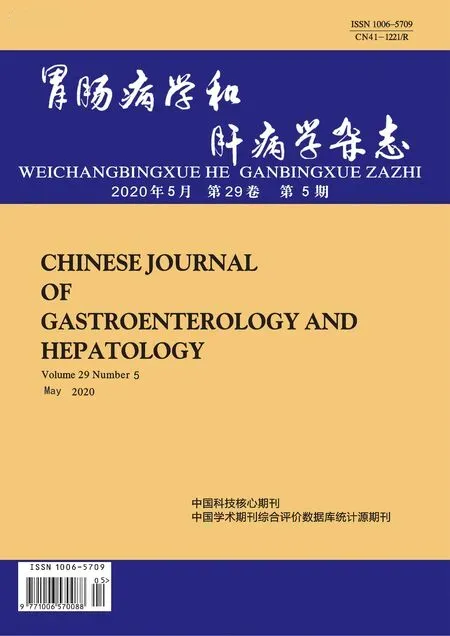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合并消化道、肝脏、胰腺多系统损伤研究
姚诚子,刘自珍,贺 娜,冯 巩,郭 菡,弥 曼
1.西安医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2.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致病因子,是不同于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一种新型β属冠状病毒[1]。2020年2月,国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将这种病毒命名为SARS-CoV-2,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的疾病命名为COVID-19[2]。病毒基因检测显示:COVID-19基因组和SARS-CoV具有86.9%的核苷酸序列同源性[1],都是以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ngiotens inconverting enzyme 2,ACE2)为受体进入细胞,引起一系列病理改变[3]。研究[4]发现,ACE2在人体各个组织广泛表达,SARS-CoV-2与机体细胞膜上的ACE2结合后进入细胞,引起局部和全身的炎症反应、氧化应激、组织及细胞缺氧等,可导致多器官功能损伤甚至衰竭,严重者导致死亡。本文主要是基于目前的研究报道,对COVID-19呼吸系统外的消化道、肝脏、胰腺等相关多脏器损伤进行分析,有助于临床医师对COVID-19患者的综合治疗,动态监测疾病进展,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
1 SARS-CoV-2相关性消化道损伤
COVID-19患者常以发烧和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但也会出现腹泻和恶心等消化道症状[5]。且部分患者以消化道症状为首诊表现,甚至比SARS-CoV和MERS-CoV更明显,提示消化道可能是SARS-CoV-2感染的靶器官。相关尸检病理结果也报道了食管、胃和肠管黏膜上皮不同程度变形、坏死、脱落[6]。这为COVID-19合并消化系统的损伤提供了更加科学的依据。COVID-19确诊患者中存在胃肠道症状的比例在不同研究中略有不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收治的89例COVID-19患者的临床资料发现[7],腹痛5例(5.6%),腹泻4例(4.5%),恶心4例(4.5%)和呕吐3例(3.4%)。钟南山团队对全国1 099例COVID-19确诊患者临床数据进行分析[8],恶心、呕吐发病率为5.5%(55/1 099),腹泻发病率为3.7%(41/1 099)。史济华等[9]对54例确诊COVID-19患者的研究表明:消化道症状在COVID-19患者中并不少见,以腹泻(22.2%)和恶心(14.8%)为主,其次为呕吐(9.3%)和厌食(9.3%),腹痛(3.7%)、腹胀(1.9%)少见,尤其是普通型患者,腹泻患者比例高达26.3%,仅次于常见症状发热、乏力和咳嗽。徐风华等[10]对251例COVID-19患者的病历资料研究分析,消化道症状主要表现为纳差(33.9%,85/251)、腹泻(12.0%,30/251)、恶心呕吐(7.6%,19/251)和腹痛(1.2%,3/251)。方丹等[11]对COVID-19住院患者的消化系统表现进行分析,发现79.1%的患者起病1~10 d后出现消化道症状,其中腹泻、恶心、呕吐和腹痛患者比例分别为22.2%、29.4%、15.9%、5.0%。Wang等[12]对138例COVID-19确诊的患者研究表明,COVID-19消化道症状发生率较高,腹泻、恶心、呕吐和腹痛发病率分别为10.1%、10.1%、3.6%、2.2%,且其中14例(10.1%)患者先出现腹泻、恶心症状,后出现发热、呼吸困难。Jin等[13]研究了74例确诊COVID-19并伴有腹泻、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的患者,高达28%的消化道症状患者无呼吸道症状。
目前,公认的SARS-CoV-2传播途径为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另外,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有研究[14]发现,在SARS-CoV-2感染确诊患者的胃肠道、唾液和尿液中能检测到SARS-CoV-2,而且在疾病中晚期,肛拭子的病毒核酸检出阳性率高于咽拭子阳性率,提示COVID-19患者的粪便或消化道分泌物也可能有传染性。钟南山院士团队[15]在确诊患者的粪便、胃肠道破损黏膜及出血处分离出了SARS-CoV-2病毒,明确了SARS-CoV-2入侵消化系统的证据。同SARS-CoV的致病机制相似,SARS-CoV-2通过与呼吸道黏膜表面的ACE2结合,引起呼吸系统感染。而ACE2除了在肺部肺泡Ⅱ型上皮细胞(alveolar type Ⅱ epithelial cells,AT2)高表达以外,还在结肠的上皮细胞、食管上皮细胞,以及小肠上皮细胞中高表达[16]。此外,另一篇基于单细胞测序的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表明[17],ACE2是由结肠细胞特异性表达的,并且与病毒进入和释放相关的基因表达呈正相关,功能富集分析显示,ACE2的表达也与肠道炎症和区域免疫应答等具有相关性,进一步说明胃肠道可能是SARS-CoV-2感染的潜在途径。病毒感染破坏肠上皮细胞,造成吸收不良,腺体分泌失衡,肠道神经系统过度活跃,最终导致腹泻、腹痛等消化系统症状[18]。
2 SARS-CoV-2相关性肝脏损伤
肝脏是人体的解毒器官,临床研究发现,COVID-19部分患者会出现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等肝酶水平的异常升高,特别是重症患者的肝酶升高更为明显,提示这些患者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肝脏损伤。尸检结果发现[6]肝脏体积增大,肝细胞变性、坏死,间质内可见少数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和(或)中性粒细胞浸润,为COVID-19合并肝损伤提供了更加确切的依据。
Chen等[19]单中心研究报道了99例COVID-19患者的临床特征,其中43例(43.40%)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肝功能损伤,其ALT与AST值分别比正常水平高出28%和35%,甚至有1例患者发生了严重的肝损伤(ALT 7 590 U/L,AST 1 445 U/L)。刘敏等[20]对30例医务人员COVID-19的临床特征分析:部分患者出现肝功能异常,重症患者肝酶升高更为显著。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报道[21],COVID-19合并肝功能损伤在轻型和普通型患者中少见,而在重型和危重型患者中多见。考虑到重型或危重型亚组病例需长期接受药物治疗,特别是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其常见不良反应包括肝功能损伤。由此得知,COVID-19伴发肝功能损伤与危重症患者密切相关,且多为继发性损伤,在提高该病认识的同时,其病因及机制值得深入探讨。
但对于SARS-CoV-2导致肝损伤的机制尚不完全明确。研究[22]发现,ACE2在正常肝组织中只在胆管上皮细胞表达,而在肝细胞中表达极低,并指出COVID-19患者的肝功能损伤可能不是由于病毒与肝细胞直接结合,而是由胆管细胞功能障碍和药物诱导、全身性炎症反应等原因造成。另有观点认为[23],SARS-CoV-2感染可激活人体免疫细胞,造成免疫细胞的过度聚集、促炎细胞因子大量释放,进而导致肝损伤。因此,“炎症风暴”也是引起肝损伤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明确指出[6],目前COVID-19尚无有效的抗病毒治疗药物,可以使用干扰素-α、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利巴韦林治疗,而这三种药长期或大量使用均会对肝功能产生不良作用。临床发现α-干扰素对于失代偿期肝病患者可能产生严重的不良反应,注射干扰素可导致肝功能轻度或中度异常,如血清ALT、AST升高,慢性乙肝和丙肝患者应用干扰素可能导致病情恶化[24]。因此,慢性肝病患者应慎用干扰素。研究报道利托那韦能明显抑制肝细胞增殖,诱导染色质边缘化、线粒体嵴消失、核固缩和胞质空泡化,并通过caspase级联系统诱导肝细胞凋亡[25],通过加重氧化应激,诱导炎症反应,加速肝脏损伤。然而,目前仍缺乏药物性肝损伤导致肝酶升高的直接证据,且无确切证据表明预防性应用抗炎保肝药物可减少药物性肝损伤的发生。临床医师应该了解哪些药物有潜在肝毒性,并在使用这些药物时加强肝功能检测,及时发现肝损伤,评估治疗用药效益/风险比,调整治疗方案。
3 SARS-CoV-2相关性胰腺损伤
研究发现,胰腺可能是SARS-CoV-2攻击的靶点之一。Liu等[26]对COVID-19患者的队列研究中发现,1%~2%的非重症患者和17%的重症患者有胰腺损伤,其中5例重症患者CT扫描可见胰腺病变,以胰腺局灶性增大或胰管扩张为主,未见急性坏死。Wang等[27]最近对52例COVID-19患者研究报道,SARS-CoV-2相关性胰腺损伤发生率并不低。其中17%的患者出现淀粉酶或脂肪酶异常,提示胰腺损伤,且在胰腺损伤患者中,有6例出现血糖异常,可能是由于ACE2受体在胰岛细胞中高度表达,SARS-CoV-2感染导致胰岛细胞损伤,进而导致急性糖尿病[27]。胰腺损伤发生的机制主要包括SARS-CoV-2的直接细胞病变效应,或间接的全身性炎症和免疫介导的细胞反应,导致器官损伤[27]。此外,部分重症患者在入院前已发生胰腺损伤,部分患者曾服用非甾体抗炎药和糖皮质激素,应考虑药物性胰腺炎的可能性[26]。
4 SARS-CoV-2相关性其他系统损伤
4.1 SARS-CoV-2相关性心脏损伤大量临床研究发现,SARS-CoV-2对心脏有潜在影响,特别是已经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Huang等[5]对41例首批确诊COVID-19患者的回顾性研究报道,5例(12%)出现了心肌损伤,主要表现为超敏肌钙蛋白Ⅰ水平上升。Chen等[28]对150例COVID-19患者(包括普通型和危重型)分析发现,约20%的COVID-19患者会发生心功能损伤和心肌损伤,14.7%(22/150)COVID-19患者存在肌钙蛋白水平的升高,31.3%(47/150)COVID-19患者存在脑钠肽水平的升高。相关病检结果显示[6]:心肌细胞可见变性、坏死,间质内可见少数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和(或)中性粒细胞浸润,更加明确地提示了心肌损伤。
SARS-CoV-2感染相关性心肌损伤的机制尚不清楚。鉴于目前的研究,可能主要原因如下:(1)病毒直接引起心肌损伤。ACE2是SARS-CoV-19感染的重要靶点,SARS-CoV-2通过其表面刺突的S蛋白与细胞膜表面的ACE2结合,侵染宿主细胞[29]。ACE2能够将部分血管紧张素Ⅱ(AngⅡ)转化为Ang-(1-9)或Ang-(1-7),而后者对心血管疾病具有调节血压、抗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和改善心功能等重要作用[4]。由此可见,SARS-CoV-19感染后,机体ACE2途径受到严重影响,其对抗RAS系统的心血管保护作用也可能会被削弱。(2)炎症因子:COVID-19患者存在多种炎症细胞因子显著升高[5, 19],短时间内广泛的炎症反应,可能导致心功能出现障碍,同时还会引起冠状动脉斑块,容易诱发潜在的心血管疾病。(3)药源性心肌损伤:在COVID-19患者的治疗中,相关药物的毒副作用也会引起心肌损伤[20]。
4.2 SARS-CoV-2相关性肾脏损伤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SARS-CoV-2可能导致广泛的肾脏损伤。一项对59例COVID-19患者的研究报道[30],63% COVID-19的患者出现蛋白尿,19%和27%的COVID-19患者出现血肌酐和尿素氮水平的升高,部分患者出现肾脏CT异常。在入院当日,40%的COVID-19患者尿蛋白阳性,提示患者早期就存在肾脏损害[30]。相关的尸检结果可见[6]:肾小球球囊腔内见蛋白性渗出物,肾小管上皮变性、脱落。这也明确提示COVID-19患者伴发肾脏病理性损伤。该病发病机制可能与ACE2有关,ACE和ACE2共同表达于小鼠和人近端肾小管的刷状缘,ACE2通过降解AngⅡ为Ang-(1-7)以抵消ACE的作用[31]。SARS-CoV-2感染后,会下调ACE2水平,ACE/ACE2的比率明显升高,诱发或加重肾脏损伤[32]。
4.3 SARS-CoV-2相关性中枢神经系统损伤SARS-CoV-2并不总是局限于呼吸道,它们还可能侵入中枢神经系统,诱发神经系统疾病。尸检病理结果报道:可见脑组织充血、水肿,部分神经元变性,提示神经系统损伤[6]。鉴于SARS-CoV与SARS-CoV-2高度相似,很可能SARS-CoV-2潜在的神经侵袭在COVID-19患者急性呼吸衰竭中起重要作用[33]。据报道[12],在36例ICU治疗的COVID-19重症患者中,有89%的患者接受了机械通气,这些危重症的COVID-19患者很有可能出现谵妄状态。这可能是SARS-CoV-2病毒感染后,AngⅡ的表达升高,从而导致病理学的改变、微血管渗透性增加和炎症反应[33]。SARS-CoV受体除了存在于呼吸道黏膜和肺泡上皮之外,还广泛存在于神经元的细胞膜[34]。SARS-CoV-2的神经侵袭特性很可能是COVID-19重症患者出现呼吸窘迫的原因之一[33]。
4.4 SARS-CoV-2对凝血功能的影响临床研究报道,COVID-19患者中50%可出现D-二聚体升高,重症及死亡患者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及D-二聚体升高的程度显著高于轻症及幸存患者[15],提示凝血功能异常。COVID-19进入机体后,可迅速被体内的病原相关分子模式(PAMP)识别,患者免疫系统被过度激活,释放大量炎症因子[5],可引发免疫反应介导造血系统损伤,或造成周围自身细胞的免疫炎性损伤、微血管体系损伤、凝血系统异常激活、纤溶及抗凝系统抑制等。
4.5 SARS-CoV-2相关性精神心理障碍重大突发灾难性疾病可引发一场精神应激风暴,人们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恐慌及失眠问题,隔离患者心理应激的程度更高[35]。COVID-19发生突然,传播迅速,除了对人们躯体上的伤害之外,对心理也可能产生不良影响。赵倩等[36]对106例COVID-19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进行评估,结果显示,抑郁、焦虑、躯体症状的检出率分别为49.06%、56.60%、69.81%,且24.53%的COVID-19患者有自残自杀观念。因此,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的救援策略和预案中,应纳入人文关怀、心理干预等措施,针对不同人群的不同心理问题进行心理危机干预,以减少疫情带来的心理损伤和后续的心理社会问题。
总结,COVID-19不仅会引起呼吸系统的典型症状,还会引起其他多脏器的损伤,导致疾病快速进展、恶化,甚至增加病死率。我们应该积极预防及延缓COVID-19的进展,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目前COVID-19还在全球蔓延,人类对疾病的认识仍然有限,还需要做更多研究,丰富相关的技术信息,更新相关知识,进一步推进科学预防。让我们共同努力,从全球卫生安全出发,加强国际合作,采取科学合理的防疫措施,战胜COVID-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