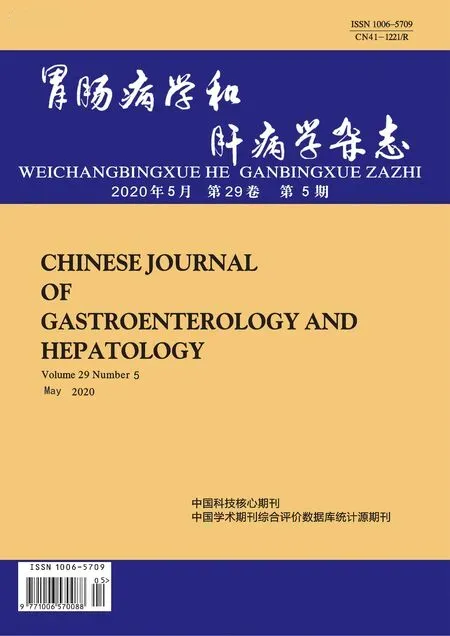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并发肠道微生态紊乱的可能机制研究
秦甜甜,康生朝,张久聪,刘 鑫,于晓辉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消化内科,甘肃 兰州 730050
由冠状病毒引发的肺部感染性疾病是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重大卫生公共事件。2020年1月7日,我国科学家首次在武汉患者的呼吸道标本中分离出致病冠状病毒,并完成基因组全长测序[1]。2月11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分别将该病毒及其引发的疾病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2-3]。
COVID-19的危害极大,具有传播迅速、致病性强、预后不良等特点。其临床表现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重症患者多在发病1周后出现呼吸困难或低氧血症,严重者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这是导致病情恶化死亡的重要原因[4]。临床还发现部分患者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随之出现不同程度的水电解质紊乱,加重原发疾病的程度。但目前为止,尚无文献报道其确切的发病机制。本文从肠道微生态紊乱角度出发,就其发生的可能机制作一概述。
1 SARS-CoV-2及其致病机制
SARS-CoV-2是一种新型β属冠状病毒,有包膜,颗粒呈圆形或椭圆形,常为多形性,直径60~140 nm,属于单链RNA病毒。与引起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相关冠状病毒有明显区别,其基因组序列约由29 kb构成,拥有10个基因,可有效编码10个蛋白[5],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目前研究发现,不同于MERS CoV以CD26作为其细胞受体[6],SARS-CoV-2与SARS-CoV相似,主要通过其表面的S蛋白识别靶细胞上ACE2受体进入细胞[7],从而引起炎症因子迅速增加,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和多器官衰竭发生[8]。
2 SARS-CoV-2感染与肠道微生态紊乱
肠道菌群是由细菌、病毒、真菌及古生菌等构成的正常微生物群,有1013~1014个。在生理情况下,肠道微生物群构成的稳态能够增强机体防御能力、促进机体健康,在一定范围内处于动态平衡。而病毒感染[9-10]等因素可引起肠道微生物组成及功能改变,从而打破肠道微生物与宿主之间长期相互制衡的状态,引起肠道微生态紊乱[11]。Qin等[12]研究发现,H7N9感染者益生菌数量减少而致病菌数量增加,即双歧杆菌数量减少,而沙门菌、大肠埃希菌和肠球菌数量增加,引起黏膜免疫功能失调及肠道损伤。Chen等[13]研究发现,H1N1感染可引发肠道菌群失调及肠道损伤,而中草药鱼腥草多糖降低了致病菌属弧菌和芽孢杆菌的相对丰度,逆转其引起的肠道菌群组成变化。对于重症肺炎患者来说,肠道菌群会发生破坏,紊乱的肠道菌群能够异常调节肠道的炎症状态,影响肠-肺免疫轴,加重病程中全身炎症反应及应激反应的程度[14-15],COVID-19也是如此。Xu等[16]发现,对于SARS-CoV-2感染合并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症状的患者,经检测存在肠道微生态失衡,具体表现为肠道的乳酸杆菌、双歧杆菌等有益菌明显减少,给予营养支持和补充大剂量肠道调节剂后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消化道症状,减少细菌移位和继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4]中也提到可使用肠道微生态调节剂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可预防继发细菌感染,但确切的机制并不清楚。
3 COVID-19并发肠道微生态紊乱的机制
目前已在COVID-19患者粪便标本中发现并分离出SARS-CoV-2[17-18],并对伴随消化道症状的COVID-19患者检测发现存在肠道微生态紊乱[15]。这提示SARS-CoV-2在造成肺部感染的同时可能还会引起肠道菌群失调,这可能是患者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的主要原因。目前,研究发现SARS-CoV-2主要和人类细胞表面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Ⅱ(ACE2)结合[19],而ACE2不仅在肺AT2细胞中表达,而且在食管上皮、回肠和结肠的吸收性肠上皮细胞中也高表达[20],提示SARS-CoV-2不仅感染呼吸系统,也可能会直接影响消化系统。ACE2是小肠细胞上皮中氨基酸转运体B0AT1表面表达所必需的,可以参与蛋白质的消化及氨基酸的吸收[21]。当ACE2缺少时,色氨酸不能有效吸收,小肠mTOR途径活性降低,进而导致小肠Paneth细胞抗菌肽表达受损,而后者又可导致肠道菌群成分改变,最终对上皮损伤引起的肠道炎症的易感性增加[22]。Hashimoto等的研究表明,ACE2突变体可以降低抗菌肽的表达,并出现肠道微生物组成的改变[23]。而ACE2作为一种羧肽酶,可催化AngⅡ为Ang (1-7),后者进一步与细胞表面受体Mas结合,形成ACE2-Ang(1-7)-Mas轴,从而通过调控多种信号通路活化,发挥舒张血管、改善内皮功能、抗氧化应激、抗增殖、保护血管内皮等生物学效应[24-25]。而众多研究表明,多种信号通路与Mas的关系密切,Ang(1-7) 能够通过Mas调节下游的ERK、P38、JNK信号通路,起到抑制炎性反应的保护作用[26-27]。此外,Ang(1-7)也可通过Mas受体直接抑制或促进肠道平滑肌细胞释放一氧化氮[28],从而干预NF-κB信号通路活化,减轻肠道的炎性损伤[29]。
SARS-CoV-2的S蛋白可通过与肠上皮细胞表面的ACE2受体结合,使得ACE2表达降低,一方面可使ACE-Ang Ⅱ轴和ACE2-Ang(1-7)轴调控失衡,Ang(1-7)表达降低及Ang Ⅱ水平相对或绝对升高,使上述保护作用明显受限,而细胞因子表达升高,诱发炎症风暴,出现全身炎症反应。另一方面,可抑制ACE2-Ang(1-7)-Mas轴,从而干扰ERK、NF-κB和JNK等多种信号通路活化,合成并释放大量炎症因子并损伤肠上皮屏障功能的同时,也可通过下调抗菌肽表达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此外,ACE2表达降低还可影响色氨酸的吸收,抑制小肠mTOR途径活性,抗菌肽表达受抑,大大增加内毒素和细菌移位引发的内毒素血症和内源性感染,从而引起并促进炎症介质的瀑布反应,造成组织广泛损伤,出现消化道症状甚至多脏器功能衰竭,导致COVID-19患者预后不良。
4 展望
SARS-CoV-2感染已成全球蔓延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严重危害人们生命健康。目前人类对SARS-CoV-2的认识仍十分有限,虽多项研究提示SARS-CoV-2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引起肠道菌群失调,从而增加患者的不良预后,但尚未有直接的临床证据证明其并发微生态紊乱的具体机制,未来仍有待于国内外学者的不断探索。本文以肠道微生态紊乱为切入点,为未来靶向治疗COVID-19提供一些可借鉴的思路,从而短时间内控制疫情蔓延,降低病死率,以挽救更多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