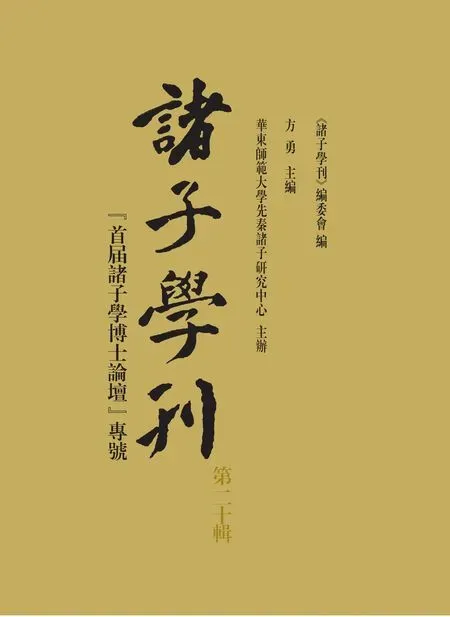論《莊子》“魚樂”爲一譬喻
(臺灣) 周詠盛
内容提要 濠梁之辯,指莊子和惠子對於“魚樂”的一場辯論。以“魚樂”爲核心,大致可以分爲兩派詮釋: 其一,以“魚樂”爲一心理狀態陳述,反映出莊子個人的修養境界與直覺。其二,以“魚樂”爲一客觀事實陳述,强調惠施對莊子得知“魚樂”的質疑。我們嘗試提出第三種詮釋: 以”魚樂”爲一譬喻陳述,即莊子之所以提出“魚樂”,是要據此來譬喻己樂。此詮釋的特别之處大致有三: 其一,《秋水》的最後三個段落,皆是以動物之樂爲核心的譬喻,共用類似的架構。其二,莊子言“請循其本”代表一種嚴格的溯源對應關係,且“濠上”具有畫龍點睛的重要意義。其三,“魚樂”原是一譬喻,但惠子卻以客觀事實的角度來解讀之,這可以説是一種誤解。在以動物譬喻爲核心的三段文本之中,由於對方預設並局限於特定觀點,所以他們誤解了莊子,而莊子以動物之樂喻己樂,就是要以譬喻來回應這些誤解。透過分析動物譬喻可以得知,樂是指主體與自然環境間的和諧互動,而動物譬喻的主要功能,不僅在於説明樂,更是要回應誤解,進而批判導致誤解的原因。據此,動物譬喻是莊子呈現樂與建立其樂之主張的方法。
關鍵詞 莊子 濠梁之辯 魚樂 譬喻 寓言
一、 魚樂: 心理狀態或客觀事實
濠梁之辯,是《莊子·秋水》最後一個段落,其原文如下: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1)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606~608頁。
這段百字左右的文本,其中並無艱澀字詞,但對於這場辯論當作何解,又是誰勝誰負,歷來卻無一致的看法。莊惠兩人的辯論焦點,集中在“莊子是否知道魚樂”這一問題的正反意見上。在諸多詮釋中,認同莊子者有之,反對莊子者有之,各有各的分析角度與論據,以下是一個大致的歸納與整理。
第一類詮釋,是以“魚樂”爲一心理狀態。《莊子》一書當中,不乏對理想人格的描寫,除了至人、神人、聖人等稱呼以外,也藉由許多具體人物的描寫,來呈現理想人格的修養境界,如南郭子綦與顔成子遊所言的吾喪我,以及孔子與顔回所言的心齋、坐忘等,都强調了主體泯滅一切區分與是非判斷,不以物我之間有着必然或根本的對立。
這樣的情況,在概念上,可以用“一”來概括,代表了主客合一或主客融合的觀點。這具體表現爲文本中的“道通爲一”“萬物皆一”“其一,與天爲徒”“與天爲一”等,它們都强調了一種物我無對,不預設自己和萬物之間有根本的區别,不以自我局限在身體之内,而是可以打破物質上的界限,進而感通萬物。
那麽,這樣的修養境界,或説是一種心理狀態,可以用在濠梁之辯的詮釋上嗎?許多注家們,不約而同地用“一”來説明莊子的立場,試圖把“一”和“魚樂”的解讀連結起來。對於如何看待“魚樂”的語意,這類詮釋至少有以下兩種延伸解讀:
其一,莊子作爲理想人格的代表,已達到了“一”的境界。在注解濠梁之辯時,王叔岷引邵雍之言“此盡己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物皆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並總結説莊子是達理體情,物我如一(2)王叔岷《莊子校詮》第二册,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8年版,第638頁。。顯然地,這是從莊子的個人修養出發來理解“魚樂”,也就是説,莊子言“魚樂”是反映出他自己已達到了感通萬物的境界。所以,“魚樂”只是莊子體認萬物的例子之一,根據其人格修養,莊子所能够感通的事物並不只是魚而已。
其二,莊子是基於藝術或審美的心態,來做出“魚樂”的判斷。也就是説,莊子把“魚樂”當成是一個審美對象,在此情況下,莊子把自己的感受,投射或轉移到魚的身上。如李澤厚説:
魚的從容出遊的運動形態由於與人的情感運動態度有同構照應關係,使人産生了“移情”現象,才覺得“魚之樂”。其實,這並非“魚之樂”,而是“人之樂”;“人之樂”通過“魚之樂”而呈現,“人之樂”即存在於“魚之樂”之中。所以它並不是一個認識論的邏輯問題,而是人的情感對象化和對象的情感化、泛心理化的問題。莊子把這個非邏輯方面突出來了。而且,突出的又並不止是這種心理情感的同構對應,莊子還總是把這種對應泯滅,使魚與人、物與己、醒與夢、蝴蝶與莊周……完全失去界限。(3)李澤厚《華夏美學》,見李澤厚《美學三書》,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頁。
由此可知,在這類解讀中,“魚樂”要呈現的其實是人之情感,或者反過來説,人之情感轉移或投射到了“魚樂”之上。在此過程之中,物我的界綫往往模糊不清,甚至根本被取消,使得人與萬物之間没有任何隔閡。值得注意的是,當物我互通、主客的分離不再,主體就能透過直覺來體會事物,而不需要任何媒介(4)某些學者强調了“魚樂”來自直覺,如康中干説:“但實際上,莊子‘循’的是他一貫堅持的直覺法,即他所謂的物我兩忘的‘物化’法或‘齊物我’法,在此法中他强調的是認識主體與認識物件間的整體性或合一性,即認識主體與認識對象間的同構性,這就是格式塔心理學所謂的‘同構’或美學中所説的‘移情’,這樣一來人與魚之間就有了‘情’上的相通了,人會將自己的快樂移入魚身上而賦於魚‘樂’的成分。”見康中干《從觀魚看莊子哲學的主旨》,《湛江海洋大學學報》第23卷第2期,2003年4月,第45頁。又如沈維華説:“莊子則是站在美學層面上,以主觀直覺的方式觀世間事物,是以物我合一,莊子和魚渾一整體,彼此有可能相知相通。”見沈維華《莊子“魚之樂”析論》,《國文學志》27期2013年12月,第145頁。。當然,這和第一種解讀並不互斥,而有相互支持的可能(5)顔昆陽《從莊子“魚樂”論道家“物我合一”的藝術境界及其所關涉諸問題》,《中外文學》第16卷第7期1987年12月。。
從《莊子》書中屢屢强調理想人格與修養境界,以及常常以莊、惠兩人的言説爲一高一低的對比來看,這類詮釋能够與《莊子》其他篇章相應。這類詮釋采取了主客合一、莊子與萬物通爲一的觀點,於是“魚樂”在濠梁之辯一開始就被肯定。
李澤厚説,惠子是邏輯的勝利者,而莊子是美學的勝利者。陳鼓應亦言,莊子持觀賞事物的藝術心態,而惠子持認知事物的分析心態(6)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10~411頁。。也就是説,這類詮釋除了描述莊子的境界,也涉及了莊、惠雙方在心態上的重大差異。我們在《莊子》一書當中,可以找到許多强調小大觀點差異的例證,如以下引文: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7)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第11頁。
這裏刻意突顯出了小知與大知、小年與大年的差異: 有的生物只能存活一年,甚至一天之中;但有的生物只把數百數千年當作一個寒暑而已。《秋水》説得更爲生動:“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虚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它們都表明,時間上或空間上的局限,將進一步導致觀點上的局限。回過頭來看濠梁之辯,也突顯了莊、惠兩人的差異,涉及了某種心態上或視野上的對比,亦即指出了莊子體大道、惠子辯小言。成玄英對兩人差異的解釋,即是最好例證: 莊子善達物情,故知魚樂;惠子不體物性,妄起質疑(8)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第606~607頁。。
這類詮釋儘管偏重不一,但並不互斥,它們都强調了莊子自己的内在心理,而非魚本身的情況。據此,與其説“魚樂”是一個客觀事實,不如説“魚樂”反映出莊子個人的修養境界與心理狀態,其主要依據,來自於《莊子》其他篇章中對“一”的詮釋,以及其他逍遥、齊物、體道的叙述。這是基於主客合一、莊子與萬物通爲一的觀點來進行的,在此觀點之下,莊子個人的心理狀態,或説其對萬物的感通,就足以讓他宣稱自己知道“魚樂”。
至於第二類詮釋,則是以“魚樂”爲一客觀事實。惠子在濠梁之辯中的發言只有兩次,是針對莊子“魚樂”的判斷而有的,它們分别是:“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與“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如果把第一次發言看做是激問法(答案在問題反面),並且按字面來看,惠子似乎是主張: 莊子必定不能知道“魚樂”,以及惠子必定不能知道莊子所知,甚至任何主體都無法知道客體的狀態。
但一個比較弱但在日常生活更爲可能發生的解讀是,惠子認爲: 如果莊子没有好的理由,就不能説自己知道“魚樂”;同樣地,如果惠子没有好的理由,就不能説自己知道莊子所知。這是基於主客二分而有的觀點,儘管主客二分不必然導出主體完全無法認知客體,但至少代表莊子需要有好的理由或證據,來宣稱自己知道“魚樂”。
在這個解讀之下,惠子第一次的發問,雖然是偏向否定語氣,但也有詢問理由的意思在;第二次的否定語句,則是强調了没有理由就不能做出“魚樂”的判斷。也就是説,惠子認爲,對於“魚樂”此一判斷,莊子有舉證責任,他第一次的詢問,是要求莊子給出證據或理由;第二次的否定,則是給出這樣一個判斷: 如果没有理由,就不能説自己知道“魚樂”。
莊子最後的反駁:“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是否能够成立?若以”魚樂”爲一個客觀事實陳述,采取主客二分、莊子和魚二分的觀點,而莊子又没有提出足够理由或證據的情況下,答案是否定的(9)如宣穎説:“與魚全無相知之理。”即是此意。見王先謙、劉武《莊子集解·莊子集解内篇補正》,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48頁。。這類詮釋,還可以有幾種進一步的説明:
其一,“安”可以解讀成“是否”或“如何”,故“安知”也可以解讀成“是否知”或“如何知”,“是否知”並没有預設對方已知,但“如何知”則預設了對方已經知道。高柏園即説:
惠子語中之“安知”一詞當理解爲“是否知”(weather)而不是“如何知”(how)。理由是,惠子在第四段之回答”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此中,惠子“人非魚,則人不能知魚樂”之立場實甚明顯。由此可知,惠子並不是先認定莊子知魚樂,而後再問其如何知魚樂,而是問莊子能否知魚樂。(10)高柏園《莊子内七篇思想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256頁。
這是針對“安”的歧義,來説“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的成立,必須預設惠子所言的“安知”是指“如何知”,因爲“如何知”才預設了已經知道並再問如何知道。“是否知”並没有這樣的預設,因爲這個問句本來就是對“知”有所疑問,並無設定已經知或不知。若采取“是否知”的解讀,“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無法成立。
其二,“知”可以解讀成“知識”之知或“信念”之知,前者不必然代表對“知”之内容的肯定,後者則藴含了相信並認同“知”之内容。陳少明即説:
王夫之對莊子最後的反詰與詮釋,可以作爲我們的例證:“知吾知之者,知吾之非魚而知魚也。惠子非莊子,已知莊子是莊子非魚,即可以知魚矣。”“知吾知之者”中的第一個“知”字,只表明惠子已經從莊子的談話中獲取了相應的語義,但不意味着他認同了莊子的説法。這猶如我們聽到有人説謊一樣,我們知道謊言的意思,但並不相信它陳述了相應的事實或者傳達了説謊者的真正想法。所以,知道不一定就是相信。王夫之附和莊子把知道曲解爲相信,實際是犯了偷换改念的邏輯錯誤。(11)陳少明《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245頁。
這是針對“知”的歧義,來説“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的成立,必須預設惠子所言的“知”是指“信念”之知,預設了惠子的相信。若采取“知識”之知,則不見得要認同知識的内容,“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也就不必然成立。
以上兩種説法,都是基於語詞使用上可能有的歧義來立論,這雖然不代表莊子刻意曲解了惠子的語意,但卻都指出“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此一問句,在語意解讀上有着很大的空間。
除了“安”與“知”兩個語詞以外,問句本身也造成了這種解讀上的分歧,設問法本就有提問(自問自答)、疑問(真的不知答案)、激問(答案在問題反面)等數種用法(12)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問句修辭法(即設問法),可有以下幾種語意: 其一,懸問,又叫疑問,是懸示問題没有答案,讓聽者或讀者自己去尋思答案的修辭法。例如:“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其二,提問,又叫“問答法”。這是爲了提起下文而發問,答案在問題之後,即作者自問自答。例如:“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其三,激問,又叫詰問、反詰或反問。即答案很明顯的表現在問題的反面。例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參見陳正治《修辭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32頁。。若把惠子的語意解讀爲激問,即解讀爲“子非魚,不知魚之樂”這一否定句,在惠子否定莊子知道“魚樂”的前提下,“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並非一個理所當然的推論,這裏的“已知吾知之”,如前所述,只能代表惠子瞭解而非肯定莊子之説;若采取疑問解讀,則惠子可能是基於肯定莊子的立場,並進一步詢問莊子知道“魚樂”的方法或理由,據此,“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是一個可能成立的推論。
這類詮釋是基於語意分歧,來懷疑莊子“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的推論,倘若這個推論不成立,則莊子就並未對自己知道“魚樂”給出任何理由或證據,我們也就難以承認莊子真的知道“魚樂”。這是把“魚樂”當作一客觀事實,采取主客二分、莊子和魚二分而有的結論,主客二分並不藴含主必然無法知客,但莊子需要有好的理由或證據,來宣稱自己知道“魚樂”。
二、 龜、鳥、魚: 以動物之樂譬喻人樂
在這一節之中,我們將提出第三種詮釋,也就是以“魚樂”爲一譬喻。在詳細説明之前,先來看看《寓言》之中如何討論寓言: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13)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第947~948頁。
“藉外論之”,可説是一語道破了寓言作爲論述策略的關鍵,即爲了避免他人所可能有的偏見,或是已有的特定觀點,而借助其他人、事、物來達到説明的效果。如父親稱贊自己的兒子,不如别人稱贊來得有效,因爲衆人普遍認爲父親必定愛護其子,已然抱有父親會刻意稱贊其子的偏見,這時就需要藉由外人來做媒,才不會有偏袒的嫌疑。
這裏的“做媒”,其實就是指模擬方法,此方法是透過具體情境或事物的類比來説明某項主題。如庖丁解牛的寓言之中,當庖丁説明自己如何在十九年來遍解數千牛,而刀刃卻仍嶄新鋒利後,文惠君的反應是:“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這代表文惠君聽到的雖然是如何解牛,但透過某些關聯性質,他實際得知的卻是如何養生。不同於直接叙述,寓言是一種基於模擬方法的論述策略,是透過了不同事物之間的共同點,來讓他人更好地理解。
此策略必須建立在幾個先決條件之上: 其一,喻依(寓言本身)與喻體(説明對象)之間,必須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如共同的性質、作用與變化等。其二,作者和讀者雙方,都對喻依與喻體有着基本相同的認知。其三,讀者必須知道作者在某一段落或語句上使用了模擬方法,方不至於按字面上的意義去理解之。如此,作者方可“藉外論之”,透過喻依和喻體之間的共同點,來讓讀者跳脱被局限的視角,從而更易理解作者所要説明的主題。
而模擬方法及其成立的先決條件,有助於我們討論《秋水》全篇當中最後三個寓言。這三段文本,皆是涉及動物的對話,最後一段正是莊惠兩人的濠梁之辯。在進一步解讀“魚樂”之前,我們先來看看另外兩段對話中動物的形象。首先是神龜曳尾的寓言: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内累矣!”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
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
莊子曰: ”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14)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第603~604頁。
這段對話中有兩個情境: 其一是現實所發生的事,即莊子與楚國大夫的互動。其二是莊子提出的動物情境,即神龜和楚國的互動。現實情境中,莊子原本在濮水旁釣魚,逍遥自在。楚國大夫所提供的高官厚禄,一般人求之不得,莊子卻認爲那是全形養生的累贅,避之唯恐不及。
由於楚國大夫誤解了莊子,所以莊子説了一個故事以明己志: 神龜寧願活着在泥地裏快樂地摇着尾巴,不願因占卜而死,儘管死後可以被供奉在廟堂之上。這裏雖然没有直接否定,但楚國大夫或讀者們應該皆能透過神龜之喻,充分感受到莊子的拒絶爲相之意。
這兩個情境的結構與作用,可由以下表格來呈現:

寓言: 神龜曳尾人與物互 動原本狀態情境一(喻體、現實)莊 子二大夫累莊子以楚國釣於濮水(逍遥自在)情境二(喻依、動物)神 龜楚國藏神龜於廟堂之上曳尾塗中情境結合莊子將曳尾於塗中
其中,動物情境是用以譬喻現實情境。神龜意指莊子,神龜身處廟堂意指莊子爲官於楚國,神龜曳尾塗中意指莊子釣於濮水。身處廟堂與爲官於楚國,對全形養生有所損害;曳尾塗中與釣於濮水,則指向逍遥自在的快樂狀態。
對於最後一句“吾將曳尾於塗中”,“吾”原本是莊子自稱,屬於現實情境;“曳尾塗中”則是神龜的逍遥自在狀態,屬於動物情境。莊子這句話,把現實和動物情境的語詞用在同一個句子之中,直接結合了兩個情境,明確地以神龜自比,來表示自己要保持逍遥自在。
在此意義之下,莊子之所以提及神龜,是要用以説明自己的意向或狀態,以回應楚國大夫的誤解。至於神龜的故事是真是假,它是否真的活了三千歲,並非重點。就算神龜的故事無可查證,甚至根本是莊子自己臨時編出來的,都不影響此寓言傳達莊子立場的功能。
接着是鵷鶵北飛的寓言: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15)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第605~606頁。
這段對話一樣有兩個情境: 其一是現實所發生的事,指莊子和惠子的互動。其二是莊子所提出的動物情境,指鵷鶵和鴟的互動。莊子來找惠子,原先並無絲毫取代惠子爲相之意,但惠子卻勞師動衆搜尋莊子的下落。
由於惠子根本誤解了莊子之意,所以莊子説了一個故事以明己志: 鵷鶵有遠大的追求與目標,鴟不知這一點,以爲鵷鶵要搶它的腐敗鼠肉,連忙出言嚇阻。莊子對梁國宰相的不屑態度,也就藉由鵷鶵之喻,生動地傳達給惠子和讀者們。
這兩個情境的結構與作用,可由以下表格來呈現:

寓言: 鵷鶵北飛人與物互 動原本狀態情境一(喻體、現實)莊 子惠 子惠子搜莊子於國中三日三夜逍遥自在相 梁情境二(喻依、動物)鵷 鶵鴟鴟仰而視鵷鶵曰: 嚇!止梧桐、食練實、飲醴泉得腐鼠情境結合惠子以惠子之梁國嚇莊子
其中,動物情境是用以譬喻現實情境。鵷鶵意指莊子,鴟意指惠子,鴟出言嚇阻鵷鶵意指惠子勞師動衆搜尋莊子,鴟得到腐敗鼠肉意指惠子在梁國當宰相。鵷鶵的展翅飛往北海、止梧桐、食練實、飲醴泉等,則意指莊子個人逍遥自在的狀態。
對於最後一句“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子”是指惠子,“我”是莊子自稱,連同惠子所相之“梁國”,這些語詞都屬於現實情境;“嚇”是鴟對鵷鶵的反應,屬於動物情境。莊子這句話,把現實和動物情境的語詞用在同一個句子之中,直接結合了兩個情境,明確地以鵷鶵自比,以鴟比惠子,來表達自己認爲梁國根本不值一顧。成玄英説:“鴟以腐鼠爲美,仰嚇鵷鶵;惠以國相爲榮,猜疑莊子。總合前譬也。”即是此意(16)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第606頁。。
同樣地,在此意義之下,莊子之所以提及鵷鶵與鴟,是要用以説明自己的意向或狀態,以回應惠子的誤解。鵷鶵北飛的故事是真是假,它是否真的止梧桐、食練實、飲醴泉,並不是重點。就算鵷鶵與鴟的互動,是莊子自己編造出來的,也不影響這個寓言傳達莊子立場的功能與作用。
據上述可以看出,兩個寓言在結構上極爲相似,並且都有明確的情境結合,讓讀者可以馬上理解到莊子的立場,可以説寓言在此充分發揮了其功能與作用。那麽,焦點看似在於“莊子是否知道魚樂”的濠梁之辯,是否也可能屬於這類寓言?“魚樂”是否可能爲一譬喻?
基於對前兩個寓言的結構分析,要判定濠梁之辯同屬涉及動物情境的寓言,以及“魚樂”譬喻了莊惠兩人之樂,至少要有以下兩點支援: 其一,濠梁之辯提及了兩個不同情境,一爲動物,一爲現實。其二,濠梁之辯有情境結合的關鍵句出現。
濠梁之辯本是莊、惠兩人對於“魚樂”的辯論,確實出現了人與動物的描述,但這樣並不足以説莊子是以“魚樂”爲一譬喻。關鍵還是在能否找出結合兩個情境的句子上,這就要先論證“我知之濠上也”承擔了情境結合的任務,以“魚樂”爲一譬喻的觀點才能够成立。
爲了叙述方便,以下再引一次濠梁之辯的全文,並加上標記:
(A)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
(B) 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
(C)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惠子曰:“(D) 我非子,固不知子矣;(E) 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莊子曰:“請循其本。(c) 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b) 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a) 我知之濠上也。”
兩種通行詮釋中,都把b句和a句中的“之”解讀爲“魚樂”。如此一來,c句對應到C句,b句中的“吾知之”是基於B、C兩句來反駁了D句,a句中的“我知之”是基於B句來反駁E句。這樣的反駁,是基於句子與句子之間的某種對應關係來進行的。
然而,莊子最後所説的“請循其本”,是要回溯莊、惠兩人一開始對話的情況,並藉此來反駁惠子,尤其是最後那一句“我知之濠上也”,正是在整個推論中扮演了結論的角色。據此,“請循其本”應該要代表一種嚴格的對應關係,是分别針對了莊、惠兩人先前的每一句話,也就是説,a、b、c三句應分别對應到A、B、C三句。其中,C句和c句都提及了莊子怎麽知道“魚樂”;B句和b句都提及了莊子知道“魚樂”;A句和a句都提及了濠梁。此對應完整涵蓋了文本的前三句話,代表A、B、C三句與a、b、c三句之間,具有一對一的溯源對應關係。
如以下表格所示,對於整個論辯過程所發生的事件與對話順序,莊子的回應其實絲絲入扣:

發生的事件莊子的回應(C)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c) 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B) 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b) 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A)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a) 我知之濠上也。
其中,A、B、C的順序同原文,也就是莊、惠兩人出遊的描述與第一輪的對話。c、b、a則是莊子在“請循其本”的説明裏,藉由溯源回推,分别針對C、B、A句來回應,最後導出其結論。
與兩種通行詮釋相比,a句“我知之濠上也”對應的是A句“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而非B句中的“魚樂”。這就引發了一個問題: a句“我知之濠上也”中的“之”,是要解讀爲“莊子出遊之樂”,還是解讀爲“魚樂”?如果采取一對一的對應觀點,則a句對應的是A句,“之”應該解讀爲“莊子出遊之樂”較爲恰當;如果采取通行詮釋的觀點,a句對應的是B句,“之”是要解讀爲“魚樂”。
我在這裏即是要把a句“我知之濠上也”中的“之”解讀爲“莊子出遊之樂”,卻也不否定“之”隱含“魚樂”。以“魚樂”爲一譬喻陳述,則“之”雖然可解讀成“魚樂”,但“魚樂”本身還是要譬喻“莊子出遊之樂”,這可以説是同時容納了以“之”爲“魚樂”與“莊子出遊之樂”兩種解讀,也就化解了a句應該要對應到哪一句的問題。
更爲重要的是,對於“我知之濠上也”一句,要如此解讀“之”,或説在以“魚樂”爲一譬喻陳述的詮釋中,“濠上”這個地名才有其重要意義。無論是把“魚樂”視爲一心理狀態或是一客觀事實,兩類詮釋都是把a句中的“之”解讀爲“魚樂”。然而,這兩者都忽視了“濠上”的重要性,“濠上”對於文本的義理解讀是多餘的,甚至把此地名給完全抹去,把A句改爲“莊子與惠子遊”,把a句改爲“我知之也”,都不會影響這兩類詮釋。
在以“魚樂”反映莊子心理狀態的詮釋中,莊子既已達到物我爲一的境界,能够因己樂而知“魚樂”,則莊子身處何地都有此境界,都能知道“魚樂”,並不局限於“濠上”。莊子知“魚樂”是否發生在“濠上”,甚至發生在别的地方,對物我爲一的境界都没有什麽關係。同樣地,在以“魚樂”爲一客觀事實的詮釋中,偏重於莊惠兩人在語意解讀上的不同,或是莊子有何證據宣稱自己知道“魚樂”。而“濠上”一詞,完全不影響這兩個論點的成立與否。
“濠上”對這兩種詮釋而言,似乎僅是一個地名,可有可無,單純記録此事件的發生地點而已。“我知之濠上也”是整段文本當中的最終結論,本來應有畫龍點睛之效,如果發生地點其實無足輕重,“濠上”二字,是否反倒變成畫蛇添足?
然而,若以“魚樂”爲一譬喻陳述,魚之出遊從容而樂,正是要説莊子出遊從容而樂。而“我知之濠上也”的“之”則是藉由“魚樂”譬喻,來指出莊子在濠梁的出遊之樂,於是濠梁的意義就不只是地名,而是代表了發生在濠梁的事件。正如後世提到濠梁,是指莊、惠兩人的魚樂之辯;莊子提到濠梁,正是代表了莊、惠兩人這次的出遊;而莊子之所以提到“魚樂”,則是即景用喻,要藉由“魚樂”來説自己或兩人出遊之樂。
如此一來,在“我知之濠上也”此句當中,“之”所代表的“魚樂”是一動物情境,“濠上”則是代表了莊、惠兩人出遊的現實情境,此句正是結合了魚游濠水中的動物情境以及人遊濠梁上的現實情境,擔任了情境結合的任務。在此意義下,“魚樂”代表了出遊的快樂,“濠上”代表了莊、惠兩人之遊,分居文本頭尾的A句“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以及a句“我知之濠上也”,才有强烈的前後呼應,“濠上”因借代了兩人這次的出遊,因代表了現實情境,而成爲詮釋中的關鍵。少了“濠上”此一地名,把“我知之濠上也”變成“我知之也”,後者就不能是一個情境結合的句子,以“魚樂”爲一譬喻陳述也就不會成立。
這兩個情境的結構與作用,可由以下表格來呈現:

寓言: 儵魚出遊人與物互 動原本狀態情境一(喻體、現實)莊 子惠 子遊於濠梁之上逍遥自在—情境二(喻依、動物)儵 魚出遊從容樂情境結合莊子知“魚樂”(莊子之樂)於濠梁之上
其中,動物情境是用以譬喻現實情境: 儵魚意指莊子;儵魚出遊從容,意指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魚樂”則意指莊子出遊之樂,或者説是意指其逍遥自在。儘管文本中並無直接描述莊子個人的感受,但莊子在其他篇章中,常常是以逍遥自在的狀態出現的。
對於最後一句“我知之濠上也”,“我”是莊子自稱,“知”是知道“魚樂”(莊子之樂),“濠梁”則指莊惠兩人的出遊,這些語詞都屬於現實情境;“之”指“魚樂”,屬於動物情境。莊子這句話,把現實和動物情境的語詞用在同一個句子之中,直接結合了兩個情境,是以“魚樂”喻己樂。在此意義之下,“我知之濠上也”扮演了情境結合的角色,融合了當下情境與動物情境,可以説是“魚樂”之喻得以完成的關鍵,也才稱得上是畫龍點睛的神來之筆。
若以“魚樂”爲一譬喻,則此譬喻的主要功能,是要透過“魚樂”的情境,來描述自己遊於濠梁之樂,這是莊子感受到自己的快樂,並透過“魚樂”表達出來。而惠子以“魚樂”爲一客觀事實,正是對莊子之意的誤解,因爲“魚樂”是否爲一事實,根本不是莊子的核心關切,甚至“魚樂”譬喻的使用,也根本不需要預設“魚樂”對應到一事實。就算事實上魚並不樂,就算魚之出遊從容是莊子的編派,“魚樂”譬喻的使用還是有其功能。如同神龜已死三千歲、鵷鶵從南海飛到北海,就算這兩者並非事實,對神龜曳尾與鵷鶵北飛這兩個寓言的功能也無影響。莊子不需要先確認那兩個事實成立才能使用這些譬喻,讀者也不需要確認它們皆是事實,才能够把握到其寓意。
據此,基於“魚樂”爲一譬喻的前提,惠子對於莊子是否或如何知道“魚樂”的質疑,根本不能成功。一方面莊子知道自己快樂,是立基於其自身的感受,這似乎是不證自明、理所當然的,其快樂的成立不需要額外的理由支援;另一方面莊子以“魚樂”喻己樂,是一種修辭或表達技巧,可以討論其生動優美的程度,但無成立與否的問題可言,就算實際上魚並不快樂,也不妨礙“魚樂”這一譬喻的功能。
詮釋濠梁之辯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解釋莊、惠兩人是在什麽層面上針鋒相對。由於莊子在書中一直是以正面形象出現,從《秋水》篇作者的角度來看,應該要能説明莊子立場的合理性。而就我所提出的詮釋,在反駁惠子的質疑以及他對“魚樂”的誤解時,莊子强調了自己出遊於濠梁之上而樂,並且是以“魚樂”喻己樂。莊子此意,正是透過動物與現實兩種情境的對應,以及“我知之濠上也”的情境結合之中,所充分展現出來的。
不僅如此,以“魚樂”爲一譬喻的詮釋,重視莊子言“請循其本”所指的溯源對應關係,以及“濠梁”一詞在文本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這是以往兩種詮釋所容易忽略之處。
三、 天樂、誤解與譬喻
在龜、鳥、魚三段文本之中,莊子皆是以動物之樂喻人樂,藉由譬喻來回應了對方的誤解。那麽,此樂是否具有什麽特殊意義?爲何對方會有所誤解?譬喻在此回應之中又扮演什麽角色?
讓我們先處理樂的問題。如果莊子僅是透過魚之快樂和人之快樂在情緒上的共通,藉由“魚樂”來説明己樂,這只是一種修辭。所謂修辭,是先感受到自己的快樂之後,才藉由動物之樂來説明己樂,其主要功能在於更好地形容與傳達。
但從以下表格的歸納與整理可以看出,動物之喻的功能並不只如此:

動 物 情 境現 實 情 境主體與自然環境的互動主體與自然環境的互動神龜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釣於濮水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莊子身爲布衣,往來各國①儵魚出遊從容於濠水之中莊子遊於濠梁之上①在鵷鶵北飛的寓言中,並未提及多少莊子本身的具體情況,這是我根據莊子書中形象而作出的一個推測。
表格左側代表三個動物情境,龜、鳥、魚三種動物,分别樂於在泥中打滚、在天空翱翔、在水中悠遊,它們各自有自己所屬的自然環境,也只有在其所屬的自然環境中,才能達到樂的狀態。表格右側則是莊子藉動物情境的自比,代表莊子自己已經處於樂的狀態之中,和身處的自然環境已有和諧互動。
龜、鳥、魚的動物情境,除了涉及樂的情緒,更是要突顯出動物之樂必須基於相應自然環境。據此,莊子用喻,是要藉由動物之樂來説明人樂也應與自然環境有緊密連結,强調了樂是主體與自然環境的和諧互動,並非僅是情緒表達(17)蕭裕民即是把《莊子》論“樂”分爲喜好意向、情緒性的高興以及平穩思維三種,而最能代表《莊子》思想特色的,無疑是第一種。見蕭裕民《〈莊子〉論“樂”——兼論與“逍遥”之關係》,《漢學研究》第23卷第2期,2005年12月,第29頁。。我們不妨把此樂稱爲天樂,因爲《天道》説:“言以虚静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這正是强調了主體與天地、萬物的連結關係。
莊子之所以用喻,不僅是爲了説明天樂,同時也回應了對方的誤解。莊子樂於濮水之旁,但楚國大夫認爲他必會接受高官厚禄,所以莊子才提出神龜曳尾之喻;莊子樂於梁國之中,但惠子害怕他想要來奪走相位,所以莊子才提出鵷鶵北飛之喻;莊子樂於濠梁之上,但惠子以“魚樂”爲一客觀事實,所以莊子才强調儵魚出遊之喻。在這三段對話之中,很明顯地,動物之喻主要是爲了回應對方誤解而有的。
不僅如此,除了回應誤解以外,莊子更要透過動物譬喻來指出導致誤解的原因,並且加以批評。從以上對三段文本的分析,莊子把天樂視爲主體與自然環境的和諧互動,並據此提出兩個批評:
其一,批評對高官厚禄的追求。追求高官厚禄對天樂有所妨礙,因爲這是把主體從自然環境轉移到人爲政治體制之中。
在神龜曳尾、鵷鶵北飛兩段文本之中,楚國大夫和惠子都預設了高官厚禄值得追求,並以爲莊子也是如此,這正是誤解的主因所在。事實上,處於天樂的莊子,根本就視世俗富貴如無物:“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要追求富貴,就必須時時考慮如何獲得並保持之,這就必須付出許多身心上的精力。但是,由於精力都用在追求過程之上,反而無從樂於富貴。這代表高官厚禄本是身外之物,它與天樂並無必然的連結,相反地,追求富貴是耗損身心,而非安頓身心。
在與仲尼的對話中,葉公子高生動地描述了這種身心損耗:
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而況諸侯乎!吾甚栗之。…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内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18)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第152~155頁。
身處政治體制之中,高官厚禄的代價,就是要奉行君主的命令。葉公子高擔憂自己無法達成外交任務,先不論任務失敗會有什麽懲罰,他所承受的極大壓力,已然煎熬身心,甚至因此陰陽失調而患病。顯然地,此情況將嚴重妨礙天樂,因爲主體處於不當環境之中,也就没有與自然環境的和諧互動可言。
其二,批評判斷是非對錯的心態。就一切言論和事物來判斷是非對錯,妨礙了達到天樂,因爲這是割離了主體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連結。
在儵魚出游這段文本中,惠子預先以“魚樂”爲一客觀事實,他一開始就没有意識到“魚樂”的譬喻性質,並進一步質疑莊子如何知道“魚樂”。由於他以“魚樂”爲一客觀事實,話題焦點遂被轉移到如何知的問題之上,故有“魚樂之辯”。這樣的誤解,其實同樣可能出現在神龜曳尾與鵷鶵北飛兩段對話之中。
以神龜爲例,若楚國大夫在莊子提及神龜時,答之以:“子安知神龜已死三千歲?”莊子答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龜之死?”楚國大夫再回:“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龜也,子之不知龜之死,全矣。”這就使原本的神龜之喻偏離其主題,形成了“龜死之辯”。
再以鵷鶵爲例,若惠子在莊子提及鵷鶵時,答之以:“子安知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莊子答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鵷鶵之飛?”楚國大夫再回:“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鵷鶵也,子之不知鵷鶵之飛,全矣。”這就使焦點轉移到如何“知”,形成了“鳥飛之辯”。
據此,惠子之所以誤解“魚樂”,是由於他執意要討論“魚樂”這一事實的成立與否。而從《莊子》一書當中來看,惠子即是預設了辯者的觀點,也就是用判斷是非對錯的心態來看待一切言論與事物。
辯者一詞,在外雜篇中出現數次,《天下》篇中則直接以惠子與公孫龍爲辯者的代表人物:“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從辯者二十一事(19)《天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絶,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黄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見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第1105~1106頁。可以看出,他們往往發出異於日常思維的言論,並樂於將其合理化,以在辯論中勝出。也就是説,辯者們是爲了勝出而辯,而非一開始就認爲這些命題合理,所以《天下》篇才説他們能在口頭上不敗,卻無法讓人心服。這在《公孫龍子》中的“白馬非馬”“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堅白石三”等著名主張之中,更是充分體現出來。
在《秋水》中,詳盡叙述了公孫龍自視甚高,但其所學卻與莊子不契。對此,公子牟先是舉出了埳井之鼃與東海之鱉的對話,以井之小與海之大爲對比,來突顯公孫龍與莊子在觀點上的巨大差異。又透過蚊虻負山、商蚷馳河、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以及邯鄲學步等實例,來説公孫龍的視角極其局限,所以無法理解莊子之言。《天下》也如此描述惠子:“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這不單强調了惠子的好辯,同時也指出其觀點局限的缺點。
由此可知,辯者們往往從判斷是非對錯的角度來面對一切所見所聞,也就是説,他們預設了判斷是非對錯的先在觀點,再從此來看待一切言論與事物。這固然使他們有善辯名聲,但也往往不能得見事物全貌,不能用同情心態來理解他人的言論。這種極爲局限的做法,使得辯者們容易誤解或刻意曲解他人,因爲日常生活中的許多言論,其本意並不在於是非對錯,而是在於説明狀態、表達情感、記録感想等等。惠子對“魚樂”的誤解,正是最佳案例之一。
在濠梁之上的對話中,惠子第一反應是詢問莊子如何知道“魚樂”,他一開始就采質疑立場,甚至就是想要駁倒莊子,這正是辯者的典型態度。這並非説我們不能討論“魚樂”作爲一客觀事實何以能够成立,而是説惠子並没有考慮莊子言“魚樂”的原意,他只是理所當然地認爲莊子必須回答如何得知。事實上,莊子在提及“魚樂”時,並非先想好有何證據才提出“魚樂”,其本意並非是要給出認知上的判斷或論證。
據此,則惠子之所以誤讀“魚樂”,之所以把“魚樂”看成是一客觀事實,即是由於他身爲辯者,在看待各種言論與事物時,預設了判斷是非對錯的觀點,故不能理解到莊子是要以“魚樂”喻己樂。由於惠子誤解了莊子言“魚樂”是在陳述事實,所以莊子才必須指出“魚樂”是遊於濠梁之樂的自比。這倒不是説惠子没有能力理解譬喻,而是説他忽視了譬喻的可能性,惠子只對判斷是非對錯感興趣,因而把話題導向了是否知或如何知。
以下這段引文,就突顯出辯者們的態度如何對身心有害: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搆,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20)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第51頁。
爲了證明己方主張正確,辯者們不僅醒的時候往來争辯,連睡夢中也要算計對方會如何辯護而自己要如何進擊。他們把對方看作是你死我活的敵人,而將所有的心力都放在辯論之上。攻擊時爲消滅對方,如機括般不斷射出弩箭;防守時堅持己見,如立下重誓般不肯認輸。在這樣的激烈争鬥之中,辯者往往没有發覺心力過度損耗,其生命力已悄悄被奪去,由於沉溺於辯論而不可自拔,使得他們生命中的其他可能就此消亡。
莊子在此詳細描述了辯者們的種種狀況,這些有害身心的狀況是由於辯者沉溺於争辯,而這種沉溺又是由於他們執著於判斷言論或事物的是非對錯。無疑地,此種態度嚴重妨礙了天樂,而莊子正是據此提出了激烈批判。
龜、鳥、魚三段文本都涉及了不同觀點之間的差異,而預設並局限於單一觀點,正是他人誤解莊子的原因所在。如王夫之即説:“困於小大、貴賤、然非之辨者,彼我固不相知。不相知,則欲以己之有,憐物之無,而人乃滅天。”(21)王夫之《莊子解》,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48頁。執著於分辨小大、貴賤、是非的這種態度,其實隱隱預設了彼我並不相知,既然不相知,就代表了彼我之間有一段落差存在。基於這種落差而要把自己的正確加諸於其他人或其他事物,就已經不是設身處地的理解,誤解也就因此而必然發生。
莊子原先已處於天樂,而楚國大夫與惠子也都有其先在觀點,雙方之間的交集是從誤解莊子開始,而後莊子才提出或强調了動物譬喻。而據本節的分析可知,動物譬喻的主要功能,不僅在於説明天樂,更是要回應誤解,進而批判導致誤解的原因。也就是説,在這三段文本之中,動物譬喻是莊子呈現天樂與建立其天樂主張的關鍵,甚至它參與了莊子哲學思想在内容上的形成過程。
餘論: 辯論或寓言?
在對濠梁之辯的不同詮釋中,由於“魚樂”是莊、惠兩人争辯的焦點,對“魚樂”的解讀,必然涉及如何解讀莊、惠兩人的差異。更明確地説,對“魚樂”的解讀,基本上決定了如何解讀莊、惠兩人的立場,從此角度出發,也就決定了如何詮釋整段文本。
若以“魚樂”爲一心理狀態陳述,則莊、惠之别就在於心理狀態或人格境界上的不同。莊子基於物我爲一來看待眼前所知所見,身爲辯者的惠子,卻是時時注意事物的是非對錯。這樣的問題意識,在於人對事物可以有不同觀點,其詮釋就以大小觀點來説明雙方差異。這種解讀導致了以下推論: 站在莊子的立場,由於物我本來爲一,其中没有任何隔閡,所以莊子只需要透過直覺,就可以説自己知道“魚樂”。
若以“魚樂”爲一客觀事實陳述,則莊、惠之别在於對認知“魚樂”的態度不同。莊子認定自己知道“魚樂”,惠子卻指出莊子缺乏認知到“魚樂”的證據。這樣的問題意識,在於人有何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認知,或是邏輯推論上的一致與否,其詮釋則以認知或推論成立與否來説明雙方差異。這也導致了以下推論: 站在惠子的立場,由於物我分離爲二,其中有一道鴻溝,所以需要好的理由才能宣稱自己知道“魚樂”。
若以“魚樂”爲一譬喻陳述,則莊、惠之别在於對“魚樂”的解讀不同。莊子是藉由“魚樂”譬喻來呈現出其天樂的觀點,惠子則是誤解了莊子言“魚樂”。這樣的問題意識,在於人對譬喻陳述有何可能解讀,其詮釋是以譬喻與誤解譬喻來説明雙方差異。這也是站在莊子的立場,由於莊子本就處於天樂狀態,並且是以“魚樂”喻人樂,他當然可以説自己知道“魚樂”。
由此可知,在濠梁之辯的詮釋過程中,用怎樣的脉絡來解讀“魚樂”,以及就何問題意識來判定莊、惠兩人的差異,決定了整個詮釋的發展方向,也決定了如何看待濠梁之辯與《莊子》其他段落之間的連結。這代表我們在詮釋的過程中,不僅是尋求了“魚樂”的原意解讀,同時也基於此解讀來説明與回答了文本中的一些問題。
以“魚樂”爲一譬喻,我們可以如此重建莊、惠兩人對話的整個過程:
莊子與惠子一同出遊於濠梁之上,當莊子提及“儵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這是藉景抒懷,以魚之出遊從容來譬喻自己出遊之樂,代表莊子充分感受到自己遊於濠梁的快樂。而面對惠子的提問:“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尚不知惠子的真正立場,所以他直接反問:“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由於“魚樂”是用以譬喻己樂,莊子身爲用喻者,當然知道自己的快樂,也知道自己所用的譬喻,故莊子知道“魚樂”是理所當然。
然而,當惠子説:“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這是運用邏輯推論來導出惠子不知莊子、莊子不知魚。身爲辯者一份子的惠子,往往只從判斷是非對錯的角度來看待言論與事物,他因而對“魚樂”譬喻有了誤解。莊子這才意識到惠子是把“魚樂”視爲一客觀事實,在此前提下,如果没有好的理由支持,莊子就不能宣稱自己知道“魚樂”。
所以莊子必須“循其本”,回溯兩人的對話到一開始的“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並藉由“我知之濠上也”的總結,來指出自己是以魚樂反映出遊於濠上之樂。在此脉絡之下,既然莊子知道自己快樂,而“魚樂”是用以譬喻莊子之樂,則“我知之濠上也”就是一無可質疑的結論,因爲莊子正是在遊於濠梁的過程中,感受到快樂並以“魚樂”喻己樂。據此,我知之濠上也正是結合了魚游濠水中的動物情境,以及人遊濠梁上的現實情境,來指明“魚樂”是要譬喻人樂。所以,惠子的質疑根本不能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以“魚樂”爲一譬喻陳述,也可説“魚樂”是描述了莊子的心理狀態,因爲“魚樂”是用以譬喻了莊子之樂。但從神龜曳尾、鵷鶵北飛、儵魚出遊等動物情境來看,這樣的天樂,其焦點在於主體與相應場域的和諧互動。僅管這與物我爲一的人格境界有所關聯,但我們也不應忽略其中的可能差異。
本文以“魚樂”爲一譬喻,並據此來詮釋濠梁之辯,如果各位讀者贊同我的詮釋,則我們應該進一步思考這段文本的定位問題: 以“濠梁之辯”來定位莊、惠兩人在濠梁之上的對話,是否適當?
在以“魚樂”譬喻爲核心的詮釋之中,與其説莊子的發言是在争辯是非對錯,不如説是在突顯譬喻的使用與功能。也就是説,辯的意義被削弱了,寓言的意義則被增强了。在對話中,儘管惠子的確是從辯者的角度出發,但莊子真的認爲自己是在進行辯論嗎?這段對話,是否更應該被視爲一個以動物之樂爲核心的寓言?在此,辯論與寓言可以説是兩種詮釋模型。採用哪一種模型,將決定我們對濠梁之上的對話有怎樣的詮釋。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探討莊子如何看待辯論: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22)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第107頁。
《莊子》一書之中,對辯論的探討尚有許多,此處無法細談,但這段文本可以看出其基本態度。辯論活動乃一是非對錯之争,用以判定孰是孰非、誰對誰錯辯論結果有四種可能: 我非你是、我是你非、我你皆非、我你皆是,由於辯論活動没有一客觀判定標準,故無論結果是哪一種,都不能保證勝方的主張必然爲是爲對,負方的主張必然爲非爲錯。
據此,加上先前對寓言的説明,可以把辯論和寓言兩種詮釋模型的區别,整理成以下表格:

雙方關係進行過程主要功能辯論持不同主張的對立兩者。藉由給出各種理由與論證,來判定各自主張的是非對錯。判定辯論勝負,也就是孰是孰非、誰對誰錯。寓言譬喻使用者與譬喻解讀者。藉由模擬方法,提出另一個情境來説明當下情境。使對方更好地理解,無是非對錯可言。
根據這個表格,辯論活動的要素大致有三;其一,相持不下的對立雙方;其二,具有用以争辯是非對錯的核心;其三,雙方提出了論證來支持己方或攻擊對方。那麽,爲何在詮釋神龜曳尾和鵷鶵北飛兩個寓言時,我們幾乎不會從辯論活動的角度出發?因爲在兩個寓言之中,基本上不存在這幾個辯論活動的要素,莊子更像是在自説自話,寓言的意味非常明顯。
但在濠梁之上的對話中,看似可以找到滿足辯論活動的幾個要素: 莊、惠兩人相持不下、争辯的核心在於是否知道“魚樂”,且雙方都爲如何知道“魚樂”提出了論證。在常見的兩種詮釋中,無論是以“魚樂”爲心理狀態,或是以“魚樂”爲客觀事實,若是聚焦於“魚樂”本身的是非對錯,並考慮有什麽論證來支持之,則莊、惠兩人之間就有勝負之别。或者是説,由於一開始就以爲莊、惠兩人在進行辯論,於是把詮釋焦點帶往了是非對錯判定與論證成立與否的方向。
把莊、惠兩人在濠梁之上的對話定位爲辯論活動,一開始就設定了用辯論勝負和理由成立與否的角度來進行詮釋。然而,從我提出的詮釋來看,在以“魚樂”爲一譬喻的前提下,用寓言來定位這段對話更爲恰當。主要理由有二:
其一,“魚樂”譬喻本身無是非對錯可言,因爲譬喻的主要功能在於更好地理解,而非給出是非對錯的判斷。在莊子確實處於天樂的前提下,以“魚樂”譬喻没有恰當表達出莊子之樂,甚至以“魚樂”是個很差的譬喻,都是可能説法;但以“魚樂”譬喻爲非爲錯,則根本不通,就算“魚樂”並不對應到一個儵魚快樂的事實,也絲毫不妨礙此譬喻的功能。
當然,《莊子》一書之中往往透過譬喻來説明某項主張,如“魚樂”譬喻即代表了莊子對天樂的主張。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可以討論是非對錯的,是天樂本身的實質内容,而非“魚樂”譬喻這個表達形式。譬喻是要使對方更好地理解己方主張,而非駁倒對方。
其二,莊、惠兩人的關係,並非辯論活動的勝者與負者,而是譬喻的使用者與誤解者。“魚樂”譬喻所要突顯的,與其説是惠子的辯論失敗,不如説是惠子誤解了譬喻所指,因爲他只關注“魚樂”在客觀事實上的是非對錯。據此,莊子之所以用動物譬喻爲方法來響應誤解,其實正是要回避這種以是非對錯爲核心的思維,“魚樂”這一譬喻並非爲了辯論活動而被强調,它本來是爲了説明天樂。
歷來對神龜曳尾和鵷鶵北飛兩個寓言,在詮釋上基本一致。然而,就莊、惠兩人於濠梁之上的對話,在詮釋上卻出現了不同的偏重與立場。根據我對“魚樂”的解讀可以看出,對於《莊子》内的某些段落,許多時候我們認爲它是直接陳述,但其實有譬喻解讀的可能。相反情況也會成立,即一般認爲是譬喻的段落,有解讀爲直接陳述的可能。那麽,如何判定該段落是直接陳述還是譬喻?要照字面解讀,還是試着找出其喻意?
在本文所討論的三個動物寓言之中,皆有情境結合的句子出現,連結了現實與動物兩種情境,據此可以判定它們是譬喻,但在没有明顯情境結合的段落裏,就需要更多綫索。然而,在某些與上下文缺乏明顯連結的段落中,就會産生很大的解讀空間,這時若是根據截然不同的問題意識來解讀關鍵命題,也就會有截然不同的詮釋方向。
譬喻和寓言的廣泛使用,是《莊子》哲學具有如此魅力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哪些段落該以譬喻或寓言的角度去看待,必須透過對文本的細緻處理方可得知,此處也無法一一細談。在此我想指出的是,譬喻和寓言不應只被視爲單純的修辭,考慮其功能如何能够支持《莊子》的哲學主張,進而開展出更進一步的問題意識,是我們得以深入探索《莊子》的一個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