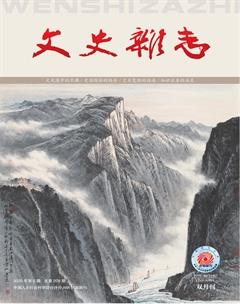张大千:大写的敦煌人
汪毅
每当说到敦煌,每当礼佛探艺于敦煌,总有一道清泉流淌过我心灵的小河,那便是张大千发自肺腑的感慨和呐喊:“敦煌,予深爱之!予深爱之!”——这里,且不说重叠词“予深爱之”的寡用,也不说两个感叹号递进在张大千行文语法中的绝无仅有,仅说其“爱”的情怀,便使人感到张大千心海中卷起的千堆雪以及裂岸惊涛。真的是,如此心声几人有,如此情怀苍天知?!
1941年春,为寻梦六朝隋唐画迹,墨妙法像,张大千开启了他为期两年七个月的敦煌临摹壁画之旅,成为敦煌人的先驱者之一。
敦煌,位于西北边地的甘肃,其拥有的价值与沧桑,非简单的判定定义所能概括。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针对陈垣就北平图书馆所藏八千余件敦煌写本编目为《敦煌劫余录》一事,学术界有“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1]之叹。这份“伤心”,是因为外国侵略者的文化掠夺(所掠文物,英国现存一万多件、法国现存六千多件、日本及美国亦存相当数量),致使敦煌学研究一度在国外。然而,敦煌似乎亦是张大千的“伤心地”,原因是他不仅生前曾被扣上一顶“破坏敦煌壁画”的大帽子,而且九泉之下还遭躺枪。难怪,张大千这个深爱敦煌之人生前忍不住在亚太地区博物馆研讨会上为自己辩诬,做“我没有破坏敦煌壁画”的解释。
对于敦煌,张大千抱负远大,确有以求“三年之艾”而振“八代之衰”的鸿鹄志向。然而,多年来说到他与敦煌,似乎总是绕不开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即是否破坏了敦煌壁画。其实,张大千“未曾破坏敦煌壁画”的结论早在1949年3月的甘肃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七次会上已明确(见本文“试问”之十二)。然而,对于这个重大话题,作为研究的需要,我曾读过若干“是”与“否”的讨论文章,甚至同当时参与敦煌壁画临摹的张心智有过直接交流。归纳起来,这些文章有学者撰的,有媒体人写的;有写得客观的,有写得想当然甚至天花乱坠的。值得推荐的是《持续发酵70余年的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公案再识》[2]一文,这是我迄今看到的全面且有力道的一篇专文。该“再识”分12节,条分缕析,逻辑关系明晰,论证和论据充分,结论水到渠成。李白登黄鹤楼时,曾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诗句。虽然我非诗人,但确因这篇专文让我放下了拟为这桩“公案”做裁判的想法,以至于换一个表达角度,即从张大千的人性、佛性、动机以及常人具有的逻辑思维和常理及常识,提出以下十四个“试问”:
一、张大千“性喜佛”,号大千居士。其早年因缘际会遁入空门,烙印佛家,法号“大千”为师父逸琳方丈所取,来自佛典“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之语,为他埋下日后赴敦煌探究佛教圣地之佛根。张大千一生钤印“大千”最多,有此印章不下二三百枚,传递了佛教思想、佛教艺术在其创作中主事的强烈信息,故可以说佛教意识深入骨髓。张大千晚年叶落归根台湾,命居所为“摩耶精舍”(既指佛教布道场,亦为佛家静修住所),其题款、钤印亦多用“摩耶精舍”,以表达对佛教境界的憧憬。试问:一个如此信奉“丧天良,遭报应”、有数十载修为的人会倒行逆施去亵渎或破坏佛像吗?
二、张大千平生倾慕敦煌,视之为心中“恋人”。在1941年至1960年目翳不能自制之前的20年里,他一直未停止对所临摹敦煌壁画的完善与复制(1944至1949年是一个高峰期),即使萍踪国外也在继续。20世纪50年代,张大千在印度画有《南无密迹金刚》,在巴西画有《释迦说法图》等,诚如他在《普贤菩萨赴法会图》题款中说,无论旅居印度,还是移居阿根廷,或是筑宅巴西,均未停止敦煌壁画的加工。1960年,张大千还整理画出北魏至宋、元、西夏的菩萨、佛之手相14幅,并逐一予以文字解释。之后,他还命门人孙家勤、张师郑最后完成他的未完稿《文殊菩萨赴法会图》《普贤菩萨赴法会图》中的细笔表现部分并题跋,以表达其敦煌情愫。由此坚信,如果不是眼疾无法细笔,张大千还会执著下去,因为他亦在努力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只不过这个“初心”,是他对敦煌艺术的发愿;这个“使命”,是他志在弘扬敦煌艺术的责任感。故张大千喟叹的“敦煌,予深爱之!予深爱之”绝非矫情,而是由衷和必然。请问:如此喟叹,千百年来几人能有?它让人想到诗人艾青《我爱这土地》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而敦煌在张大千眼里,不正是他爱得深沉的这方“土地”吗?难怪,晚年的张大千(时81岁)还以饱满诗情感叹“自种沙州门外水,可怜肠断采莲歌”(沙州即古敦煌)。如此情怀,非常人所及,正可谓“用情多深,爱有多深;付出多大,爱有多大”。试问:一个有如此挚爱的人可能去伤害他深恋着的“恋人”吗?
三、张大千有一方特殊印章“老弃敦煌”。以此语入印,他意在鞭策自己笃力摹画敦煌,表达探艺不止的精神。除临摹敦煌壁画,张大千还是中国以个人名义为敦煌洞窟编号第一人,即“张氏编号”。张大千还喜绘荷花(佛家为之般若花),一生创作近千幅(仅赠友人谢玉岑的便逾百幅),甚至还写下“荷花世界梦俱香”等诗句。他的敦煌之旅,既是探索佛教艺术之旅,又是礼佛之旅。他在所临敦煌壁画的落款中,常书“清信弟子”“近事男”“大千居士”“敬摹”“敬橅”“敬写”等;还为寺庙书匾“大雄宝殿”等等。试问:一个如此有佛性及善根和敬畏佛教艺术的人,能冒佛之大不韪去破坏以佛教题材传世的敦煌壁画吗?
四、在敦煌莫高窟第251窟(张大千编号249窟)壁上,尚清晰地留有张大千的题记:“此窟塑像壁画皆六朝也,为世界极不得见之古物,来者应如何爱护之。”此题记为1941年,即张大千到敦煌的当年。如此匠心呵护遗产,足见其保护敦煌壁画意识之强烈,告诫后人用心之良苦,真所谓苍天可鉴。试问:一个有如此敬仰之情、敬畏之心的倡导保护文物者可能出尔反尔去破坏壁画吗?
五、张大千到敦煌仅几个月,便向国民政府要员于右任建议由政府加大力度保护敦煌壁画。于右任由此倡设“敦煌学院”(成立时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后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并提名张大千为首任主持人。这在1941年10月的《新华日报》《中央日报》《西部日报》等均有报道。因张大千执意要做职业画家,后来才改为由常书鸿担纲敦煌学院。試问:作为大力建议保护敦煌壁画和拟任敦煌学院主持人的张大千会去破坏壁画吗?
六、1942年9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隶属教育部,同时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颁发聘书,聘张大千等七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试问:作为筹备委员会委员的张大千,难道他不知道责任在肩而去破坏壁画吗?
七、1943年2月,张大千在专著《莫高窟记》自序中,不仅笔伐流窜至敦煌的白俄军人对壁画的涂抹毁坏,而且控诉华尔纳用树胶粘壁画留下的斑斑残迹以及斯坦因、伯希和的窃取掠夺。试问:一个与之不共戴天的人可能去同流合污破坏敦煌壁画吗?
八、当年,莫高窟中寺至下寺修筑有一条长长的围墙,于1944年竣工,被常书鸿誉为“莫高窟的万里长城”。鲜为人知的是,这个“长城”却源起于张大千1943年向甘肃省政府的建议以及他前期的经费投入。(他甚至还出资雇工清理洞窟中的沙砾。)对这段历史,张大千弟子巢章甫在《大风堂逸史》[3]一文中写道:“师(张大千)捐资于洞前筑转墙数里以御之。”试问:一个如此用心、用情、发力、倾囊修筑莫高窟“万里长城”以保护敦煌的人会去破坏壁画吗?
九、1943年8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甘肃首府兰州举行,《西北日报》曾在当月13至15日连续三天在头版刊出启事。当时兰州乃系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发声地。在兰州展出,与其说传递的是张大千“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的信息,不如说是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叫板。试问:如果说张大千破坏了敦煌壁画,他敢在流言蜚语的发源地兰州大张旗鼓、光明磊落办展览吗?
十、1947年,张大千以大风堂名义出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画册。这本画册,是笔者目前看到的第一本宣传敦煌壁画的大型彩色画册,并以“大风堂”名义的行为方式来助力敦煌艺术。试问:如此大魄力,当时有哪个机构及艺术家能做到?作为如此殚精竭虑去宣传敦煌的人,会去破坏敦煌壁画吗?
十一、1970年、1978年,张大千参加“中国古画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亚太地区博物馆研讨会”。会上,他为自己辩诬:“当时曾有人說我破坏壁画,在这里,得澄清一下。”对张大千辩诬的这种感觉,真让人不乏“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之慨。试问:如果不是坦坦荡荡的君子,他敢在国际会议上一再“澄清”吗?
十二、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呛声肇始于1943年,正式提案起于1948年7月甘肃省参议会第十六次会议。经立案调查、函证,1949年3月甘肃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七次大会做出最后结论:“省府函复:查此案先后呈奉教育部及函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电复:张大千在千佛洞(又名莫高窟)并无毁损壁画情事。”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该最终结论被压入卷宗,既未对张大千公开致歉,也未对社会公布。1948年8月,兰州解放。囿于这个最终结论石沉档案大海而不为人知,致使后来不明真相者陈词再起,让张大千继续背锅于“破坏敦煌壁画”,且不断发酵,以致误解再误解。对此,我不得不说,今天我们应该还张大千一个迟到的、久违的道歉!试问:如果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作为权力机构的甘肃省参议会当时能有如此结论吗?
十三、在谈及“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时,陈寅恪对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影响的评价是:“敦煌学领域中的不朽盛事,更无论矣。”[4]而张大千却自谦地说:“过去学术界对我在敦煌的工作,为文评赞,实愧不敢当。但是能因我的工作而引起当道的注意,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使国人普遍注意敦煌壁画的文化价值,也算略尽书生报国的本分了。”试问:在敦煌学领域做出“不朽盛事”和欲“使国人普遍注意敦煌壁画的文化价值”而努力“尽书生报国本分”的人可能去破坏敦煌壁画吗?
十四、敦煌壁画是中华艺术菁华之一,集北魏至元约一千年来人神百态之大成,既是形象历史的代表,亦是中国人物画断代史的准绳。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团队,乃以他为核心,包括其子侄、弟子与喇嘛画师等人。张大千系公认的大画家,亦是著名的画史评论家。作为画家对敦煌,张大千具有“全能”的表达才情,系敦煌壁画临摹、传播领军人之一,敦煌学者苏莹辉称其为“临古与创新第一人”。据笔者比较和统计,张大千至少可以列出14个“最”而力压其他敦煌壁画临摹者:投入财力最大(400万,几乎拖垮贷款的银行);临摹最早(就敦煌区域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的完整性而言。李丁陇赴敦煌的时间虽早于张大千,但仅临摹了莫高窟壁画,时间为8个月);临摹时间最长(两年七个月,如加上赴敦煌之后的陆续完善或复制,时间长达20年。此比较不包括常书鸿、段文杰等敦煌体制内的画家);临摹面最宽(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三危山塔壁无不涉及);临摹数量最多(摹本及其复制件计约300幅,粉本若干。摹本及其复制件主要为四川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及民间、寺庙收藏,粉本收藏仅孙凯便达约50幅);临摹壁画总面积最大(逾300平方米,其中单幅面积最大者为《劳度叉斗圣变》,纵925厘米,横345厘米,约32平方米);临摹的作品时间跨度最长(包括北魏至元代约一千年);临摹精准性最高(采用玻璃纸蒙描壁画,而此方法后来已不再使用);临摹水准最高(张大千赴敦煌时,已有近20年职业画家生涯的艺术积累,特别是曾有1935年在洛阳临摹《天女散花图》和1940年在青城山画《南无观世音像》等经历);临摹最具创造性(在观看李丁陇临摹敦煌壁画基础上,于资金、物资、学术、团队组织等方面准备更充分,故而起点更高,难度更大,挑战性更强,即透过壁画表象研究分析,直接采取恢复原貌临摹而非写生或复制。凡现状有变色或破损处,尽可能研究和推测其本来面貌,以尽量还原壁画本真);洞悉最深(对敦煌壁画中历代画迹演变的点评提要钩玄,感悟精辟);价值最高(一是张大千作为临摹敦煌壁画唯一的佛家弟子,融进了“除一切苦厄”的佛教情结、境界和理想;二是张大千作为职业画家,其学养和表现能力尤其突出;三是以蒙描方法临摹壁画原作,其构图、线条更为精准;四是收藏价值与市场拍卖价格最显);影响最远;传播最广。试问:有如此“最”综合表现的人会去破坏敦煌壁画吗?
至于对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评价,且不说20世纪40年代一批著名文化学者的若干高度褒赞,仅列出以下几位当代资深、权威敦煌人的表述,即可见眉目——
常书鸿:张大千肩担了承先启后的工作,是备受艰苦的卓绝英雄。(载李旭东著《张大千与敦煌》,团结出版社,2018年。下同)
段文杰:张大千一行到敦煌临摹壁画,在敦煌学发展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史苇湘:我在敦煌已呆了30多年,说张大千破坏了敦煌壁画,有什么根据?莫高窟的492个洞窟中,有哪个是他破坏了的?
樊锦诗:张大千确实破坏甚至盗窃了敦煌壁画等种种流言,这种民间传言,说明不了什么!我们敦煌研究院的人绝不会说张大千破坏了壁画……张大千至今留下的明显痕迹,只是对洞窟的编号,而编号是研究工作必须做的。
赵声良:敦煌壁画临摹,张大千作了很大贡献。临摹敦煌壁画最有名者当属著名画家张大千。1941年春,张大千远赴敦煌,后留敦煌临摹壁画,最终一举轰动画坛。传播敦煌艺术张大千功不可没。(此条载《四川日报》,2017年1月2日)
鉴于上述,我自然要说到另一个时髦话题“莫高精神”,即特指的与敦煌石窟有关的敦煌人精神。当然,我还要由此及彼说到“我与敦煌”的张大千。
2019年9月,我曾参观莫高窟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瞻仰了一代又一代敦煌人的不朽史迹,不禁感怀:这里的特殊地理环境特别是张大千所处的那一个时代,是中国乃至世界任何一处石窟区域所不具有的。这个特殊,构成了敦煌人与敦煌石窟的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关系,传递了特殊历史记忆的信息,从而提炼出伟大的人文精神。这个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5]的时代精神。故对一代又一代的敦煌守护者或开拓者,我既崇敬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王旭东、赵声良等这样的敦煌人(我曾与段文杰、樊锦诗、赵声良院长有过交流),又敬重像张大千这样不遗余力临摹敦煌壁画、传播敦煌的敦煌人。较之起来,作为先驱者之一的张大千的坚守(临摹敦煌、研究敦煌、编号敦煌、保护敦煌),在那个特殊時代需要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既要体验“平沙莽莽黄入天”的荒凉寂寞,又要感受“风头如刀面如割”的三九严寒,其客观条件岂止“艰苦”二字可以概括!张大千的坚守较之后来者,无疑属于一种“特殊坚守”,除要承担独立投资的巨额经济压力,而且“四无”——无工资、无差旅报销、无工作经费、无今天体制内的其他物质保障条件,也就是做了一件应由政府来做的事。他的坚守,还在于把这批价值连城的敦煌壁画临摹作品,分别捐赠给四川省博物馆(187件)、台北故宫博物院(62件)。故他的坚守,更显情怀与操守,更显艺术追求的韧性,更显独立人格魅力,更显奉献的标杆意义,更显“沧海横流,英雄本色”的云水气度,体现出一个纯正而天才的艺术家超常的能力和特别的文化精神。
张大千的坚守(临摹敦煌壁画),还影响到段文杰、史苇湘、李承仙等赴敦煌之举(笔者于1994年曾向段文杰核实),甚至惠及敦煌文物研究所,即临摹的壁画成为敦煌同人临摹范本(1956年至1961年期间,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四川省博物馆借走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119幅以临摹学习、研究)。作为职业画家,张大千的文化结构和艺术特质以及贯通古今的发散思维无疑是一流的,故他在临摹中特别强调研究与创新,甚至有临摹是读书的经验。由此可以说,在1956年至1961年这段时间里,敦煌同人临摹的相同(尺幅、题材等)摹本一定意义上是“参考”或“借鉴”张大千的,或者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表现及其理论、主张,影响了敦煌同人的临摹、研究、创新乃至某些理论思考(囿于历史客观条件,敦煌文物研究所同人临摹的壁画,绝大部分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除临摹外,张大千还非常重视对敦煌艺术的传播。其方式,主要有展览、出版、学术推动三个方面。张大千推出的一系列临摹敦煌壁画展览一如其临摹,依然是独木撑大厦,依然是在没有今天体制内提供的任何物质条件保障下进行的。故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张大千是“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特殊践行者。遗憾的是,我们对他“特殊践行”的认知、宣传、肯定实在不够(这也是我撰此文呼吁的原因之一)。屈指算来,其展览传播时间竟长达27年(1942—1969年),涉及国家有印度、日本、法国,涉及地区有敦煌、兰州、成都、重庆、西安、上海、香港、台北。(有的国家和地区为多次。)
在传播过程中,张大千胸怀鸿鹄之志,具有国际视野,即“在他的二百余幅摹品完成之后,最终的目标是美国”[6]。无疑,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率先走出国门,具有时代引领意义。1950年(1月、2月、4月),张大千首先在印度推出以临摹敦煌壁画为主体的“张大千画展”(展出临摹敦煌壁画作品23幅,其中莫高窟的18幅、三危山的1幅,榆林窟的4幅),其间考察阿旃陀石窟并将他所临摹的敦煌壁画艺术作比较研究,诚如罗家伦在画展序言中所言:“我非常肯定的是,他是在这个特殊领域的骑士并是第一人”[7]。1956年4月与7月,张大千分别在日本、法国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专题展”,开拓画坛新纪元,使敦煌这部中国古代艺术的辉煌大书通过展览形式与国际交流,让世界听到其本初的声音乃至中华文明的声音!此传播,特别是首在曾经的佛教国度印度的传播,体现了张大千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展示了他的敦煌情怀及人文理想,探索了中印文化关系中“迄今尚未辨别出的、缺少联系的跨文化的美术”[8]。其过程,既是张大千不断塑造“当代玄奘”的过程,又是检阅他靠一己之物力、财力、心力、毅力、眼力来创造艺术家奇迹的过程,更是他在某些方面体现时代先进性的过程。屈指数来,张大千于1950年在印度举办“张大千画展”迄今刚好70年。该展览分别应印度美术学会、泰戈尔国际大学美术学院邀请,在新德里、海得拉巴与博尔普尔举办,凸显了敦煌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品质,“活化”了敦煌艺术,系临摹敦煌壁画作品走出国门开先河的标志,在印度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奠定了张大千“敦煌艺术,国际表达”第一人的地位。2020年,时逢中(国)印(度)建交70周年,也是张大千首次将临摹敦煌壁画作品推向国际70周年暨临摹敦煌壁画走出国门70周年,具有包括践行“一带一路”的特殊意义。
张大千生前的直接传播,使敦煌壁画的文化影响深远。1983年,张大千去世后,两岸文博机构特别是四川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掀起了“敦煌旋风”,展览此起彼伏,但遗憾均未迈出国门。2011年,笔者还努力倡导比照“《富春山居图》合璧展”而于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9]无奈功亏一篑。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专题展览或有相当部分临摹敦煌壁画作品的展览先后巡展于北京、广州、南昌、成都、澳门、台北、高雄、昆明、上海、沈阳、太原、杭州、(成都、长春、台北、深圳联展)、无锡、海口、大连、澳门、内江、重庆。(有的为一地多次展。)如果将张大千生前直接举办的敦煌壁画展和后来两岸文博单位举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加起来,总数达45个,而且巡展还会继续下去。其展览时间,迄今为止近80年(1942—2019年),使固化的敦煌得以“移动”传播。如此长的展览时间和展览场数,创下了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的历史奇迹,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的作品能与之比肩。
在出版物传播方面,海内外出版有关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图录(画册)、评论特辑等计达40余种,时间跨度(1944—2019年)近80年(尚未包括张大千在《申报》《风土什志》等报刊发表的临摹敦煌壁画作品,亦未包括海内外若干报刊对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评论),让“移动”的敦煌产生了不可低估、不可取代的影响。这也是没有一个艺术家能比肩的,堪称空前。
在学术传播方面,张大千发表有专文、专论,出版有专著,出席有国际学术讨论会。其中,专文有《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自序、《敦煌莫高窟记序》《张大千谈敦煌石室(上下)》《话说敦煌壁画》《张大千临橅敦煌壁画序言》《我与敦煌》等,专论有《谈敦煌壁画》,专著有《张大千先生遗著莫高窟记》(《莫高窟记》),出席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台北中国古画国际学术研讨会”“亚太地区博物馆会议”并作《我与敦煌壁画》演讲。
综上所述,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和出版物的这两个“近80年”及其学术传播,奠定了他在敦煌研究史上和“敦煌学”中不可取代的地位,堪称敦煌人文的一座高峰,让人仰止。故我既点赞“敦煌守护者,寂寞人间世”的敦煌人,更点赞像张大千这样的“敦煌传播者,智慧人间世”的敦煌人。他们系敦煌“守护”与“传播”这辆文明马车的宏伟车轮,推动着敦煌文明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张大千无愧于敦煌艺术代表性的先驱者、临摹者、研究者、创新者、传播者,无愧于敦煌人,更无愧于大写的敦煌人!
注释:
[1]转引自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15年版。
[2]载李旭东:《张大千与敦煌》,团结出版社,2018年。
[3]载巢章甫:《海天楼艺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
[4]陈寅恪:《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载陈寅恪:《讲义及杂稿》,三联书店2015年版。
[5]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关于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重要讲话的通知》,2019年。
[6]《敦煌壁画展览——张大千三年的心血,艺术上独立大投资》,载《新民报》1944年5月23日。
[7][8]罗家伦:《大千画展》序言,1950年。
[9]汪毅:《寻踪张大千:台湾之旅》,九州出版社,2011年。
链接:
两岸所藏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作品,以四川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代表。其中,四川博物院藏187幅,臺北故宫博物院藏62幅(包括一幅碣墨拓本),均为张大千捐赠。“两院”所藏各具千秋,不乏互补,构成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主体。相对比较而言,四川博物院藏品的特点是:尺幅较大(尺幅最大者为《劳度叉斗圣变》),题款较少(最长题款为《夜叉》,约160字),未完稿较多(38幅,见《张大千临橅敦煌壁画》,四川省博物馆编,1985年);内容除临摹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时期的敦煌全幅壁画像之外,还有佛、观音、供养人、劳度叉斗圣变、伎乐天等单幅临摹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的特点是:尺幅较小(尺幅最大者为《文殊菩萨赴法会图》,纵353.1厘米,横211.8厘米),题款较多(最长题款为《普贤菩萨赴法会图》,200余字),个别系未完稿(《毗沙门天王像》未设色、《北魏藻井》);内容除临摹北魏、西魏、隋、唐、宋、元时期的敦煌壁画像之外,则有北魏长卷连环画与北魏、隋、唐藻井图案等摹本(其中藻井图案达27幅,见《张大千先生遗作敦煌壁画摹本》,台北故宫博物院编,1983年)。
临摹古代绘画是一种艺术活动,顾恺之有“摹拓妙法”之说。临摹壁画方法多种,用玻璃纸(透明纸)蒙描壁画为其中一种。该方法相对高效、精准,利于临本与壁画保持同等大小;故通过玻璃纸从壁画印模画稿,几乎是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那个时代画家临摹壁画的流行方法。后来,尽管我们不认同这种有影响壁画原貌的临摹方法,但只能历史地看,即回到张大千的那个特定时代去看;否则,就近乎苛责。
作者:一级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