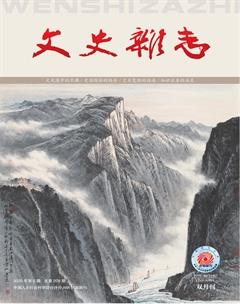集腋成裘?多财善贾(下)
张学君
二、山陕商帮的经营特点和山陕商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山陕商帮从清初起在四川从事金融和商业活动,延续时间长达200余年,牢牢植根于四川社会经济之中,其经营活动是卓有成效的。只是因为19世纪60年代以后,四川社会经济在朝廷掠夺政策和长期战乱的摧残下陷入全面凋敝,山陕商人的经营活动才逐步走向衰落。那么,山陕商人在清代四川的金融、商业活动有什么特点?山陕商资本对四川社会经济有无进步作用?笔者仅就这两方面,作一点分析。
(一)山陕商帮的经营特点
山陜商人在四川金融和商业活动中取得成功的原因很多,主要因素在于具有顺应社会经济需求的若干经营特点。他们多财善贾,随机应变,稳操传统市场的胜券。
1.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扩大金融活动范围
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从事金融活动的商人多限于借贷、典当等剥削活动。清代前期,这类活动已不能适应日益繁荣的商品流通需要,特别是不能适应大宗商品的长距离贸易的需要。山西商人雷履泰从往返四川、天津贩运铜绿的贸易活动中,摸索出银钱汇兑办法,采用代收代汇方式,使商家免除了银钱推挽之苦,获得出纳收发之便,加速了商品和资金的周转;而后,从事这一经营活动的山西票号如雨后春笋在四川和全国各地风行。银钱汇兑遂成为山西商人积累巨额财富的重要途径。
2.利用盐茶引法弊端,独占专卖商品转运之利
盐茶等重要商品关系国计民生。清初即实行产地与销岸挂钩,核定各州县引额,招商颁引。四川盐茶均以引为运销单位。《清盐法志》卷二百五十五,《四川十二·运销门·截验》中记载,雍正十二年(1734年)规定:川盐每水引一张配正耗盐5750斤,每陆引一张,配正耗盐460斤;乾隆六十年(1795年),水引每张增至6500斤,陆引每张增至520斤;道光三十年(1850年),水引每张增至9000—10000斤,陆引每张增至640—800斤。《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四十二《征榷十四》记载,顺治间(1644—1661年),四川定边茶每引一张,配正茶100斤,附茶14斤;清末每引一张配大茶120斤(一包)或小茶120斤(二包),建立起一套产运销体制。这一制度试图从控制重要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入手,达到以产定销,“裕课便民”的目的。但是,盐茶引法只是清统治者的主观臆想,实行起来是“流弊殊深”,事与愿违。
以川盐引法为例。按引法规定,根据各州县地方大小,确定引额多少,“就县富民佥充商人,县或二三人或七八人,或十数人,分领引纸为坐商”[1]。充当引商者,必须是本地“殷实之户”。而实际上“本地之商殷实者少”[2],贪得无厌之人乘机“专其利”,以多占引张为利源所在”。当其领引之初,或领引十余张、或数十张,至多者百余张”[3]。坐商无力承运,西商(即山陕商人)乘虚而入,采取“租引代销”办法,向坐商“认给引课”。他们取得引商资格后,“察地方之光景,改配引张之多寡,本商贪得引利,西商之增引于彼无涉,所配盐斤,不得浮于定额,且有重照两次之弊”[4]。西商所以能随意增引,也是引法弊端所致。引法按丁分引,但销区“畅滞靡常,或以此县代销彼县之引,或以彼商认销此商之盐,互相认代,弊端丛生。久之,即按其认代者著为定额。而私行认代,仍所不免”。部分家资丰裕的坐商领引承运后,不善经营,又挥霍无度,“加以官吏陋规日增月益,不数十年,大半家资荡然。领引到手;无力运盐。始另觅殷实之户代为运销而收其租”[5]。于是,广大部分引张又落入西商之手。
西商租引承运川盐,其典引期限有一二年者,有三五年者,久暂不一。“本非世业,无所顾忌”,只想在最短时期,赢得最大的利润。因而,他们在租引期间,利用合法身份,从事非法活动,拼命榨取,实行摧残性经营,主要作法有四:首先抬价求售,在其租引销盐地区任意提高盐价,使“小民有食贵之虞”[6]。其次增引夹带、走私,利用其合法行盐引张,或反复买运,“重煦两次”;或改配、代销,以求增引多配;或与场商勾结,公然夹带,通过长江水道,运往湖北荆宜,或贵州施南、永顺各路销售,谋取暴利。[7]再者,既行私盐于他商引岸,又垄断租引销区为私有,排斥他商侵销,收养无聊匪徒为缉私巡役,对依法挑盐40斤的老弱残疾盐贩一律作为私枭打击。因此,销区贫民对西商恨入骨髓,不断激起武装反抗风潮。[8]最为弊端者,拖欠挪用课羡,延不交库,以壮大经营实力。西商采取类似的手法取得了边茶、大茶和部分腹茶的专销权。其结果造成盐茶引滞课积,价格高昂,商家获得垄断暴利。[9]
3.从事大宗商品长途转运,获巨额商业利润
山陕商人善于利用四川与外省隔绝的自然地理形势,大规模转运四川盐、茶、丝、棉、夏布、中药材等土特产品,转而从外省购回四川急需商品,取得由于两地买卖价格间的巨大差额而形成的巨大利润。如陕商向康藏运销边茶,而换回藏区土、特、畜产品。一些陕商采取不等价交换,“大秤、大斗进,小秤、小斗出”的欺诈手段和预买附息方式贸易,一般获利50%—200%。通常的情况是,边茶一封(18斤),可换取羊毛100斤。[10]陕商在川盐长途运销中,更是以谋求巨额差价为目的。贵州为川盐主要边岸,没有其他食盐来源。陕商利用这一情势,囤积居奇,抬高盐价。清代俗云:“黔人十种粟不能易一斗盐”,直至清末,茅台盐百斤,仍值白银二两左右,大大高于四川盐价。[11]咸同时期(1851—1874年),陕商为求垄断销售,在仁怀合组运销网络,独占黔岸市场,赢得超额利润。[12]此外,陕帮还善于选择运销时机。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淮盐运道阻塞,两湖淡食,需盐孔急。陕商乘机冒险闯关运盐下江,在湖北贸易,获得一斤盐换一斤棉花的厚利。在食盐严重短缺的时侯,售价竟高达一斤盐卖一斤白银之巨。陕商在“川盐济楚”的十余年中,得到了难以数计的高额利润。[13]
4.依靠封建特权保护,获得官商地位
山陕商人之所以在四川金融、商业领域获得巨大成功,形成首屈一指的客籍商帮,乃与他们始终寻求封建特权保护,千方百计获得官商地位息息相关。山陕商人在四川缺乏宗族乡党关系作社会基础,又没有直接的政治势力庇护,在四川兴旺发达是很不容易的。山陕商主要通过下述途径获得特权保护和官商地位:
(1)充当各级地方政府金库,为官方储存各种生息银两;甚至为朝廷垫支、汇兑、解送官银和军饷。
自清初起,陕商在各州县城乡的当铺、钱庄、盐号均替各级官府、书院和公益事业存放生息银两。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曾令各省督抚将军筹议兵丁恤赏生息银用途。四川决定将各营交商生息之款数万两,全数提回解目,归还原本。[14]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蓬州知事张彦烈,将充公、捐纳银两共300两,归入书院,每年收息银30两。[15]同年,温江士民募修菁峨书院白银340两,交两当商每月每两二分行息,每年共收利息银81.6两,作书院开支。[16]巴县监生彭元臣等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共捐银2800余两,兴建敦义堂,作义葬之用。其银交当商生息,轮流收管,每年约收息银140两,购木置棺。[17]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由于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大量对外赔款导致国库空虚、入不敷出,求助于苛捐杂税,却导致财权下移,尾大不掉。山陕商票号、字号进一步成为四川地方政府存放各类公款的可靠金库。仅据咸丰十年(1860年)资料统计,四川布政使司存放全省各大票号、字号的款项就包括:缉捕生息本银、堰工生息本银、捐输生息本银、缉捕“夷匪”生息本银、照票生息本银、号舍生息本银、续案孤贫生息本银、筹款生息本银、藏饷生息本银、藏台公费本银、八旗孤贫养瞻本银、代营弥补公费本银、城重等营公费本银,共计13项,合计白银30万两。[18]4月,川督曾望颜令将防边生息与缉捕生息银提用,共计23000余两。[19]同光(1862—1908年)以后,朝廷搜刮名目剧增,四川全省仅新增津贴捐输银即达400余万两之多。[20]四川人民负担沉重,普遍拖欠。官府为完成地方榷额,往往“向票号筹借”巨款,认给利息,定期归还;甚至地方杂派,也由票号钱庄借垫。[21]
(2)充任朝廷财政收支、汇兑要务。
鸦片战争后,山陕票号、钱庄已作为朝廷收支、汇兑公款的重要渠道。据统计:1891—1911年,包括四川在内的山陕商票庄代汇公款数合计为154711654两。[22]光绪十年(1884年),川督丁宝桢坚持由西商汇兑解部地丁钱粮各银。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户部向四川指拨甘肃饷银98万两,即由天成亨票号汇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川承摊庚子赔款,第一次付银220万两,亦由协同庆汇出。四川某些军政大员也通过票庄汇兑大量私款。如成都将军崇实私营土药,所积白银由票号汇兑北京,仅汇水即费银13万两,其汇银总数为二三百万两。[23]安徽芜湖道童瑶圃卸任返川,将搜括的10万两白银赃款交蔚丰厚汇回重庆,存放该号,每年支取1万两,10年取完,不计利息。
山陕商人通过上述与官方的密切金融合作,实际上早已求得封建特权保护。如光绪十一年(1885年),朝廷的加增饷源,饬令票号承领部帖(类似营业执照),每年纳帖课600两。川督丁宝桢以川省票号均系领本贸易,并非自拥巨资,请予免课。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川省票号周转不灵,川督鹿传霖还特别批准拨库款12万两,发交票商,不取利息。
5.独特的经营素质
山陕商人在四川金融、商业中的巨大成功,除上述因素外,还在于他们独特的经营素质。西商经营素质,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点:
(1)崇尚商业道德,讲求信誉。早期陕西三原县商人马仲迪,在川经商时,售货信条是:“务完物(商品质高量足)、无饰价(不抬价)、无敢居贵”,赢得了客商的信赖,“诸贸易至者,知不知,无不从交观公”[24]。清代前期,各地陕帮庄号大多以信誉为经商基本原则,经商讲究明码实价,童叟无欺;典当、借贷大体遵守定章,因此为各地商场信赖借重。此外,陕商受雇于人,亦能尽忠职守,不避艰险。如三原刘志春,在温江“执业商号”,适逢李蓝农民军进攻温江,“伙友悉逃,志春守职不去,事平,号东以此重之”[25]。
(2)具有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西商在四川成功者大多由“帮贸苦积”[26]。如创设温江泰和昌号的陕西渭南县焦氏,曾在成都帮贸14年。[27]他们大多在商界经历了长期磨炼和辛勤积累,为他们开创自己的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精明能干,具有敏锐的商业眼光。山陕商人善于洞察经济社会信息,同时能及时加以利用,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如山西商人根据清初商品经济繁荣,长途贸易大发展的趋势,开创了票号业务。如陕商利用盐茶引法,控制了贵州、康藏盐茶贸易等,都是明证。
(4)组织严密,办事认真负责。清代陕商当铺、钱庄遍布全川,其存放、借贷、抵押办法,均有严格的章程。如定规利息三分,腊月十五以后减价二分,当商一律照章办事,从不抬价谋利,因而在广大城乡信誉很高。俗云:“老陕最善放账”。陕商在商业活动中亦是如此,如陕商在贵州仁怀建立协兴隆盐号,下属70多个分号,从大掌柜到分号掌柜,职责明确,分工具体,待遇优厚。按陕帮习惯,每三年帖请股东到仁怀总号算账一次,算账完毕提出6万两白银三股均分,每股2万两,余利全部移作营业资金。平日股东不得在号内支取分文,也不得在号内食住。这一制度,陕帮严格遵守,从不违反,因而营业蒸蒸日上。
由于山陕商人具有上述经营特点,因而在四川金融和商业活动中稳操胜券。
(二)山陕商资本开始向产业资本转化
清代山陕商人资本同前代商人资本相比,已有显著的变化,其主要标志是,它不仅开始通过发放贷款、收购产品的方式控制生产过程,而且开始直接投资生产,使自身向产业资本转化,具有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形态。
山陕商资本控制小商品生产的最初形式,主要是“假贷子钱”。以川盐为例,“四岸行商务十余家,悉是陕西大贾,资本甚巨”[28];而富顺、犍为两场“半皆穷灶,买水煎盐,佣工薪炭,咸资借贷,商人购盐,长短应付,复乘艰窘,故昂其值”[29]。陕商于是乘机控制贫弱灶户。又如丝商向井研县贫户假贷“丝黄钱”,让他们提供廉价生丝。预付货款,如重庆商贾对江津、隆昌夏布的收购,习惯提前一年付给夏布行部分货款,再由这些行家向接受定货的四乡农户发出付款通知,每年成交额达20万两白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山陕商资本自清代前期开始,就不断向井盐业资本转化,大规模投资自贡、犍为等盐场井灶。在自贡盐场,陕商采用“直接投资”“做下节”“佃煎”“杜卖”等多种手段源源不断地开办新井,接办收买旧井,租佃卤水、天然气等,直接经营盐业,获取剩余价值。最典型的例证是;道光七年至八年(1827—1828年),自贡大场商李四友堂与成都陕西盐茶大贾高某订立合约,合办自贡盐井。高某一次投资白银3000两,加入李氏产业,扩大经营,先后开凿卤井7眼、天然气井3眼,水火俱旺,获得极大成功。另一典型例证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自贡大场商王三畏堂开放扇子坝,与陕商合办新井,“出山约”规定:地主出一井三基(井基、碓房、车房、灶房基),每开凿一井,客方出押山纹银400两,主客按比例分配收益,客股期滿交还主人。陕商资本另一个投资重点地区是犍为盐场。犍为盐场先于自贡繁荣,故有“金犍为,银富顺”的俗语。陕商对这一地区的盐业极为重视,他们专门向生产济楚优质花盐的“十提”(十大灶)投资。到清中叶以后,陕商资本已控制了其中的“六提”。同治间,陕商在四川各盐场中的投资比例已占绝对优势。四川布政使刘蓉说:“川省各厂井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30]由此可见,陕商向井盐业资本转化的倾向是很明显的,其进步性应予肯定。
三、山陕商资本衰落的历史原因
清代四川山陕商人虽有直接控制手工业和向井盐业投资的事例,但从山陕商资本的积累水平看,转向产业资本的比重十分微弱,不代表其资本的主流。山陕商资本的基本形态一直未能突破商业资本的范畴,终清之世,很少出现新的投资趋向。与此同时,山陕商资本由于自身的封建性和晚清社会经济的全面衰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微的道路。据笔者初步考察,清代四川山陕商资本衰败的主要原因是:
(一)封建性的挥霍
山陕商人作为客籍商帮,大多视四川为经商口岸,视原籍为终养乐土,落叶归根观念很强。在不少记载中可以看到,他们经商稍有积累时,即将白银运回原籍。如三台县陕籍利川、泰昌两当,“每年运回陕西之数莫可限量”[31]。陕商原籍多系大家庭,往往在家族析居时,将川省庄号银钱瓜分。咸丰十一年(1861年),西安府渭南县焦承武向其侄索取四川温江县泰和昌号产业白银3300两,“其银由川号拨给”[32]。陕商吕渭振在成都开设的金盛元号,光绪四年(1878年)吕氏兄弟析产时,号银7600两,即由原籍之弟提去3800两。根据学者调查:巨额资金转移原籍后,为光宗耀祖,一部分用于修建宗祠、坟墓,购置田地产业等,也适当开销于怜孤惜贫、修桥补路慈善事业方面,以联络乡情;更多的财富,则作为窖银收藏,以为子孙后世财富。[33]
(二)捐纳、报效
清代商人捐纳、报效问题,已有不少著作论及。捐纳为清廷弥补财政亏空办法。随着后期财政支出恶性膨胀,捐纳名目繁多,商人,特别是山陕商经营的盐茶、票号、钱庄、当铺首当其冲,负担沉重。据有关论著披露,山西票号仅咸丰二年至三年(1852—1853年)捐纳总额即达白银267万两之巨。[34]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咸丰四年(1854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有西商参加的捐纳、报效共14次,捐银总数达140余万两之巨。在如此巨额流通资金被清廷搜括的同时,西商换回的是有名无实的大量虚衔、封典。这些虚衔、封典虽然充分满足了西商由商而绅的精神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们的商业利益不受地方势力侵犯,但随着大量商业流通资金不断流失,必然使他们经营的商业和金融业受到致命打击,从而导致其在四川的衰落。
(三)遭受战乱的毁灭性破环
清代后期,云、贵、川战乱频仍,其间特别是咸丰五年(1854年)发生的李永和、蓝朝鼎起义,横行数省,历时六载,在四川攻占60余个州县;对四川城乡经济的破坏特大。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后,四川发生的红灯教反清风潮波及全川,数年不绝。辛亥保路运动以后,四川新旧、主客各军大肆抢掠银行、庄号、商家店铺,进一步加剧了四川商业和金融业的破产。山陕商帮在全川动乱的冲击下,性命、财产朝不虑夕,所操商业和金融业不断亏折,难以为继,不得不卷款逃回原籍。成都府温江县陕帮老号益顺和,“因蓝大顺之乱,所有号内现银尽数兑回陕西。不意同治元年,陕西亦遭回乱广……川号兑回本银俱已散失”[35]。川盐销往贵州四岸(分别由永宁、仁怀、涪州、綦江为口岸)的行商十余家,“悉是陕西大贾,资本甚巨,迨至黔乱(即咸丰四年至六年贵州发生教军和苗民起义,席卷贵州东南、东北大部分地区)”,相率歇业;秦中又遭回祸,家产荡然,不能重整口岸。清代前期,劍阁县下寺场为陕西经商城镇,“场多富人”;咸同时期,“兵荒迭见,农困商敝”[36]。
成都为山陕商票号、钱庄、当铺和各类商业聚集之区。辛亥保路运动中,成都发生兵变。乱军首抢大清银行、浚川源银行、藩库,次及商业场、私家银号、票号和东大街各商号,公私财货抢掠一空,损失不下千万金。犍为县陕西富商两家,辛亥以后“均各歇业”[37]。新繁县清中叶以来,秦商多达18家,“国变后遂辍业无闻矣”[38]。总之,山陕商人作为清代四川重要的客籍商帮,在辛亥革命以后已湮没无闻。他们在四川商业、金融业中失去了原有的影响。他们曾经辉煌的历史,亦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注释:
[1][29]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五。
[2][4][7][8]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山货》。
[3][6]《四川盐法志》卷二十二《征榷三·纳解》。
[5]王守基:《盐法议略》。
[9][28]《四川盐法志》卷十三《转运八·官运上》。
[10]《清代四川藏区的边茶贸易》,《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11](清)光绪《仁怀厅志》卷二。
[12]《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7—159页。
[13]《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62—163页。
[14]《蜀帑出纳汇览》卷中《当本生息》。
[15]《蓬州志》卷四《书院》。
[16](清)嘉庆《温江县志》卷三十六《捐施》。
[17]《巴县志》卷二《恤典》。
[18]四川大学整理《巴县档案》第二册,第58—60页,1860年(咸丰十年)。
[19][20][21]《巴档抄件》,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40页、348—349、626页。
[22]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第136—139页。
[23]欧阳昱:《见闻琐录·后集》卷二《将军汇费》。
[24]温纯:《明处士马公暨配硕人景氏墓志铭》,《温恭毅公文集》卷十。
[25]民国《温江县志》卷八。
[26]《清代名臣判牍》卷四。
[27][32][35]《樊山公牍》卷二。
[30]刘蓉:《奏清筹办川省盐厘折》,《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七《征榷五》。
[31]民国《三台县志》卷十二。
[33]参看张正明:《山西工商业史拾掇》,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页。又: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田培栋教授为研究西商问题,曾专门赴山西、陕西商人原籍考察。上述部分史实承蒙田老师提供,谨志谢意。
[34]孔祥毅:《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
[36]李榕:《下寺场陕西会馆记》,民国《剑阁县志》卷九。
[37]民国《犍为县志》卷六《经济》。
[38]民国《新繁县志》卷四《礼俗·工商业》。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