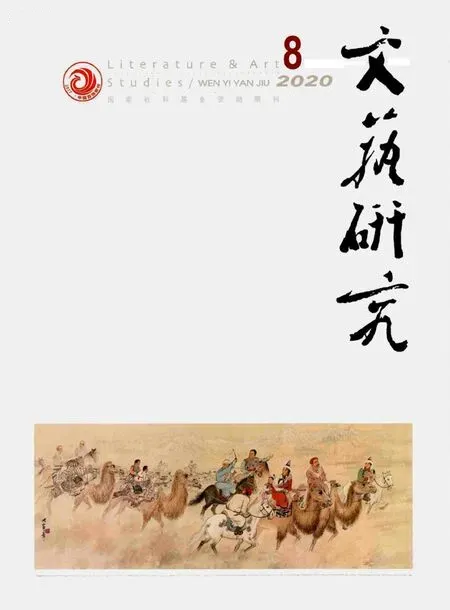通人传统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
赵普光
通人传统是中国人文传统中重要的流脉。“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故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①所谓通人,王充《论衡·超奇篇》曰:“博览古今者为通人。”②中国传统文人重淹博,而耻为专家。这当然和传统的教育方式有关,刘东所谓“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之初,不管中华文明缺乏什么,也绝不缺乏通识教育”③的判断,大体是符合事实的。只是中国古代的人文教育与时下所谓通识教育并不完全相同,“中国传统教育,也不提倡通才,所提倡者,乃是通德通识”④,故“中国教育则在教人学为人。天生人,乃一自然人。人类自有理想,乃教人求为一文化人、理想人”⑤。即使在现代学术和教育体制建立之初,通人传统依然赓续不绝。如近现代的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鲁迅、周作人、钱钟书以及金克木等,无不既在多个方面有精深研究,又绝不局限于某一学科,而是能够融会贯通,接近通人之境界。
而至当代,由于分科越来越细密,专家日多,通人传统几成绝响,出现了“学问上的分工愈细,而从事于学的人,则奔驰日远,隔别日疏,甚至人与人之间不相知”⑥的现象。具体到人文教育,“今日大学教育之智识传授,则只望人为专家,而不望人为通人”⑦。这与萨义德所说的情况类似:“今天在教育体系中爬得愈高,愈受限于相当狭隘的知识领域。”⑧这种专业化现象,在文学上表现为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分途。在当代中国,作家和学者都已经专家化,作家往往是职业文人,学者几乎都是专家,各自画地为牢,看似独领风骚,实则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⑨,而非完整的人。钱穆的话至今言犹在耳,“今天世界的道术,则全为人人各自营生与牟利,于是职业分裂”,“职业为上,德性为下,德性亦随职业而分裂”⑩,颇具警示作用。
尽管如此,事实上,凡是有着重要影响和突出成就的作家,其创作背后大致都有着勤勉的文化追寻、自觉的理论意识和一定的学养积淀。在当下文坛,已有作家意识到知识学养、文化修养等对自己创作的重要性,意识到现代性科层体系的钳制和规训,他们尝试通过“文”“学”兼通的写作使自己的生命保持润泽。本文从“文”与“学”融通的角度,探寻文化修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互渗、互为滋养的复杂关系。重提通人传统,对专业化、科层化日益严重的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应具启发意义。
一
文学是文化的表征,它不是从森林荒野中冒出的怪物,似乎与文学之外的一切都密切相关,存在着通的现实或可能。在近代中国的专业化倡导与实践中,对文学进行系统化、科学化的研究,在带来文学革命的同时,也造成了新的问题。将中国文学提纯之后进行专门的创作实验和学术研究,容易将文学与其得以生长的原生态的人文森林割裂。然而,文学之树要想成长、鲜活、生动,需要在人文森林中与其他学科自然地相处、融合、竞争。所以,有必要将文学之树重新还原到那个本属于它自己的人文森林之中,使之自由生根、自然成长。
要使文学接受文化的滋养,则文学家须首先成为一个有根之人。这就要求文化与学养在文学家的心灵深处扎根。大凡影响较著、作品质量较高的作家,多有文化与学养的自觉⑪。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名的作家中,贾平凹算是在此方面较为自觉的一位。写作之外,他性喜收藏,其生活浸淫于秦砖汉瓦的历史气息和文化氛围中。他曾记述自己“上书房”的陈列:“每个房间靠墙都竖有大型的木格玻璃柜,下三格装着书籍,上三格放了各类收藏的古董,柜子上又紧挨着摞满秦、汉、唐时期的陶罐。而书案上以及案左和案前的木架上又摆放了数十尊石的木的铜的佛像和奇石、瓷器。地上也随处堆着书籍、石雕、砖刻、根艺、缸盆。”⑫这些秦汉陶器、拓片、铜镜等,于贾平凹来说,不仅是器物,更是承载着文化的密码。终日与历史断片、文化遗迹相处,其文学写作难免散发着呛人的历史文化的烟尘和气息。对此,冯骥才解释说:“细看被平凹摆在书桌上的一样样的东西:瓦当、断碑、老砚、古印、油灯、酒盏、佛头、断俑……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人文的碎块与残片,从中我忽然明白这些年从《病相报告》《高兴》到《秦腔》,他为什么愈写愈是浓烈和老到。”⑬贾平凹曾谈及写作《古炉》时收购了一尊明代的铜佛,这尊铜佛给予他神谕般的启发:“这尊佛就供在书桌上,他注视着我的写作,在我的意念里,他也将神明赋给了我的狗屎苔,我也恍惚里认定狗屎苔其实是一位天使。”⑭
贾平凹的创作风格是有迹可寻的,这个轨迹的变化与其自觉的文化追寻相关。从书写农村改革,到刻画都市人性的畸变与沉沦,再到关注超越性的精神存在,他在矛盾、冲突中试图追求一种近于神秘主义的文化寄托与皈依,其创作与秦汉陶罐、佛首等古董一起,寄托、投射着他的精神探寻。因此,贾平凹的文学创作风格逐渐从清新走上朴拙、混沌一路。
文化积淀与学养结构的来源、方式有多种。与贾平凹不同,自称“素人作家”的莫言,其早年的文化接受方式就主要是“用耳朵阅读”⑮。莫言的知识来源,首先是民间文化,他表示:“故乡的传说和故事,应该属于文化的范畴,这种非典籍文化,正是民族的独特气质和秉赋的摇篮,也是作家个性形成的重要因素。”⑯这种“非典籍文化”,亦即作为小传统的民间文化构成了他童年汲取的主要文化资源。当然,莫言事实上也用眼睛阅读,“文革”粉碎了其中学梦,他只好“在夜晚的油灯下和下雨天不能出工的时候”读书⑰。他说:“在绝望中,我把大哥读中学时的语文课本找出来,翻来覆去地读,先是读里边的小说、散文,后来连陈伯达、毛泽东的文章都读得烂熟。”⑱他在童年时读过《封神演义》《三国演义》等古典章回小说,还有《青春之歌》《破晓记》《三家巷》《林海雪原》等革命文艺作品。在部队担任政治教员并兼职图书管理员时,他“读了很多文艺方面的书”⑲。后来在北师大研究生班学习时,他甚至萌发“做一个‘学者’型的作家”的念头⑳。笔者曾对此做了大致的统计,发现莫言明确提及的作家、作品约有145位/部,其中中国古典作家、作品有18位/部,中国现代以来的作家、作品有53位/部,外国作家、作品有74位/部,中国与西方约各占一半。如果按照出现频率来说,他提及中国文学更频繁,其中尤以蒲松龄为最,现代作家谈及较多的是沈从文,而当代文学中的“红色经典”则是其早年的重要阅读对象。可见,在莫言的知识体系中,以蒲松龄为代表的传统小说是其创作资源的底色,而具体到莫言的语言风格,应与1949年后三十年间的独特文风的熏染和积习关系密切。
至于很多研究者一贯强调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对莫言的影响,其实与其早年的“非典籍文化”的积淀有关。也就是说,域外文学思潮与莫言所熟悉的中国民间文化发生了化合。与莫言同乡的张炜曾说:“拉美文学的气息与中国民间文学的气息是颇为接近和相似的……东夷文化、楚文化等就很像拉美,很有些‘魔幻’……这里的作家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开始听民间故事,这是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什么狐狸黄鼬,各种精灵,荒野传奇,应有尽有,那可不是拉美传来的。”㉑在这个意义上,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之于莫言的影响,其实是为他打开自我世界提供了契机。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给莫言带来的,首先是叙事技巧的启发。莫言从《十三步》开始就有了自觉的理论意识。这时的莫言注重小说结构的实验,而这是从人称上开始的。人称的变化,其实是视角的转换,这会带来结构上的调整和移动。《十三步》将所有人称交织运用,小说结构发生巨变。也就是说,接触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后,莫言创作的结构意识明显增强。这样强烈的自觉意识和自觉实验,也是他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长篇小说的重要原因。更为关键的是,作为他者的马尔克斯、福克纳,激活了莫言长期被压抑于心灵深处的对民间文化的记忆和体验。莫言曾谈到第一次接触马尔克斯作品时的心情:“我之所以读了十几页《百年孤独》就按捺不住内心激动,拍案而起,就因为他小说里所表现的东西与他的表现方法跟我内心里积累日久的东西太相似了。他的作品里那种东西,犹如一束强烈的光线,把我内心深处那片朦胧地带照亮了。”㉒于是自《白狗秋千架》开始,莫言笔下“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地理概念”,“从此就像打开了一道闸门,关于故乡的记忆、故乡的生活、故乡的体验就全部复活了”,“对故乡记忆的激活使我的创造力非常充沛”㉓。故乡记忆的激活不仅是复现故乡的历史事实,更能打开曾经的情绪、体验及心理世界。马尔克斯、福克纳让莫言长期没有觉察的自我世界开始苏醒,使他意识到自己的文化根系。于是,逃离马尔克斯、福克纳这“两座灼热的高炉”㉔,反而成就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莫言的自觉意识,并最终成就了其文学世界。也正是这种方法的自觉与丰富的乡土经历化合在一起,催生了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让他逐步找到适合自己的文化土壤。对此,张炜的描述很准确:“在文学上,拉美文学的嵌入,使中国当代作家纷纷找到了自己的‘抓手’。当然,这个过程中一定还会强化自己的生活经验,使二者在深部对接起来。拉美的舶来品会跟自己的文化土壤搅拌在一起,让不同的颗粒均匀地混合起来,然后再开始培植自己的文学之树。”㉕
二
文学的根基在文化,而文化的根本则在人。对人之为人的终极关怀的理解决定了人的生存方式,进而呈现出相应的文化形态和面貌。此处的“人”,不是指被专业化、技术化的“单向度的人”,而是完整、健全的人。人的健全,就是将生命打开,把人性的本然发挥出来,摆脱蒙昧状态,展现出人性的光辉与尊严,体现出“上下与天地同流”㉖的独立人格,最终实现生命的自觉的过程。
职是之故,文学是生命的学问。与任何其他专业和门类相比,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主体——人,最忌专门化、专业化。被专业化的人,往往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被切割。人不是机器,文学也不是技术活。要想使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抵达超越性的境界,作为主体的人应该是“通人”,而不能是码文字的“专家”。作家不能是只会形式炫技的词章家,学者也不能是唯知寻章摘句的考据家,而首先应是一个完整的人,即所谓“通人”。如此才能通过文学表现生命状态,体察和阐释文学中的生命状态。反之,只追求文字“颜值”的单纯词章家,无法实现文学的生命化;只会堆砌话语、拼凑理论的学问家,无法体察文学的生命感。所以,打破支离的隔绝,实现生命的自觉和融通,才能使文学真正成为生命的学问。
生命意识的自觉,对写作极为切要。对此,钱穆曾说:“文化乃群体一大生命,与个己小生命不同。个己小生命必寄存于躯体物质中,其生命既微小,又短暂。大生命乃超躯体而广大。”㉗所以,笔者以为,生命意识即意识到个体生命其实是融于历史、宇宙之中的。意识到这一点,方能接近或实现个体生命与历史、宇宙的融通,进而实现对个体生命的纵深开掘和体认。故牟宗三说:“生命总是纵贯的、立体的。”㉘唯如此,方能对生命持包容之心,以同情之理解去体察自我之外的生命,所谓悲悯由此成为可能。文学是内在于生命的。正因为内心深处诗意的葆存,所以无论何种艺术,比如诗、书、画,虽形式不同,它们追求的目标都应是生命境界的抵达。生命与文学的切己发现,是作家能够寻到创作之源的根本。作家的创作即是生命与生命的相通、融合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安忆将小说命名为“心灵世界”,因为作者是“在他心灵的天地,心灵的制作场里把它(指小说——引者注)慢慢构筑成功的”㉙。当然,更进一步说,笔者以为王安忆将小说命名为“心灵世界”其实并不准确,“生命的世界”要更加恰当。
生命有一个本真、纯澈的质,这在儿童身上保留和体现得更加充分。所以,很多作家都极为关注儿童,试图从童眸中发现另一个更真实的世界。我们看到,一旦书写童年,作家的情感、记忆等内在世界便会无法抑制地打开。迟子建认为:“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㉚贾平凹曾有一配画文字《黎明喊我起床》,写一只失去了父母的小鸟,其情态让人内心怦然㉛,读此文能看到中年之后颇有老气和沉郁之相的贾平凹还有清新、柔和的底色,这自然源于他仍未尽失的儿童之眼。与此类似,贾平凹的画,虽然无法以美称誉之,但“能说有童趣、有逸气、有拙趣、有憨趣、有蔬笋趣,还有一些漫画式的调侃调子……犹如出自孩童手笔”㉜。发现儿童生活,其实是发现自我,发现人的生命本身。莫言曾说自己写作时感到“不是一个成年人讲故事给孩子听,而是一个孩子讲故事给成年人听”㉝。当然必须指出,童年视角和叙事的采用,是切近生命的一种方式,并不意味着采用儿童视角就一定能抵达生命意识融通与自觉的境界。毋庸讳言,除极个别作品,莫言整体上对童年书写的专注程度还远远不够。相比而言,萧红《呼兰河传》、林海音《城南旧事》等作品,似乎更能透射出儿童之眼的纯澈,表达出生命的美好。
儿童的眼睛和心灵,因少有“污染”而更加纯粹。丰子恺曾慨叹儿童“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㉞。同样是观看世界,儿童之眼与成人之眼差别甚大。成人因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功利算计、利害权衡,得失的忧患往往成为其获得更深切的生命感受的障碍,儿童反而能够直接觉察到生命的本质。借用笔者曾论及的“用脑”和“用心”的区别来说,孩童往往用心去体会,而成人总是用脑去算计㉟。成年人往往从外在的概念出发观察事物,影响和限制他们对外部世界更真实、更深入的感知体验。而孩童看待外部世界,往往是从体验而不是概念出发,使他们反而能够更直接地发现事物(世界)的本相。在这个意义上言,赤子之心最具“通”的意识。
与此类似,通人因其融通,而不陷于狭隘的专业之网,更易看见或接近生命之本相。文学创作的前提之一,是作家对生命的体验与通感。如果要对生命有体验,就不能从概念出发,而是要先从生命体验出发,用孩子一般的眼睛和心灵去体验世界,发现自我。这种自我,在童年还是一种不自觉的存在,即处于存在却又未被意识的状态,而在阅读与体验、思索的融通中,被重新唤醒,从而生命意识就由不自觉走向了自觉。
三
现在,让我们返回到“文学”的本义上思考“文”与“学”的关系问题。从本源上说,文学不仅是文字的纯粹艺术形式的呈现,更应有人的学养、见识、思想的内蕴㊱。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文与学的会通。换言之,文学应该是审美(艺术、形式)、学养(见识、思想)的融合与淬火。
文学创作与学术涵养之间互动和会通的现象,在“五四”新文学中相当普遍。及至当代文坛,就整体看,这种会通现象却日渐稀缺。但如细致考察,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一些作家创作的某些方面还是能找到文、学会通的痕迹。关于作家创作与学养的关系,莫言曾以叶兆言为例指出,现在很多作家缺少叶兆言身上的书卷气:“这种书卷气是在长期的生活环境里边熏陶出来的,是潜移默化的。别的人当然也可以引经据典,说很多掌故,但是那个味道不对。”㊲这实际上已经暗含着学养的会通问题:学养并不仅仅指读万卷、诵千篇,而是指要将之融于生命之中,化于创作之内。贾平凹也曾意识到文与学的关联,这从他大量的读书札记、文论、叙录等可以看出。贾平凹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谈及自己的阅读与顿悟的过程:“原来散文的兴衰是情的存亡的历史。散文是人人皆可做得,但不是时时便可做得;是情种的艺术,纯,痴,一切不需掩饰。”㊳其实,笔者想进一步指出,“不需掩饰”的本色文字,最不易为之。当去了色彩、抒情和堆砌的辞藻,卸下粉饰而“素面朝天”后,文学只有靠作家的学养、见识、思想来打动人。正如董桥所言,文章“须学、须识、须情,合之乃得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谓‘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㊴。洗尽铅华后,作者真实的面目开始直接面对读者,于是唯同时具备学、识、情并将三者熔铸于一身者能为之。
不论客观上是否能达到心向往之的境界,在主观上提升学识以滋养创作的当代作家不乏其人,由阅读与写作的关系可以发现其创作变化的蛛丝马迹。贾平凹对所读之书、所观之物非常敏锐,其文风的每一次转变,都与此相关。他在1983年与友人的信中说,“多读外国的名著,多写中国的文章”㊵。在1985年,他明确谈到自己的阅读选择:“特别喜欢看一些外国人研究中国古典艺术的专论,这是一种无形中的中西融合,从中确实使我大有启示。”㊶他早年还曾专门比较废名(冯文炳)与沈从文:“冯氏之文与沈从文之文有同有异,同者皆坦荡,平泊,冷的幽默。异者冯多拘紧,沈则放野,有一股勃勃豪气。”贾平凹对废名的创作技法和特点有过详细的归纳,并联系当时的文学创作,刻意自省:“当今文坛,林斤澜、何立伟有冯之气,吾则要拉开距离,习之《史记》,强化秦汉风度。”㊷所以,从《九叶树》开始,贾平凹的创作透露出师法古典文学的刻意努力㊸。此后,贾平凹开始远离为文的清浅,文风大变,作品越来越透露出神秘主义倾向,这与他渐趋沉溺于边缘神秘文化,而缺少对刚正浩大文化气质的汲取有关。说到底,这可视为作家在文化修养和见识通透上难以达到理想状态的表现。在文化气质方面,同为陕西作家,熏染儒家气质的陈忠实与散发民间道家气息的贾平凹就形成颇有意味的对照。二人文学作品气质上差异的形成,与其文化的取径有关。
由此可见,学术修养、文化积累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互渗、互通对于作家所起的作用,并非“生活源泉”说所能完全解释。有研读经典作家、作品自觉的作家,其精耕细作的文本解读,常常别具作家之眼。如毕飞宇近年来对古典小说的读解,就别有会心。他对小说的故事叙述逻辑非常关注,且特别留意小说如何设置关键性情节。他曾谈及林冲被逼上梁山的过程中,非常关键的地方是“风”和“雪”㊹。《水浒传》是部古典传奇之作,这些细节设置一眼望去似乎与毕飞宇本人的小说并不构成直接对应的关系,然而如果我们细细阅读他的作品,比如《上海往事》,就会意识到,小说叙事的步步推进,在逻辑上也都通过关键的节点推动故事展开,使一切都在逻辑中环环相扣,有《水浒传》的影子。大致上,作家阅读时的眼光与其写作时的笔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关联和互动。毕飞宇在论及《红楼梦》时,特别留心日常生活中人物之间反常的情感关系。比如在谈到《庆寿辰宁府排家宴,见熙凤贾瑞起淫心》时,他尤其注意到,小说于细微处体现出王熙凤与贾蓉的关系,即他们二人与日常逻辑不同甚至相反的心理关系㊺。对这类细节别有会心的研读、观察,与其小说家的眼光很有关系。在小说《推拿》中,毕飞宇在展示小孔与王大夫、小马之间的关系时,有的细节就很有意味,能暗示出人物之间微妙复杂的情感关系。比如,小孔因为称呼问题,抡起枕头来打小马,“枕头不再是枕头,是暴风骤雨。抡着抡着,小孔抡出了瘾,似乎把所有的郁闷都排遣出来了。一边抡,她就一边笑”㊻。小孔暧昧的内心以及三个男女之间的隐秘情感,通过这一细节微妙地暗示出来:他们之间好像很平常却并不平常,有着莫可名状的复杂情感关系。
四
先有对象之实,继有对象之名,后有对象之学,此为古今学术之通例。文体的命名和研究,亦不例外。“学”之出现,本是研究、深化的必然,但问题在于,“学”一旦出现,就会反过来作用于研究者,积习既久,会使人忽略了上述通例,以至于将后来形成的“名”(概念)与“学”(理论)作为考察和研究不证自明的前提。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后设的文体之名和文体之学,也是一种想象和建构。很多人的头脑中,小说、诗歌、散文就应该像文学概论所定义的那样。这种分门别类是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文学繁盛发达,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表象繁荣掩盖下的另一种单一,压抑了文学本来具有的多种可能性。
比如小说,“毫无疑问,小说的理论是小说之后的产物,在没有小说理论之前,小说已经洋洋蔚为大观”㊼。然而一旦小说之名形成,小说之学大盛,人们就会从小说之名去倒推这一类文体的特点,凡不合小说定义者,自然就会排除在外。这种名、实的倒置,不免会规约作家的写作,让作家在动笔之前,脑海里已经有了一套既定的文体规范。这种外在规范内化为自觉的规训,最后形成了集体无意识。所以贾平凹甚至断言,“当小说成为一门学科,许多人在孜孜研究了,又有成千上万的人要写小说而被教导着,小说便越来越失去了本真”㊽。
与纯粹的学术研究不同,作家写作时应清醒地认识文体的这种后设性,不能过分拘泥于文体规范的限制。这种清醒和自觉,在写作中的表现之一是文体界限的突破与文体风格的互渗。比如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汪曾祺的《陈小手》等作品,几乎所有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都认为是小说,但细味之,我们可以发现,其淡到极致的语言、几乎无事的叙述、隐匿不彰的情绪所带来的风致、韵味又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小说有明显距离。事实上,文体并不如理论规定的那样泾渭分明。如果不拘泥于既定的所谓现代的小说概念,《陈小手》似乎更暗合传统的文人笔记体例,《竹林的故事》其实更接近于中国的文章传统或者说散文(不是后来狭隘化之后的抒情气息强烈或描写成分浓重的散文)传统。
而说到散文,这一文体的模糊与互渗现象更加复杂㊾。贾平凹主持《美文》杂志时曾呼吁要突破狭隘的散文观念,“还原到散文的原本面目,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鼓呼大散文的概念,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鼓呼真正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外的这个时代的散文”㊿。贾平凹最初办《美文》时倒是确实有意“大开散文的门户”,“并未列入过作家队伍,但文章写得很好的科学家、哲学家、学者、艺术家等等,只要是好的文章,我们都提供版面”。通观《美文》会发现,该杂志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贯彻了这一主张:作者的身份不局限于职业作家,散文内容也明显溢出了通常的那种抒情性、描写性的散文范围。贾平凹在《读稿人语》中明确说:“把文学还原到生活中去,使实用的东西变为美文。”不能不说,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定西笔记》《我是农民》等混沌的写作实践与这样的散文观念不无关系。
贾平凹在呼吁散文改革时鲜有提及周作人的散文观,但是如果我们回顾当初周作人在《美文》一文中的主张,可以发现贾平凹的倡导,在无意间呼应了周作人的“美文”观念。若将周作人专论散文的《美文》《文艺批评杂话》《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等综合观之,可以体会到,周作人对散文的观念是开放与融通的,包括“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若再联系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亦能发现:周作人将冰心清澈见底、清丽细腻的文章与废名、俞平伯浑朴、古雅的文风相比较,暗含着对散文文化底色的体认。
一个优秀的作家须有且会有“越轨”的勇气和胆识。莫言也曾言及,作家要通过各种手段,使文体的含义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化。“各种文体实际上就是对作家的束缚就像笼子对鸟的束缚一样,鸟在笼子里是不安于这种束缚的,要努力地冲撞,那么冲撞的结果就是把笼子的空间冲得更大,把笼子冲得变形,一旦笼子冲破,那可能是一种新的文体产生了。”所以,在优秀作家的创作中常会有溢出与冲破现象。换言之,作家的创作实践,并非将某种文体纯化、固定的过程,而是文体杂糅互渗、不断增生的过程。比如莫言的《生死疲劳》,可以说是在“恢复古典小说中说书人传统”,也可以视为溢出现代文学意义上的小说边界的一种“越轨”实践。
五
地球本没有经线、纬线,它们只是勾勒于地球仪上的假设。经纬线之出现,盖源于人们为了区隔和定位的方便。类似地,宇宙自然、社会现实、内在精神本是一个综合整体的存在。明乎此,就应意识到,学科、专业之划分,从根本上说,类似于经纬线的“创造”。所以,在专业化如此细密的当下,具有超越的意识,具备通人的素养,不被“文学经纬”所限,才能使研究基于真实的“文学地球”,而非基于虚拟的地球仪般的“文学模型”。现代学术已演进到今天如此繁复、细密的地步,研究和创作要继续推进和创新,整合融通成为必然。文学创作、研究的突破,往往要有一定的超越意识,而不能被那些并非不证自明的概念限制。当文学还处于混沌原初的状态时,亟须专业化来推进文学形式的完善与审美的纯粹,然而一旦文学走向纯粹,就可能会流于纤巧,演变为形式的操练,那么通达意识将重新成为文学突破瓶颈的关键。故此,从混沌走向专门化,再从专门化走向融通,文学创作和研究之推进就能螺旋式地前行。
在当代社会,学科经纬线的区隔,专门化、科层化的日益严密,已带来了某种遮蔽:“蔽于分而不知合……蔽于知与用而不知其更高的价值……蔽于一尊而不知生活之多元……蔽于物而不知人……蔽于今而不知古,或蔽于进而不知守。”专家化的作家、职业化的学者容易成为某种门类、领域、方向的知识生产者,如同流水线上的工人,生产了知识,却同时可能将自身以及接受知识的受众变成机器。在此过程中,人的精神也渐趋支离:“随着不可避免的专业化和理智化的过程,主要作用于物质领域的进步,也将精神的世界分割得七零八落;生活领域的被分割,进而使普世性的价值系统分崩离析,信仰的忠诚被来自不同领域的原则所瓜分,统一的世界于是真正变成了‘文明的碎片’。”如何修复碎片化的文明,恢复人精神的完整,实现人的生命自觉,也是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的迫切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重识通人传统,发掘新时期以来影响较著的几位作家的文、学互渗倾向,就颇具意味了。但必须补充指出的是,本文虽然提到几位作家,但这并不表明笔者完全认同他们的创作,更不是认为他们已经具有了通人风范。事实上,他们离通人传统还很远。以他们为例,笔者意在表明,除了个人的天赋外,他们的创作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作家中比较突出,并有相对的可持续的创作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对文化修养的追求。但由于特殊时代的限制,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见识,如果放在更大的范围中和更高的要求下,当然绝非无可指摘。
总之,以超越二元切分、非此即彼的统合研究思路,从通人的角度,考察当代文学中仍有隐约留痕的文、学兼通的人文传统,思考为何及如何将专业化切割成的单一面孔恢复成统一、完整的人,思考重塑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文向度的可能,这种研究取向的意义不容小觑。我们知道,萨义德所定义的知识分子,要溢出专业领域之外,而中国传统的“通人”则与萨氏所说的知识分子相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是通人,而不仅仅是专家。这就让笔者想起冯克利在评价韦伯时所说的,韦伯不仅是社会学专家,而且在“追求一些更具普遍性的东西”。这种对“更具普遍性的东西”的追求,意味着对知识分子精神内涵的坚守,也意味着对通人传统的继承。
①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14页。
② 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07页。
③ 刘东:《全球化时代通识教育的困境》,《文汇报》2010年7月31日。
④⑩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23页,第226页。
⑤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2页。
⑥ 钱穆:《学与人》,《历史与文化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版,第195页。
⑦ 钱穆:《改革大学制度议》,《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⑧ 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7页。
⑨ 参见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⑪ 本文所说的学养和文化修养,并非仅指有过所谓系统的学校教育经历。很多时候,文化自修和天然复杂的生活阅历反而能够促进学养和生命的融通化合。
⑫ 贾平凹:《震后小记》,《顺从天气》,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18页。
⑬ 冯骥才:《四君子图(代序)》,《文章四家:贾平凹》,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⑭ 贾平凹:《〈古炉〉后记》,《文章四家:贾平凹》,第336页。
⑮ 莫言曾回顾说:“我在童年时用耳朵阅读。我们村子里的人大部分是文盲,但其中有很多人出口成章、妙语连珠,满肚子都是神神鬼鬼的故事。我的爷爷、奶奶、父亲都是很会讲故事的人。我的爷爷的哥哥——我的大爷爷——更是一个讲故事大王。他是一个老中医,交游广泛,知识丰富,富有想象力。在冬天的夜晚,我和我的哥哥姐姐就跑到我的大爷爷家,围着一盏昏暗的油灯,等待他开讲。”(莫言:《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什么气味最美好》,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19页)
⑯㊼ 莫言:《超越故乡》,《会唱歌的墙》,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第200页。
⑰ 莫言:《我的中学时代》,《什么气味最美好》,第9页。
⑱⑲ 莫言:《我的大学梦》,《什么气味最美好》,第18—19页,第21页。
⑳ 莫言:《我的大学》,《什么气味最美好》,第16页。
㉑㉕ 张炜:《拉美文学中的加西亚·马尔克斯》,邱华栋选编:《我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华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页,第12页。
㉒ 莫言:《故乡的传说》,《我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第4页。
㉔ 莫言:《两座灼热的高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杨守森、贺立华主编:《莫言研究三十年》上,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页。
㉖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5页。
㉗ 钱穆:《大生命与小生命》,《晚学盲言》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93页。
㉘ 牟宗三:《自序》,《生命的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㉙ 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3页。
㉚ 迟子建:《北极村童话》,《迟子建文集》第1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㉛ 参见贾平凹:《黎明喊我起床》,《贾平凹语画》,山东友谊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㉜ 朱以撒:《大精神与小技巧》,《贾平凹语画》,第130页。
㉞ 丰子恺:《从孩子得到的启示》,《缘缘堂随笔》,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3页。
㉟ 赵普光:《世间几人真书痴》,《博览群书》2013年第12期。
㊱ 关于文学观念的演变,参见赵普光:《如何的现代,怎样的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中国意识》,《文艺研究》2014年第3期。
㊳ 贾平凹:《关于散文的日记》,《关于散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4页。
㊴ 董桥:《自序》,《这一代的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页。
㊵ 贾平凹:《学习心得记——与友人的信》,《关于散文》,第29页。
㊶ 贾平凹:《我的追求》,《关于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4—25页。
㊷ 贾平凹:《读书杂记摘抄·〈冯文炳选集〉》,《关于散文》,第71—72页。
㊸ 对此,丁帆在1984年给贾平凹的信中有论及,参见贾平凹:《关于〈九叶树〉的通信》附“丁帆来信”,《关于小说》,第19页。
㊹㊺ 参见毕飞宇:《“走”与“走”——小说内部的逻辑与反逻辑》,《钟山》2015年第4期。
㊻ 毕飞宇:《推拿》,天地出版社2017年版,第85页。
㊽ 贾平凹:《〈白夜〉后记》,《关于小说》,第80页。
㊾ 比如周作人20世纪30年代后的散文写作将文与学熔铸,已经远离了现代一般意义上的所谓“纯散文”一路,知堂法脉实为现代散文文体的一个异类。但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太大,无法绕开,在作为学科和专业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不能不将周作人放在散文家中叙述。若是写作风格类似周氏散文的其他人,基本上不大可能进入文学史视野。因为研究者可以以不是散文、不算文学的理由轻率地排除这些文字。其他文类也存在这样的现象,比如面对既不像诗歌又不是散文的某种文学体例,就出现了所谓“散文诗”的折衷命名。其实命名暧昧的本身就反映了文体的交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