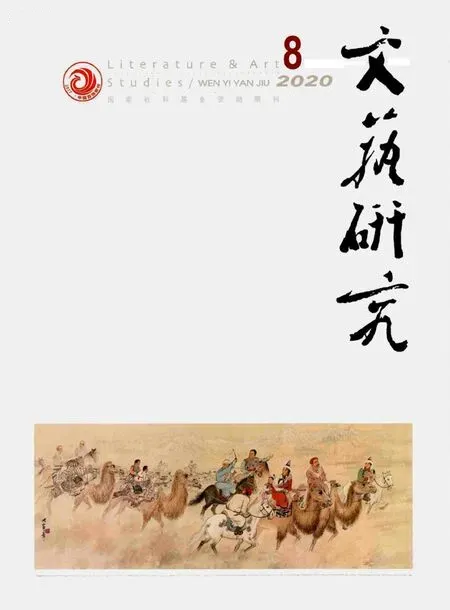生命意识与李白之纵酒及饮酒诗
詹福瑞
王安石评李白说:“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①说李白诗篇中多妇人,似言过其实,但说其诗中尽酒,却是实情。对于白之纵酒和饮酒诗,旧说多以发泄政治失意解释之②,此自有道理,但既不全面又失之皮相。实则白之纵酒,根在洞彻生命之本质所产生的苦闷,追求心灵的自在与自由。
一
饮酒诗,在李白年青时并不多见。白出川到金陵后,始作饮酒诗,如《金陵酒肆留别》,然此时饮酒多是逢场作戏,如魏颢《李翰林集序》所写:“所适二千石郊迎,饮数斗,醉则奴丹砂舞《青海波》。满堂不乐,白宰酒则乐。”③也是有意学谢安的生活作风,故作风流。但是,李白长期客游他乡,久之也有了独酌排遣苦闷的习惯。如詹锳《李白诗文系年》系于开元十四年(726)的《秋夜板桥浦泛月独酌怀谢朓》,诗中云“独酌板桥浦,古人谁可征?玄晖难再得,洒酒气填膺”,就是李白月夜独酌于江宁板桥浦怀念谢朓之作。此后,李白诗中多有以“独酌”为题者,如《独酌》《月下独酌四首》《北山独酌寄韦六》《春日独酌》《独酌清溪江石上寄权昭夷》等;诗中有时也提到“独酌”,如《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之一:“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可见,“独酌”已经成为李白喝酒的习惯。
李白之纵酒,多以为是在长安放还后④。其实“酒隐”安陆的十年,喝酒已成为他生活中的常态。他写给其妻许夫人的诗云:“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赠内》)“太常妻”用东汉周泽故事:“世人为之语曰:‘生世不谐,作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⑤解说此诗者,都以为是李白与夫人戏谑之语⑥,其实是写实。李白有他的天下抱负,并不满足于家庭生活,十年蹉跎,虚度生命,其内心应该极为苦闷,饮酒因此成为他排遣苦闷的生活方式。
开元十八或十九年间,李白有一次京城之行,然寻求政治机会未果,失意而返。这十年间,李白漫游于河南嵩山、洛阳,湖北襄阳,山西太原,最后移家山东兖州。这一时期,李白“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是其纵酒放歌的第一个高峰期。独酌仍是他喝酒的日常状态,开元二十二年,白与元丹丘偕隐嵩山颍阳时所作《北山独酌寄韦六》,写其隐居深山的闲适生活:“坐月观宝书,拂霜弄瑶轸。倾壶事幽酌,顾影还独尽。”其中就有顾影自酌。然而更多的是呼朋唤侣的豪饮,如写于开元二十二年的《襄阳歌》。山简为晋代名士,其纵酒故事见《晋书·山简传》⑦和《世说新语·任诞》⑧。李白游襄阳,有感于山简故事而发为此诗,如朱谏所言:“此即襄阳旧事以寓感慨之意。”⑨此诗虽然是演绎山简饮酒故事,但诗之主旨却值得注意。《李诗直解》说:“此白负才不偶,故纵饮放旷。言万事皆虚,独酒为真也。”权力如秦之丞相李斯如何?“咸阳市中叹黄犬”,临东市而叹黄犬,岂能比月下的一杯酒!百姓为其立了遗泪碑的羊公又如何?“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古碑材,龟头剥落生莓苔”,其碑之龟头剥落,霉苔生矣。唯清风、明月与自己同在,醉如玉山自倒的身体是真,所以“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当百年与酒同生死耳!此诗有对人生的三重否定:否定了权力,即否定了功名;否定了身后声名,即否定了不朽;否定了巫山云梦,即否定了男女情爱。对于人的生命而言,这些都是虚假的,真实的生命,就是山公那样的烂醉如泥,醉生梦死。显然这是李白功名受挫后一时的愤激之语,天宝初李白再入京城,也说明功名对于他来说,仍然是人生最重要的目标,而且一生都未放弃。但此诗也不能仅仅视为李白的假想,借酒浇愁应是他真实生活之一部分。此后李白所作的饮酒大篇,主题大都类此。
天宝初,李白被玄宗召入翰林,出入宫中,陪侍玄宗左右,但饮酒的生活习惯没有改变。不过此时李白交往的多为朝中名士,他此时喝的是名士酒。他的第一个酒友应是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贺知章。《本事诗·高逸》:“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⑩天宝六载(747),贺知章已经辞世,李白《对酒忆贺监二首并序》忆及此事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没后对酒,怅然有怀,而作是诗。”诗之一:“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不唯是酒友,亦是知己,因此李白的怀念充满深情。《流夜郎赠辛判官》也记载了李白在长安的饮酒圈子:“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著金鞭。文章献纳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酒友是五侯七贵的贵族,并与贺知章、李璡井、李适之、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等结为“八仙”之游。此时的纵酒,一洗独饮的落寞和江湖狂饮的放浪不羁,显示了士人的气度与风流。当然醉酒也误事,但在当时士人看来,这才是名士风流。魏颢《李翰林集序》:“上皇豫游,召白,白时为贵门邀饮,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杜甫《饮中八仙歌》也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⑪都是把李白醉酒作为名士风流来写的。即使是玄宗也如此对待之,并给予包容。所以关于李白在宫中的传说,醉使高力士脱靴、贵妃斟酒、醉草嚇蛮书等,当非无稽之谈,都应有真实生活的影子。
天宝三载,李白被玄宗赐金放还。从李白离开长安到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之乱,是李白又一个十年漫游时期。李白一入京城,未能寻找到政治机会,离开时虽然不免有政治理想不得实现的寂寞与失落,但毕竟对未来还充满希望。而此次长安的遭遇,则是进了朝廷,有了实现理想的机遇,却得而复失;而且此次离开,既是自己无奈的放弃,也是玄宗的决定,李白失去的可能是永远远离长安,远离朝廷,远离政治,功业之抱负、人生之理想可能永远不得机会实现,所以李白此次的政治挫败感远远超过了他一入京城之不遇。这一时期,纵酒以排遣政治苦闷是李白的重要生活方式,如写于天宝十二载的《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云:“蹉跎复来归,忧恨坐相煎。无风难破浪,失计长江边。危苦惜颓光,金波忽三圆。时游敬亭上,闲听松风眠。或弄宛溪月,虚舟信洄沿。颜公三十万,尽付酒家钱。兴发每取之,聊向醉中仙。过此无一事,静谈《秋水篇》。”这是李白北上燕蓟回到宣城所作,略见此一时期的心理与生活。在心理上,他既为国家面临的危机忧心如焚,又为自己无力参与政治而憾恨。而其生活则是百无聊赖的,只有靠饮酒打发日月,“或眠敬亭而听松风,或泛宛溪而弄水月,尽沽酒之钱以罄醉乡之趣,读《秋水》之篇以求养生之术而已矣,此外无所为也”⑫。
李白的饮酒诗此时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从作品看,多见李白独酌或与友朋纵饮,而且醉酒似乎成为常态。因此,此时期的诗中,多有以“醉”为题者,亦多醉态描写。如《月下独酌四首》之四:“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这是写要醉的愿望。《醉后赠从甥高镇》:“匣中盘剑装鲐昔鱼,闲在腰间未用渠。且将换酒与君醉,醉归记宿吴专诸。”所写的是自己已经半醉,兴如奔马,所以,以剑换酒,一醉方休。当然更多的是酒酣而歌舞。饮酒而歌,酒酣而舞,应是唐人聚会习见的场面。《月下独酌四首》之一:“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这是诗人举杯对月而舞。《梁园吟》:“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连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赌酒酣驰晖。酣驰晖,歌且谣,意方远。”既有分曹赌酒,又有对酒而歌。《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白发对绿酒,强歌心已摧。”《五松山送殷淑》:“载酒五松山,颓然《白云歌》。”已然醉意朦胧,勉强而歌,聊抒郁闷罢了。此为醉酒而歌,还有醉后而舞。《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袖长管催欲轻举,汉中太守醉起舞。”此为太守醉后起舞。《过汪氏别业二首》之二:“永夜达五更,吴歈送琼杯。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此是诗人酒酣起舞。而《鲁中都东楼醉起作》:“昨日东楼醉,还应倒接罢堆离。阿谁扶上马?不省下楼时。”则写诗人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还应”乃是诗人醉醒后的回忆,是否如山简倒戴头巾,谁扶着上的马,如何下的东楼,都不得而知了。《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醉来脱宝剑,旅憩高堂眠。中夜忽惊觉,起立明灯前。”此为醉后醒来之状。也有醉后的走马,如《自广平乘醉走马六十里至邯郸登城楼览古书怀》:“醉骑白花骆,西走邯郸城。扬鞭动柳色,写鞚春风生。”可谓醉酒后的春风得意。还有醉后的失态,《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绮裘乌纱巾与酒客数人棹歌秦淮往石头访崔四侍御》:“草裹乌纱巾,倒披紫绮裘。两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酒客十数公,崩腾醉中流。谑浪掉海客,喧呼傲阳侯。半道逢吴姬,卷帘出揶歈。”诗人乌纱帽不整,紫绮裘倒披,十余个酒徒手舞足蹈,喧呼笑闹,惹得岸上人拍手嘲笑,指点揶揄,真如《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所言“高阳小饮真琐琐,山公酩酊何如我”,醉后放浪之态的确堪比酒徒山简。
至德二载(757),李白坐永王璘罪系狱浔阳,乾元元年(758)流放夜郎,二年获释,往来于江夏、浔阳、豫章、金陵、宣城一带,直到去世。李白获囹圄之罪,幸得遇赦而归,打击之大可想而知,故写有《万愤词投魏郎中》:“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恋高堂而掩泣,泪血地而成泥。”可谓呼天抢地,泣血成泥。但是李白饮酒、醉酒依然如故。乾元元年流夜郎初离浔阳时所作《流夜郎永华寺寄寻阳群官》云:“朝别凌烟楼,贤豪满行舟。暝投永华寺,宾散予独醉。”从诗意看,当是从凌烟楼上船,与“贤豪”们一路饮酒,到了永华寺,李白已经酩酊大醉。上元二年(761),李白流放夜郎回到宣城时所作《赠刘都使》中写道:“而我谢明主,衔哀投夜郎。归家酒债多,门客粲成行。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所求竟无绪,裘马欲摧藏。”李白举债虽然未必真是酒债,但负债在身、生活困窘当为事实,故有求于刘都使,却没有结果。但此时的李白仍然多有喝酒的宾朋,一日而倾千觞。他不仅饮酒如故,酒间歌舞亦如故。《对酒醉题屈突明府厅》是上元元年李白寓家豫章时所作,诗人访建昌县衙,然故人建昌县宰不在,醉题其诗于厅中,故有“陶令八十日,长歌《归去来》。故人建昌宰,借问几时回”之句。从诗中也可看到李白的醉态:“风落吴江雪,纷纷入酒杯。山翁今已醉,舞袖为君开。”是一个人对雪饮酒以怀故人,醉后又对雪而舞。写于上元二年的《对雪醉后赠王历阳》:“君家有酒我何愁,客多乐酣秉烛游。谢尚自能鸲鹆舞,相如免脱鹔鹴裘。清晨兴罢过江去,他日西看却月楼。”谢尚、相如二句用典,是用二人比主人和客人,以司马相如所穿之鹔鹴裘贳酒,比王历阳待客饮酒之豪爽;而以谢尚能作鸲鹆舞,写自己醉后之舞。同是上元二年作的《送殷淑三首》,从诗看,则是喝了一夜送别酒:“痛饮龙筇下,灯青月复寒。醉歌惊白鹭,半夜起沙滩。”醉后而歌,惊起一滩白鹭。醉而歌舞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李白去世前,宝应元年(762)所写的《九日龙山饮》云:“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虽为罪臣,依旧是自斟自饮,对月而歌而舞。
李白不仅喝酒如故,纵酒时的万丈豪情亦丝毫不减,如写于乾元二年的《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江夏赠韦南陵冰》:“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之三:“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醉后答丁十八以诗讥余捶碎黄鹤楼》:“黄鹤高楼已捶碎,黄鹤仙人无所依……待取明朝酒醒罢,与君烂漫寻春晖。”这些饮酒诗多呈狂态,动辄扫平鹦鹉洲,捶碎黄鹤楼,铲去君山,借洞庭赊取月色,醉杀洞庭秋色,极尽夸饰之能事。看似酒兴豪情不减当年,甚至胜过当年,实则蕴含着一个老者贾其余勇夸其酒胆的意态,已经有了“佯狂殊可哀”(杜甫《不见》)⑬的意味。
二
李白之纵酒,首先是为了挥斥政治失志之忧愤。而他一生矢志不移追求功业,源自对生命本质的认识:生命不仅要自然归于死亡,而且在世的时间亦十分短暂,生命的意义即在于济天下、得荣名、享不朽。所以他政治上所遭受的挫折,实则就是他追求生命价值与意义所遭受的打击,饮酒挥斥忧愤就是挥斥生命之苦愤。
玄宗召入翰林之前,李白寻找不到晋身的政治机会,苦于时光虚掷,荒废年华。进入朝廷之后,又为玄宗对自己以倡优蓄之而苦恼,于是浪迹纵酒。赐金放还,更使其失去实现理想抱负的信心。“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宣州谢朓北楼饯别校书叔云》)可以说,李白一生都在为政治抱负不得施展、生命价值和意义不得实现而忧虑苦闷,因此饮酒成为李白排遣苦闷的一种生活方式。《月下独酌四首》之四即反映出李白借酒浇愁的心理:“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所以知酒圣,酒酣心自开。辞粟卧首阳,屡空饥颜回。当代不乐饮,虚名安用哉?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之所以乐饮,是因为心中愁绪万端,只能借酒浇熄,使心情变得开朗,醉酒之境就是万事不扰的仙境。所为何愁?《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写道:“傅说板筑臣,李斯鹰犬人。飚起匡社稷,宁复长艰辛!而我胡为者?叹息龙门下。富贵未可期,殷忧向谁写?去去泪满襟,举声《梁甫吟》。青云当自致,何必求知音!”傅说乃负土筑墙之人,李斯亦传为牵黄犬、驾猎鹰之人,二人皆贫贱而起为重臣者,而李白自己却未遇知音,功名无就,富贵无期,故心中充满深深的忧虑,醉酒以排遣心中之惆怅。又写于天宝八载的《醉后赠从甥高镇》云:“江东风光不借人,枉杀落花空自春。”此诗依旧是写光阴不等人、人生易老而英才不得其用之意,所以诗人要倾家以换酒钱,与友人悲歌酣饮以求一醉。“时清不及英豪人,三尺童儿唾廉蔺”,真乃一肚皮的牢骚!连三尺儿童都要唾弃廉颇和蔺相如这样的将相之才,可见今日之“清明盛世”,真是无须人才了,有多少英才埋没民间啊!诗人反话正说,对朝廷的用人之道极为不满。
李白以酒挥斥忧愤的诗中,常常纠结着生命存在的诸多矛盾。如具有代表性的诗篇《将进酒》,或以为作于开元二十三年,或以为作于天宝元载⑭,然玩其诗意,显然是李白长安放还后为释放苦闷而作,因此诗中充满了情感与思想上的矛盾。
首先,美好的生命与生命苦短、人生易老之间的矛盾要用酒来缓解。生命是美好的,然而黑发转瞬即白、不复再青,人生岁月之一去不回,若黄河东流向海,没有回波。生命易逝如此,安得不及时行乐、饮酒为欢!这样的诗,在李白集中有很多,如《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碧草已满地,柳与梅争春。谢公自有东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今日非昨日,明日还复来。白发对绿酒,强歌心已摧。君不见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黄鹂愁醉啼春风。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卧桃园东。”时间长河的特点是日复一日,既不为物亦不为人而暂停,所以当一位白发之人面对碧草如茵、柳梅争俏、黄鹂鸣春之景,暮年之悲感自会十分强烈,所以要惜此春光、莫辞一醉。《待酒不至》抒发的是同样的情感,山花向人笑时正好是喝酒之时,春风与醉客两相宜,趁此春光及时为欢。
在此类诗中,如《春江花月夜》那样最有宇宙意识也最唯美者当数《把酒问月(故人贾淳令予问之)》:“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晖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姮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闻一多评价《春江花月夜》说:“更敻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⑮闻一多的评价可挪用于李白此首饮酒诗。“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只此一问就是深沉而又寥廓的宇宙之问。不过在永恒的穹空与明月面前,李白没有错愕,因为诗人对月亮之永恒的认识是清醒的,此问乃是明知故问。此问的归宿在人,在不识古时月亮的今人,在不识今时月亮的古人,在于似流水一样来而复去、去而复来不停逝去的人流。在月亮面前,人是如此之易逝,人生是如此之匆促!而此时的月亮则似宇宙老人,悲悯地看着可怜无助的人。诗人也没有憧憬,没有悲伤,因为他知道这无法改变,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旷达地面对这一切,对月饮酒,快乐地度过此生。
李白生命苦短之叹,皆与其功业理想未能实现相关,因此人生易老、及时行乐,所反映的是生命短促而功名理想迟迟未能实现的矛盾。
其次,自恃为天纵奇才与对玄宗倡优蓄之的愤懑,要用酒来消解。李白被玄宗召入翰林,而且颇受礼遇,对于布衣之士李白而言,其所追求的功名自可说获得了成功。不过,玄宗对李白的认识和使用,前后有很大变化。李白初入朝廷时,玄宗对其甚为器重,“降辇步迎,如见绮、皓……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李阳冰《草堂集序》),且欲委以“纶诰之任”(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即中书舍人之职。然而,或因为同列者的谗言,或由于李白经常醉酒承诏,玄宗非但未委以重任,而且故意疏远之。李白在宫中,不过陪侍玄宗、承诏以写歌诗。这样的待遇与他的政治抱负差之甚远。不过,李白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⑯,自信个人为天生的俊才,终究会得到重用,酒资之钱何须虑也,尽情纵酒为乐而已。
其三,钟鼓馔玉生活的虚幻给诗人带来的幻灭感,要用酒来填充。李白出身寒素,出于快乐主义的生命观⑰,他对钟鸣鼎食的富贵生活还是充满向往的。但长安三年,出入宫廷,陪侍皇帝左右,多与豪贵交,耳濡目染,体验并熟悉了王侯贵族的豪奢生活之后,李白认识到了这种表面奢华所掩盖的空虚。尤其是遭到玄宗体面的黜退,使李白更增加了钟鼓馔玉生活不过一时的幻灭感,酒即成为他忘却这一切的麻醉剂。
其四,圣贤的寂寞与纵乐者留名的矛盾,要用酒来开释。本来,历史上留名者多为圣贤、英雄,或建功立业,或著书立说,皆可不朽。李白对此不是不知,他的诗中,对此歌颂甚多。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可能有两个含义:要么是圣者贤人生前皆寂寞,如果是这个意思,则李白是为圣贤的命运鸣不平;要么是死后寂寞,而此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圣贤的实际情况是生前寂寞而身后有名,并不寂寞。如果是后一个意思,则李白是在说愤激之言,说反话,即圣贤建立了不朽功业,立言传世,又有何用?反不如饮酒作乐者既享乐于现世,又留下了身后之名,如“斗酒十千恣欢谑”的陈王曹植。这种玩世不恭的反语,充满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
写于天宝九载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可视为《将进酒》的注脚。萧士赟注以为此诗“造语用事,错乱颠倒,绝无伦理,董龙一事,尤为可笑,决非太白之作,乃元儒所谓五季间学太白者所为耳”。朱谏亦赞同此说⑱。其实,只有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和《将进酒》放在一起,才会看到二诗在情感、思想基调上的一致性。《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之“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就是《将进酒》“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压缩版,不用分析,即可看出其思想情感的相同之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之“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就是《将进酒》“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的补注。荣华富贵之不足据,不仅表现在此种生活之空虚,还表现在政治之不公平、仕途之险恶、世事之无常。李邕本为玄宗朝名士,历任括、淄、滑州刺史,后入朝,“后生望风内谒,门巷填溢”⑲。但为人嫉妒谗毁,不得留于朝中,出为北海太守,后被李林甫附会罪名而杖杀。诗中所言“裴尚书”,当为裴敦复,玄宗朝曾为刑部尚书,为李林甫所嫉,贬淄川太守,与李邕皆坐刘勣事被杖杀。二人贵为刺史、尚书,然终不免一死。李白自身遭遇之变化无端,虽然不能与李邕、裴敦复命运之惨烈相比,但从玄宗以特例召入翰林,备受恩宠,到遭人谗言毁谤,以致玄宗故意疏远、放还江湖,亦与李、裴二人颇为相近。因此,与其汲汲于功名、留恋于官场,不如远离权力的绞杀场,饮酒去也。《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之“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由来贱奇璞”,“孔圣犹闻伤凤麟”,就是《将进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的详细注解。
总之,李白饮酒,首先是为了抒发政治抱负不得施展、生命价值与意义不得实现的苦闷。从积极意义上说,他的饮酒诗是对黑暗政治的一种抗议与批判。如林庚所言:“他说:‘钟鼓馔玉不足贵’,‘一日须饮三百杯’,‘一醉累月轻王侯’!这里尽管是强调了饮酒,而它的实质却正在于那‘轻王侯’的歌唱上。”⑳正因为如此,他的这一类饮酒诗任达放荡,其激愤之情感常以放达之语出之,如“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情感之抒发性、冲击性都很强。当然,李白之饮酒,不仅仅是借酒浇愁、释放其政治苦闷而已,也有以酒来舒缓对生命、对生活、对人世间许多矛盾纠结不得其解心绪的意图,这样的饮酒诗,是考察李白丰富的内心世界的重要通道。
三
李白的饮酒是为了借酒醉麻痹自己的神经,暂时忘掉政治理想不得实现、生命苦短等愁烦,如《友人会宿》所说:“涤荡千古愁,留连百壶饮。良宵宜清谈,皓月未能寝。醉来卧空山,天地即衾枕。”他留连饮酒,是为了消除“千古愁”,醉酒之后,方有“天地即衾枕”的大自在。《拟古十二首》之八亦言:“月色不可扫,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萤飞百草。日月终销毁,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见此树老?金丹宁误俗,昧者难精讨。尔非千岁翁,多恨去世早。饮酒入玉壶,藏身以为宝。”诗人说,客愁似月色一样不可扫除,亦不可言说。但他还是说了,他所愁者,乃在天地日月终有尽时,渺小如人者更何以堪!所以他要藏身玉壶,即藏身酒乡,委身于大化。《拟古十二首》之三:“长绳难系日,自古多悲辛……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诗意与此相同。
这虽然是李白对待现实的一种消极的行为,但反映到其饮酒诗中,却呈现出诗人通过饮酒达到精神自在、心灵自由的积极意义。在这些作品中,李白自觉地融入了庄子的遗情和外物思想,并把它生动地表现在诗的境界中。或者说在醉酒之中,其精神状态恰与庄子的“坐忘”之境相契合,以至于他的饮酒诗对醉态的描写已经超越了对酒的物质的感官的享受,上升到了审美的态度,形象地描绘出精神出离世外的自由与自在。
庄子尚自然,讲“人的自然化”,“讲人必须舍弃其社会性,使其自然性不受污染,并扩而与宇宙同构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庄子认为只有这种人才是自由的人、快乐的人”㉑。怎样才能成为这种快乐的、自由的人?方法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外物”“坐忘”与“遗情”。《庄子·大宗师》借颜回之口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㉒所谓“坐忘”,就是不知有身体,不知有精神,不知有外物,“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㉓。
李白饮酒,所要寻找的正是此等不知有我、不知有外物之妙境。《春日独酌二首》之二:“我有紫霞想,缅怀沧洲间。且对一壶酒,澹然万事闲。横琴倚高松,把酒望远山。长空去鸟没,落日孤云还。但恐光景晚,宿昔成秋颜。”《独酌》:“春草如有意,罗生玉堂阴。东风吹愁来,白发坐相侵。独酌劝孤影,闲歌面芳林。长松尔何知,萧瑟为谁吟?手舞石上月,膝横花间琴。过此一壶外,悠悠非我心。”此处,李白所愁者,依旧是光阴催逼人老,依旧是孤独于人世的悲伤,但是作为对待生命的快乐主义者,李白要寻找解脱之道,因此而有世外之思,因此而有升仙之想。但既然一时无法成为神仙,姑且饮酒以达到神仙境界,于是他在月下松间弹琴饮酒,看落日于云中而没,飞鸟于长空而渺,怡情于美酒、美景与音乐之间,淡然忘掉一切。《自遣》:“对酒不觉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写的亦是酒后远离人间、与自然一体的境界。在《山中与幽人对酌》中,不仅是人与物的天地,也写人与人的关系:“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我醉欲眠卿且去”,用的是陶渊明故事。据《宋书·陶渊明传》,陶渊明喜喝酒,“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㉔。李白用此故事写人我之间的真淳关系,诚如《唐诗真趣编》所云:“‘我醉欲眠卿且去’固是醉中语,亦是幽人对幽人,天真烂漫,全忘却行迹周旋耳。”㉕酒后的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真淳,宛如天籁。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的饮酒诗有诸多作品同其山水诗、游仙诗一样,都表现出一种心灵摆脱拘束,获得自由、陶然忘机的境界,即审美的境界。《月下独酌四首》之二:“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天若不爱酒”,为何天上有酒星?“地若不爱酒”,为何地上有酒泉?由此可见天地都是爱酒的。李白就是要证明人之爱酒是符合天性的。酒中之趣或曰酒之秘密,在于喝上三杯可通大道,喝了一斗合于自然。这个自然,就是庄子所说的道。庄子以坐忘达于自然,而李白却是以醉酒达于自然。此之自然,就是心灵摆脱了一切束缚,获得了释放与自由。在《月下独酌四首》之三中,李白对一斗合于自然的状态作了具体描述:“三月咸阳时,千花昼如锦。谁能春独愁?对此径须饮。穷通与修短,造化夙所禀。一樽齐死生,万事固难审。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三月里的独酌,固然是孤独引起的,这有《月下独酌四首》之一可证。而千花似锦的春天,更加剧了诗人的寂寞愁烦,只有一醉,才会解此孤独与寂寞。醉中世界,是一个死生、天地、物我同忘的空灵世界。这样的醉中世界就是庄子“吾忘我”的境界,与坐忘、心斋所达到的境界颇为一致。《春日醉起言志》把这样的醉态写得十分逼真:“处世若大梦,胡为劳此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觉来眄庭前,一鸟花间鸣。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说是言志,但与一般的言志诗有很大不同。诗人并没有直接写志,而是描写他的醉态和醉中生活。春天之所以恼人,就在于它既是生命勃发的季节,又是勃发的生命凋零的季节,而且这一生命的转换是那么的短暂与突然!诗人因此对瞬间存在而又终归虚无的生命本质有了洞彻,感慨人生若梦,对酒自斟自饮以求一醉。此后的浩歌已是醉中之歌,所以一曲终了就进入陶然忘情的中圣境界。由此来看,李白之志,就是以醉中之梦应对人生之梦,争取精神的自由。这种超然于现实世界之上的情感和态度,就其本质来看,乃是一种审美的态度。“因为超出眼前狭隘的功利,肯定个体的自由的价值,正是人对现实的审美感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本质特征。”㉖此种对于生存状态的审美的态度,起自物质,达于精神;缘自现实之苦闷,却进入超越现实的快乐和适意,是士人的个体生命意识高度觉悟后而产生的对于生命目的的更深层次的追求,是典型的中国士人的生命意识。
再进一步深究,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美感?是心力战胜人世欲念与利害关系所产生的崇高感。一般认为,带给人震撼的崇高美来自自然的巨大或事件的奇伟,然而亦如叔本华所说,事实上崇高之美也来自人心灵的力量㉗,这里就包括对生活中利害关系的全然超脱而达到的心理平衡。乔治·桑塔耶纳论美感说:“如果我们因为意识到这个世界的苦难而要求自我解脱称为禁欲主义(斯多葛式)的崇高,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有一种通过维持心理平衡而求得自我解脱的享乐主义(伊壁鸠鲁式)的崇高。”又云:“崇高感本质上是神秘的,它超越一切清晰的知觉并催生出统一感和包容感。道德领域内同样如此,我们胸中的各种感情互相抵消,最后这些感情在包容中平静下来。这是享乐主义者达到超脱和完美境界的方法,它刻意吸取一切本能欲望达到禁欲主义者和遁世苦修者故意舍弃一切本能欲望所达到的同样目的。因此,即使对象没有对不幸的表现,也有可能被感动而取得构成崇高感的自我解放。”㉘乔治·桑塔耶纳的话用来分析李白饮酒诗所产生的美感,再恰切不过。在中国古代,酒与色往往连在一起,同为人的欲望的代名词,如上文所引王安石评价李白,说其诗十之八九不离妇人与酒,就是从人的欲望的角度评价李白诗歌,并从道德的高度给予批评。李白饮酒自然亦从欲望出发,但是最终却升华到脱离欲望、摆落利害、遗物忘我的境界,酒在其中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正是酒激发了诗人精神的力量,使之战胜了个人的得失欲望,战胜了人世的苦闷、烦恼,达到了心灵的平衡,使灵魂归于平静和熨贴。此类饮酒诗所产生的崇高感,即来自平静、超然的诗之境界中所蕴含的诗人强大的精神力量。
四
把饮酒上升到审美的态度,这在唐代饮酒诗中实为罕见。唐之饮酒诗,一类是宴乐酒,如魏元忠《修书院学士奉敕宴梁王宅》、张九龄《奉和圣制登封礼毕洛城酺宴》、宋之问《麟趾殿侍宴应制》、李峤《甘露殿侍宴应制》㉙,多谀颂之作。一类是饯别酒,如杜甫《王阆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别之作》:“万壑树声满,千崖秋气高。浮舟出郡郭,别酒寄江涛。良会不复久,此生何太劳?”㉚多写别离之情。一类是排忧酒,如孟郊《劝酒》:“白日无定影,清江无定波。人无百年寿,百年复如何。堂上陈美酒,堂下列清歌。劝君金曲卮,勿谓朱颜酡。松柏岁岁茂,丘陵日日多。君看终南山,千古青峨峨。”㉛此诗与李白饮酒诗最为接近,亦是有感于人生易老、岁月难留,劝人以饮酒解除苦闷。在写以酒排忧的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杜甫《醉时歌》,作于天宝十三载春,原注云:“赠广文馆博士郑虔。”㉜郑虔见赏于宰相苏颋,被颋推荐为著作郎,后遭人诬告私撰国史,因罪外贬十年。开元二十五年,唐玄宗因爱其才,置广文馆,任虔为博士。虔与李白、杜甫友好,颇具才华,其诗、书、画被玄宗称为“三绝”,但其生平穷饥坎坷。关于此诗主旨,《杜臆》的解释最为准确:“此篇总是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非真谓垂名无用,非真薄儒术,非真齐孔、跖,亦非真以酒为乐也。杜诗‘沉醉聊自遣,放歌破愁绝’,即此诗之解,而他诗可以旁通。自发苦情,故以《醉时歌》命题。”㉝《杜诗言志》亦云;“读先生此诗,几疑其为好饮者也,然而非先生也。又或谓先生托此而逃焉者,亦非也。盖好饮止可加于嵇、阮,而托而逃焉者,第可施之于靖节。而先生则以经世之才,急用世之志,所遭不偶,与郑虔负‘三绝’之望,徒就广文之冷署者略同。故一腔牢落不平之气,聊寄于曲糵以自遣。”㉞诗中写自己与郑虔“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㉟,虽然经常喝到忘掉你我的程度,但从此诗看,他们一起纵酒,是为了排遣穷愁不得志的苦闷。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如渑之酒常快意,亦知穷愁安在哉”㊱,亦属此类。
还有一类是闲酒。中唐诗人中,元稹和白居易的饮酒诗最多,后者多属闲酒类,如《适意二首》之一:“一朝归渭上,泛如不系舟。置心世事外,无喜亦无忧。终日一蔬食,终年一布裘。寒来弥懒放,数日一梳头。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㊲诗人置身世外,知足无求,或临花而醉,或夜酌而眠,皆是闲适生活之写照。皮日休《闲夜酒醒》写的也是醉酒醒来后的闲适之感:“醒来山月高,孤枕群书里。酒渴漫思茶,山童呼不起。”㊳这类饮酒诗很容易与表现了超然境界的饮酒诗相混,实则是有区别的。闲酒,喝的是闲适酒,饮酒是其闲适生活之一种情状,并非如超然酒那样在醉酒中全然忘却了世界,忘却了自我。
细数唐代饮酒诗,大致不出以上四类,而像李白那样直接描写饮酒并进入陶然忘机境界的作品并不多见。李白的此类饮酒诗,在唐代很难找到知音,上溯到晋宋时期,从陶渊明的饮酒诗中可以发现同类作品。从深层次看,李白吟咏生命意识的诗歌,多有陶渊明的影子在,尤其是其遗情舍物的情怀,与陶渊明《饮酒诗》颇为相近。陶渊明《饮酒诗》之七:“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谁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㊴本来陶渊明息交绝游,已经是遗忘俗世了,“今持菊饮酒,则连我遗忘俗世之情亦忘之矣”㊵。此诗不写饮酒之醉,但只一句“杯尽壶自倾”,就写尽了杯空壶倒的醉酒之状。而日落西山,万籁俱寂,只闻归鸟飞回林中的鸣叫,已然是醉中心灵与自然合为一体的精神状态。《饮酒诗》之十四写醉后之状:“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㊶相与挈壶而至、来请诗人喝酒的父老们,醉酒之后已经言行不能自主了,而诗人则进入了悠悠然不知有我、不知有物、不知身在何处的精神境界。所谓的酒中深味、酒中真趣,就是此种悠然忘我的自由情状。这种精神境界,与李白的“醉后失天地”“曲尽已忘情”完全相同,是一般饮者亦会获得,而只有深谙庄子逍遥之理的人才会在诗中表现出来的审美诗境。
① 惠洪:《冷斋夜话》,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3页。
② 如唐汝询评《将进酒》云:“此怀才不遇,托于酒以自放也。”(唐汝询:《唐诗解》,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李诗直解》评《襄阳歌》曰:“此白负才不偶,故纵酒放旷。”[佚名:《李诗直解》卷四,清乾隆乙未(1775)刊本]
③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本文所引李白诗文及诸家注评、研究资料皆据此书,仅随文注明作者、篇名、注家等。
④ 李阳冰《草堂集序》言李白在翰林遭玄宗疏远:“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亦曰:“同列者所谤,诏令归山,遂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
⑤ 《后汉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579页。
⑥ 詹锳系此诗于开元十五年,“疑是初婚后与其妻戏谑之词”(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郁贤皓、倪培翔认为系“自嘲醉酒之甚,戏谑安慰许氏夫人”(郁贤皓主编:《李白大辞典》,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⑦ 《晋书·山简传》:“简优游卒岁,唯酒是耽。诸习氏,荆土豪族,有佳园池,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晋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29页)
⑧ 《世说新语·任诞》:“山季伦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倒载归,茗艼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罢堆离。’”(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66页)
⑨ 朱谏:《李诗选注》卷四,明隆庆六年(1572)刊本。
⑩ 孟棨等撰,李学颖标点:《本事诗 续本事诗 本事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⑪⑬㉚㉜㉝㉞㉟㊱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7页,第2418页,第2933页,第410页,第415页,第415页,第410页,第697页。
⑫ 朱谏:《李诗选注》卷八。
⑭ 安旗系于开元二十四年,认为“此种特点之诗,求之开元前期不可得,求之天宝年间亦不可得,实非此期莫属”(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299页);郁贤皓系于开元二十三年(郁贤皓:《李白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页);王运熙、杨明以为天宝初作于梁宋、东鲁一带(王运熙、杨明:《关于李白〈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远别离〉的写作年代》,《李白研究论丛》第1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
⑮ 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唐诗杂论》,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18—19页。
⑯ 此句一作“天生我身必有财”,又作“天生吾徒有俊材”,敦煌残卷作“天生吾徒有俊才”,于此可见李白修改诗句的痕迹,参见《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360页“校记”。
⑰ 詹福瑞:《“人生得意须尽欢”——试论李白的快乐主义生命观》,《文艺研究》2018年第8期。
⑱ 朱谏曰:“士赟此论大概得之。”(朱谏:《李诗辨疑》卷下,明隆庆六年刊本)
⑲ 《新唐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757页。
⑳ 林庚:《诗人李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㉑ 李泽厚:《哲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9页。
㉒㉓ 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57—259页,第259页。
㉔ 《宋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88页。
㉕ 郁贤皓:《李太白全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2934页。
㉖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㉗ 叔本华指出:“悲剧使我们超越了意欲及其利益,并使我们在看到与我们意欲直接抵触的东西时感觉到了愉悦。”(叔本华:《叔本华美学随笔》,韦启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1页)
㉘ 乔治·桑塔耶纳:《美感》,杨向荣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181、182页。
㉙㉛㊳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56、596、632、692页,第4196页,第7093页。
㊲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29页。
㊴㊶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52页,第268页。
㊵ 方祖燊:《陶潜诗笺注校证论评》,(台湾)兰台书局1971年版,第146页,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