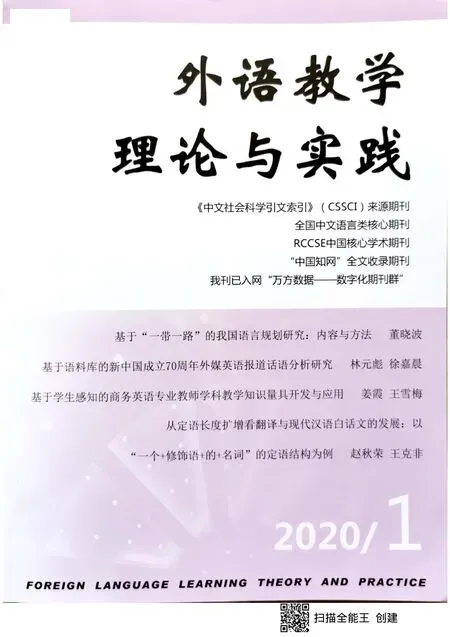西方翻译伦理代表理论批评与反思
湖北大学 吕 奇 华中科技大学 王树槐
提 要: 国内翻译伦理研究一定程度上缺乏“理论自觉”与“学术自信”,对西方翻译伦理理论模仿借鉴多于批评反思。以中国传统中庸思想为视角,从伦理观、本体论与方法论三个维度对以贝尔曼异质伦理、韦努蒂存异伦理和皮姆译者伦理为代表的西方翻译伦理理论进行批评与反思,可发现真知灼见中亦有偏颇之处,有失中正、中和与中行。借中国视角,观西方理论,于扬弃中寻求古与今、中与西的圆融调和,为丰富国内翻译伦理研究路径与内涵提供启示。
西方学界认为,解释学传统的翻译研究(尤其是功能目的论和极端解释学代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提倡诠释,肯定误读,强调意义的延宕性,导致了翻译缺乏标准,令翻译实践陷入一种虚妄、怀疑、无定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局面。为了挽救这一缺乏约束的权力真空局面,翻译伦理研究逐渐兴起(Pym, 2007: 24-44),现已成为当下翻译研究的一大重要领域。
吕俊的《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是国内学者关注翻译中伦理道德的发轫之作,他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引入翻译学研究中(吕俊,2001: 261-281),构建了翻译伦理研究的雏形;后又借鉴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正式提出了翻译伦理学的概念(吕俊、侯向群,2006: 271)。其后,国内翻译伦理研究陆续展开,主要着力于四个方面: 构建翻译伦理学的设想、译介国外翻译伦理研究成果、运用国外翻译伦理研究成果研究翻译实践问题和翻译伦理问题的理论探讨(骆贤风,2009: 14-17)。
过往十五年,国内翻译伦理研究以“照着说”、“套着说”居多,而“接着说”、“反着说”相对较少。诚然,西方的翻译伦理研究较之中国起步更早,理论模式也更为成熟;但前者有其产生的特定政治动机、文化背景和社会语境,并非金科玉律,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由于国内翻译伦理研究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这也导致了其“理论自觉”与“学术自信”的缺失。具体体现在:“削足适履”式照搬或套用西方翻译伦理理论规约中国语境下的翻译实践要远多于以中国传统思想为视角对西方翻译伦理理论进行形而上的批评与学理上的反思。鉴于此,本文将另辟蹊径,借用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从伦理观、本体论和方法论三个维度对西方翻译伦理研究代表人物贝尔曼(Antoine Berman)、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皮姆(Anthony Pym)各自提出的翻译伦理理论进行批评与反思,(1)事实上,诸如切斯特曼、罗宾逊、赫尔曼斯等西方学者也曾提出有一定影响力的翻译伦理理论;但限于篇幅,本文仅选取贝尔曼、韦努蒂、皮姆为个案进行探索式评述,侧重典型性、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并非暗示或强调其具有普适性、普遍性(universality),也并未否认其他学者翻译伦理理论的独异性(distinctiveness)。洞察其学术价值与偏颇之处,并加以扬弃,以期为丰富国内翻译伦理研究路径和研究内涵作出探索与尝试。
1. 西方翻译伦理代表理论回顾
之所以选取贝尔曼、韦努蒂、皮姆及其理论为代表,主要是鉴于此三位学者在西方翻译伦理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与相对代表性,以及较为成熟的翻译伦理理论: 贝尔曼是西方扛起翻译伦理研究旗帜的先行者;韦努蒂是贝尔曼异质伦理的传承者,也是将翻译伦理研究提升至国际文化政治高度的推动者;皮姆是在求“异”伦理盛行的西方翻译伦理理论思潮中率先倡导求“同”思想的开拓者。以下分别对三位学者的翻译伦理理论进行简要回顾。
1) 贝尔曼的异质伦理
作为西方翻译伦理研究的先行者和代表人物,法国当代语言学家、哲学家、翻译理论家贝尔曼于1984年在《异的考验》(L’epreuvede1’etranger)中最先提出“翻译伦理”这一概念,并且认为要构建翻译学研究框架,翻译伦理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领域;他主张对翻译及译者进行现时代的思考,且须从翻译史、翻译伦理和翻译分析这三个维度展开(Berman, 1984: 23)。
贝尔曼翻译伦理的核心在于“异质”。在他看来,翻译所作的努力应立足于“揭露异质的存在,让读者意识到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Berman, 1992: 4)。而这种异质究竟是外显还是内隐,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译者的主观选择: 译者在面临两种语言或文化间进退维谷却仍旧遭受诟病的处境时,应当以“反抗”的姿态扭转这种对翻译造成压迫的局面。而这种反抗式翻译的伦理目标是在书写层面与他者建立关联,通过引入他者异质来丰富自我,这一目标也必将正面冲击一切文化所具有的本族中心主义,击碎每一个社会都试图保有的自身纯洁无暇的自恋情结,由此也带来了杂糅的暴力(Berman, 1992: 16)。
贝尔曼希冀借助伦理规约促使翻译凸显异质。他提出了“纯目标”的概念,将其视为翻译的伦理目标,这一目标要求翻译对异质抱以欢迎和尊重的态度;与纯目标本质对立的,则是“失败的翻译”(bad translation),即崇尚本族中心主义的翻译(Berman, 1992: 4)。贝尔曼将纯目标对应的伦理机制称为“积极伦理”(positive ethics)。与此同时,在翻译过程中,文化上的抗拒力会导致原文发生走样,这是无法避免的情形;而译者也难免不会偏离翻译伦理的要求,即出现“变形”(deformation)倾向,从而构成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明晰化(clarification)等12种变形系统(Berman, 2000: 288)。
总体而言,贝尔曼的翻译伦理理论可视作一种欢迎他者、反对文化自恋的模式。异质这一核心观念贯穿了他的翻译伦理理论始终。贝尔曼力图借助翻译活动来打破语言和文化的密闭圈,去迎接看似陌生的他者,进而“将外国作品原文中被隐匿的事物挖掘出来,实现对译入语民族本土语言和文化的有效建构”(杨镇源,2013: 59)。
2) 韦努蒂的存异伦理
另一位倡导翻译之“异”的代表人物是美籍意大利学者、翻译理论家韦努蒂。近年来,韦努蒂在国际译坛多是站在弱势民族的立场之上,以抵抗西方话语霸权的斗士姿态出现。
韦努蒂所主张的翻译伦理是“存异伦理”(ethics of difference),这种翻译伦理对将翻译神秘化并视为顺理成章、无碍交往行为的“归化论”提出质疑,认为翻译必须留存译入语的异质特征(Venuti, 1998: 11)。韦努蒂翻译伦理理论的形成,源于他对翻译场域中不平衡权力关系的认知。他在《翻译之耻》(ScandalsofTranslation)一书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于“道貌岸然”的文化霸权主义立场: 主观上无论译者意愿如何,客观上,译者作为翻译行为主体,必然是本国体系与机构剥削、借助外国文本和文化的共谋,这种行为是“翻译中最令人不齿的丑闻与耻辱”(Venuti, 1998: 4),其可耻之处就在于: 欧美中心主义铁幕之下的翻译,出于巩固欧美霸权话语的目的,明明压制了异质的进入,却自诩为“透明”翻译,让读者相信其读到的译文即是原文本身。这种幻象,掩盖了翻译背后强势民族文化霸权在意识形态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操控下,对处于边缘地位的弱势民族及其话语的压迫与欺凌,也使翻译沦为欧美中心主义的工具和文化殖民主义的帮凶。
基于此,韦努蒂极力倡导将翻译中受到压制的边缘化话语予以凸显,摆脱欧美中心主义的禁锢,以抵抗的姿态来突出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并借此作为向西方国家话语霸权和文化霸权挑战的利器,由此他提出了“存异伦理”。韦努蒂声称:“我所支持的伦理立场在于能够促使翻译在阅读、写作等各方面对语言与文化差异表现出更多的尊重(Venuti, 1998: 6)”。韦努蒂秉承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的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两种翻译策略,并对归化和异化与流畅和阻抗分别从伦理层面与话语层面阐释了其运作关系。韦努蒂尤其青睐异化,认为它是一种“极为可取的……策略上的文化介入”,能够突出“外语文本中固有的语言文化异质性”,可以通过一种不流畅、陌生化或异质的翻译风格使得译者显形,同时凸显源语的异质身份。韦努蒂认为此种方式能够反抗英语语言世界不平等和暴力式的归化文化价值观(Munday, 2016: 226)。而后,韦努蒂又提出了“少数化翻译”(minoritizing translation)的概念(Venuti, 1998: 10),并引入了美国学者刘易斯(Lewis)“妄用的忠实”(abusive fidelity)这一概念,(2)“abusive fidelity”一词,国内学界尚无统一译名。或曰“僭越性忠实”(杨镇源,2013: 93),即“承认译文与原文间存在僭越模糊的关系,不仅避免流畅式翻译,而且抵抗原语背后的主流中心文化价值”(Venuti,1995: 24)。
综上所述,韦努蒂的翻译伦理理论吸收了后殖民主义和解构主义思想,他的存异伦理与贝尔曼的异质伦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即从伦理的视角对传统的透明翻译和归化翻译发出公开挑战,这种存异伦理不仅鼓励“异”的存在,而且号召译者(尤其是弱势民族的译者)显形,凸显边缘民族语言和文化话语,以阻抗欧美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
3) 皮姆的译者伦理
较之前文所述的两位主张求“异”的学者,翻译伦理研究领军人物之一的澳大利亚学者皮姆则更为偏向于求“同”。这种“同”,体现了某种基于译者在跨文化交际中与他者的合作与协同伦理。
皮姆于1997年在其专著《论译者的伦理》(Pouruneethiquedutraducteur)中阐发了他的翻译伦理理论: 他明确质疑贝尔曼的异质翻译伦理,认为其“过于刻板、过于抽象化”(Pym,1997: 9)。在具有社会学背景的皮姆看来,贝尔曼的翻译伦理过于理想化,实用性不强,归根结底是一种以经典作品为本位的“翻译”伦理,而非以职业译者为本位的“译者”伦理,这样很容易导致译者与目标语受众和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因此,皮姆将翻译视作“一项交际行为,是一种为某一客户而提供的、针对既定接受者的职业性服务;译者所处的位置在两种文化的交界处,而并不仅仅归属其中任何一个文化社群”(Pym, 1997: 10-11)。
为此,皮姆主张构建一种以译者为中心的伦理,并用“译者伦理”来取代“翻译伦理”,这也为翻译伦理研究赋予了更多的职业属性,并且注入了更多的跨文化交际元素和实用主义成分。继而,皮姆又提出翻译的“文化间性”这一概念,并借鉴格莱斯的合作原则,认为翻译是一种带有合作性质的集体活动,翻译在伦理层面面临一种集体责任。他认为译者从接受翻译任务那一刻起,就不仅仅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使者,他(她)必须肩负起职业译者应当肩负的责任,这样才能促使他(她)所从事的工作有助于实现长期稳定的跨文化合作(Pym, 1997: 136-137)。
总而言之,皮姆“倾向于从译者的‘文化间性’出发,针对各种形态的翻译活动,去探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展开交往合作的译者的职业伦理;这是一种以一定的翻译目的为指导,考虑到社会、经济以及译者责任等各方面因素的功能主义的翻译伦理观”(王大智,2005: 56)。从社会意义上讲,皮姆竭力呼吁翻译伦理的回归(Pym,2001: 129),在描述翻译学研究盛行的译学界强调伦理规约的重要性,提醒人们对翻译伦理研究加以重视,强化翻译伦理意识,强调对职业译者的研究,并从跨文化合作的角度来审视翻译实践,这些都推动了翻译伦理研究的发展。
2. 西方翻译伦理代表理论批评与反思
诚然,上述三位西方学者的翻译伦理理论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某些观点或陷入非黑即白的范畴式思维(categorical thinking)与钟摆式的怪圈,或为了追求局部精彩而堕入以偏概全的陷阱,存在一定商榷的余地。
对此,我们不妨借用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对其加以批评、反思,进而达到补偏救弊的目的。何谓中庸?北宋程颐曰: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王国轩,2006: 46)。孔子曰: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张燕婴,2006: 83)。可以说,中庸之道,是人最高的德性标准,是解决问题的至善之道,也是中正、中和、中行三者的融合。故而借用中庸思想对西方翻译伦理理论加以批评与反思,亦可从如下三个维度展开:“中正”乃伦理观维度,意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中和”乃本体论维度,意即万物间的对立统一,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中行”乃方法论维度,意即通权达变,体用合一。
1) 贝尔曼: 强调他者差异却评判标准单一
作为最早提出“翻译伦理”概念的学者,贝尔曼对翻译伦理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旗帜鲜明地确立了翻译伦理研究的学术地位,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大潮中,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对翻译研究造成冲击的情况下,贝尔曼力图实现对翻译的伦理规约,其异质伦理以打破本族中心主义与文化自恋主义为目标,强调尊重他者差异,主张发挥译者作用,通过他者显形来助力不同民族语言文化间的交互发展,这种交互发展观反映出贝尔曼在本体论层面寻求“中和”做作的努力,也体现了其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伦理诉求。
尽管如此,贝尔曼异质伦理在伦理观和方法论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陷。首先,贝尔曼将排斥异质、崇尚本族中心主义的翻译视为“失败的”翻译;而欢迎异质、摒弃本族中心主义的翻译则是“成功的”翻译。这种评判标准未免有些简单粗暴,有失“中正”,因为对待异质的态度,仅仅是翻译伦理评价指标之一,不宜以偏概全,也不宜太过极端。事实上,我们很难见到绝对意义上欢迎或排斥异质的翻译,而大部分翻译都是介于这两端之间,况且译者对待异质的态度也不一定会是一成不变,而是起伏波动。因此,不宜以异质去留为标准来评判复杂的翻译行为,亦不宜以成败来为翻译贴标签,而应客观、全面地对待翻译中的异质。
其次,受到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贝尔曼的“纯目标”设定或多或少有些理想化,这一点直接体现在他对待“变形”的排斥态度上。贝尔曼认为“变形”会对译文语言的建构性角色和意义重构形成阻碍,使其偏离纯目标,从而造成翻译伦理的沦落(Berman, 2000: 297)。这种对于“变形”的排斥态度在方法论层面未免有些僵化,缺乏一种“中行”式的通权达变。因为在翻译实践中,译本是否能够引入异质以及是否需要进行“变形”,并非译者一厢情愿,而是会受到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当今译坛两位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和蓝诗玲在翻译莫言和鲁迅的作品时,为了更易于译入语国家读者接受,均在一定程度采取了“变形”的做法。葛浩文“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时,甚至把原作的结尾改成了相反的结局”(李景端,2014)。故而辩证来看,归化翻译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实现异化干预的效果: 有时译者向读者隐匿一部分语言和文化异质,实际上是间接帮助了译文融入译入语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土壤,使原文带有的另一部分异质有机会扮演贝尔曼所说的“建构性角色”;反之则可能会愈发远离贝尔曼所谓的“纯目标”。正如谢天振(1999: 140-142)所言,文学翻译的“变形”属于一种“创造性叛逆”,它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其“意义是巨大的……在文学媒介、实现影响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明显的”。故而在方法论层面对待翻译“变形”系统不宜一味排斥,视其为异质伦理的绊脚石,而应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相时而动,使异质更好融入译入语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土壤。
2) 韦努蒂: 挑战文化霸权却转为以暴制暴
如果说贝尔曼的异质伦理还带有几许纯粹的浪漫情怀,那么韦努蒂的存异伦理则颇富现实主义色彩。作为向西方话语霸权宣战的斗士,韦努蒂将翻译伦理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和国际文化政治的高度,并高度关注翻译实践背后不公正的文化政治等因素,而这一点正是贝尔曼所忽视的。毕竟翻译不是发生在真空当中,不是乌托邦式的存在,翻译伦理应当结合当下文化政治语境,更多地将现实因素纳入考量范畴,才能更为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从这层意义上讲,韦努蒂的存异伦理在方法论上具有某种“时中行权”的现实意义。
然而物极必反,韦努蒂的存异伦理存在泛意识形态化倾向。诚然,意识形态对于翻译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是操控作用,但它毕竟不是翻译的本质属性。韦努蒂将翻译伦理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本无争议,但他片面夸大意识形态在翻译中的作用,仿佛几乎任何翻译活动背后都有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操控。其后果是“把翻译过程中正常的语言转换、感情表达和意义传递都置于政治斗争的框架中,拒绝承认翻译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具有客观规律的活动”(张景华,2009: 143)。因此,在对待翻译活动的文化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时既要将其作为翻译活动背后的重要影响因素,认识到强势民族文化霸权以翻译为工具对弱势民族文化话语权的压制,又要考虑意识形态之外的其他维度对翻译伦理和翻译活动的影响,不宜过分夸大其作用,造成泛意识形态化和唯意识形态化,这会掩盖翻译文本内部转换规律和本质属性。故而从方法论层面而言,“中行”应体现为存异伦理观照下异化翻译策略的适度运用、执两用中;而不宜一味追求译者的“显形”与“翻译腔”的运用,这样只会损害目标语受众的利益,过犹不及。毕竟,翻译实践中“没有百分之百归化的译本,也没有百分之百异化的译本,有的只是程度的不同,从归化到异化其实是个不间断的连续体(continuum)(张春柏,2015: 13);一流的译者一定是居于“隐身”和“显身”之间: 他的译作绝不只是原文在另一语境中的简单复制,而是呈半透明状的相似物(王宁,2016: 92)。一言以蔽之,译者“显形”须有度而为。
此外,由于韦努蒂改善译坛权力关系的愿望强烈,甚至略显激进,不免走入了“以暴制暴”的极端,致使他的存异伦理在伦理观和本体论层面均有失客观,难言“中正”,亦难言“中和”。韦努蒂的伦理立场大都建立在边缘和弱势民族本位,借助异化翻译为其语言和文化争取阵地,但在处理与欧美强势语言和主流文化关系时则放大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这种文化仇富情结未免有些矫枉过正了。孙艺风(2014: 6)也认为“韦努蒂在英美文化语境内,指谪翻译中的我族中心主义暴力,但漠视翻译对目标语文化的潜在暴力”。因此,韦努蒂一方面为营造翻译场域中强势与弱势民族语言文化平衡对等而努力;另一方面又在翻译伦理上持有过于偏颇的立场,不但并未促成译坛权力天平归于平衡,反而使得这种关系从一种不平衡走向另一种不平衡,在把强势民族视作不共戴天的仇敌情况下,韦努蒂这种对弱势民族的“尊重”竟化作一种“袒护”,着实是由翻译之耻演变为翻译之憾了。儒家伦理强调“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不提倡以暴制暴的原始正义。故而欲求“中正”,须以公平、正直态度来对待各民族语言与文化,将翻译建立在公正的伦理立场之上。同情弱者不等于一味偏袒,不可为打破欧美语言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任性”而为,矫枉过正。欲求“中和”,须将翻译这一工具用作对话而非对抗,不宜盲目实行道德绑架,而应保持各民族语言和文化间的动态平衡,寻求“从双峰对峙走向融合共生”(蒙兴灿,2009: 109)。
3) 皮姆: 打破二元对立却难以成全道义
相对韦努蒂的存异伦理,皮姆的译者伦理属于另一种意义上的务实,它更为强调翻译伦理在实践语境中的可操作性,也更突出翻译中“人”(译者)的作用。首先,皮姆借鉴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以“文化间性”为核心,凸显翻译伦理的主体间性意识,让译者更多肩负起协调翻译活动参与方利益关系的主体责任,旨在实现译者与读者、审查机构、出版商、赞助人等多方行为主体间的合作共赢,而非一种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故而在本体论层面,皮姆这种旨在改善文化间关系的译者伦理较之贝尔曼和韦努蒂要显得更为圆融,在本体论层面体现了“中和”思想。
其次,皮姆主张译者打破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势,转而在二元之间进行选择(Pym, 2007: 183),由此译者从事翻译有了更大的自由度,译者从“文化间性”出发,在翻译过程中根据客户需要,同时结合译入语文化的翻译规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决定译与不译、采取何种策略去译。翻译成为了在诸多主体间关系影响和制约下的伦理抉择过程,翻译伦理也不再局限于某种单一模式,评判标准也更为灵活,这些都增强了翻译伦理在复杂实践语境中的张力,足见皮姆在方法论层面所折射出的“中行”思想。
皮姆的译者伦理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较贝尔曼和韦努蒂更具辩证性、动态性与操作性,然而其本体论层面的“中和”与方法论层面的“中行”却使得其在伦理观层面存在偏离“中正”的危险。实用与功利往往只一线之隔,合作与合谋也仅仅只一步之遥: 由于皮姆的译者伦理是基于译者与他者之间的合作与互利互惠,这就很可能导致翻译伦理的功利主义倾向,使得译者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违背道义和职业操守。科斯基宁批评这种以“互利”为基础的逻辑有导致“伦理扭曲”的可能(Koskinen, 2000: 73)。这一批评给皮姆译者伦理的美好愿景浇了一盆冷水: 合作共赢并不一定意味着成全道义,甚至有可能为了牟取利益而牺牲道义。因此,要在伦理观层面力求“中正”,须在译者与读者、审查机构、出版商、赞助人等多方行为主体间的合作中找到平衡之点;译者应恪守中道,坚持原则,不应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亵渎职业操守和伦理底线。
此外,皮姆的译者伦理在“中正”方面还有一点不足,体现在他主张译者作为各方利益的协调者与合作关系的维持者,要在文化间的空间中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不应受本国本民族立场的左右,这种对译者的角色定位未免有些理想化。例如,在时政、社会新闻报道编译中,译者通常会依照本国本民族立场对报道叙事进行操控,通过对译文叙事的介入、干预与建构来参与社会现实建构,使之根据特定目的在潜在受众中塑造本国形象。此种情形,时常使得译者难以保持绝对中立,而陷入某种伦理悖论,在两难处境中面临艰难的伦理抉择。
3. 结语
以贝尔曼、韦努蒂、皮姆等学者为代表的西方翻译伦理研究比中国起步更早,理论模式也更为成熟,在特定阶段,借鉴西方翻译伦理理论是必要的。然而,国内翻译伦理研究已经走过十五个年头,我们不能盲从跟风、裹足不前,总是停留在译介国外翻译伦理研究成果阶段;亦不可削已之足、适人之履,不顾中国语境去生搬硬套国外翻译伦理理论。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翻译伦理理论是心怀谦恭与敬畏之情投以仰视;而如今是时候从东方视角与其平视,与之对话。正如潘文国(2016: 7)所言: 大变局必然要求学术研究的转向,其中最根本的是要重新建立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的自信,转变研究立足点和视角,变一百年来的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变由西观中为由中观中、居中观西、中西互释;大变局下新的学术研究路子应该是: 从中国关注出发,借鉴西方经验,创新中国学术。有鉴于此,本文正是以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为视角对西方翻译伦理理论加以批评与反思,在方法论上,并非意欲竖起理论的国界藩篱,也并非用“中餐”文化去简单粗暴地妄议“西餐”文化,用“筷子”去取代“刀叉”;而是胸怀“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汲取西方翻译伦理理论之养分,既看到其学术价值,又洞察其偏颇之处,对其加以扬弃。正所谓“通体融洽,主客互济,寻求古与今、中与西的圆满调和”(刘宓庆,2012: 46)。
事实上,中国传统思想尚有深厚底蕴有待挖掘,中国传统译论中也不乏对译者德性的思考,只是大多湮没于印象式、点评式的散论与随感等诗性话语之中,难言缜密,难成体系,智慧的火花难以化为至理的烈焰。如能从中国传统思想和译论中寻真知,从西方翻译伦理理论中觅灼见,则对丰富国内翻译伦理研究路径和研究内涵有所启示,对国内翻译伦理理论研究中实现“理论自觉”、树立“学术自信”、道出“中国话语”亦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