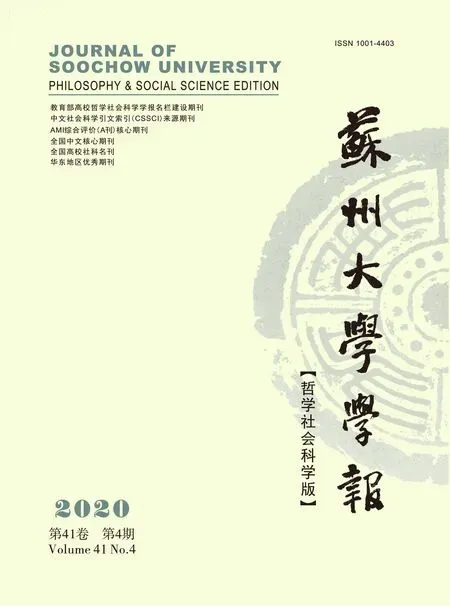钱仲联近代文学知识结构的形成及其诗学观
罗时进 杨 霖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学者们都有一定的自我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是通过接受教育与自我学习而汇聚的知识体系;提升到学术层面,谓之学术修养;复由内在兴趣或外部需要驱动,便形成学术研究的方向。钱仲联先生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修养是淹贯四部的,无愧为世纪学者、一代宗师。但客观来看,他于四部之学更博通于文史,尤深邃于文学;在清代诗歌研究方面表现出当世无出其右的修为与贡献,而对近代诗人、诗歌研究的兴趣几乎贯穿了整个学术生涯。
一、家族关系:钱仲联近代文学知识结构形成之条件
家族出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学者的知识结构的形成。人,具有社会性,而家族便是他的原初性社会环境,这个环境先天地成为其成长起点,也是其知识根源。研究一个学者的初时育成和后来修为,对其家族境况的了解,无疑是重要环节之一,而对于研究钱仲联先生的近代文学知识结构来说,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
冒效鲁先生为钱先生之故交,读两夫子1942年唱酬之作《酒座和答冒效鲁》与《梦苕和余酒座见酬诗再柬一首》可感其苔岑之契。1977年冒效鲁《寄钱仲联吴门即祝其七十生日》有“乞食岂同吴市客,医诗待丐越人方”语[1]115;1988年冒效鲁逝世,钱仲联《悼冒效鲁》有“四十年前梦尚温,灯边南北两王孙”语[2]332,都涉及钱先生的生平。冒诗用乞食吴市与扁鹊医方典故,写其生活情态与诗歌创作,而字面上勾连出“吴越”颇见巧喻;钱诗则就“两王孙”自注曰:“君为成吉思汗裔,余为吴越王后”,直接道出湖州钱氏家族乃钱镠后裔。
根据钱仲联先生所撰《自传》[3]209-223,知其高祖以上无科名,自曾祖父孚威,始考为秀才,从此拉开了一个文化大家族成长、壮大的序幕。他的祖父钱振伦,字楞仙,是著名文学家,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与曾国藩为同年。在晚清以骈文家闻名于世,有《示朴斋骈体文》《示朴斋骈体文续》行世,谭献的《复堂日记》和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都将其推许为清人学唐骈文的典范;振伦兼擅笺注之学和文学文献整理,有《鲍参军集注》《樊南文集补编》《唐文节钞》等。
论及钱仲联先生的家族文化影响,不能不注意他的祖母翁端恩。翁太夫人是清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次女,协办大学士翁同龢的姐姐。她在晚清女性作家中颇有声名,有《簪花阁诗钞》《簪花阁诗余》行世,阮元曾为其“绿庄严馆”题额。钱氏和翁氏的联姻,自然有助于钱仲联先生与近代诗人的连接,而这种连接首先是家族成员本身。其作于1933年的《病榻怀人绝句》组诗,所怀者有钱氏家族一脉的,也有翁氏家族一脉的。涉及钱氏的如第十一首:
少接余杭讽籀书,晚标新异骇群愚。竹林何日从谈艺,一把今吾换故吾。[2]74
诗后自注:“家叔父玄同”,钱玄同是仲联叔祖父振常之子。振常为同治十年(1871)进士,与张佩纶同年。他与兄长振伦联袂进行学术研究,合著《樊南文集补编笺注》《玉溪生诗笺注》等,张尔田先生《念奴娇·仲联依其大母占籍虞山,绘梦苕庵图嘱题,效吴蔡体赋此》有“曾说樊南兄弟好”句,即指此事。玄同有一同父异母的兄长名恂,为薛福成门人,光绪十六年(1890)随薛氏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其间尝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仲联父亲钱淲,从叔父玄同,从兄稻孙、穟孙等,都是因钱恂的关系而赴日留学的。钱恂夫人单士厘,著有国外游记《癸卯旅行记》,“以三万数千言,记二万数千里之行程,得中国妇女所未曾有”[4]钱恂《癸卯旅行记题记》,21;又编有《国朝闺秀正始集再续集》,无愧为晚清民初女界之杰出者。
《病榻怀人绝句》中涉及翁氏的如第十三首:
手辑瓶庐稿几编,湖楼茶梦记当年。古藤图卷应无恙,回首前尘一惘然。[2]74
诗末自注曰:“表兄翁忍华”,从本诗知翁同龢的诗稿就是由仲联先生的这位表兄编纂的。与钱氏家族相比,翁氏更为显赫,文脉更加深远博丽。翁咸封,翁同龢祖父,乾隆四十八年(1783)举人,官至海州学政。其子翁心存,服官四十年,为晚清重臣,有《知止斋诗文集》传世,钱仲联先生称其为“是皆宰相而无惭为专家诗人”[5]钱仲联《翁同龢诗词集序》,1。自翁心存始,江南常熟一个已历经数代科甲兴盛的家族进入最为辉煌的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先看心存长子同书一脉。同书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屡列二等。曾任贵州学政、侍讲学士,迁少詹事,咸丰间授安徽巡抚,著《药方诗文集》。同书子曾源,为同治二年(1863)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曾桂,历官江西按察使、浙江布政使、护理江西巡抚。曾源子斌孙,光绪三年(1877)进士,曾任翰林侍读,辛亥任直隶提法使,著述颇富,有《笏斋覆瓿集》《五代故事》等。斌孙之子之润,少时与同邑杨圻、汪荣宝、江震彝同称“江南四公子”,官刑部主事。在京师又与杨圻、王景沂、曹元忠、章华等结社,争以词鸣,尝辑刊《题襟集》。
再看心存次子同爵一脉。同爵是凭家族余荫成为国子监生的,咸丰元年(1851)入仕,历官兵部主事、兵部员外郎,湖南道台、署按察使、布政使,陕西巡抚、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著有《皇朝兵制考略》等,曾在常熟西门外建翁氏义庄,推助翁氏家族发展。长子曾纯,同治元年(1862)承恩候选同知,以同知即选,官至衢州知府,著有《芝祥随笔》等。次子曾荣,同治十年(1871)着赏举人,任户部四川司行走。三子曾翰,同治元年十二月过继给翁同龢为嗣子,咸丰八年(1858)举人,任内阁中书,官至内阁侍读。曾纯子奎孙,光绪八年(1882)以监生特赐举人,服官工部二十年,宣统三年(1911)隐退家乡,工诗,有《柏园吟稿》传世。曾荣子顺孙,举人,曾官工部郎中,宣统三年在沪上与唐文治交游颇密。
至于心存三子同龢,作为一位清末重臣、文学巨擘深为世人所知。值得注意的是,同龢与其姊感情甚深,钱振伦去世后,翁端恩携全家回常熟娘家,同龢购得县城引线街老屋三进,供其居住生活。光绪十八年(1892)六月端恩病逝,噩耗传至京师,他“竟日气结僵卧,不能一事”,六月十九日日记云:“同龢于姊丧未之敢忘,今日为安葬之期,尤惨切。”[6]126可见丧姊之痛。钱振伦弟振常进士及第后,同龢与这位“翁家婿弟”交往频繁。后来,钱振伦的三女儿云辉嫁于优贡生俞大文之子俞锺銮,而俞大文之妻正是翁端恩的姐姐翁寿珠。这一姻亲关系,在《梦苕庵诗话》中见载:
舅祖翁松禅,自戊戌放归后,即闭门不出。初居西门外锦峰别墅,有依绿草堂、延爽山房诸胜。余十五六岁时,读书于此,今则其地已易何姓矣。公居此不久,嫌近城市,移居白鸽峰。时往相见者,余姑丈俞孝廉金门锺銮,亦即公之甥也。[7]42(1)按,俞锺銮乃俞大文继室龚氏所生,翁同龢仍以亲外甥视之,故仲联师亦称之“姑丈”。
如果说钱振伦与翁端恩是钱、翁家族首次联姻,俞锺銮与钱云辉是第二桩婚姻,而钱恂孙女即钱稻孙之长女钱曼新嫁给翁氏后代翁之龙,则成就了钱、翁两家累世联姻的佳话。
客观来看,这样的家族背景为钱仲联先生对近代文学知识广闻博识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他这一辈学者中,能够亲近或瞻望近代文人的,或许不少,但像钱仲联先生那样长期沉浸于近代文化世家氛围、亲炙于近代文人获取直接感知者,并非很多;而不仅以其家世且因才华得到晚清民初文人接纳、称赏者,则罕有其匹了!这里我们不妨读一读他的《自传》,一窥其与近代文人之关系:
我的姑丈俞锺峦,也是翁同龢的外甥,治顾亭林之学,诗文都学亭林。在我治学之初,得到他的不少指授。十七岁中学毕业后,又经他的介绍,进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就读。
唐(文治)先生是我舅祖翁同龢的门生,与我家有渊源,故督促我学习,比对其他同学更为亲切。
陈衍先生为我(梦苕)庵题匾……陈衍虽是同光体诗人,但眼界开阔(其后在无锡国专任教时),每星期在唐师家与陈衍等宴饮一次,以为至乐。
(1940年)到达上海在国专分校授课,老朋友王遽常、夏承焘等都在同校任教……校外则又与李宣龚、夏敬观、杨无恙等重温诗酒,酬唱旧梦。[3]211、212、215、216
无锡国专是钱仲联先生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与近代文人结交的重要平台,这正缘于其姑丈俞锺銮的介绍,而校长唐文治先生恰恰又是翁同龢的门生、翁顺孙的友人。舅祖翁氏家族的背景在其人际交往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众所周知,钱仲联先生以笺注之学闻世,其中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是《人境庐诗草笺注》与《沈曾植集校注》,而究及黄遵宪、沈曾植与钱先生的关系,又同样贯连着家族脉络。钱先生说:
注黄诗还有一些私人关系,则因黄氏随薛福成为驻英使馆参赞时,我伯父钱恂也在薛处,与黄氏为同僚,两家有世交渊源。……黄氏从弟遵庚,闻知我在作黄诗注,不辞千里,特地到无锡访我,更给我很多手稿资料,并口述许多有关诗篇的本事,这使我的笺注大大提高了质量。
王(遽常)是近代名儒沈曾植的晚年学生,沈氏也出自翁同龢的门下,与我家有渊源。……上海公私藏书丰富,乃鼓起我笺注《海日楼诗集》十四卷的勇气。在上海,与沈先生嗣子慈护先生缔交,于诸家刊印集本之外,得读其笔记、手稿无数,补充不足。通过交谈,详细了解诗篇本身,交游往来等等。[3]214、216
所谓“私人关系”,亦即“家族渊源”。钱、翁本即桐荫世家,一旦相互连接便成为硕大的文化丛林,生根在吴越大地盘绕错节,不断延伸脉系。除前述翁端恩的姐姐嫁于俞大文,钱振伦的女儿又嫁于俞大文之子外(2)钱、俞两家联姻颇密,钱仲联先生的大姨祖母、三姑母和一个姨妈都嫁给俞家。见赵杏根《诗学霸才钱仲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尚有钱氏与沈氏联姻。钱先生的母亲即著名诗人沈汝瑾的表妹,而钱夫人沈毓秀是其表姐,同样是亲上加亲。其《病榻怀人绝句》组诗最后两首所写“姨表兄俞运之”和“表兄沈之茂”,即近代诗人俞鸿筹和沈寿松,诗云“当年同沐谢家春”,“怜予真气消磨尽”[2]76,可见一往情深。家族情感,历经几个世代不免会淡薄、消减,但对于光绪末年出生的钱先生而言,世家茂林的光华直接映照在他身上,每一棵树上的枝桠,他似乎都能够触摸到;每一片树叶的露珠,都给予他以文化滋育;当他站到现代社会的大地时,晚清虽成历史,但并未远去,近代文坛仍清晰地呈现在他的视野中。
二、继承与超越:钱仲联的近代诗学观
钱仲联先生站在近代与现代历史的衔接处,家族的背景使他天然占据着文化高原的地位,具有形成近代文学知识结构的优胜条件。但他学术视野开阔、知识结构渊博,对近代诗坛具有一种超越性的体认,这种体认源于家族又非家族背景所限。
这大体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江南虞山诗学传统的启沃。自明代以来虞山诗坛渐趋兴盛,明末清初钱谦益主盟文坛半个世纪,虞山诗派得以建立并形成“钱、冯两派”[8]20。有清一代虞山诗人之多、著名诗人之多,颇胜于他邑。《梦苕庵诗话》中记录“吾邑”诗人甚多,而诸多近代诗人事迹亦亲闻于“吾邑”先进。二是以诗会友与近代诗人广泛交游。《梦苕庵诗存》存诗始于1922年,也就是说他15岁即开始进行诗歌创作,24岁与王遽常先生合刊《江南二仲诗》赢得声誉,25岁在《申报》发表有关淞沪抗战的诗作,引起黄炎培、金松岑等名家赏叹,由此与不同文学主张与创作风格的作家交往,诗学视野为之开阔。三是厚植学术根柢,博通而精识,诚如饶宗颐先生所评:“钱老博通众学,旁及释氏,其诗文多摭用之;他对整个清代诗学之理解,学术界无出其右;而他的文学批评,稳妥有力,众人咸服。”[2]饶宗颐《梦苕庵诗文集序》,2
综观钱仲联先生平生学术,对近代诗坛的研究贯穿始终,成果最为丰厚。1926年19岁时,以第一名毕业于无锡国专,当年在《学衡》杂志第51期发表《近代诗评》而一鸣惊人。24岁开始进行《人境庐诗草》的笺注工作,标志着关于近代诗人及其作品的评论与笺注工作双轨并行地展开了。钱先生的“诗坛点将录”系列非常有名,其中《近百年词坛点将录》(3)按:钱先生因朱祖谋《清词点将录》只列榜名而无成文,于1981年春撰成《光宣词坛点将录》。后因观点有所改变,又作《近百年词坛点将录》。《近百年诗坛点将录》《道咸诗坛点将录》《南社吟坛点将录》都属近代诗歌史研究,连同《论近代诗四十家》等论文,经钱先生“点将”的近代诗人已400余人。1988年至1990年他相继编成《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与《近代诗钞》,分别由上海书店和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为近代诗人研究建构了丰富的文献基础。事实上,在《梦苕庵诗话》和《清诗纪事》中,近代部分所占比例相当大;而《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三百年来浙江的古典诗歌》等论文,道咸以降以至光宣部分的论述,都几占半数。可以看出,他对近代诗坛之熟稔几臻如数家珍的程度,其近代诗学观亦由此形成。兹作简要概括:
一是对近代诗总体地位的评价。他对清诗有“超明越元,抗衡唐宋”[9]钱仲联《怎样研究清代诗文》,166的基本定位,这与近代章炳麟“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语则不足诵”[10]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439的判断不同,与晚清文廷式“国朝诗学凡数变,然发声清越,寄兴深微,且未逮元明,不论唐宋也”[11]56的观点截然相反,有返本归正之功。可以说,这个“大判断”成为清诗研究的巨大基石,是近三十多年清代诗歌之所以在国内外学界引起重视的主要根据。对二百六十多年的清诗史,他最称赏的是清初和晚清两端,而就这两端来说又更重后者。他说:“晚清诗歌的成就,正与清初期可以先后媲美,在思想性、艺术性的创新方面,更突过了清初。”[9]钱仲联《清诗简论》,180“近代诗歌在艺术上的成就也达到了唐宋、清初以来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在它发展后期矗起的又一座高峰。”[12]钱仲联《近代诗钞·前言》,21显然,他对康有为《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中对近代诗“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的评价持肯定态度,其《近代诗评》直接给予“跨元越明”的评骘或即受其影响。他论近代诗人及其作品,每下“前代诗人从未有过”“空前大手笔”[9]钱仲联《怎样研究清代诗文》,167这样的评语,都有参古望今、截断众流的气度。
二是对近代诗精神价值的肯定。近代历史显著区别于以往历代的是外国列强的入侵使民族矛盾变得极为突出,而社会底层对统治力量的反抗在动摇封建社会大厦的同时也冲击了民生基础,造成严重创痛。在晚清七十年中,士人忧国忧民情怀形成的诗性书写与以往有极大的不同,“风人慷慨赴同仇”的精神体现得更为鲜明,钱先生对此给予高度赞扬。他认为这个大动荡时代中产生的诗歌,“所表达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感情,虽然由于诗人所处的阶级地位的不同,各各打上了不同阶级的烙印,体现了不同的层次和深度,但在反对外国侵略、主张国家昌盛这一点上,各个诗派的进步的诗人却几乎是一致的。应该说,它是近代诗歌之魂,是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爱国主义的优秀传统而又闪烁着时代光辉的精华所在”[12]钱仲联《近代诗钞·前言》,20。他在《清诗简论》中进行“鸟瞰”,只作“前期诗歌”与“后期诗歌”之分,其界线即鸦片战争,因为鸦 片战争诗歌已经富有“时代精神的新内容”,具 有后期清诗“先驱”意义[9]钱仲联《清诗简论》,179,而“这一 时期的爱国诗歌,无疑都应该汇入近代诗歌主流之中”[13]。
三是对近代诗歌新变的激赏。因家族关系,钱仲联先生与近代不少“放眼看世界”者有较为密切的联系,这对于他形成“何谓近代”,“何谓近代诗人”,“何谓近代诗坛格局”,“何谓近代诗界之人文情怀”等认知具有重要作用。从诗界启蒙者龚自珍到诗界革命者黄遵宪,他都保持着深刻的理解与同情。他称龚自珍“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启一世之蒙的诗人”,“自觉地以诗歌为武器,以他那历史批判家的锐利眼光和那枝横扫一世像彗星一样光芒四射的诗笔,深刻地剖析了他所生活着的那个社会……清醒地揭示了清王朝已历史地进入了它的末世”。[12]钱仲联《近代诗钞·前言》,2他对“龚诗在胜朝,不囿旧天地”[9]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家》,332是何等激赏!而只有理解了他对龚自珍不遗余力的推崇,方可理解其何以对晚清“诗世界之哥伦布”投入极大的研究热情;何以将“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看作对旧诗藩篱的突破;何以视“镕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为近代诗发展的标志。近代诗人的革新性尝试是多方面的,几乎无所不有、无处不在,可以说“新变”是近代诗史的大纛,也是钱先生据以辨识近代诗特征的重要标尺。
四是对各种流派风格的包容。钱先生家族诗学传统兼有六朝与唐宋,仅就翁氏一脉来说,“知止胎三唐,瓶庐苏黄徒。楚魂郁孤愤,寄意存江湖”[9]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家》,340已足以广其所宗。因此,在近代诗歌内部结构层面的分析上,钱仲联先生对各种诗学宗尚、风格流派显示出有容乃大的姿态。因其与沈曾植、陈衍等晚清同光体诗人有种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他对宋诗派诗人有精深的研究,也极为推尊,甚至对同光体“宗祖”郑珍给予“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9]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家》,335的极高评价,在《浣花诗坛点将录》中点其为“天立星双枪将董平”,以为“胡光骕推为清代诗人第一,不为过也”。[9]钱仲联《浣花诗坛点将录》,57同时对宗汉魏六朝唐诗且与明七子有一定关联的湖湘派也实事求是加以肯定,如论王闿运“七子去不返,死灰燃湘中。托塔首天王,八代扇余风”;邓辅纶“几辈学神仙,谁见赤霜袍?弥天白香翁,高揖谢与陶”。[9]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家》,338-339其《近代诗钞》中,确乎以道咸宋诗派及后期同光体诗人较多,但对汉魏六朝派、唐宋兼采派、诗界革命派同样推尊,亦给予西昆体派、南社诗人适当选录比例。(4)按,在《近代诗评》中,钱先生开宗明义:“诗学之盛,极于晚清。跨元越明,厥途有四”,其所论四派即宗宋派、汉魏六朝派、唐宋兼采派和诗界革命派,未将西昆体派和南社诗人作为体派专门提出,盖为“品騭所及,断自咸同”之故。见周秦、刘梦芙编校《梦苕庵诗文集》(下册),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511页。正是在其广幅视角下,近代诗的波澜壮阔得到充分显现。
钱先生在《近代诗评》中谓“诗学之盛,极于晚清”,其纵横捭阖,概论各派,俨然已脱雏凤之形。历经半个多世纪,他对部分作家的认识、评价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其视野更加广博开阔,诗学观念更加老成坚碻。金天羽序《梦苕庵诗》有(仲联)“异日者,图王即不成,退亦足以称霸”语[2]金天羽《梦苕庵诗序》,4,此评移之钱先生的近代诗学研究,似亦恰当。
三、树立典范:钱仲联近代诗选的特色
杰出的文学史家之所以杰出,既在于他所掌握的文学史料之丰富为他人莫及,而学理性思考总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展开;同时还在于他不但能够证明什么,还能够指明什么。指明,有多种途径,编撰文学作品选本,是主要途径之一。其实与他所认知的范围相比,在选集中用来作为“标本”的较为有限,故每一个“标本”的“指明”都有不可忽略的意涵与价值。
钱仲联先生编著的清代诗歌选本有《清诗三百首》(岳麓书社1985年)、《清诗精华录》(齐鲁书社1987年)两种,其中包括了部分近代诗歌作品。近代诗歌选本有《近代诗举要》(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近代诗三百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近代诗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三种。其中《近代诗举要》选诗人46家106首,与其他两种比较,规模较小。严格地说,《三百首》是《诗钞》问世的前奏和准备,除了更注重普及性读物的特点外,《三百首》与《诗钞》编著的意旨一致,表达出他在近代诗歌史上希望“指明”的一系列问题。
晚近的近代诗选本,主要有孙雄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陈衍的《近代诗钞》和吴闿生的《晚清四十家诗钞》。孙本虽称“诗史”实属“诗选”,包括了御制和宗室亲王作品,固有存史之用,但选目不精,且印制未全,影响有限。吴闿生为桐城派文学家吴汝纶之子,所收家数原本较少,且主要为桐城一脉,局限性明显,亦不足论。陈衍为近代诗坛巨子,其《近代诗钞》凡24册,收录诗人370家,一时颇具影响。钱仲联先生《近代诗钞》《近代诗三百首》在入选诗人、选录作品上都具有与陈本明确的针对性,特色也正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关于入选作家。钱先生毫不讳言陈衍的《近代诗钞》在选录作家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作为同光体派的巨擘、同光体的诗歌评论家,《诗钞》在选取诗人时,明显地体现了同光体派的观点。“收录的诗人虽很广泛,但仍以宋诗派为主,而一大批代表了进步潮流或艺术成就卓越的其他流派的诗人却很少甚至没有选入。”[12]钱仲联《近代诗钞·前言》,21-22钱先生曾列举出陈衍《诗钞》一份遗珠名单,他们是:张维屏、林则徐、龚自珍、张际亮、汤鹏、黄燮清、贝青乔、释敬安、金蓉镜、夏曾佑、丘逢甲、将智由、黄人、张鸿、金兆蕃、章炳麟、王瀣、陈去病、许承尧、秋瑾、杨圻、孙景贤、程潜、苏曼殊、郁华、黄侃、柳亚子、陈隆恪、胡光炜、杨无恙。其数达三十人之多。
平心而论,在操持选政过程中保持一定的理论倾向和个人审美爱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另外陈散原入选后其子隆恪是否必录,也容有可议;秋瑾这样革命色彩极为鲜明的诗人是否入选,对陈衍而言亦可任自斟量。但开时代风气之先的龚自珍、驰誉道光文坛的张际亮、诗界革命的巨匠丘逢甲等都弃而不录,就很难理喻了。南社诗人群体宗唐与宗宋畛域分明,陈氏只选诸宗元、黄节、林景行、林学衡等与宋诗派往来密切的诗人,而主盟人物陈去病、柳亚子却排除出选录名单,则只能说过于眼光偏狭。[12]钱仲联《近代诗钞·前言》,23
钱仲联先生的《近代诗钞》广收百家而尽录以上诗人,在规模有限的《近代诗三百首》中也几乎完整地保存了这份名单,绝不是为了充实近代诗人的排名榜,而是希望完整、客观地反映近代诗史的历程,显示出大江九派、百舸争流的诗界局面,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结局留一真实影像。其实就审美品位和艺术倾向而言,如柳亚子等人与钱先生并不相同,但并不妨碍将其视为近代代表性诗人,所体现的正是文学史家的胸襟。
关于选录作品。每一个诗人,都是一个具有复杂的社会性和文学性的个体。一般来说,选本所录应是最能代表其人文学个性和艺术成就的作品。但陈衍将《近代诗钞》作为“宋诗派”之“诗谱”,并不考虑诗人的主体创作风格。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入选作品本已很少,而所选者并非他们提倡诗歌革新的代表作。“梁启超,是揭橥诗界革命旗帜的总代表,一时豪杰,奔趋其下,影响所及,远及南溟,他自己的作品,天骨开张,才情纵横。《朝鲜哀词》五律二十四首,《赠台湾逸民林默堂兼简其从子幼春》《南海先生遊欧美载渡日本国居须磨浦之双涛阁述旧抒怀敬呈一百韵》,都是煌煌巨篇,不朽史诗,康有为手评,屡以杜甫相比,而(陈氏)《近代诗钞》都不选入;相反,所选二十首,都是褪去了诗界革命的颜色,而比较接近宋诗派的作品。”[12]钱仲联《近代诗钞》,22
钱仲联先生选近代诗,以树立典范为宗旨。所谓典范,是思想倾向与历史发展趋势一致,而艺术表现体现其诗学观念,典型地表现出个人的风格特征,在近代诗歌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标识意义的诗作。典范的未必是经典的,但内涵着经典的某种要素。在“以诗存人”与“以诗证史”两个指向上,显然着重点在于后者。当然其所证成的不仅是社会历史,也是诗歌史本身,亦即这些作品不是单一维度的叠加或延伸,而能够在总体质性上表现出近代诗歌史的特征与走向。
因此,反映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演变的作品都进入了钱仲联先生的视野,其《近代诗钞》之闳博圆照,无疑是远超陈本及民初以来同类选本的;即使以《近代诗三百首》来看,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张维屏的《三元里》、黄遵宪的《冯将军歌》、贝青乔的《咄咄吟》、樊增祥的《闻都门消息》、康有为的《戊戌八月国变纪事》、柳亚子的《哭宋遁初烈士》等都赫然在列;而黄遵宪表现异国事物的《锡兰岛卧佛》、金天羽痛陈民生疾苦的《悯农》、丘逢甲描写自然风光的《秋溪即目》等,或以放眼看世界而别开生面,或利用传统题材抒发现实感怀,都使其诗选散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同光体派作家如沈曾植、陈三立、陈衍的作品自不可少,但只是作为一种流派和风格的重要代表而已。
这里需要对钱仲联先生近代诗选的“南方色彩”略加说明。所谓“南方色彩”即其入选者以南方居多,作品表现的现场也多在南方,其实这在相当程度上正体现了“近代”之义。南宋以降中国文化重心南移,明清两代长江以南不仅环太湖地区为人文渊薮,赣南、湘南、岭南、闽南也呈现出文化发展繁盛气象,人才辈出,各领风骚。而从历史现实来看,鸦片战争以后外患内忧的重大事件多发生于南方,这里往往是事件的第一现场,恩格斯也正是从中国南方人民反侵略斗争中“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14]22,故而近代诗史上南方作家、作品占有较大比重,而典范之产生也多在南方,自有其必然性。当然,钱仲联先生近代诗选的“南方色彩”也有特定的地域与家族影响。从《梦苕庵诗话》来看,所论近120位清代诗人(含入民国初年者)顺康雍乾嘉五朝不足20人,而道咸以还近百人中光宣两朝即有71人[15],其中占籍江南乃至虞山乡邑者甚多,且不少诗人都与其家族有种种关系。缘此,钱先生具有直接获取他们的诗集并从中精选的可能。这股“源头活水”自然增强了选评近代诗歌的“南方色彩”,也从原生性上提高了诗选的质量。
1999年《钱仲联学述》出版,其中有论:“近代诸家的诗作,我很早就有广泛的阅读、精心的思考,同时我还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体会个中三昧。因此,直到现在,当初的论断还站得住脚。”[16]61又是二十余年倏忽逝去,重读钱仲联先生《近代诗评》发表以来一系列相关成果,深感先生对中国近代诗歌研究贡献至巨。这是一座仰之弥高的学术雄峰,今天我们再度审视“近代”那七十多年诗歌史时,对他贴近得几如身在其中的研究收获,足可视为第一手文学史料和最珍贵的学术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