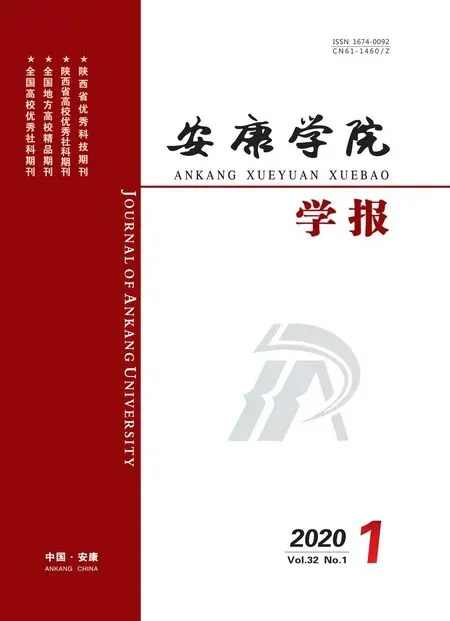“游”与庄子的理想境界
张 甜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游”线贯穿《庄子》一书,但《庄子》中的“游”字反映着不同的哲学含义,表达了不同的审美境界。“游”旨在追求以精神自由为最高理想的审美境界。朱良志先生在《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一书中说:“《庄子》的‘游’强调精神上的超越,具有生命领域的强烈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的‘游’论奠定了文人生活情感和自然审美体验的群体特征。”[1]381综观以往的研究,学界对庄子之“游”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其哲学内涵、相关概念、特征以及现实意义等方面,而关于庄子“游”词群的哲学意蕴及其达到审美境界所经历的心灵之游研究较少。本文立足于庄子“游”和“出游”“游戏”“自由”等一系列哲学概念,通过对“游”词群哲学意蕴的探讨,进而分析其所向往的“游”之生活及理想境界——审美境界。
一、“游”之意
“游”之基本义呈现多义。“游”有在水中游行的意思。无论是在水下面游动,还是脚踏入水中而游,都指“游”。《邶风·谷风》道:“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旧唐书·高骈传》说:“蝗自西来,行而不飞,浮水缘城而入府地。”“游”又有在陆地行走的意思。《齐风·载驱》道:“鲁道有荡,齐子游敖。”“游”有时也特指位置的迁移、变化、移动。《说文解字》解释“游”作为“旌旗之流也”。“游”原本指的是在天空中飘扬的旗帜,后来被认为是位置的变化,即从一个地方变为另外一个地方。据日本学者白川静所著的《中国古代文化》一书所说:“游,古代的书籍是‘斿’,因为旅行,故书作‘游’及‘遊’,像‘旅’一样,用旗子表示出行……它的旗帜是氏族神的标志,族神的栖息地,当氏族出行时……虽然上帝没有表明他的立场,但他可以自由地在任何地方旅行。”[2]《说文解字注》将“游”注解为“出游,嬉游,俗作游”。在西方,人们一般认为“游”之意就是游戏、游玩、玩耍。《广雅释诂》注释为:“游,戏也。”
庄子之“游”既有基本义,又有延伸意。从某种意义上说,庄子“游”的延伸源于其基本意义的发展、转化和衍生。在这里,庄子的“游”绝对不是物体运动的简单描述,而是寻求生命的意义。据不完全统计,在《庄子》一书中,“用其本意的有40多次,其余的‘游’之内涵都有所扩展和升级,并发展成为特定精神活动状态的新类别”[3]127。“游”一字共出现100多次,首篇《逍遥游》用“游”做篇名,该篇主要围绕“游”论述,另有《知北游》也用“游”做篇名。“内篇”“外篇”与“杂篇”都有“游”字,其在7篇“内篇”中出现30多次,13篇“外篇”中出现50多次,8篇“杂篇”中出现20多次。同时,从庄子之“游”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的深刻影响可以看出,“游”旨在对生命本体之意义的探寻。“游”对后世的影响不仅从侧面表现庄子“游”的无穷魅力,而且从中隐含着后世对庄子“游”之生活的向往、憧憬、追求。如“游于万化”“神游”“心游”等都可以在庄子哲学中找到。嵇康在《赠秀才参军》中曰:“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苏轼在《答黄鲁直书》中说:“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在《送文与可出守陵州》中又说:“清诗健笔何足数,逍遥齐物追庄周”,可见苏轼亦受到庄子的熏陶和触动。总之,“游”是庄子经常使用的审美范畴之一。
二、庄子“游”之生活
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他虽生活贫困,但始终追求着自己所向往的“游”之生活。庄子之“游”是“出游”“游戏”,还是“自由”?怎样的“游”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游”?在这里,“游”是以追求精神自由作为最高理想。若想获得“游”之生活,必须具有一种追求自由的超越力量。陈鼓应曾指出:“庄子哲学中的‘游’非常特别,他广泛运用‘游’的概念,用‘游’来表达精神的自由活动。”[4]
(一)“游”与庄子“出游”的美感
庄子“出游”所获得的美感,实际上是创造精神的自由,展现生命的本质。“出游”主要是指A到B的空间旅行、观光、娱乐的过程。庄子“出游”的审美对象主要借助于外部之美,他通过“游”入茫茫宇宙中,“游”入自然山水中,以感官直接同审美对象相接触或借他人的“出游”来隐含表示自己从中获得的美感。如“庄周游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山木》),庄周出游于一座有大猛禽出没的山丘,看见一只大鸟从南方飞来,从而心生美感;“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与惠子在濠水的桥上游历,由于水里的鱼儿而获得“出游”的美感;“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知北游》);“老聃西游于秦”(《寓言》);“孔子游乎缁帏之林”(《渔父》) 等。庄子丰富多彩的“出游”生活及其在出游中的哲学感悟,无不体现庄子“出游”是一种寻找主体精神自由的感知方式。
庄子之所以“出游”,一方面,他想凭借“出游”这一广阔的土地,免受“外物羁绊”达到“为所欲为”的自由境况;另一方面,“出游”的非理性、非强制性、非限制性的特性,正好匹配庄子此时此刻对于精神自由活动的向往,匹配他顺其自然的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思维方可扎根、萌芽、生长、成型。庄子在“出游”中所达到的审美之“游”,是一种短暂的心灵愉快、瞬间的感官冲击、刹那的审美享受和须臾的美感体验,必须要借助外物才能够获得的愉快之感,是一种“有待”之游。因此,庄子毅然决然地选择“游戏对待社会政治问题、游戏对待现实世界、游戏对待生死祸福、游戏对待人生所有可能的生活期望”[5]。
(二)“游”与庄子“游戏”的乐趣
庄子“游戏”所获得的乐趣,其实依然是为创造呈现生命真性的精神自由,这与西方人对“游戏”的理解不同。在这里,游戏之“游”偏重于玩世不恭的外在状态。庄子有意识地逃避现实世界,追求自己所向往的“游”之生活。王博曾这样评说处于“游戏”中的庄子:“庄子有意识地拒绝着世界的召唤(如权力),……他非常喜欢的一个字眼——‘游’——更适合表达这种状态。‘游’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也不是不可分割的,这是庄子选择和世界相处的方式。”[6]在《庄子》一书的33篇中,大多都与这个“游戏”有关,“游戏”作为追求自由的核心。如“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夫列子御风而行”(《逍遥游》)等等。其中,列子御风而游、藐姑射山神人则乘云气、驾飞龙,依然为有待之游,算不得真正的自由。冯友兰同样认为:“逍遥游从大鹏的高飞说到列御寇的御风,庄子认为这些‘游’不是完全地自由自在逍遥,因为都有所待。”[7]
“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一针见血地指出庄子那万般无奈的心理状态。刘笑敢指出:“从现代理论的角度来看,庄子和郭象所讲的快活不是真正的自由,最多只能被视为逃避和消极自由。他们的快活不是自由意志的表现,也不是对现实的转变,也不是对现实欲望的实现,而仅仅是对现实的适应、接受和逃避。”[8]“游戏”仍然不能使庄子从世俗中解脱出来,庄子更不可能改变这个现实,最终还是要返回到现实的人生。在“游”之生活中,“游戏”的乐趣是稍纵即逝的,较精确地说,只能称之为相对的自由,并没有带来持久“游”的快乐。
(三)“游”与庄子“自由”的快感
庄子所追寻的“游”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游”呢?这里的“游”,就是“无所待”的绝对自由。任何“有待”,即相对的自由,在庄子看来都不是真正的“游”,也就是不自由。方东美先生曾说:“如果一个人想要真正获得精神自由,他就不能有待,所以他怎么能无待?正是在这一生中从事的人们有着在自己的生命世界中自足的使命。”[9]因此,若要领悟到“有待”是造成人生不能自由的根本原因,只有摆脱“有待”(客观对象和主观心理的束缚),才能了解“以道观物”的真理以及“道通为一”的真理,才能获得自由。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庄子论‘道’,其主旨并不是‘道’是否存在,而是在怎样去‘体道’‘悟道’,在他的视域里,体道者为‘真人’,‘与道合一’则为‘游’,‘道’是‘游’的理想栖居地。”[10]
“游”入真实的生命体验中。同时,摆脱世俗的功名、利禄、情感、欲望等的束缚,即外物的束缚,时空的限制,泯灭“物”“我”的界限,也是至关重要的。庄子的“庖丁解牛”就是一种高度的、无所对待的创造性自由。工具、对象和技术等完全被人们所使用,甚至忘却了自己,达到屠宰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陈望衡先生认为,为了在现实生活中获得身心自由,就“必须像庖丁那样通过实践去掌握牛之‘必然’”[11]。如“梓庆削木为鐻”“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斫轮者之事”等,都是一种高度的创造性自由。
总之,“游”之生活要求审美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现实的束缚。无论是“出游”还是“游戏”,都不是绝对的自由。“出游”到“游戏”再到“自由”是逐级超越而生成的,从“有待”到“无待”,虽在本质上不同,但其都具有追求精神自由的意义和趋势,特别是在表现特征方面。正如凃光社所说:“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常常处在物我不分的混融状态,庄子在扭曲、压抑、异化、摧残人之天性的生存环境中,自由只能从心理、思维、精神中去寻求、获得,其极至从本质上说只是一种精神的存在。”[3]27
三、庄子“游”之审美境界
庄子之“游”是一种追寻,一种修炼,一种追求精神自由为最高理想的审美境界。庄子“游”之审美境界不能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实现,只能在体验宇宙真理和拥抱自然的过程中实现。庄子“游”之审美境界的实现必然要经历一段从“认识自我”过渡到“保护自我”,最后达到“超越自我”的艰难历程。在这段历程中,思维水平和精神境界层次的决定权在主体,精神境界和思维创造的把握权亦在主体。
(一)认识自我
自我是先天的本能和欲望,是人最为原始的状态。庄子通过“出游”,借助外部世界来获得短暂的美感,从而感受到自我真实的存在,即短暂性“物我两忘”。无论是“濠梁之游”“游于玄水”,还是“游于商丘”,主体都离开了原有的生活环境,在更广阔的世界中寻求自我的方式,突出了感官的自由。《庄子·至乐》言:“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委她而处”,仍然是一种形体上的自由自在,是短暂的境界美。现实的困境与人生的困惑,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解脱。庄子意识到自我最终将回归现实世界。归根结底,庄子借助“出游”所获得的美感变成保护“自我”的精神武器是行不通的。正如陈鼓应指出的那样:“庄子不是站在认知的角度,而是以美好的态度观赏。当庄子正在观看时,他发出了广大的同情,并将自己的情谊投入其中,与外物相互汇通交感,进入凝神的境界,事物的界限和自我的思想溶解和融合成为一体。”[12]
(二)保护自我
游戏之“游”偏向于外在的玩世不恭状态。为了保护自我,庄子一方面“安时而处顺”(《庄子·养生主》),“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另一方面表达其对现实人生的不满,只想在荆棘遍地的环境中为“自我”寻找安身立命之地,正如故事“庖丁解牛”所言“彼节者(骨节处)有间,而刀刃者无厚”(《庄子·养生主》)。庄子可以避免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冲突,即“两耳不闻天下事”。但是,“游”于人世间,关键还是要在缝隙中小心翼翼地游戏。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庄子独特目的不是要找到一种传统的保护自我的方式,而是要开拓新的方式,从‘死生无变于己’‘忘我’(即超我)来寻求精神的安宁。”[13]116
庄子意识到这种以游戏姿态解脱人生痛苦的方式,仅仅是欺骗自我,内心并不是真正的快乐,终究不能从水深火热之中走出来。庄子亦意识到人在自己的思想指导下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但这种为了保护自我而脱离社会实践、回避社会矛盾、完全陶醉在内心自我解放之中的修养方法是有价值限度的。因为“当一个人没有以自我中心的视野看待这个世界时,他就能了解世界那种不是‘为我’而设定的恒定性和坚实性,并由此找到存在的背景根据”[13]304。正如《应帝王》篇所言,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帝王。庄子最终破除自我所获得的境界美,顺着万物的自然之性,寻找某种个人生活的新意义,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在“超越自我”新思路中寻求庄子“游”的审美境界。
(三)超越自我
庄子是如何实现以精神自由为最高理想的审美境界呢?那就是超越自我,但如何超越自我呢?“游心”,庄子的“游心”是灵魂的旅程,是灵魂的兴奋剂。“自由在‘游心’中体认和获得,是精神领域对生命的畅游。”[3]46“游心”的前提必须是“虚静”。徐复观指出:“庄子以虚静为体的人性的自觉,实将天地万物涵于自己生命之内,以与天地万物直接照面。”[1]57“心斋”“坐忘”“吾丧我”是当下的态度,就是只有《大宗师》所谓“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心境的主体才能“游心于无穷”。“无己,无功,无名”是“游心”(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的桥梁、中介,即“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
“超越自我”最关键的是应当具有体道、外生(把生死置之度外)、外物(不计较贫富得失)、外天下(排除对世事的思考)的境界。在自我的超越中,庄子入浑然之境,“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天下》),进入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与万物同游”(《齐物论》)的审美境界中。“四海六合之外”,“无何有之乡”,都反映了庄子试图“超越自我”,获得灵魂的自由。
总之,“认识自我”和“保护自我”,两者都沉浸在“自我”的世界当中,都被外物所束缚,都是有“所待”的相对自由。虽本质不同,但两者皆有放飞自我之趋势。只有“超越自我”才能达到审美境界,即精神自由为最高理想的境界。“庄子的人格思想具有超越的精神,这种超越精神是以绝对自由境界为最高目的,这也是庄子生命哲学和美学哲学的灵魂”[14]。正是在此基础上,庄子一方面对现实社会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又通过“自我体悟、自我直觉,自我超越”的方式,努力克服外界的束缚,寻求灵魂与道之间的衔接点,从而达到与天地精神往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精神得到升华、人性得到解放。
庄子之“游”,游得逍遥、游得自在、游得尽情、游得尽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