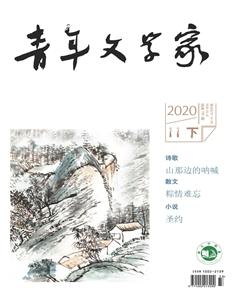作者?译者?读者
摘 要:卞之琳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在如何处理译者与原作者、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关系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为人们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翻译思想。他认为,译者要忠实于原作者的自由创造,力求与原作者达成心灵上的契合。同时他也肯定译者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意识,认为译者可以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自由。卞之琳相信译文读者再创造能力的发挥,认为读者有能力去创造性地理解、接受翻译作品。因此,他不一味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而是主要以原文的语言风格与表现形式将异域文化忠实地传递给译文读者。
关键词:卞之琳;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
作者简介:肖曼琼(1962.4-),女,汉族,湖南衡阳人,博士,硕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比较文学。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3-0-03
浏览本篇文章标题,读者也许纳闷:译者与原作者、译者与译文读者,这应该是主体性、主体间性理论的衍生物,是西方的舶来品,在卞之琳等老一辈翻译家的笔下似乎没有这类西方理论的“狂欢”,为何用来探讨卞之琳的文学翻译思想?的确,卞之琳没有阐述过主体性、主体间性等方面的理论。但是,他却以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很好地诠释、演绎了这些理论。对于译者来说,原作者与译文读者好似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制约着译者的翻译行为;译者如果置之脑后,就会歪“经”易取,真“经”难求。因此,译者翻译文学作品,心中需要装着原作者和译文读者,需要受原作的制约。对于如何处理译者与原作者、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关系,卞之琳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将这些译者头上的“紧箍咒”化为手中的“金箍棒”,为人们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翻译经验与翻译思想。
第一节 译者与原作者
翻译是译者用一种语言传达原作者用另一种语言表现的思想和情感的行为,是译者与原作者情感的交流与精神的沟通。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能无视原作者的存在。译者对原作者的认识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作的面貌与质量。由于译者直接面对的不是作者而是作品,这就使原作者容易处于“缺席”和“失语”的状态。有学者认为,作品是独立于作者的,对作品的理解与认识自然应该独立于作者,不应受到作者的制约和威胁。[1](P61)在翻译界,无视原作者,甚至对原作进行大量删减改编并获得成功的情况的确存在,譬如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大翻译家林纾。他在完全不懂外语,更谈不上对原作者进行研究的情况下,通过与懂外文的朋友合作,以耳受手追的方式翻译了近二百部文学作品,其译作影响深远、深受读者喜爱。但是,就翻译本身而言,林纾的译作绝非上乘之作。原作的内容在其译作中没有得到忠实再现,原作者的风格也变成了林纾本人的风格。譬如他翻译的哈葛德的小说,小说原文“滞重粗滥”,林纾无法了解原文风格,因而译得“明爽轻快”。[2](P530)虽然林译文笔优于原作,在读者群中产生了轰动效应,但从翻译原则上讲并非上策。卞之琳对这种译作优于原作现象不以为然。他说:“译得比原著还好,不管可能不可能(个别场合个别地方也不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对原著欠忠实,既算不得创作,又算不得翻译,当然更不是艺术性翻译的理想。文学作品的翻译本来容易惹动创作欲不能满足的翻译者越出工作本分。实际上,只有首先严守本分,才会出艺术性译品。”[3](P54-55)他坦言:“有人称赞我翻译的‘四大悲剧比莎士比亚的原著好,这令人很不愉快。果真如此的话,只能证明我翻译的失败——翻译过来的比人家货真价实的东西还好,那就不是莎士比亚,而是彻头彻尾的改编了。”[4](P39)由此可见卞之琳对原著和原作者的尊重。他希望自己的翻译能像原作者的创作一样,希望自己的翻译就是原作的忠实再现。
卞之琳在《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一文中谈到了译者对原作者应采取的态度。他说:“原作者是自由创造,我们是忠实翻译,忠实于他的自由创造。他转弯抹角,我们得亦步亦趋;他上天入地,我们得紧随不舍;他高瞻远瞩,我们就不能坐井观天。”[3](P55)这段文字表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以忠实于原作者的思想和风格为准则,力求与原作者达成一种心灵上的契合。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也可看出,卞之琳是不赞成对作品的理解与认识应该独立于作者这一观点的。作品诞生后在物理意义上的确已脱离作者。但是,它在思想、情感及風格层面与作者仍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译者翻译作品,如果要忠实再现原作面貌、产生高质量的译作,就不能将原作者束之高阁。卞之琳把原作者摆在译者理解与表达原作过程中的核心位置。在他看来,译者应竭力向原作者靠拢,洞悉作者表达思想与情感的独特的方式,然后采取相应形式忠实传达出原文内容。他借高尔基的话表明,译者如要准确地用目的语传达原作精神,就应该“对作者全部的复杂的技术手法和用语嗜好、对作者词句之间优美的音节和特性,一句话,即对他的创作的种种手法获得应有的认识。……应该读遍这位作家所写的全部作品,或者至少也得读读这位作家的公认的一切优秀作品。”[3](P55)。卞之琳的翻译,就是在对原作及原作者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从他众多的译序前言中可得到佐证,尤其是他在翻译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前前后后,将莎士比亚的作品及其生平、思想艺术、创作技巧、行文风格和时代背景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汇编成专著《莎士比亚悲剧论痕》。因此,他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时,能很好地领会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的思想、感情与文体风格,并在译作中予以忠实再现。
卞之琳把原文作者摆在译者理解原语文本、创造译本过程中的核心位置,认为译者“居原作者下风”,对原作者应“亦步亦趋”、“紧随不舍”,[3](P55)这似乎应和了当今学术界所批评的传统翻译理论是把原作者放在“主人”的地位,把译者放在“奴仆”的地位,原作者掌控着文本的话语权,译者缺乏自主意识、处处受原作者支配,这种传统的作者与译者的主仆关系抹杀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果真如此吗?卞之琳果真把原作者当作“主人”,把译者看成“奴仆”,认为译者只能受原作者支配、制约,没有自主意识和创造精神的吗?请看他的下面这段话:
艺术性翻译本来就是创造性翻译。保持原著的风格也只有通过译本自己的风格——肯定了这一点,有足够修养的译者就可以在严守本分里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自由,充分运用自己的创作灵感。肯定了艺术性翻译只能求“维妙维肖”而不能求“一丝不走”,有足够修养的译者就不会去死扣字面,而可以灵活运用本国语言的所有长处,充分利用和发掘它的韧性和潜力。[3](P56)
这段话表明,卞之琳没有因强调原作者的核心地位而否认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译者在形成译作的过程中,既要受原作者认知模式和表达方式的制约,又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卞之琳的翻译实践充分体现了他作为译者这一翻译主体所发挥的能动作用。对他来说,优秀译作是译者与原作者主体间性和谐交往的结果,他的许多译作就是如此。他在对体现原作者初始视界的文本进行解读与重构过程中,总是仔细领会原作精神,努力实现与原作者的视界融合,并在彼此的视界融合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实现对作品意义创造性的理解,如他翻译的格雷的《墓畔哀歌》。这首诗常常被人们引用、称赞。这一方面得力于格雷高超的艺术技巧与审美情感;另一方面也归功于卞之琳译者主体性作用的充分调动与发挥,归功于他那精彩的译笔再现出来的审美佳境。卞之琳深厚的语言和艺术修养,使他能够感悟作者的创作思想和审美情趣,与作者产生感情上的共鸣,从而译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佳译。从传统的观点看,它反映了译者对原作深切的领悟和精当的表达。如果沿用现代解释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说,它则反映了译者与作者的视界较好的融合。
综上所述,卞之琳能辩证合理地处理译者与原作者的关系。他不回避原作者这一制约因素,尽可能全面地认识原作者,认真细致地领会原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意蕴,并在译作中最大程度地再现出来,表现出了对原作者最大的忠诚。同时,他在理解原作时,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而是充分利用自己深厚的学养,对原作进行创造性的理解,然后用最接近于原作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将原作的内容与形式忠实准确地再现出来,使原作的生命之花在其译作中得到最旺盛、最蓬勃的绽放。
第二节 译者与译文读者
译者翻译作品是供读者阅读、欣赏的,译作的意义与价值,只有通過读者的阅读和欣赏才能体现出来。一部作品如果没有读者的阅读参与,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它要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展示其思想和艺术魅力、获得“后起的生命”,除了译者的努力外,也必须有读者的阅读参与。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应考虑原文作者,还需考虑译文读者。他应在忠于原文作者的前提下,尽量适应译文读者的阅读视野。实际上,译者从事翻译时,下意识里会对译文读者做一番预想、估量。他们会揣摩译文潜在读者的统觉背景,预测他们的接受视野,以此来设定译文的读者类群。
关于译文读者,卞之琳没有专门的理论阐述。不过,他在动笔翻译时,往往会预计或设定自己译文的读者群类。譬如,他在《英国诗选·译者前言》中说,他的这部译诗集“旨在不仅为国内一般读者参考、借鉴,而且供写诗、谈诗者提供欣赏西方诗的一本入门读物”[5](P9)。这里所说的读者,就是卞之琳翻译时心目中的潜在读者,它包括了一般读者,不过主要还是受教育程度颇高的知识分子。卞之琳的这一主要潜在读者对象,在他检讨自己的诗歌创作《天安门四重奏》时表达得更为明确。1951年,他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天安门四重奏》,诗歌发表后招致许多责难和批评。读者批评它“把诗变成谜语”、“难懂”,给人“支离破碎的印象”、“迷离恍惚的感觉”。[6](P29)在那个诗歌形式与语言单一化、模式化的年代,面对这些批评与责难,卞之琳只能虚心接受。他发表了《关于<天安门四重奏>的检讨》一文,检讨自己深入浅出的思想修养与艺术修养不够、对作品的读者对象做出了错误的估计。他在文章中说:“我当初以为《新观察》的读众大多数也就是旧《观察》的读众,只是刊物从本质上变了,读众也从本质上改造了。我以为这些知识分子对这种写法大致还看得惯,那么只要诗中的思想性还够,多多少少会起一点好作用。”[7](P32)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卞之琳写诗的读者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从卞之琳的创作风格与译作特点来看,卞之琳心目中的潜在读者主要是在同一阵营的文学工作者,或者说很受了教育的知识阶层。
接受美学认为,潜在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影响着作家的写作过程。它“对激发作家创作冲动、欲望,指导作家确定创作的方法、原则和观察、概括生活的视角、方向,帮助作家进行符合读者需求的艺术构思和写作,都有重要的意义”[8](P280)。文学翻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学创作。因此,潜在读者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制约译者的翻译过程,影响译者翻译方法的选择和译文语言风格的表现。卞之琳心目中的潜在读者主要是较高层次的读者。他们一般具有较完整的知识结构和较强的理解力与阅读力,容易接受新知识、新观念、新事物,能通过译本与原作者对话交流,在阅读与交流中感悟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表达特色。因此,卞之琳在翻译中更多地使用直译的方法。他尽量将原文的内容与形式忠实地传递出来,向读者原汁原味地展示异域文化,让他们更为直观地去感受、理解并接受外国的文化观念、知识体系和表现形式。运用直译方式,努力保持原作风貌,让读者去靠近作者,是卞之琳的潜在读者群类作用于他的翻译策略选择的结果。同时,它也体现了卞之琳对读者思考力、理解力、接受力和再创造力的信任。他一贯反对剥夺读者再创造能力的发挥,反对译者为了让读者透彻理解原文而去填充空白,认为读者有能力去创造性地理解、接受作品。他在《浪子回家集·译者序》中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过程比喻为“剥蕉”。他说:“剥蕉的过程自有其价值,……把蕉心剥出了给读者,实是剥夺了读者。”[9](P295)这里的“剥夺了读者”,就是指剥夺了读者对作品的创造性理解与接受。
卞之琳译作的潜在读者对象不只局限于较高层次的读者,还包括一般读者。对于一般读者,他不是迁就、迎合,而是引导。他坚持自己的翻译原则,保持原作的内容、结构和语言风格,让读者在与原作者不断的对话中不断地领悟原作,以拓展并建立新的语言图式与文化图式,提升他们的期待视野,使他们的阅读欣赏水平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这一目的,从他所说的译诗旨在“为国内一般读者参考、借鉴”中可以见出。
在处理译者与读者及原作者之间的关系方面,卞之琳更看重对原作者的忠实。他对原作者或者说对原文的重视胜于对读者反应的重视,用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的话来说,就是“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让读者靠近作者”[10](P42)。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心中没有读者,不为读者所想。恰恰相反,他对读者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他曾要求译诗者译完诗歌要向读者说明原诗形式,认为这样“才算是对作者和读者尽了责”[11](P185)。他本人在译完每首诗时,都会不厌其烦地将原诗形式向读者交代清楚。在诗歌语言形式的选择上,他也表现出了强烈的读者意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卞之琳开始译诗时,翻译界存在着两种语言表达形式:文言与白话。卞之琳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古典文学修养,但是,他翻译诗歌不用文言形式而选择了白话,这除了更贴近原诗形式、与他所处社会文化语境息息相关外,还是他的读者意识的反映。因为在当时,白话已经成为最接近人民大众的语言形式,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用白话译诗完全符合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有利于读者更好地阅读、欣赏原诗。他在翻译斯特莱切的传记作品《维多利亚女王传》时,不仅将原作神形兼备地传译了出来,而且还在必要的地方作了注,并编制了皇室世系图、萨克思·科堡世系图以及维多利亚朝历任首相表。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为中国读者的便利起见”[12](P300)。卞之琳处处为读者着想,他在翻译过程中,对于原文特有的文化内涵、文字游戏等造成的晦涩难懂的地方,会通过注解来减少、消除读者的理解障碍。作品翻译之后,他常常会写前言、后记或相关文章,幫助读者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这些文字起到了沟通读者与原作者的桥梁作用,表现了他对读者的负责精神。
总之,卞之琳能妥善处理译者与译文读者的关系,在译文读者与原文作者之间起到了很好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他能正确估计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能充分预测、考虑他们的阅读需要与接受水平,并采取相应策略以实现作品视界与读者视界的融合,使读者与原作者的沟通、对话得以顺利进行。同时,他不一味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而是主要以原文的语言风格与表现形式将异域文化忠实传递给译文读者,使翻译传播外国文化、丰富本土文化的目的得以完好的体现。
参考文献:
[1]易丹. 从存在到毁灭[M].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
[2]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A]. 钱钟书. 钱钟书作品集[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3]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燊. 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J]. 文学评论,1959(5).
[4]张继合. “看风景”的卞之琳[A]. 张继合. 滋味:与50位文化名人聊天[M].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
[5]卞之琳. 英国诗选·译者前言[A]. 卞之琳. 卞之琳译文集(中卷)[M]. 江弱水整理.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6]洪子诚,刘登翰. 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卞之琳. 关于“天安门四重奏”的检讨[J]. 文艺报,1951( 12).
[8]朱立元. 接受美学导论[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9]卞之琳. 浪子回家集·译者序[A]. 卞之琳. 卞之琳译文集(上卷)[M]. 江弱水整理.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10]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 Eng. trans. Waltraud Bartscht, in Rainer Schulte. & John Biguenet. E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1]卞之琳. “五四”以来翻译对于中国新诗的功过[A]. 译林,1989年(4).
[12]卞之琳. 维多利亚女王传·中译本重印前言[A]. 卞之琳. 卞之琳译文集(中卷)[M]. 江弱水整理.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