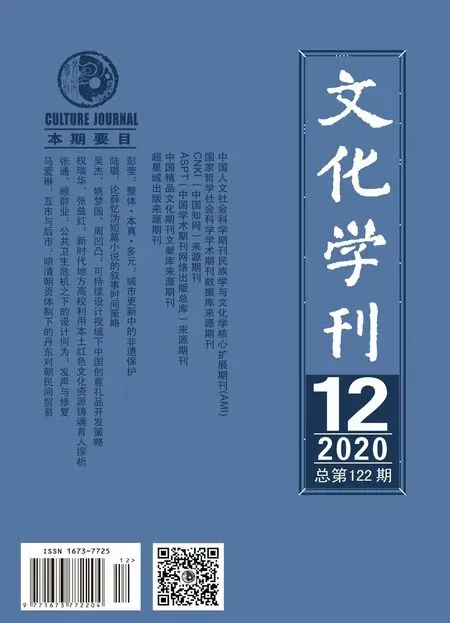清代南昌府育婴事业探析
汪 言
育婴慈幼是我国慈善事业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及至清代,育婴机构的数量和管理机制均较前代有了长足发展。时南昌府的育婴事业尤为发达。现笔者以地方志为基础,以南昌府的育婴机构为研究对象,梳理其设置概况,考察育婴机构的运作,并尝试分析南昌府育婴事业兴盛的原因,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清代南昌府育婴机构的设置
早在顺治三年(1646),江西赣县就有了清代最早的育婴机构[1]243,而南昌府的慈幼事业则要稍晚于此。康熙十一年(1672)丰城县育婴堂的建立,开启了南昌府育婴事业的先河[1]243。此后,南昌府建立了一批育婴机构,育婴事业得到不断发展。现笔者根据地方志,对清代南昌府的育婴机构作一简单统计,参见表1。
由表1可知,清代南昌府育婴机构数量较多,且分布广泛,几乎各州县都建有育婴机构。而且一些州县又设有多所育婴机构,如南昌县于康熙二十年(1681)建有育婴堂,又在同治二年(1863)修建了育婴(公)局;武宁县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修建育婴堂,又于同治九年(1870)建立乐善堂。
二、清代南昌府育婴机构的运作
(一)婴孩的管理方式
收养婴孩是育婴机构的首要职责,一些育婴机构的收养对象比较宽泛,男女皆可被收养,如南昌县的育婴公局[2]。相较于男婴,一些育婴机构则更为注重对女婴的收养,如奉新知县吕懋先倡办的育婴局是“收养女婴”[3]490,而奉新县的进城乡育婴会其收养对象则为“近地女孩”[3]493-494。
而在养育婴孩的方式上,各育婴机构根据其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育婴方式,总的来说主要有四种:一是堂养,即由堂内乳妇抚养。如南昌县育婴堂常在堂内的乳妇有60名,另额外还有8名[4]。二是自养,即由婴孩父母自行抚养,而婴堂会给予补贴。如武宁县育婴堂规定:每名婴孩先由婴堂“给钱一千文”,待婴孩满月后或由其亲生父母“自行抚育”,之后每月会给钱三百文[5]532。三是抱养,如罗溪育婴会对于收养“他人初生之女”的情况给予补贴[4]。四是寄养,一般是将婴孩寄养在乳妇家中。武宁县育婴堂因房屋“不敷居住”,而将婴孩寄养在“城居乳妇”家中,这样既方便查验,也可节约经费以扩大育婴范围[5]531。而一些婴堂的养育方式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如新建县育婴堂先由父母自养,待婴孩满月后再行堂养[6]。

表1 清代南昌府育婴机构设置概况表
在育婴机构的帮助下,婴孩往往会被他人抱养为子、为女、或为童养媳。若男孩被收养为子可“从其姓”而“不得嗣其宗”;若女婴被收养为女或收作童养媳“亦取结状备查”,且严令禁止女婴在将来被“流为奴婢”,若有人违反则“查岀重究”[5]533。可见,机构对于婴孩的出路作了详细规定,且尤为关注女婴的未来,此举也符合育婴的初衷。
(二)婴堂的管理制度
严格的管理体制是婴堂可以长久生存的关键因素之一。清代南昌府育婴机构的内部管理以董事制与轮值制为主,如南昌县育婴堂“董其事者”有绅士宋鸣琦、万承绍、陶士遴、黄中楷、戴诚亨等人[4];又丰城县育婴堂“除以前倡首邑绅泰和教谕举人文炳溪、湖南署龙阳知县陆运景、湖北候补县丞陆运升、浙江长林盐大使陆际元代理……县丞陆昌经、监生任芳华、从九余学海、州同涂仁寿、监生刘滋槐、例贡刘经畬、武生葛合鹏、例贡李曰林、职员陆鳌、武举周定邦、教职陆如照、生员周宗瀚等按年轮月董司其事”[7]。据此可知,首先堂董的担任者大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或为地方官,或为士绅,或为科举知识分子。这些人大多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组织能力,在地方社会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是担任婴堂董事的不二人选。其次所谓轮值制,即堂内各位董事“按年轮月”管理婴堂事务,这样既可以使堂董互相分担公务,也可加强堂内董事的互相监督。武宁县育婴堂又对绅士职责作了规定:“收养事宜先拟绅士经管,嗣须另设公所、筹给薪米等项又滋糜费,故仍官为经理,以归简易。”[5]531-532可见,武宁县育婴堂的士绅主要负责婴孩的收养,而“另设公所”与财务等项仍由官员经理。
(三)婴堂的经费收支
综合各地的情况,南昌府育婴机构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政府拨款,如南昌县育婴堂“经费归府经照输管,每年由藩库核发津贴银六百两”[4]。二为个人捐款,又包括官捐和民捐。在同治年间丰城县有多任知县为当地的育婴事业捐资助款[7]。又乾隆三十二年(1767),监生帅步云向奉新县育婴堂捐田一亩二分[3]490。三是租息收入,如义宁州育婴堂在黄土岭下周家巷内有公馆一所“岁收租钱几十千文”[8]。此外,一些育婴机构会将政府拨款或捐资投入商业生产。同治年间,多任地方官员将南昌县育婴公局的资金“发典商生息”;光绪三年(1877),巡抚刘秉璋又将筹集的一万两经费“发典商生息”[2]。此类收入与拨款或捐资相比更有可持续性,而房屋等不动产的租金收入也更有稳定性。
合理的经费支出是育婴机构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总的来说,南昌府育婴机构的经费支出大致有四种:一是建立或购买育婴场所的费用,乾隆二十三年(1758),贡生蔡秉宽曾捐银一百二十四两,购买“余姓屋基”建立奉新县育婴堂[3]490。二是养育经费支出,如武宁县乐善堂对于生女难以抚养者则“每月给钱一千文”[5]536。三是薪资奖赏支出,如南昌县育婴堂“给乳妇银百四十两,米二百六十石零”[4];此外,一些机构还设有奖赏“抚婴一年期满给赏乳妇每名钱一千二百文,续增赏钱二千四百文”[2]。这种奖励可以调动乳妇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育婴成效。四是其他项目的支出,奉新县育婴堂规定:若堂内无婴孩收养,其每年所收的租谷“拨普济堂支用”[3]490。
三、清代南昌府育婴事业兴盛的原因
(一)溺女之风盛行
江西省的溺婴之风由来已久,及至清代,溺婴陋习已然成为当地社会的痼疾。而清代南昌府的情况亦是如此,多数州县都有溺毙婴孩的情形,其中女婴又是这一陋俗的主要受害者。如在武宁县溺女的行为已“相习成风”[5]2158。而靖安县的溺女之风更令人骇然,靖安县每年新生的女婴“不下数千”,但“愿养者”仅十之一二,而“溺毙者”则有十之八九[4]。可见,在靖安县溺女已成为社会常态,也正是因为溺女陋习的盛行,使得育婴机构更加重视对女婴的收养。
(二)地方政府的推动
严重的溺女之习,引起了地方官员的痛恨与不满。靖安典史崔宏道对此感叹道:“予痛心疾首,恨习俗之相沿,而恬不为怪也。”[4]各地的官员积极倡导育婴机构的建设,以推动南昌府育婴事业的发展。除前文所提到的政府拨款与官捐以外,多地育婴机构的建立者也为地方官员。由表1可知,南昌、新建、丰城、靖安、武宁、奉新等县的育婴机构都由地方官员修建或改建。可见,以地方官员为代表的政府势力对南昌府育婴事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民间力量的支持
除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以士绅为代表的民间力量对于南昌府育婴事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他们不仅参与育婴机构的管理,为南昌府育婴事业的发展捐资助款,而且也自发组织建立育婴机构,这对于南昌府育婴事业的发展颇为重要。由表1可知,康熙年间建立的丰城县育婴堂,乾隆时期建立的奉新县育婴堂,道光年间进贤县建立的两所育婴堂,以及同治年间建立的进城乡育婴会等育婴机构的创建都离不开民间力量的支持。可见,在清代的多个时期,都有民间力量参与南昌府育婴事业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