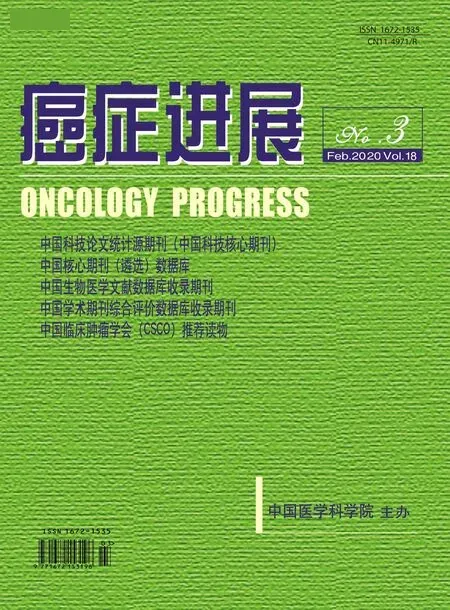肿瘤患者爆发性疼痛相关研究进展△
李黎,卢幻真#,丁利萍,于嘉翔,张妹宁,杨恒
1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射波刀治疗中心,南宁530011
2广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南宁530001
2017年,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Committee of Rehabilitation and Palliative Care,CRPC)提出,爆发性癌痛(breakthrough cancer pain,BTcP)是难治性癌痛的一种[1],患者可出现睡眠障碍、焦虑、绝望感和无助感[2],增加医疗负担,影响日常生活,降低生活质量[3-4]。研究表明,BTcP的发生率为23%~93%,主要与肿瘤的进展情况及临床环境等因素有关[5];BTcP在骨及腹部的发生率较高,分别为73.9%、33.1%[6]。目前,中国对BTcP的评估尚未形成统一。本文就BTcP的发展、诊断、评估、影响因素及预防策略进行综述,旨在为进一步制定预防BTcP的方案提供参考。
1 BTcP的发展
1990年,Portenoy和Hagen将BTcP定义为“一次暂时性的大于中等强度的严重或折磨人的痛苦感受”[7],但这一定义受到诸多学者的反对,随后,其他关于BTcP的定义和诊断标准陆续发表,其中最合理的定义为:以“充分控制基础性疼痛”为前提而发生的剧烈疼痛。目前,国际上普遍推荐的是2009年英国和爱尔兰姑息治疗协会(Association Palliative Medicine Great Britain Ireland,APM)发表的定义[8],即在基础性疼痛控制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自发或某些因素的诱发下突然出现的短暂疼痛加重,分为诱发痛和自发痛。
2002年,欧洲姑息治疗协会首次就BTcP的评估和给药方式达成专家共识[9],指出从患者出现BTcP至消失期间的疼痛强度、部位、性质及加重或诱发因素应进行动态评估,并采用简明疼痛量表(brief pain inventory,BPI)记录疼痛情况,辅助动态观察BTcP的强度。对于大部分放化疗的肿瘤患者而言,不良反应不可避免,进行BTcP初级治疗的价值有待进一步确定。2014年,护士将欧洲肿瘤护理学会制定的BTcP指南[10]中的新理论、新知识应用于临床实践中,对BTcP的进一步理解和管理也将更好的提升肿瘤患者爆发性疼痛的评估及全面管理。随后,西班牙[11]、加拿大[12]及意大利[13]也相继就BTcP的评估、管理及治疗达成共识。一般的肿瘤疼痛指南继续支持口服类阿片类药物作为治疗药物,而特定的BTcP指南始终支持使用透皮贴剂作为缓解药物。2019年,CRPC制定了中国的BTcP专家共识[14],共识包括BTcP的诊断标准、评估方法、治疗原则、阿片类药物风险评估及管理等方面。目前,尚无BTcP的国际共识,若对BTcP的定义和诊断标准达成国际共识,对BTcP的管理将非常有益。
2 BTcP的早期诊断
2.1 BTcP的诊断标准
1999年,APM的Portenoy等[15]最早提出BTcP的诊断标准,并于2011年由Davies[16]更新,更新后的BTcP诊断标准需同时满足以下3个方面:①患者在前1周的疼痛时间>12 h/d;②基础性疼痛得到充分控制(充分控制即患者没有疼痛或出现轻微疼痛,疼痛时间<12 h/d);③有缓慢加剧的疼痛。2019年,中国的BTcP专家共识[14]将疼痛强度具体化,使筛选的标准更加明确,包括以下3个方面:①患者前1周存在持续性的基础性疼痛;②患者前1周的基础性疼痛得到充分控制(疼痛数字评分≤3分);③存在短暂疼痛加重的现象(疼痛数字评分≥4分)。
2.2 BTcP的特异性评估工具
BTcP的有效管理有赖于充分的评估、个体化治疗及充分的再评估过程,理想的评估工具可多方面了解爆发痛,并对爆发痛的动态变化作出评估。临床常用的疼痛评估工具包括数字分级评分法(numerical rating scale,NRS)、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 score,VAS)、Wong-Baker面部表情疼痛量表(faces pain scale,FPS)及口述描绘评分法(verbal descriptor scale,VDS),但这些方法只能单维的评估患者的疼痛强度;多维评估工具可用于疼痛患者的整体评估,包括BPI、麦吉尔疼痛问卷(McGill pain questionnaire,MPQ)、整体疼痛评估量表(global pain scale,GPS)等,但对爆发痛的部位、性质、频率、持续时间、诱发因素及用药后疼痛缓解满意度等方面不能进行特异性的评估,目前,国外常用于评估BTcP的工具包括Alberta爆发性疼痛评估工具(Alberta breakthrough pain assessment tool,ABPAT)和爆发痛评估工 具(breakthrough pain assessment tool,BPAT)。
2.2.1 ABPAT 1990年,Portenoy和Hagen[7]提出爆发痛问卷(breakthrough pain questionnaire,BPQ),该问卷虽早已用于临床研究,但尚未得到正式验证。2008年Hagen等[17]学者在此基础上制定了ABPAT,包括基础性疼痛、爆发痛强度、部位、性质、持续时间、发生频率、可预测性、用药效果等,共3个模块,第一模块(1个条目)及第三模块(2个条目)由医师或护士完成,第二模块(15个条目)由患者完成,该工具的总体一致性水平在国家专家组成员中为80%,在国际专家组成员中为88%。2015年,Sperlinga等[18]开展的共纳入249例肿瘤患者的多中心研究证实,ABPAT是一个公认的BTcP评估和特征描述工具,有利于发现肿瘤患者未被满足的需求及探索BTcP的治疗结果。但ABPAT条目较长,不便于爆发痛的临床评估,将其用于BTcP评估的研究较少[4,19]。目前,国内尚未发现ABPAT的中文版。
2.2.2 BPAT 2014年,Webber等[20]制定了 BPAT,共14个条目,其中9个条目涉及患者在过去1周的爆发痛发生情况,包括部位、频率、诱发因素、缓解因素、发作持续时间、最强疼痛强度、典型疼痛强度、爆发痛发生时的沮丧程度和爆发痛发生时的对正常生活的阻碍程度;其余5个条目与爆发痛疼痛治疗相关,包括药物类型、药物的有效性、药物发挥作用的时间、患者是否出现不良反应和不良反应的困扰程度。Shin等[21]将其韩化(BPAT-K),参与者均能在10 min内完成评估,Cronbach'α为0.743,重测信度为0.782,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0.694~0.854,与 BPI、疼痛管理指数、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on Oncology Group,ECOG)体力状态评分密切相关,证实BPAT-K是一种考虑肿瘤部位、ECOG体力状态评分及照护环境,有效且可靠的BTcP评估工具。目前,国内尚未发现该工具的中文版。
3 BTcP的影响因素
3.1 患者因素
3.1.1 基础性疼痛BTcP的发生率与患者基础性疼痛的评估时间及强度有关,复杂性、伤害性或神经性的基础性疼痛等均可导致BTcP。采用NRS评估疼痛的强度,当基础性疼痛强度由3升高到4时,爆发痛的发生率也相继由15%提高至20%;采用ABPAT评估患者过去1周、48 h及24 h的基础性疼痛强度,其BTcP的发生率会依次升高[22]。研究显示,患者存在的基础性疼痛强度更高时,会导致爆发痛的发生率增高[23-24];严重的基础性疼痛强度是BTcP强有力的预测因子[19]。表明肿瘤患者应对癌痛的过程中,应优化基础性疼痛的镇痛方案以限制BTcP的发生次数。
3.1.2 肿瘤类型 疼痛是肿瘤患者常见的症状之一,爆发痛是患者恐惧出现的强烈不适体验。不同类型的肿瘤患者会发生不同强度及频率的爆发痛。Mercadante等[23]研究显示,与肺癌、胃肠道肿瘤及乳腺癌等恶性肿瘤患者相比,头颈部肿瘤患者BTcP的发生率较高,这可能与患者在接受长时间头颈部放疗过程中,出现的吞咽困难、口腔黏膜炎等诱发因素有关。但另一项研究发现,前列腺癌患者发生BTcP的频率较高,而乳腺癌患者发生BTcP的强度较低[25],这可能与研究的样本量较少、研究较早有关。研究显示,接受盆腔三维放射治疗合并肛周痛的肿瘤患者,BTcP的发生率为48.6%[26]。目前,关于BTcP与肿瘤类型的关系,尚无系统研究,随着时间变化,可能与医疗技术水平治疗方式及患者认知的提高有关,也可能与纳入研究对象的基线差别较大有关。
3.1.3 年龄及卡氏功能状态(Karnofsky performance status,KPS)评分 研究显示,除环境因素外,老年及KPS评分较高患者的BTcP发生率相对较高[23,25]。这可能与老年人耐受性相对较差或发生不可预测的神经性疼痛较少、体力活动更多有关。但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果,Deandrea等[27]纳入19篇观察性研究,对BTcP的发生率进行了系统评价,结果显示,年龄对BTcP的发生无影响。这可能与各研究中研究对象年龄的选择上较随意或纳入文献较早有关,故不能轻易地下定论某特定的年龄组BTcP的发生率。
3.1.4 心理状态 多项研究探讨了BTcP对心理状态的影响,而对患者发生BTcP前心理状态的关注较少[2-3,19]。研究显示,采用肿瘤患者心理分期评估的心理状态与BTcP的发生率密切相关,处于协议期及接受期患者BTcP的发生率较低,而处于否认期、愤怒期及沮丧期患者BTcP的发生率较高[28]。因此,BTcP发生之前心理状态的负性变化可能对BTcP发生也存在影的响。医务人员应重视评估及预防存在负性情绪或有负性情绪危险的患者,减少BTcP的发生。
3.1.5 服药依从性 按时正确服用止痛药物的患者,BTcP的发生率相对较低[28]。范祖燕等[29]研究的结论与此相同,服药依从性高的患者的BTcP发生率较低。临床医师应根据患者的基础疾病、基础性疼痛、BTcP的发作特征及对疾病进程的全面评估,制订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以稳定基础性疼痛,然而临床中部分患者担心药物的成瘾性及对用药相关知识的欠缺,服药依从性较差。由于药物在体内药代动力学及药效动力学的变化,患者未按时按量服药,可导致血药浓度未达到有效浓度而诱发BTcP。
3.2 医务人员因素
柏冬丽等[30]发现,护士对BTcP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偏低,其中,知晓率最低的部分是对BTcP的评估,正确率仅为7.1%。陈乐等[31]的研究显示,仅46.1%的护士对恶性肿瘤患者的BTcP进行了评估,34.4%的护士使用了疼痛评估工具评估BTcP,医护人员在BTcP评估内容的记录上实施率均不高;护士对BTcP知识的正确率为37.6%,处于偏低水平[32];护士区分基础性疼痛与BTcP的能力随着肿瘤护理经验的积累而呈正向变化。临床工作中,肿瘤患者发生爆发痛时,一般由主管医生处理,而护士在此过程中只给予传达的作用。同时,护士对BTcP的未及时评估或相关知识欠缺,也可能会增加患者爆发痛的发生率。此外,主管医师未及时评估或调整患者疼痛及止痛药的服用情况,使镇痛治疗不足、止痛药给药次数或剂量间隔过长,也会导致BTcP的发生,即所谓的“剂量结束时疼痛”。BTcP的发生可能还与医务人员BTcP相关知识欠缺、评估不及时、多学科疼痛管理团队意识不足、较少优先考虑疼痛病理生理学来决定治疗方法及神经性癌痛治疗困难等因素有关[33]。
3.3 环境因素
与普通肿瘤病房及癌痛病房相比,在姑息治疗环境下的患者,发生爆发痛的次数相对较少[6]。居住于姑息治疗环境的多为老年及KPS较低的肿瘤患者,这类患者时长伴有混合性疼痛综合征,且肿瘤科医师在患者疾病治疗过程中,通常有更多的机会对爆发痛进行早期诊断,而姑息治疗的医师只在患者临终阶段才诊断爆发痛[34];此外,在肿瘤治疗和姑息治疗中,爆发痛发生率的差异可能仅仅是由于抽样设计所致。Deandrea等[27]研究显示,临终关怀病房爆发痛的发生率较高,疾病的不同阶段可能与不同的严重程度、转移灶的数量和大小及疼痛的不同致病机制有关,临终关怀医师可能比其他医师更敏感地认识到这一临床情况。关于BTcP与环境的关系,应在严格设计研究的基础上,扩大样本量及控制变量,进一步探讨。
3.4 可预测性因素
可预测性的BTcP发病更快,可预测癌痛患者的BTcP峰值时间和持续时间较短[4]。体力活动和吞咽是诱发BTcP发作的最常见因素,约35%的患者存在可预测的BTcP[25]。一般情况下,接受化疗或放疗的患者常出现的黏膜损伤,也可能在吞咽时产生可预测的BTcP[35];而腹部内脏恶性肿瘤患者,在进食时易出现BTcP[36],这可能与进食后胃肠蠕动,肿瘤刺激神经有关。具有普遍伤害性部分(如骨转移)的患者往往会出现可预测的BTcP,而患有神经性疼痛的患者更可能出现不可预测的BTcP,且疼痛强度较强[23];从病理生理学分析,体力活动引起的BTcP与伤害性纤维的分子作用靶点异凝集素 B4(griffonia simplicifolia isolectin B4,IB4)结合纤维有关,而与表达瞬时感受器电位香草酸受体1(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vanniloid receptor 1,TRPV1)的纤维无关[37]。
3.5 其他因素
研究发现,BTcP强度与人体血浆内皮素1(endothelin 1,ET1)水平呈线性相关[38-39];当ET1水平>30 pg/ml时,患者易发生BTcP,这可能与ET1可直接激活伤害感受器有关[40]。一项针对乳腺癌患者的研究显示,患者夜间睡眠中断,BTcP的发作频率会增加[41],这与疼痛知觉的昼夜节律相关;Campagna等[42]研究发现,接受家庭护理和临终关怀的晚期恶性肿瘤患者,BTcP发作高峰在中午12:00和下午1:15,骨转移和内脏转移患者BTcP发作的高峰在下午12:15和12:30。国内研究者利用疼痛的时辰学理论,调整肝癌患者给药的阵痛方案,可明显改善疼痛控制效果及患者满意度[43]。
4 BTcP的预防策略
4.1 加强护理人员培训
肿瘤科护士是癌痛管理的主体,在控制癌症患者的疼痛和减轻痛苦方面起着关键和积极作用,其对BTcP的认知水平将直接影响其对BTcP患者的管理。研究显示,64%的护士所护理的患者中有41%~80%的患者经历过BTcP,但大多数护士不确定BTcP发作的基本特征;约1/3的受访护士表示,他们没有使用BTcP评估工具或指南来帮助诊断BTcP[44];国内的一项调查显示,99.6%的护士希望参加BTcP的相关培训[29]。医院或科室可通过提供专科培训班、科室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学术会议及进修学习等提高护士BTcP相关知识水平。在常规控制癌痛时,护士需要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止痛治疗方案、BTcP引起的疼痛强度变化,以及未缓解的疼痛的有害影响和患者的社会文化背景等。Mercadante等[45]在急性疼痛缓解和姑息治疗病房中实施BTcP的监测和管理方案,对护士进行强制性的知识理论培训,提高其评估和治疗BTcP的能力,定时评估、定期检查,并严格记录BTcP发生时患者的需求,BTcP发生的时间、强度、频率、用药及疗效等,此方案的实施使得护士能正确评估发作次数及从护士使用BTcP药物中受益的患者例数,值得研究者参考借鉴。
4.2 提高患者对BTcP的认知能力
良好的认知能力可提高患者的服药依从性,控制基础性疼痛强度,避免可预测性的诱发因素等,从而减少患者BTcP的发生。最佳疼痛控制的最重要障碍之一是患者对阿片类药物的认知不足。目前,国内外对癌痛患者的教育方式多样,教育形式不仅局限于患者对信息的被动接受,而鼓励其主动参与也成为有效的教育形式。颜运英等[46]通过明确患者问题、鼓励其主动表达情感、参与制订疼痛管理目标和计划及效果评价的赋能教育形式干预患者的疼痛,干预4周后,患者BTcP发生率降低。以患者为中心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促使患者主动参与,从而提高其对疼痛及BTcP的认识,缓解其心理压力。此外,在疼痛教育的同时给予心理干预也可降低癌痛患者发生BTcP的每日人均次数[47]。Shin等[48]研究探讨了关于疼痛特征的患者教育与良好实践模式之间的联系,为使患者对BTcP有良好的认知能力,医生应定期评估患者BTcP发生的强度及频次,告知患者BTcP与基础性疼痛的区别,提前为患者预备缓解BTcP的药物并提供明确的指导。
5 小结与展望
肿瘤患者爆发痛的发生会加重医疗服务的负担,严重影响其生存质量,加强对肿瘤患者BTcP的筛查与评估很有必要,而肿瘤科护士在控制癌症患者的疼痛和减轻痛苦方面起关键作用。因此,规范BTcP的筛选评估流程及临床实践指南对预防BTcP的发生、提高服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①制定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的BTcP护理实践指南。目前,临床实践存在BTcP的评估、处理、参与管理及健康教育等方面较欠缺,严重影响实践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同时,BTcP的发生率较高,阻碍治疗方案的实施及疾病的转归。国外已发布较多BTcP临床实践指南,而中国大多基于专家共识或临床经验规范护理实践,尚缺乏基于证据的BTcP护理实践指南。②汉化或编制本土化BTcP评估工具,目前,国内尚未检索到特异性BTcP评估工具。中国学者可在借鉴国外评估工具的基础上,汉化或编制符合国内医疗服务环境及社会文化背景的BTcP评估工具,重视BTcP的筛查与评估,避免诱发因素,早期干预,降低其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