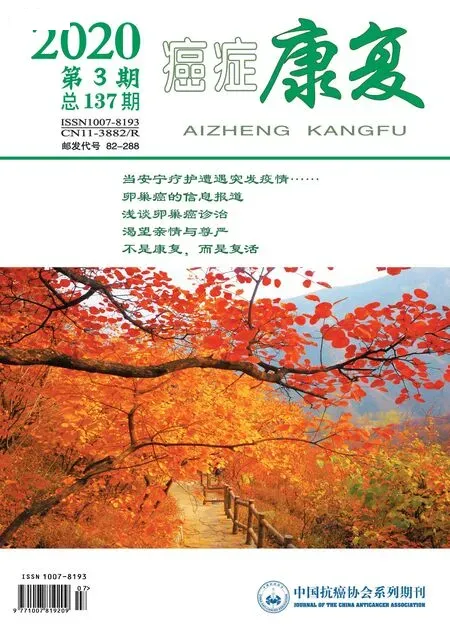《医路如荷》——我在荷兰当医生(六)
□吴舟桥
编前:作者在赴欧洲留学时深入具有西方特色的荷兰医疗体系中学习工作了4年,真正直面并参与到时常被大众误读的西方医疗系统中。在留学的日常生活中,他又以患者和旁观者的视角记录下了发达国家的医疗和社会福利制度下的所见所闻所感。
本书不仅将真实的荷兰医疗现状还原给大众,击破不实传闻,还通过医者、患者和记录者的多重身份,将中国与荷兰的医疗制度进行了客观对比。对制度的探讨看似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经过作者亲切平实的笔触加以解读,就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值得每个人深入思考。
经作者同意,《癌症康复》杂志选登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荷兰急诊的另一面
在荷兰待了几年,很庆幸自己没去过急诊,因为虽然前文里我的朋友把在荷兰急诊说得那么轻松平常,但它其实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刚到荷兰的时候,我的室友脚崴了,却一直不去离家不到一公里的鹿特丹医学中心看急诊,即使脚踝肿得像个包子,也只是在家里休息和冰敷。当时我非常不解:情况这么严重,医学中心那么近,为什么不去急诊看病?但在荷兰时间久了,我也慢慢了解到,在荷兰看大医院的急诊并不是想去就能去的。这话听起来可能很稀奇,后来我的另一个朋友崴脚后,我才知道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正确地看病。如果只是崴脚,而非开放性骨折之类的严重外伤,病人应该先打电话给自己的家庭医生,而不是直奔大医院的急诊室。如果家庭医生觉得没有大碍且在家庭诊所就能解决,那么就不需要去大医院的急诊。如果家庭医生觉得情况很严重,必须要尽快去专门的医院,才能被很快送到附近医院的急诊进行治疗。当时,家庭医生看了我这位朋友之后发现尽管没有骨折,但韧带损伤比较严重,就开了转诊信,于是我的这位朋友很快被送到了附近的急诊。
大医院的急诊诊疗过程其实和我们中国很像:等待叫号、医生首诊、做检查、等结果、再次诊治。最大的差别在于:病人在去急诊之前需要得到家庭医生的批准。可别小看这道批准程序,这对于提高急诊效率并且合理分配医疗资源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你去过国内大医院的急诊室,可以回想一下那种体验:人声嘈杂、队伍冗长、永无止境的等待、医生和其他病友焦躁的情绪……进入急诊就仿佛有无数蜜蜂在头顶嗡嗡环绕,归根结底用一个词概括——人多。但其中的每个病人都是需要来大医院急诊救治的重病人吗?并非如此。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国内急诊的日常工作是应付极为常见的简单伤病,而这些伤病其实并不需要来大医院治疗,很多都是校医院、社区医院能够搞定的,例如简单的伤口处理,有些病人甚至根本不需要急诊治疗,而最让急诊医生郁闷的就是病人进门说:“医生,我在门诊挂不到号,所以来问问您……”
病情不太严重而来大医院的患者在大医院治疗至少不会对他们不利,但那些真正出现了严重伤病必须在大医院急诊才能够及时救治的病人,却很可能因为医生资源被小伤病所消耗而耽误了治疗,错过诊治的最佳时机。
在荷兰鹿特丹医学中心工作的这几年里,尽管我没有在急诊轮转过,但每次去那里似乎都只看到一两个病人。开始我还误以为这是因为荷兰人口实在太少所致,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家庭医生制度筛掉了很多不需要来大医院的患者,使得大医院的急诊医生能够集中精力救治重病人。那里的大夫告诉我,如果有病人来了,他们整个团队就会围上去开始抢救。我就曾亲眼见过在医学中心的停机坪上,直升机刚停稳,一个团队就冲上去对刚抬下来的患者进行抢救,那个场面和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欧美医学剧中展现的一模一样!
你可能又要问:如果荷兰人明知是小问题还坚持要去大医院看病会怎样呢?医院总不能拒绝诊治吧。针对这个问题,荷兰人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医保拒付。因为荷兰的医疗支出都由商业保险覆盖,因此不难想象这种浪费医疗资源的行为会直接减少他们的收益。而急诊这种可能瞬间产生大量开销的地方,保险公司更会时刻紧盯着。所以,如果发现病人去急诊看了不该急诊看的病,那医疗保险就会拒付,病人会自己支付高昂的医疗费。
有多高昂呢?我有一次去耳鼻喉门诊看病,医生只是随便看看,事后我就收到了两百多欧元的账单。急诊费用更高,通常光是诊疗费就高达几千元人民币,如果全部自费的话,一次急诊就可能花掉患者几万元人民币。面对这样的天价账单,那些只有小伤病却想要硬闯大医院急诊的人们恐怕都要三思而后行了。
欧洲的公共设施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共设施才是体现人文关怀的细微之处。
欧洲机场的无障碍设施
我的朋友在摔断骨头之后没过几天就需要因公出差回国。她一个人从荷兰回国,带着大包小包和拐杖,坐着轮椅转机飞15个小时,想想都是泪。但也正是这一路,才能看出不同国家的无障碍设施水平和服务理念到底如何。一起来听听朋友的经历:
到达阿姆斯特丹机场后,停车场里有随时可借用的残障轮椅,我一路按照指引标志来到芬兰航空公司柜台。让人心寒的是,一般航空公司都会提供的残障人士优先办理手续的服务在芬兰航空柜台“消失了”,我几次被冷酷地告知要去排二三十米长的队伍等候,心里满是失落和气愤。最后,我和排在队首的乘客沟通之后,还是很快如愿以偿优先办理了。托运行李之后,在残障人士区域里,我和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及残障人士一起等候叫号,再由专人护送登机。一名工作人员陪同一名乘客从统一的残障人士等候区进到飞机里,通过的很多关卡都是最优先、最快速的。陪同我的美女工作人员帮我完成了海关查检和安全查检前后的行为,我只需要坐在轮椅上默默地欣赏她优美专业的动作。其间,机场还有专用小电车拖着我们直达候机门,避免了推轮椅的麻烦,也节省了时间。最后,她帮我把所有行李提上飞机并祝愿飞行顺利,以此完美结束服务。
之后,在飞机上,芬兰航空的工作人员对于我这样需要把脚架起来的伤病人员视而不见,我提出加位或换座的请求也被婉言拒绝,直到转机后乘坐国际航班的大飞机才被关照。到了上海浦东机场,各项设施和人员的服务总体来说还可以,但对于专人推轮椅护送时不肯出电梯并送我上汽车的情况,我着实不能理解。
这让我想到了曾经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的南航门事件。飞机上的病人出现危重病情,但由于各类“规矩”所限,就是没人愿意转运病人,即使病人已经生命垂危。这样的事件发生后,虽然国内很多航空公司都有了规则上的变通,但朋友回国这一路上两个机场的不同体验,还是说明了不少问题。
前几天,我的另一个朋友推着婴儿车在北京的地铁里尝试了所谓的无障碍通行,结果发现,虽然已经有很多看似为特殊人群设计的便利措施,但它们并没有实现真正的便利。同样地,即便是在荷兰的机场,芬兰航空公司对待残障人士的态度和机场本身的设施比起来就“冷漠”很多。很多人抱怨咱们国内的医疗大环境略显“冷漠”,但是要改,也要一步步来,一下子改好并不容易。正如我朋友说的那样:“不喜欢崇洋媚外地说国外的月亮更圆,但在医疗改革这条道路上,国人要经历的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体贴的瑞士疗养院
瑞士的医疗想来以高大上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曾经多次说瑞士的疗养院特别高端。我在前往瑞士圣加仑参加欧洲结直肠大会期间,碰巧有机会在他们的疗养院参观访问,也真正见识到了那里的真实情况。
“天呐,太美了!”我拉开房间的窗帘,美景映入眼帘。这家疗养院在小城旁边的山坡上,所有的房间窗户都是大落地窗,像画框一样收入了远处蓝天碧水的美景。然而,疗养院的硬件设施并非特别先进,配置基本上和国内四星级酒店差不多,而且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跟酒店区分开。但这里的人性化和体贴程度却让人时刻感受到与四星级酒店的不同。例如,在整个疗养院内所有的地方都做到了轮椅自由出入,对门窗宽度、把手高度都做了精心调整。此外,在房间及各类公共区域都有紧急按钮,一旦出现特殊情况可以很快通知到疗养院的医护人员。服务员会给每个新住户特别仔细地介绍整个疗养院每个区域的功能,不厌其烦地指出所有应急按钮的位置。
疗养患者中不少都是患有运动相关疾病的,有骨折的,也有做了腰椎、颈椎手术的,康复锻炼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而疗养院的健身房有很多器械就是专门为了这些患者运动康复而设计的。这在国内不少康复医院里也是有的,但普通疗养院可能就没有这么完善的硬件设备了。
这里并没有把前来疗养的住客当“病人”。餐厅是共用的,无论是康复过程中的病人还是健康人,都能在环境优美的餐厅里用餐。而服务员还会特别细心地帮助用拐杖或坐轮椅的患者准备特殊的装置放拐杖或固定轮椅。这点让我很有感触,因为国内不少医院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另外,针对患者的不同医疗情况,他们提供的菜单也各有不同。比如,有些患者不能食用高脂饮食,菜单上会特备表明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
虽然对前来疗养的病人照顾细致,但他们仍然把患者当成普通人来看待,并没有因为患者受了伤或者拄着拐杖就把他们局限在房间或是小范围内,这跟我们国内很多“疗养机构”的设定很不相同。他们鼓励所有人享受疗养院的服务,桑拿泳池都不在话下,甚至会带这些患者去周围徒步,亲密接触大自然。于是,我在每天下午都能看见一群拄着拐杖、推着轮椅的人们成群结队地在疗养院周围的树林里面谈笑风生,真是快活!
不知道这样一家疗养院是不是符合大家心目中对高端疗养院的预期,但我心中的高端标准并不是硬件上的豪华一流,而是让每一个住客都暂时忘记自己是个病人,要带着疗养的任务“住院”,就像是住在酒店里享受一段假期时光。这就是我在欧洲观察疗养院的最大体会:医疗的目的很多时候是“让病人做个正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