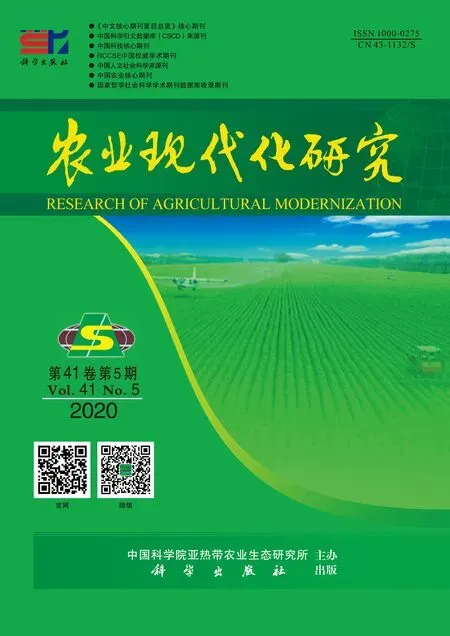中国工业大麻种业创新发展策略研究
赵浩含,陈继康,熊和平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205)
大麻(Cannabis sativaL.)是大麻科(Cannabinaceae)大麻属(Cannabis)一年生草本植物,是最古老的作物之一,其中工业大麻是限定农业安全利用的品种类型[1]。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麻种植面积达到16万hm2,并长期居全球首位,是重要的生产国和出口国[2]。近年来,由于大麻二酚(CBD)等大麻素的开发和利用成为强劲的产业增长点,国内工业大麻产业呈井喷式发展,对种业的创新目标、路径和支撑产业发展的模式提出了新要求。种子作为最基本的农业生产物资,是提升现代农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我国是大麻起源中心,种质资源丰富,且长期开展引种、选育工作,但重在纤维和籽粒用途,针对大麻素利用的育种工作滞后。随着该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国外种业企业通过不断强化科技先发优势,结合知识产权、基因专利等手段对我国种子企业实行压制[3],将严重阻碍我国工业大麻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因此,针对种业发展滞后对我国工业大麻高质量发展提出严峻挑战的问题,探讨构建我国工业大麻种业创新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大麻因其植株中含有致幻成瘾的活性成分四氢大麻酚(THC),各缔约国一般依据联合国《经1972年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简称《1961公约》)[4]和各国《禁毒法》监管或禁种,加之化纤和棉花在纺织应用中的替代、高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大麻种植面积自20世纪80年代持续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兴利避害,国际上逐步形成共识,将大麻植物中致幻成瘾的毒性成分四氢大麻酚(THC)含量低于0.3%(雌株花穗干物质百分比),不具备毒品利用价值的大麻品种类型称为工业大麻[5]。2018年中国实施的《工业大麻种子 品种》(NY/T 3252)农业行业标准规范工业大麻的概念为:植株群体花期顶部叶片和花穗干物质中的四氢大麻酚(THC)含量<0.3%,不能直接作为毒品利用的大麻作物品种类型[6]。工业大麻茎秆、籽粒、花叶乃至全株均是优质的原材料,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其纤维可加工应用于纺织[7]、造纸[8]和复合材料[9]等行业;麻籽可直接或加工食用,可应用于食品保健等行业[10];花叶提取物可应用于医药[11]、化妆品[12]等行业。大麻二酚(CBD)是工业大麻中重要的化学成分,具有抗焦虑、抗炎症、抗癫痫等作用[13-14],是目前工业大麻产业开发的焦点。随着对大麻二酚(CBD)、大麻萜酚(CBG)等大麻素类物质研究的深入,在确保大麻毒品成分含量在安全指标范围的前提下,有关国家积极开发工业大麻的医药利用价值,为人类健康作出新的贡献[15]。因此,探讨工业大麻种业发展路径,必须综合考虑其独有的法律、技术和产业特点。
近年来,全球工业大麻的关注度日益增高,各国在专利申请等方面加快布局[16-17],然而我国种业发展的滞后严重阻碍了工业大麻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18]。新形势下如何把握时机,推动创新工业大麻种业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总结了我国工业大麻种业发展态势和取得的成绩,分析其存在的问题,进而从政策保障体系、多元育种体系、生产经营体系和国际合作体系方面论述了全面提升国内工业大麻种业创新发展的路径,以期引导工业大麻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1 中国工业大麻种业发展态势
1.1 构建全国行业标准和地方法律规范相结合的政策保障体系
2018年由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起草的《工业大麻种子》(NY/T 3252)3个系列农业行业标准正式开始实施,标志着国内首次从国家层面规范了工业大麻的概念和种子标准,并为品种、种子质量和常规种繁育技术提供了适用性、科学性和权威性的标准参考,实现了工业大麻种子质量有标可依,繁育过程有章可循,对促进工业大麻产业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指导作用。
由于工业大麻与毒品大麻的区分主要依据生产标准(THC含量)而非生物学标准,不是零风险,因而生产必须依法管控。山西、甘肃、安徽和河南等传统产区以收获大麻纤维和籽粒为目的,不适用《1961公约》,管控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云南和黑龙江两地通过地方立法,规范了工业大麻种植与加工的范畴和程序。2010年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布实施《云南省工业大麻种植加工许可规定》,成为国内首个以法规形式监管工业大麻种植的省份,采取许可证制度申请种植。2017年新版《黑龙江省禁毒条例》实施,明确将工业用大麻和毒品大麻区分开,对工业用大麻品种选育、种植、销售和加工进行规划引导和监督管理,采取备案制申请种植。由于“工业大麻”和“工业用大麻”概念内涵不同,“工业用大麻”是指大麻作物在工业方面的用途,与“工业大麻”本质上不同,根据《1961公约》,“工业用大麻”限于纤维和种子,其他用途的种植排除在外[19],因此两地当前的产业格局不同,云南以花叶加工为主要导向,而黑龙江以纤维和种子为主。推动地方立法仍然是当前各地引导工业大麻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法律保障,但从种业源头促进工业大麻符合低毒标准,甚至无毒化,将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另外,很多欧盟国家限定的工业大麻THC含量标准为<0.2%[20],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不同的标准,其种业“走出去”必须充分考虑THC含量的“双标”问题。
1.2 推动育种创新主体由公益性科研院所向企业转变
由于工业大麻生产需要特殊管控,长期以来种质资源的交流、新品种的商业化程度均较低,品种选育的公益性特征明显,因而逐步形成了以公益性科研院所为主体的育种创新体系。国内长期从事工业大麻育种工作的机构主要包括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等。种质资源是育种的基础,中国是大麻起源地之一,大麻种质资源丰富[21]。至2017年12月,通过国内地方品种、野生资源收集和国外引种,国家麻类种质资源中期库收集保存大麻种质资源883份,居于世界前列[22]。其他各科研机构均有可观数量的大麻种质保存,并陆续培育出新品种。
在CBD热潮的推动下,近年来市场机制在工业大麻种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步增强,育种人才、技术、资源向企业流动的趋势显现,产学研结合度提升,工业大麻商业化育种体系正在逐步建立。目前,开展工业大麻种业领域相关研发活动的机构主要为具有深加工能力的医药、纺织等企业,主要方式是以知识产权转移为纽带,委托公益性科研机构进行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承包、培训和中介等服务,并通过建设工程技术中心、实验室、科研工作站等种业产业化技术创新平台,积累了一定的创新资源。整体来说,企业在工业大麻育种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仍然薄弱,但发展速度快,企业和人才积极性高,为构建“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业体系开启了良好的局面。
1.3 创新以多元化和多用途为特色的育种技术体系
工业大麻产出的主要初级产品是籽粒、纤维和代谢产物三类,进而深加工为2.5万余种产品[23]。研究该三类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形成,将不断加深对工业大麻生物学的理解,并影响市场对种业发展路径的调整。同时,工业大麻种子有THC含量的限量标准、生产过程有依法管控的程序、工业大麻植株性别分化的复杂性等因素,使得其品种选育与其他作物相比极具特色。以收获籽粒和代谢产物为目标的工业大麻种植,定量除雄或构建分枝多的全雌性群体是获得高产的重要措施[20],而纤用种植则更倾向于构建分枝少的雄性群体[24]。工业大麻代谢产物种类众多、功能丰富且成分间往往存在互作效应,极具挖掘价值,但同样对育种技术提出更高要求。不同群体构建的需要和高效实施多用途之间的矛盾,必须依靠多元化的育种技术才能得以解决。
自2008年国家麻类产业技术体系建立以来,以产业链为导向,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为核心,育种目标由单一纺织纤维用向专用、兼用和多用途深层次拓展。重点针对高纤维品质、高CBD含量、低THC含量、高蛋白和高油脂等多用途的大麻种质资源进行鉴定和挖掘,随着分子育种技术在工业大麻上的应用,繁育手段不断精准高效化,育种手段从常规育种向分子标记育种突破,初步形成了针对三类产品的育种技术体系。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依托国家麻类产业技术体系工业大麻育种岗位等项目资助,在长期开展大麻素含量和大麻性别的遗传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传统育种与现代育种相结合的技术手段,形成了工业大麻化学诱导性别转变技术,实现了全球首项低纬度地区工业大麻全雌品种研发及高效制种技术,花叶产量较雌雄异株增加22%以上,提高了种植生产的经济效益,避免了私自留种带来的安全风险,为监督管理提供了新路径[25]。
1.4 形成良种区域化的种植格局和技术服务体系
我国大麻生产种植主要分布在西南的云南、贵州和四川,东北的黑龙江、吉林和辽宁,西北的山西、甘肃、内蒙、陕西、青海和宁夏,中部的安徽和河南等地。受2017年以来全球市场需求和生产格局变化的影响,国内形成了云南省以花叶用、黑龙江省以纤维用、山西省以籽粒用为主的生产布局,目前国内通过登记认定工业大麻品种有29个[26]。
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云南省依托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推动工业大麻育种目标从最初主要用于替代传统较高含毒量大麻品种向多用途开发利用转变,在全国率先选育出“云麻”系列工业大麻品种10个。目前主要推广品种为“云麻1号”、“云麻7号”和“云麻8号”,其中“云麻8号”其药用成分CBD含量达1.33%,种植遍及云南省除临沧市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外的14个市州,2019年有效种植面积达0.80万hm2。合法供种单位有云南工业大麻股份有限公司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年产种子80 t,供种量可满足2.67万hm2种植需求。2020年云南全省申请种植面积超过13万hm2,获批许可种植1.33万hm2,供种量能够满足当前需求但具有极大潜力。同时,云南省工业大麻种业与精深加工产业协同发展优势明显。在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等机构的协作下,2014年成立的汉康(云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了全球第一条高纯度CBD工业化生产线,2015年成立的云南汉木森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依托当地特色资源开发的全谱精油产品,在全球极具竞争力。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选育有“中大麻”系列纤用品种和高CBD含量品种“中大麻杂1号”等,其中云南素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于2019年联合育成的“中汉麻1号”CBD含量达到3.19%。黑龙江省依托黑龙江省科学院、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培育出以“龙大麻”系列[27]、“庆大麻”系列[28]为主的品种,2019年有效种植面积达0.93万hm2,种植区域以绥化市青冈县和黑河市孙吴县为主。2017年黑龙江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投资成立黑龙江康源种业公司,主要开展工业大麻育种、繁种和种子经营及推广,年可销售优质工业大麻种子500 t,且因地理环境优势,工业大麻种植机械化水平高、纤维品质全国领先。山西省工业大麻种植面积达1.40万hm2,在晋中市榆社县实现集中连片种植,其中依托山西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培育出的“汾麻”系列[29]、“晋麻”系列[30]为高蛋白、高油脂籽粒用品种。
2 工业大麻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法律政策保障有待完善
从产业发展来看,国际国内产业发展形势乐观。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工业大麻纤维和短纤维的进口贸易量一直在1万t左右,进口总额也基本保持稳定,2018年全球累计出口工业大麻纤维(不含纺织产品)1.29万t;大麻籽的国际贸易更为活跃,2000年以来出口贸易量和贸易额一直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且进口贸易额大于出口贸易额,说明各国对大麻籽需求量不断增加;两者整体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据Patsnap数据库数据表明,目前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50件以上的企业有78家,近3年专利公开量平均达到2896件/年,其中在中国区的增长尤为迅速。仅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云南省境内新注册成立的从事工业大麻相关业务的企业近160家。巨大的产业发展需求,亟待加快法律政策保障。我国目前缺乏国家层面或跨区域协同的工业大麻法规体系,对工业大麻种业管控带来严峻挑战。一是区域间管控机制差异导致跨区引种、供种、用种的合法性存在盲区;二是以省级登记或第三方评价方式认定的品种在跨区应用中缺乏统一的规范程序;三是生产者自留种导致品种混杂、退化和变异的问题[31];四是种植与生产的无序化竞争问题加重负向反馈种业发展。
2.2 良种繁育水平发展滞后
国外自20世纪初,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开始工业大麻新品种选育工作,研究实力较强且国际合作紧密,研究方向涉及化学成分遗传性分析、性别遗传性、分子标记遗传改良等[32]。虽然我国是大麻起源中心,但长期以野生资源或地方品种为主,品种选育工作起步时间较晚[33]。近年来我国参与工业大麻种业相关研究的机构和人才队伍迅速增加,但缺乏顶层设计和分工协作机制,新参与者大多集中在高CBD含量的种质引进与培育方面,这与美国等国家面临的问题相似[34]。在资源搜集方面,我国相关研究机构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种质资源收集、鉴定工作,但与构建和共享核心种质的需求仍有较大差距,种子资源的垄断性和独占性也进一步阻碍了资源共享。育种目标确立方面,具有明显的“跟踪式”研究特点,缺乏前瞻性的攻关思路。育种技术方面,目前仍以传统方法为主,分子标记、转基因和基因编辑等现代生物技术仅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品种育成方面,CBD含量与国外差距较大,“云麻8号”CBD含量不足国际上高含量的25%。种苗繁育方面,种植生产仍以大田播种为主,单性别种苗繁育体系滞后,繁种基地与欧美现代化设施工厂化种植相比差距较远。科研资源分配方面,同质化竞争问题普遍,市场主体力量薄弱,整体投入偏少。总的来说,我国工业大麻育种技术资源分散、储备不足、效率偏低的问题仍然突出。
2.3 商业化育种体系亟待加强
2018年以来,工业大麻在资本市场掀起热潮,可口可乐、丝芙兰等全球多家知名企业争相布局工业大麻产业。但随着热潮褪去,企业应从资本炒作驱动向产业内生驱动转移,完善产业链布局,夯实其在工业大麻产业发展中的根基。现阶段我国整体商业化育种合作效率较低,资源技术集中分布于科研单位,受制于企事业单位性质和目的不同,减弱了科企合作的意愿[35],科研单位和企业育种人才缺少合作交流,企业缺乏高水平育种人才制约了种业商业化进程。知识产权是企业角逐市场的利器,以巴斯夫等为代表的跨国企业将工业大麻种业研发作为重点关注领域,在全球专利布局上的领先态势明显,国内专利主要集中在工业大麻纤维提取与制备等方面[16],种业相关专利占比低。由于目前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强度较弱,对育种权利人保护力度不够[35],挫伤了科企合作育种的积极性。标准化生产方面,缺乏全国性工业大麻品种鉴定技术规程或管理办法。生产流通方面,种子销售和进出口等方面尚无政策保障。
3 中国工业大麻种业创新发展路径
在工业大麻成为全球焦点的新形势下,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发展战略,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发挥特色作物经济优势,积极主动参与,促进资源整合,探寻工业大麻种业发展路径。加快构建工业大麻现代种业政策保障体系、多元育种体系、生产经营体系和国际合作体系,全面提升国内工业大麻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补齐短板,保障工业大麻种业安全生产流通,引导工业大麻产业健康稳定发展。
3.1 完善政策保障体系,引导种业健康有序发展
加快出台全国性工业大麻种植生产指导意见,从顶层设计规划,杜绝非法生产。鼓励传统种植区域地方立法和建立跨区域产业协作机制,推动形成区域性和跨区域相结合的种业规范程序,促进生产、加工、流通的全国协作,通过试点先行,实现稳步发展。推进制定全国性工业大麻品种鉴定办法或技术规程,降低工业大麻不当或违法利用风险,从源头保障品种安全性和规范性。提高知识产权培育引导和保护力度,构建以企业为产业主体、公益性科研机构为基础研发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工业大麻商业化育种体系,发挥市场在种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工业大麻良种供应许可制度,制定工业大麻良种补贴政策,配合自留种限制、野生种铲除等安防措施,保障种子种苗的合法、安全供给,引导种业健康有序发展。黑龙江省等已有立法的区域进一步细化规范工业大麻种植加工管理标准。加快企业管理制度的建设,补充和完善国家及地方管理制度,形成全国、地方、企业三级管理制度架构,实现从科研到市场的闭环管理。
3.2 培育多元育种体系,加强科学生产技术储备
培育以企业与公益性科研机构相结合的多元主体,确立以纤维、籽粒、花叶等为主要用途的多元目标,通过企业自主研发和引导资源整合联合攻关的多元创新路径,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村增绿的目的。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为指导,对大麻种质资源开展系统收集与保护,以国家麻类种质资源中期库为核心,与区域单位种质资源库形成衔接体系,完善种质资源信息共享平台,强化育种创新基础。构建创新育种体系,充分利用原有公益科研单位研发先行优势,加快关键种业技术攻关;鼓励有实力的种子企业组建研发机构,引导工业大麻种业研发机构整合,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分享为纽带、以资源集聚为特点的技术创新联盟[36]。构建现代分子育种技术体系,加强工业大麻性别分化和单性别群体构建等方面的基础研究[37],加快实现工业大麻育种向精准化、高效化转型升级,继续发挥我国纤维用种、籽粒用种的优势,加强医药用种等多用途品种的基础研发,以提高纤维产量为目的,培育纤维用品种;以提高种子产量和营养成分为目的,培育籽粒用品种;以提高有益大麻素含量为目的,培育医药用品种。以多用途为育种导向,创制优质专用及兼用品种,提高产业抗风险能力。以设施化栽培为主攻目标,制定高效制种技术,推动种子精选加工与种苗繁育技术水平提升。
3.3 打造生产经营体系,实现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以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和提高管控效率为目标,以扶持龙头企业为抓手,加快现有种子繁育基地向现代工厂化种植基地提档升级,推动以单性别植株繁育为特点的商业化育苗推广体系。根据政策法规、区域条件、用途需求等情况,逐步引导建立北部、中部和南部工业大麻良种繁育基地,打造全国区域化、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的工业大麻供种基地,制定相关技术管理标准,引导工业大麻种子生产向优势生产基地集中。提升科研单位公益服务能力,支撑打造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鼓励企业自建繁种基地,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提升商业化育种创新能力,延伸工业大麻种业产业链。建立第三方服务支撑平台,发挥其在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纽带作用,在基础服务、知识产权等方面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使科技资源向企业流动规范化、合理化、标准化。建立集聚科技研发、种子繁育、销售推广于一体的工业大麻种业龙头企业,实现育繁推一体化发展,打造种业品牌,加快提升种业竞争力。
3.4 初探国际合作体系,提升种业发展的竞争力
保障和不断提升大麻素原料供给能力是工业大麻种业发展的重要方向[38]。据统计,截至2019年1月,全球已有41个国家宣布医疗用大麻合法,超过50个国家宣布CBD合法,选育和应用高CBD及多种有益大麻素含量的工业大麻品种成为全球热点。截止2017年末,世界各国先后选育出80多个工业大麻品种,其中大部分品种可以商业化获得[39]。在国家种业对外开放政策并未大幅放松变动背景下,综合考虑国内种业科技发展趋势和开放政策调整的影响[40],加快制定工业大麻种业国际交流指导意见,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条件下,初步探索工业大麻种业国际合作方式,充分利用“一带一路”、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非合作论坛等国际化平台,引进国外优质种质资源,推动与种质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合作,学习先进现代设施农业管理技术和种子加工流通技术,加强基础研究交流合作,提升国内工业大麻科研创新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