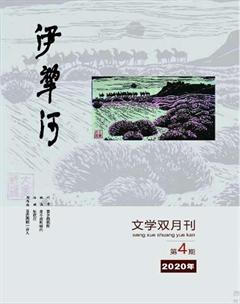苦马豆
刘亮
没有想象中的残垣断壁,眼前竟是一块白地。
我张目四望,没错,在我的身旁,还有两排保存较好的房子,可跟它们紧挨着我特意来看的那排房子呢?怎么就凭空不见,成了一块白地?
不,也不能说是白地,还有一地的碎石子,几丛贴地而生叶片浑圆长满尖刺的骆驼刺,甚至还有一株孤零零的花,蒙着一层碱土的青叶间,红艳艳地绽着好几朵,微风中轻轻摇曳,在一片瘠土之上显得分外夺目。枝叶与花中间还点缀着一些含苞待放的花骨朵,神似初恋少女的红唇。
那花我并不陌生,小时候,孩子们都叫它羊尿泡。名字很不堪,花却开得千娇百媚。
那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我的出生地,西距哈密200公里戈壁滩上那个名叫七角井盐化总场的企业正值辉煌,生产的工业盐、硫化碱等化工产品供不应求,每年上交的税占全地区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因为工资高,别说本地的年轻人没有外出谋生的打算,就连哈密市的待业青年也纷纷报名参加盐化总场的招工考试,削尖了脑袋想成为盐化总场的一员。而今天,曾经身为国家二级企业的盐化总场已不复存在,曾有的几万居民纷纷搬离,剩下的人口已不足千,每每想起总会忍不住心酸。
记得当时我上初二,不算小了,却还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未来,因为除了语文其他科目学习成绩都很一般,所以偶尔想想,也不过是像父辈们一样,成为一名盐化总场职工。出门上班,回家吃饭,然后顺理成章地娶妻生子,衣食无忧地生活在这个被戈壁滩包围的小镇,根本就不敢有考上大学,离开七角井去大城市生活的念想。
那是一个星期天。
那天的太阳格外好,亮晃晃的,悬在澄澈的蓝天白云之间,散出无尽的光和热,至今仍在我记忆中闪耀。现在一样有大太阳,一样有蓝天白云,给我的感觉却要比那时衰老憔悴得多,远不如从前鲜活。
我甚至记得,那天我穿的是一件白衬衣、一条黑裤子,如果再别上一枚团徽,父母肯定会以为学校又要举办什么活动了。
活动当然没有,可我要做的事,对我来说意义却比学校搞一场文艺节目、开一次运动会更重大。
我要去见李梅,我们班最漂亮的那个女生,今天是她的生日。
李梅是这学期开学时转到我们班的,听说来自于一个名叫杭州的地方,很美,也很遥远。班里来新同学对我来说并不稀奇,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基本上每一学期班里都会多一些新面孔,就像雨后突现的春笋,当然,也会有一些熟悉的老面孔消失。听爸说,七角井盐化总场最早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兵团解散才交给哈密地区。当年,来这儿搞开发的军垦战士成分很杂,单从地域来讲,可以说五湖四海到处都有。他们工作忙,孩子多的话,常常会送一两个回内地,让家中的父母帮着抚养。有的是小时候就送回去,成年了再接回新疆;也有的是等孩子十一二岁足够大了才送回去,陪伴已经年迈的父母。
李梅跟我一般大,那年也是十三歲。她有着一张精致白净的瓜子脸,两条乌黑油亮的长辫子,眼睛老是忽闪忽闪着让人心里痒痒的,很舒服;她还爱笑,见谁都是一副友好的笑。要是遇上什么开心事,就像银铃摇响,撒下一地的快乐供人分享;更重要的是,她还会跳舞。每次班里搞活动,都少不了她。跳得最多最拿手的是一支名叫《雁南飞》的独舞。当我第一次见她单脚着地,另一条腿向后高高翘起,两条手臂轻柔地摆动,身体与地面几乎平行,如大雁扑扇着翅膀翱翔于蓝天时,那一刻我的呼吸似乎消失,连心脏也停止了跳动。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美的舞蹈,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艺术,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美。
这么多年过去,也许是七角井的人和事、七角井的日子太单调太无味,也许是少年时代的青葱岁月本身就值得留恋。我始终记得李梅的舞蹈,始终记得那一幕。
后来,对舞蹈一窍不通也不怎么感兴趣的我曾有机会,进入诸如国家大剧院等场合欣赏舞蹈节目,每次,台上的舞者都会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李梅,于幻觉中看到她在舞台中央翩翩起舞,每次都会让我神伤很久。而且,演出再精彩再专业,我也找不到第一次看李梅跳舞时那种惊艳的感觉。
和我那颗“砰砰”乱跳的心贴在一起同频共振的是一本书,琼瑶的《窗外》。班里的女孩子都喜欢读琼瑶的小说,我相信李梅也不例外。那本书的扉页上,还写着“李梅,祝你生日快乐!”的字样。这几个字是我工工整整一笔一划认认真真写出来的,一点也不像平时写作业那么潦草。不过八个字,却花了我一晚上的功夫,光酝酿情绪就喝下了两罐头瓶白开水。落款我用的是两个“L”,我名字的拼音缩写。
不光是书,其实书里还藏着秘密,另有玄机。
当然不是情书,哪怕面对自己心仪的女孩,那时候的我也没有给她写信表白的胆量与勇气。书里夹的是一张小小的邮票,上面印着一个年纪轻轻却满头白发的女孩子,穿一身白衣裳,一个人在那跳舞。她仰着头,白发披肩,一条腿往后翘起,两只手举到空中,似乎是在呼唤或是迎接什么,看上去很美也很凄惨。邮票上并没有写女孩子的名字,只有“中国人民邮政”几个汉字和“54”“1973”两个数字。据给我邮票的小霞说,那个女孩子叫白毛女,头发是被一个叫黄世仁的大坏蛋欺负白的。她还说,这张邮票是1973年发行的,年纪比我们都大,很珍贵。
也许是生活无忧,手头还有几个闲钱,当时的盐化总场集邮风气很盛。那年“十一”,也就是奥运会正在韩国的汉城举行,即将落幕时,盐化总场也成立了集邮协会,并举办了首届邮展。
小霞喜欢集邮,我却是一窍不通。之所以想把它送给李梅,是我觉得邮票上的白毛女跳舞时,身姿舒展和李梅一样优美。她们都喜欢跳舞,就冲这一点,我相信李梅一定会喜欢它。
在我的注视下,眼前的羊尿泡一个花骨朵微微颤着,叶片似乎打开了一些,像是也在呼吸,频率急促了许多;而我视线中的另一朵花,蒲扇般张开的花瓣仿佛醉了酒的红颜,更红更艳,艳得连天上的日头都黯淡下去。
这样贫瘠缺水的戈壁滩,这样泛白干焦的碱土地,能开出这么美的花,偏偏花的名字还那么土那么俗,成千上万的汉字组合,什么名字不好,偏要叫羊尿泡,真是让人感慨无语。
我的心忽然一动,我相信羊尿泡绝不会是这花的学名,它肯定会有自己的正经名字;而我,每次看到它只是觉得美,很感慨,却从没想过认真地去了解它。因为熟视,所以无睹,不光是对这羊尿泡,对身边的亲人朋友其实我们也常常如此。
我从心底发出一声叹息,就像很多年前的那天一样。如今想想都觉得丢人。
20多年前的那个星期天,我也是站在这里。当然,那时这里还不是一片白地,实实在在地有着一排房子。
由于最早来七角井搞开发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战士,后来才交到地方,所以这儿的建筑全部是营房式的。一排排有着船形拱顶的红砖平房,沿着场里唯一一条柏油马路两旁的林带次第排开,平平整整,规规矩矩,光看外表,你家、我家、他家全都一个模样,
即使这样,我还是很容易就找到了李梅的家,我已经打听得很清楚,她家是左手第二个门。
站到李梅家门口,不知为什么,我好不容易鼓起来的勇气竟然一下全没了,仿佛被人踩扁的一颗羊尿泡,手千辛万苦地抬起来了,却不敢往门上落。我唇焦口燥,喉咙里干干的,似乎身体里的水分全给太阳烤干,心更是“砰砰”狂跳着,似乎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我退回到房子旁边的林带。七角井的人工林带,大都是一种格局,中间种杨树,两边是沙枣树。我躲到一棵歪七扭八、枝叶茂密的沙枣树后面,深深呼吸了几下,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等我再度鼓起勇气走到李梅家门口时,很奇怪,好像她家门口有一个看不见的吸管,只要我往那一站,就会把我体内的精气神全吸干,让我蔫头耷脑、手足无力。
从李梅家门口到那棵沙枣树,再从那棵沙枣树到李梅家门口,我一共往返了三次,连身边的沙枣叶子也“沙沙”响着像在笑我。还好路不远,不过八九米,并不费事。
见了李梅,说什么?对我来说这是个大问题,总不能把书塞给她转身就走吧。她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她的身影她的声音这一年来始终陪伴着我,我做梦都想让她做我的女朋友,可我不能让她知道这一点。
如果她知道了,那最终失望的一定是我。她肯定不会再理我。
跟平时老是围在她身边那些长得帅的、学习好的、家境好的、胆子大敢跟她开玩笑能把她逗乐的男生们相比,我确实是太平庸。我的心思,还是埋在心底,我一个人知道最好。
在班里,生性内向不爱说话的我一直是最不起眼的一个。我本以为,李梅永远也不会注意到我,永远也不会理我,更别说冲我笑了。没想到,她来第三天第二节语文课一下课,在教室门口很偶然的一个照面,她就跟我说话了,“你作文写得真好!”话说完还给了我一个灿烂的微笑,灿烂得就像戈壁滩上刚刚升起的一轮红日,带来满世界的光明与希望。当时我一下子就傻了,慌得不知所措,好像一截木头,全身肌肉都僵了下来。等我缓过神来时,她已经侧着身子,灵巧地从我身边一闪而过。
这时我脑子里最先出现的念头是,她会不会以为我是故意挡住她,不给她让路啊?这么一想,我马上就慌了,抹一把脸,脑门子上全是汗。我觉得,后来我一紧张一害怕就流汗的毛病,就是那時落下的。然后我才又想起,刚才语文课上,张老师表扬了我写的作文。
若干年后我曾反思,上学时我之所以语文成绩还过得去,作文写得也可以,一方面是因为我从小爱看书,另一方面则是我怕张老师的缘故。
不光我怕,可以说班里没一个人不怕他。他有一手飞粉笔头的绝活,指哪打哪,百发百准。上课时候——尤其是那些学习成绩一般还爱捣乱的男生——谁敢发呆走神、说悄悄话、看小说、揪旁边女生的辫子、往前面同学背上粘纸条,都会领教他的绝技,我就因为走神挨过两次。
有过这两次教训,课堂上,我渐渐地不再走神,不再去想故事里去西天取经曾经路过七角井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不再去想故事里的黑脸张飞、白脸赵云还有一辈子红着脸不知道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的关云长,不再去想故事里的玉麒麟、黑旋风还有景阳冈上喝多了酒仍能打死老虎的武松。我尽量认认真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张老师的一举一动,尽可能原原本本仔仔细细地记下从他嘴里吐出来的每一个字,就连话语间夹带的唾沫星子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我相信,屈服于那些粉笔头的学生绝不止我一个;而对那些挨了粉笔头还屡教不改的,张老师不多说什么,直接拖到教室后面罚站,谁还敢犟,他就踢屁股,真踢。而挨了踢的学生,没有一个不老老实实认罚,更没有一个敢去找校领导告老师的状,哪怕是回了家连父母都不敢讲,害怕再挨一顿骂,遇上脾气暴躁的家长,再加一道“皮带炒肉”也不奇怪。老师不严对学生不打不骂就不是好老师,当时大多数家长都是这么认为的。
许多年后,我成为了一名靠写作为生的文字工作者。当我有幸进入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时,当我参加全国青创会坐进曾召开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京西宾馆3楼1号会议室时,当我有缘成为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的一员时,当我正式加入中国作协时,我会一次次地想起七角井,我出生成长的那个戈壁小镇。我想,这首先要归功于张老师,其次是李梅,是她的夸奖让我对写作文更有兴趣劲头更足。此外,那些统治着我们课堂生活五颜六色的神奇的小粉笔头也功不可没。
我在李梅家门前转来转去,始终没能把勇气鼓足。如果她不理我了,连我现在还能见到的她那春风旭日一样的笑也将彻底消失。
最终,我把那本夹着邮票的《窗外》从她家院门底下塞了进去,一边塞一边自嘲地想,这本书如果名叫《门外》,跟我眼前的处境就更契合了。
返家的路,没走出多远我又后悔了,不停地骂自己没出息,哪怕她不愿接受我的礼物不愿做我女朋友也算一种结果,这么不明不白下去算什么?
正独自怨尤,迎面撞见军子和另两个同学。“走,学校打乒乓球去!”军子扬了扬手上的乒乓球拍,唤我。“不去。”正没好气的我想也不想地拒绝了。军子一怔,脸上现出几分尴尬,最后又冲我晃了晃球拍,自顾走了。
他不知道,其实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在班里我的朋友不多,他跟我走得算是最近的,又是一番好意,我不该这么怼他。而且,乒乓球我也爱打,也许是身体不够壮实,足球、篮球、打群架、攻城、“斗鸡”(这游戏跟鸡无关,而是人一脚独立,另一脚用手扳成三角状,膝盖朝外,单腿跳着用膝盖去攻击对方,若对方双脚落地,则为赢得战斗)这些属于七角井男孩子的游戏,从小我就不怎么参与,乒乓球是我最喜欢的体育运动,直到今天都是。
军子走后,两个我在心里又斗争了一气,仿佛奔赴战场,我毅然转身,重新向心目中的女神靠近。
再次站到李梅家门口,我抻长脖子耸起肩深吸一口气,咬着牙正要敲门,门内却忽然传出一个有几分熟悉的男声:“地上有本书!”
我一惊,赶忙回头,快步重新躲进了林带。
瞪大眼睛等了大概两三分钟,这期间,我已经大致判断出那个男声是谁。仿佛有特异功能,眼睛能穿墙透视,一个有着挺拔身材英俊面容的男生身影自动浮现在我眼前,心底也多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吱扭”一声门终是开了,一前一后出来两个人,后面那个一袭红裙手里捧着《窗外》的苗条身影不用说正是李梅,而先出来的那個,果然就是何青——我们全班人人服气,演讲比赛总拿第一的班长,从小学一年级至今年年不落的三好学生,盐化总场副场长的儿子,北京知青的后代,在天安门和万里长城前照过相的人。
证实是他,我的心彻底地凉下去。跟他相比,哪怕我的作文写得再好,李梅也不可能选我。
“这书是谁送的?”何青的语气显得很平静。
“看不出来,这字好像没见过。”李梅把书举到眼前,翻开扉页飞快地看了一眼又合上。
“那不是有落款吗?两个‘L。”
“猜不出来,管他是谁呢?反正我知道不是你。”李梅笑意盈盈地伸手,亲昵地挽住何青的胳膊。她的声音比平时更柔更细,而且这柔与细的白开水中还添了蜂蜜,多了点平时从没听过的撒娇的味道,十足一个深陷爱河的小女生,就像电视里琼瑶剧中的女主角。
李梅的声音、动作让我彻底傻了。那时候的七角井,谈恋爱也是很纯洁的,男生敢拉女孩子的手,已经算是很大胆的举动了。女孩子主动挽男生,我还是第一次见。
“看来他还挺了解你哦,知道你爱看琼瑶的言情小说。”何青把头歪向李梅,笑了。
“你吃醋了是吧?告诉你,你拿来的我才爱看,不是你给我的我才不看呢。”说到这,李梅把书随手往地上一丢。
“不要你也不能随便乱丢啊?让人捡到了往外一说,对你多不好,还以为你跟人家怎么了呢。”何青站住,想了一会,弯腰把书捡了起来。
“你想要就拿着好了。”李梅语气轻松不当回事地道。
眼睁睁地看着《窗外》还有白毛女落到何青手里,我真想跳出去大吼一声:“那是给李梅的!”可我只是咬响牙攥了攥拳,再没有任何动作,连大气都没有出一口。我知道,不光《窗外》、白毛女,连《雁南飞》和李梅现在也落到了他手里;我知道,不管任何人,哪怕是我的亲人,我的父母哥哥姐姐,在他们看来,何青都比我更适合李梅,他们才是金童玉女天造地设的一对;我也知道,如果这时我跳出去,场面只会更加尴尬,而我将承受更多的羞辱。
“别送了,你该回家了!”从我眼前走过去时,何青把手里的书当扇子,轻轻扇着道。
“回去也没事,再走一截呗。”李梅缓步向前挪着,她的眼睛,从头到尾基本上一直落在何青身上。
“你身上有一股沙枣花的味道,真香……”何青挽着李梅,和她说笑着。
沙枣花?
我怔怔地看着眼前的一树沙枣花。
金灿灿的阳光下,只见一朵朵小小的黄里透白的沙枣花,就像一个个怕见生人脸上含羞的小女孩,藏在枝叶间,隐住身形。
虽然沙枣花就在眼前,但起初我并没有留意到它的香味,何青话说完,仿佛一道闸门被打开,一股沁人心脾的甜香滚涌着激荡而出,一会儿就塞满了我的鼻腔、我的气管、我的心肺、我的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让人觉得说不出的舒坦。
有生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这么认真地打量沙枣花。虽然看上去,它们并不起眼,可从它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却覆盖了整个七角井,还有七角井周边,那些铺满黑石子的戈壁滩。
眼前似乎蒙上了一层水雾,两人的背影在我视线中越来越模糊……
“怎么到这儿来了,害我找半天。走,羊肉汤炖好了,绝对的纯天然绿色无污染有机食品,你在城里吃不到的。”军子中气十足的声音从身后响起,或许是受了惊吓,眼前好几朵花都颤了起来,连花骨朵的身子也在往后缩。
“随便转转。”我回头冲他笑了一下。说实话,我现在还真有点佩服他。据我所知,他之前一直在哈密做生意,不敢说大富大贵,却也有房有车,俨然中产,在所有走出七角井的人里算一个成功人士。但不知经了什么事,他不说,我也没好问,几年前忽然就离了婚,孩子抚养权也没要到手。这些都不值得我羡慕,关键是离婚后他一直是一个人,没想着再婚,而是回了七角井,买了五十只羊,在以前的老房子里住着,当起了羊司令,每天撵着羊屁股在戈壁滩上转悠,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你咋想的?”有一次电话聊天时,我曾问过他。
“人这一辈子能活多久?搞那么累干什么?自己开心就好。”他回得简单。
想一想,他说的很有道理。比起五光十色的城市,七角井确实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别的不讲,单说走路,在这儿每向前一步,我的整个脚掌都会完整地踩在坚实的土地上,心底会油然而生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只觉浑身轻松;而在城市,在快节奏的生活磨砺下,我,就像一根时刻紧绷着的弹簧,脚不沾地,在不停地往前赶,忙着永远也忙不完的工作,心从未如此安然。
有人可能会嫌在这儿生活不方便,可那也得看是对谁,就好比军子,有车,更重要的是不缺钱,隔三岔五就去哈密、鄯善耍一圈,采买些东西回来,来回不过半天功夫,实在称不上麻烦。
面对羊肉汤的召唤,我不再矜持。临转身前,我又看了一眼曾在李梅生长的地方生长绽放的那株羊尿泡。眼下花仍艳着,再过个把多月功夫,入了秋,果也该熟了。
羊尿泡的果实形状正如它的名字,像羊尿泡,也像人的肾脏,如果文雅一点,也可以说像圆灯笼,里面还有籽。小时候,没事的孩子们常常把它们摘了,扔地上踩,就为了听那“噼啪”一声闷响;有些大人也参与进来,据说那是一味中药,可以补肾利尿;不光摘果子,他们连根也挖,说是可以治肝硬化腹水、肾炎水肿、慢性肝炎、血管神经性水肿等症。
春夏生长,抽枝散叶,开花,红艳艳地妆点死寂的戈壁,然后便是秋天的粉身碎骨、尸骨无存。这就是羊尿泡的一生,它的宿命。
按老人们的说法,李梅的命也苦。
1996年,按国家政策,何青全家迁回了上海。作为我们那一届全班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当时他还在武汉读书。走前,他向李梅发誓,等自己毕业在上海安顿下来,情况好些后一定会回来接她。头两年,何青还常给李梅写信,可再往后就没了消息。包括李梅父母在内,很多人劝她,说何青去了大城市,心花了,肯定不会再回来找她,让她死了这条心,再找一个。李梅却是谁都看不上,直到今天还是单身,2001年盐化总场破产不复存在后,居民开始大规模搬离七角井,李梅的父母、哥哥、妹妹都走了,可她不走,继续守在七角井,在从山北三塘湖油田去往哈密经过七角井的省道边开了一家小饭馆兼旅社,主顾除了镇上的干部,全指着那些过往的司机。
据说,这些年,被李梅拒绝过想当她男人的男人不下二十个。
据说,前些年,李梅去过上海,至少四次。
据说,近些年,李梅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因为只要出得起钱,她能满足顾客的一些特殊要求。
我高中毕业时,盐化总场已经是日薄西山,无法安排工作的我只能选择离开,开始四处漂泊、打工,所以关于李梅的消息,其实我都是听来的。
一说到李梅,很多人都会骂何青,说他没良心,是陈世美。我却不这么认为。也许,在那些人看来,何青回到上海会生活得很幸福,可他们又哪知道,身在大城市的苦处?我想,如果何青真的很爱李梅的话,他肯定希望能给她幸福。可他有这个能力吗?不管他在七角井如何出色,可到了上海,别的不说,光一套房子还有李梅的户口和工作就会愁白他所有的头发。在物欲横流而又无比庞大的世界和现实面前,个人的力量是那样的渺小、微不足道,爱情,更是不堪一击。
如果给不了心爱的人幸福,何青好意思来接李梅吗?考虑到现实种种,对这段感情,他说不准早就死心了。
李梅的遭遇让我感慨,让我感慨的人其实还有很多。盐化总场破产后,有门路有本事的家都搬走了;没搬的,家里年轻力壮的也差不多都出去打工了,留下来的,大都是些老弱病残。最可怜的也是这些出去打工的人,连农民工都不如,碰上企业不景气了,農民工回到家还有一亩三分地,可七角井呢,想种地都没有。
另外据我所知,在七角井,像何青和李梅这样因为盐化总场破产倒闭,一方或是双方离开小镇而分手的恋人还有很多。连我和小霞也可以算入其中。
我父亲和小霞父亲是战友,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一起转业进疆,多年来两家你来我往关系一直很好。因为小霞家没男孩,所以我一出生小霞父亲就认我做了干儿子,两家大人还坐在一起给我们订了娃娃亲,如果盐化总场效益再好几年我没有离开七角井,那八成我和她会成为一对。
比我大一岁相貌平平的小霞,我已经很多年没见了。虽然对她没什么感觉,可我至今怀念她的温柔。那些年,不管是让她补我撕烂的衣服、给我讲题写英语作业、给我端茶倒水送吃食,还是看上她手头的什么东西,只要我开口,她从不曾拒绝。
听说她如今依然生活在哈密,男人是开出租车的,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日子过得还算不赖。这让我很是欣慰。
“我们来自远方的沙漠,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伴随阵阵的驼铃声,伴随阵阵的驼铃声,来到了夜上海……”
耳畔忽然响起一阵歌声,跟在军子身侧的我从远处苍茫的戈壁收回目光,斜了一眼正拨弄着手机的他。
“知道这歌谁唱的吗?”军子问。
“谁?”这时我的心仍留驻在戈壁,只是听到歌词中“夜上海”几个字时,我心里莫名其妙最先想起的竟然是何青。
当年,见证了李梅和何青的爱情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走出镇子,忧郁地徘徊在戈壁上,看日出、日落、骆驼刺、羊尿泡、刺旋花、红柳、四脚蛇,还有一地碎石。可以说,广袤的戈壁小到每一块我目光所及的石头里,都藏着我的影子,见证过我的喜怒哀乐。
我知道,戈壁间没有砂石覆盖的浮土地上,那一个个小指肚大的圆洞里隐藏着的玄机,拿一根细草棍,伸到洞里一圈圈搅,慢慢地,浮土上就露出一个没有芝麻大的活物,孩子们叫它“土牛牛”,连它带土一把抓到手上,静静地等着,眼见着那小东西渐渐隐去身形,不一会,就会感到手心一阵麻酥酥地痒,让人纳罕:那肉眼都辨不清的小东西,会对自己生活的土地爱得如此深沉,这般执着。
我知道,只要是有太阳的晴天,站在戈壁上,极目望出去,可以看到远处日影下有齐膝深的洪水,水浪翻涌着,在戈壁石滩上咆哮奔流。那不知从何而来的洪水看上去那样真实,却是假的,根本不存在。明知道那是假的,可它看上去却偏又那么逼真。我给它起名叫“水影”。那时我就知道,人世间,有很多事就像这“水影”一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难以言说。
我也知道,戈壁上最顽强的生命要数骆驼刺。它虽然贴地而生永远也长不高,但极度的干旱、烈日的烘烤、严冬的摧残,什么都奈何不了它,只要春天一到,照样抽枝发芽。那时我就告诫自己,生活中要像它一样顽强。
七角井让我怀念,不光是因为它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可以说,只有在七角井,我才有最安稳的睡眠,即使有梦,也是香甜的;只有在七角井,我才有最好的胃口,哪怕粗茶淡饭,也能大快朵颐、酣畅淋漓;只有在七角井,我才有最从容的步伐,就算路走错了,也知道回家。在那儿,我不会感到沉重,不用伪装。我可以做我想做的,说我想说的。那是一种彻底地放纵,那是一种真实的自由。是的,那就是生养我的小镇,那就是我永不会回头的青葱岁月。
“巴特尔·邓勇,还有印象吗?”军子举着手机问。
邓勇?这名字我熟。他也是七角井人,印象中,从1990年到我高中毕业,他一直是学校的音乐老师,只是没教过我而已。他爸爸是汉族,妈妈是蒙古族,在汉族名字邓勇前面加个巴特尔就成了他的蒙古族名字,大家都这么叫。
“这首《沙漠人》就是他唱的,现在上海生活,也算国内小有名气的一名歌手了。”
上海!又是上海?我一方面为邓勇的成就感叹,从七角井到上海,我知道这段路绝不寻常,其中有着无数的艰辛;一方面为再次听到“上海”这个词而感慨。2010年,世博会召开期间,我曾到过上海,南京路、外滩、城隍庙、人民广场、世博园都转了,除了人多,上海留给我的印象一点都不好。
“我们远离曾经的蹉跎,为了一个美丽的传说,跟随匆匆的脚步声,跟随匆匆的脚步声,开始了新生活……”
歌声持续。最初开始听时还没什么,知道这歌是我熟悉的土生土长的七角井人巴特尔·邓勇唱的以后,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歌。
以前喜欢刀郎,不光因为他是在新疆唱红的,更重要的是他写的词、谱的曲,还有他那饱经沧桑似乎在岁月的风尘中浸染了无数个世纪的嗓音,正好能打动我契合我;而现在喜欢巴特尔·邓勇,理由更简单,他是七角井人,他也是在眼前这片被戈壁环绕的废墟上长大的。
“李梅也在,都是老同学,一块喧喧。”军子一边调着手机音量,一边说道。
李梅?我一怔,眼前再次闪现出那个单脚着地,另一条腿向后高高翘起,两条手臂轻柔摆动的倩影;然后,是《窗外》和白毛女,是两个紧贴在一起越来越小的脊背;最后,是满戈壁开得轰轰烈烈无拘无束红艳艳的羊尿泡……鼻际,则始终弥漫着一股沙枣花的甜香。
这一切,她肯定毫无所知。而我呢,现在该怎么面对她?
短时间内我找不到答案,但我并没有慢下自己的步伐。
就像巴特尔·邓勇歌中唱的,跟随时代匆匆的脚步,我们都已经开始了新生活,现在的我已经足够成熟,面对问题,再不会像二十几年前一样选择逃避了。
回到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怀念军子和李梅一起炖的那锅羊肉汤。我发现,他们在一起干什么都很默契,我似乎不用再为李梅的未来担心了。我甚至觉得,军子之所以回七角井,很大可能是为李梅。
我还查了一下资料,羊尿泡果然有它的正宗学名:苦马豆,虽然比羊尿泡好听点,可也好不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