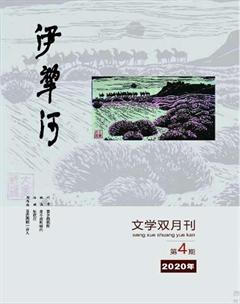两山记
周华诚
坐对一山空
1
我在九峰山上一角,凌空之处,看见一把空椅子。这是七月,山上有些闷热,间或还飘洒几丝小雨。人群即将散去下山,而我忽然对檐廊尽头的风景产生好奇,便穿过短短的檐廊来到悬挑的平台,顿时,一股山风拂面而来。那风是从竹林与峡谷出发的,从满目的翠绿里出发的,一下与我迎面相遇。
平台上的一把空椅子,似乎充满了深意。它在等待一个人坐下。我回头望了望人群,公子君、魏君他们还在禅寺与岩壁之下驻足闲谈,似一时没有下山的意思,我便在那张椅子上坐下来。此时此刻,坐下来,面对这一山的空净,面对满目的苍翠与青绿,枝叶摇曳,风吹云动,草木空寂,梵音袅袅,顿觉内心澄澈一片。
一把空椅子,在那悬挑的平台之上,一定是有所期待的。不是我,或许便是另一个人。那个人是谁?这九峰山,算不得多么热闹的景点,即便是节假日里,也没有多少人上山来(这从石道上苍翠的青苔可以判断),遑论普通的工作日了;然而这也倒正合了我们的心意。但凡熙熙攘攘如菜市之地,我们在城市中就可以感受了,何劳费事专程来此。这距离市区尚有数十公里的九峰山,便因其清寂而添了一分幽意,也是难得的了。
遥遥寄微入远方。我坐在这里,便有些出神。我仿佛能听到檐角传来风铃的轻微声响,那声响若远若近,若即若离,若有若无,与苍翠的绿意、白色的烟岚混在一起,四面飘送;而我觉得,风也走到我身边来,山岚也走到我脚下来,这椅子四面气韵流动,这山谷中万物有灵,人竟也有些飘飘欲仙。
2
魏君一头钻进九峰禅寺里面,与大师父言谈甚久。那确是一个清修之处,地方不大,也颇为幽暗的样子。岩壁底下、石墙上,都缀满星星点点的水珠。水珠圆滚滚,久也不落,偶尔啪嗒一声滴落下来,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倘若有人安坐在此,静心修禅,是一个佳处,即便不修禅,也是一个佳处。譬如说在夏天,山下躁热如火炉一般,这里也一定是充满清凉的。人说,无上清凉。人从山下的世俗凡间逃避,而逃向哪里才有一个世外之地呢?唯有修行,面壁,听水珠滴落,才可以获得内心的宁静罢了。
這样想着,我穿过山洞的水帘——那几天正好下过雨,山上蕴含着丰富的水分,便从这岩壁之隙冒出来,淌下来,形成一个水帘洞天的样子。我穿过之时,便有雨点落在我的额头,仿佛是一种自高处降落的谕示。
魏君是我同学,我俩曾在京城共读四月。上次一别,也有一年多了。此际又在浙中重逢,当是赏心乐事。想那时离校之际,魏君还送我一册哲学的书。分别与重逢,都是普普通通的事,自然分别不必过于伤怀,重逢也不必陷于狂喜——只觉得都是淡然欢喜,坦然迎接。公子君与晓敏君,是我谋面二三次的朋友,却因为文字的关系,仿佛觉得已经认识很久。此外,亦有初次结识的朋友,譬如张君。这样的相遇,也都是一种淡然欢喜的机缘。
我等数人一路行来,爬山涉水,相互之间时常戏谑打趣,没有一个正经的样子,也没有一个持重的样子。然而,到底都是写作的朋友,心性赤诚,行路或聊天,正经或不正经的话,聊来也都有些意思,至少,有一种天然的意趣在,也是难得。也正应了一句很俗的话——很多时候,路上的风景并不重要,与谁一起去看那风景才重要。
我从岩洞里出来,晓敏君还举着相机拍一块石碑上刻的字,久久地站立,也不说话。魏君还站在岩壁之下。魏君身形福相,与禅寺的大师父聊得正投缘,后者一直送他出了水帘洞来。我远远望过去,这二人站在一起,便有一股气象在。
公子君后来谈及她在许多年里与许多寺院有密切往来,也与庙里的僧人颇多交往,因而对于这样的山中清修的生活,出世与入世的距离,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有她自己的体悟。本来,我也是想听她再多说一说的,我一直以为,写小说的人,对生活的看法,是有着更为刁钻的角度与眼光。可惜公子君后来却没有多说了。我倒是想起汪曾祺作过的一个小说《受戒》。
我问晓敏君,碑上写的什么——原来是“九峰禅寺简介”,不是什么老的东西。石记曰,九峰禅寺原名九峰寺,坐落于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汤溪镇南,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嗯,掐指一算,距今也有一千五百多年了,于是又不禁仰头去看那藏在岩石间的禅寺,以及岩壁上的水帘。
我避了人群,随处踱步,这山野之中,藏着我喜欢的事物。古树,青苔,雨水,飞鸟,独自的时候更能发现那些奇妙之处。此时,一把空椅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椅子正对出去是一片竹林,准确地说是一片竹林的高处,只看得见苍翠一片,摇曳一片。竹林是动的,只有那把椅子,安若磐石地摆在那里。
3
雨水挂满每一片树叶,九峰山向我呈现出千百万年以来唯一的样子:每一片树叶都是新的,每一滴雨水也是新的。
上山与下山路上,低头看见脚下每一个台阶,都觉得值得俯身观察。青苔在阶隙中生长,蚂蚁不惧湿漉漉的鹅卵石的道路,雨后即出来游历。路的两旁,山坡上长满各种乔木灌木。枝桠藤蔓。有一种苎麻植物,当地的朋友说可以拿来吃,十几年前她就采摘过,取大米与芝麻一起,借助流水的力量,放在水碓中捣……脑海中便浮现出一个画面:涧水清清,碓声阵阵,山野中的人家取食自然之物,晨昏之间,在丛林间行走。
在金华市,像九峰山这样的景点很多,许多都比九峰山有名。然而我们去了九峰山,自有它的道理。很多史书记录,中国禅宗的始祖菩提达摩,在这里圆寂的。起初我们都不信。安徽九华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香火之盛甲天下。这座九峰山,说来也是宗教名山,曾几何时,儒释道各方高人共聚于此,并存共荣。譬如说,达摩就为九峰山留下了“可以震撼世界的生命踪迹和文化财富”。这话,是洪铁城先生说的,洪先生站在上山小道的一侧平地处,透过密密匝匝的竹林向我们指点达摩洞的所在——他说洞内现存仙床、仙桌,可以佐证达摩曾在此生活。
菩提达摩和释迦牟尼一样,是古代南印度人,原是南天竺香至国国王的第三个儿子,父王去世后,辞别兄嫂出家为僧。梁武帝普通元年即公元520年,由师傅授意来到中国。他先上了少林寺,教众人习武以强身健体,自己则面壁静坐9年,然后将法器、衣钵和一部《楞伽经》传给慧可,离开少林寺云游四方。有学者认为,“达摩到中国实际上生活了50年左右时间。这有魏杨炫之著的《洛阳伽蓝记》中所载,达摩活到150多岁而终。另有胡适也认定,达摩在中国住了50年之久。”
康熙《汤溪县志》记载:梁天监年间,达摩曾为离九峰山不远的证果寺开基,亦即奠基。最后,达摩在九峰山的仙洞内,禅坐七七四十九天,圆寂。时间是公元566年。这与达摩活了150多岁、在中国生活了50年左右是基本吻合的。
洪先生博学多识,是建筑学家,亦是当地文史学者,几天来带领我等众人行吟山水,勘览古建。在重重枝叶遮蔽之间,洪先生悉心讲解,对面山岩之上的秘密被一一揭示:达摩圆寂后,其弟子按当地最高规格“悬棺葬”的形式,将其棺木安放在九峰禅寺前最高处的岩洞内。在那洞口,有一对天然岩石形成的神兔、神龟把守。这神兔、神龟至今仍在。顺手指的方向,我们看见叶动风摇,岩洞缄默,神兔神龟是那恪守秘密的证人,既不说是,也不说不,它们沉默不语,在一千五百多年的风雨之中,将自己也守护成了一个亘古的秘密。
4
从九峰山回来,闲读一本书,《八婺古韵:金华市博物馆基本陈列》。随便一翻就翻到了“贯休和尚”一节。唐代贯休和尚,我之前有所涉猎,是在写《流水的盛宴:诗意流淌钱塘江》那本书时遇到他的——贯休俗姓姜,少有奇才,七岁时投奔兰溪的和安寺圆贞禅师,出家为童侍。贯休记忆力超强,日诵《法华经》千字,过目而不忘。又雅好吟诗,吟寻偶对,彼此唱和。贯休受戒之后,诗名日隆,又善画罗汉,远近闻名,成一代诗僧画僧。贯休有一句诗:“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遂也有人称他“得得和尚”。
读这本书时,一眼瞄到:“贯休和尚……曾出任金华九峰禅寺住持。”
会遇到的人,终会在某些地方遇到。在一个博物馆里见过贯休的罗汉图,真是“状貌古野,绝俗超群”,而且“笔法略无蹈袭世俗笔墨畦畛”。当时我在九峰禅寺,并不知晓这一节,若是先就知道贯休也在此修行过,当去寻觅一下,是否有贯休留下的什么踪迹吧。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象中,贯休也一定这样在岩壁前打坐,面对一山的空寂与苍翠,画画或写字,参悟与修行。
魏君,公子君,晓敏君,我们一路依然戏谑打闹,说些正经或不正经的话。我们说,其实我们也都在修行,只是在这俗世的生活中间;修行不只是隐于深山,不只是每日面壁参禅,其实认认真真生活,亦就是修行。所谓认认真真生活,是指那样一种:不敷衍,不潦草,不虚伪,不逢迎,只是天然素朴,遵从一心地去生活。
我对魏君说,你从北方来,为什么今日会在这里,为什么与这样几个人相遇,相遇之后会发生什么,都是有缘由的,绝非空穴来风,无缘无故而来。而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会登九峰山,之后又为什么会分别,亦是机缘促成。与人与物,与山与水,分别与重逢,这都是值得天然欢喜的事。
九峰山下来,公子君云游天下去了,不时从微信里给我们发来身在土耳其的照片:那些身着黑罩袍的女人,那些异域的风情。张君则不时发上来美食图片,腴美的鹅肝煎得恰好,鲜甜的海胆覆于米团之上,生鱼片散发着色泽,使人迷醉。魏君回到北方,偶尔夜深之后冒出来说话,譬如说想念南方什么的,令人怀疑他是不是又喝过酒了。晓敏君则甚少说话,仿佛潜入生活的水下,做着久久远远的事情,一如他在山上面对一块碑时的样子。
这火热的生活,令人赞颂。
这也使我不时想起九峰山,想起那张空椅子,想起我在那张椅子上坐下来,那短暂的时空中面对一座山的寂静。
“寂静并不是指某些事物不存在,而是指万物都在的状态……寂静就像时间一样存在,滋养着我们的内心。”
梵净山走神
1
二禾君,我低头的时候,就看见一片云向我走过来。
云是会走的,而且走得很快。经历悬崖与峭壁,经历手脚并用的攀爬,经历腿脚打颤的心惊,此时我们终于登顶。登顶之后,平步青云,两腋生风,云雾奔涌,气象万千。便觉得,所有来路的艰辛,都有了交待,都不值一提。便觉得,所有的心惊胆战都是过往,都是经历。便没来由地想起不着四六的诗句,比如:“岁月忽已晚,我生君未生,不敢高声语,白云生处有人家。”
二禾君,我登的是梵净山之顶。
我以前没有到过梵净山,只是从贵州的好友丹玲的口中听说过这样一座山。我们有一位同学,多年饱受失眠之苦,他有一次无意中聊起自己的失眠,丹玲便邀他去山里小住,说入山之后保准不再失眠。她说那是一座仙山,一座清静之山。其实,也别说什么失眠了,便是有什么抑郁难平,有什么心结难解,到梵净山里住上十天半个月,就一切都好了。
好了,就是好了。可什么是“好了”却很难说,及至我们登上梵净山,我一下子明白了过来。这座山的好,别处所无。且不说它是著名的弥勒菩萨道场,也不说它位列中国十大避暑名山之类——名头且不说它,它的好,在于它自身。
二禾君,它的原始洪荒,如此令人着迷。梵净山的顶称作金顶,那也是我从未见过的景象:巨大的石头,耸立在武陵山脉的高峰之上,金顶是突然站立起来的石之巨人。在这个巨石的周围,亦有无数巨大的石阵。这样的气势,用什么词来形容呢?难,好像只有在电影上,比如《阿凡达》或《哈尔的移动城堡》那样的幻想电影,才可以见到如此恢宏的局面——仿佛它只该在想象中存在;而且,须是上帝的视角才可以观看。人的视角是不够的,太低了;至少,得是一只鹰的高度,穿过云层,俯瞰这座星球。如此,才可以看见,在天地之间,那大山的体量,巨石的体量;那云聚的速度,雾散的缓慢。如此,再细心地找一找,才可以发现,在大山深处,你我在哪里,人类是何等微小。这样一来,我们也就知道了,所谓的天地造化,是什么意思。
二禾君,请原谅我,面对一座梵净山,我有点语无伦次。但我愿意把它的大,或者它最激动人心的一部分说与你听。在那之外,我也愿意把它的小,或者它最微不足道的美说与你听。譬如,悬崖上正在盛开的小花,湿壁上苍翠蓬勃的青苔,以及我们一步一步从峭壁蜿蜒向上攀登着的、直入云端的无数个石阶。有山之大者,亦有山之小者,这是我所见的梵净山。
此刻,穿过云雾,穿过7896级或者更多台阶,穿过袅袅梵音,我们终于抵达世界的顶端。我想起博尔赫斯的一句话,然后我把它搬用過来——“梵净山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大,使它显得大的是阴影、对称、石头、草木、漫长的岁月、我的不熟悉、孤寂。”
善哉,使梵净山变大的,的确是它的“空”。当我站在云端,眼前却只有“空”。云雾奔涌,佛光一现,内心是空的。空空如也。金顶上的百年古刹,当梵音响起,空谷回声,回声也是空的。空空如也。一花一叶,一虫一猴,山之大愈见山之小,天地便也是空的了。空空如也。
我想起那位失眠的同学,便觉得丹玲说得对,他是应该来登一登梵净山的。他来登一登梵净山,揽一怀梵净山的云雾回去,便可以无忧无虑地睡。回去以后,管他是在北京,还是纽约,晚上倒头便能睡——梦里有山有水,梦里云雾缭绕,梦里满满的都是——空。
2
二禾君,我在梵净山看山,非看山也,乃观烟云,观气象,观草木耳。
宋人韩拙说,云之聚散不一,轻而为烟,重而为雾,浮而为霭,聚而为气。山水佳者,在气也。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二禾君,我在西湖边住着,便能得湖水云天之气,常见不可见之景。世人皆以西湖为天下景,不辞万里而来,却常常不得要领,殊为可叹。西湖之胜,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雪湖不如雾湖。雪湖雾湖,可遇而不可求。乃因其不易见也,却最见其婉约意境。然而今之世人,有几人可以如此与湖相对?
二禾君,现今之人眼中山水,与一千年前人眼中山水,早已大不同。古之人看山水,初用眼看,继尔用心看。春景则雾锁烟笼,夏景则古木蔽天,秋景则天色如水,冬景则借地为雪。今之人看山水,初用眼看,继尔用手机看。技术性的假眼睛,取代了凡胎肉眼的真欢喜。现代人喜欢这样:戴着口罩呼吸,对着屏幕谈情,透过摄像头观看一切。
今天的我们是山水的虚假爱好者。我们在城市里造假山,造园林,或把房子盖到山里去,把汽车开到山里去,却不愿意真诚地去观看一座山。不愿意花上一个白天或一个夜晚,认认真真地看山。二禾君,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梵净山吧。然后,用一个春天一个夏天一个秋天一个冬天来看山;再用几十个晴天与几十个雨天,几十个阴天与几十个雪天来看山;如果有幸,再陪着一百只鸟儿、一百只猴子、一百只蝴蝶一起看山。啊,光这样想想,我就觉得很好。
二禾君,如果你也要来梵净山,我们还可以这样看山:不说话,静静地,听一整天山。或是闭上眼睛,耐心地,闻一整座山。
3
现在,让我们静静地在路边坐下来,看一座山明晦变幻。这时候,你随手用桐叶折了一个花兜。
阔大而被毛的桐叶被三面折叠起来,再用一根纤细的竹枝穿结而过,它就成了造型可爱的花兜。一个桐叶的花兜,它有一枝长长的柄,看起来更像是蚕或者别的小生灵结出的茧状物——它如此生动,且灵秀,又实用,可以用来舀水,可以用来盛放刚摘的果实与花朵。而桐叶不一样。桐叶上有细密柔软的毛,像毯子一样包裹果实与花朵。长长的叶柄富有弹性,带动整个花兜晃悠起来,无论是娇嫩的花朵还是汁液丰富的果实都在花兜之中备感安全,仿佛深陷一只茧的怀抱。
一个小小的花兜,几乎把童年整个儿地装载回来。
王祥夫在大湾村溪水边的房间里,倒出半碗墨汁,他要开始画画。在许多人围观下,他先慢慢地裁纸,把宣纸裁成条幅;再选毛笔——当然不会有多么称手的笔,他用指肚摩娑毫毛,感受笔尖的软硬度,摇摇头却还是坚决地选定了一枝;然后用毛笔探进一碗清水里,又把笔尖伸进墨碗里蘸了一下,然后就在纸上很快地画起来。水,或者说墨,就在纸上氤氲开了,像水气或者藤蔓。水墨在纸上爬行,笔触没有到的地方,水墨自己就蔓延过去,青葱一片。
他在纸上画了一块石头,又在石头边画了一丛菖蒲。
一块石头就是一座梵净山,一丛蒲草就是整座山的美好。
后来我们去了满家村。那个寨子是历代苗王屯兵的地方。寨子的城墙是用千层岩石板砌成的高墙,占据天险,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苗家妇女拦在寨门外,用米酒迎接众人。进了屯寨之后,我们四处闲逛,后来一位年轻的村民,叫吴亮明,带我们去了后山的溶洞。
那是一个巨大的隐秘的山洞,钟乳石甚多,一柱一柱倒垂下来,殊有可观。此洞宜屯兵,宜遁世,宜纳凉,宜幻想。譬如我认为此洞还具有某种力量,当人进入之后就能进入另一个时空。仿佛外部世界瞬间停止,或是“冻结”,而入洞之人,便平白无故地获得了某段“意外的”时间。出洞之后,外部世界随即“解结”,与上一刻“冻结”之时平滑衔接。世事如常,静水深流,而世间也无人知道你们刚刚去过哪里,干了什么。
在梵净山及梵净山周边行走的几日,我对一类东西特别感兴趣——折耳根、山蕨粑、野笋子、猫猫豆、野葱、蕨苔,都是吃的,都是山里之物。对了,还有薄荷。我摘一片薄荷叶放在嘴里,过一会儿又摘一片薄荷叶放进嘴里。我觉得这样吃,可以吃出一座山来。这是与梵净山的另一种亲近。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梵净百里,我只折一只花兜。是的,二禾君,我所能记得的梵净山,大多是这样的一些细节,而不是什么宏大叙事。当然,我这样看山未免偏颇,然而以山之大,以我之小,无法认识一座山才是对的。不知梵净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又何足怪也。
从梵净山回来后,我接着去一位中医博士处取药。早春风寒,咳嗽小恙两三个月绵延未绝,吃了医博士的药,梵净山回来不久居然全好了。我便去翻出那个药单细细察看,十五六种草药,其中居然有一味钟乳石,这真是十分有意思。我遂又一次记起梵净山,记起梵净山溶洞里的鐘乳石,记起梵净山的缥缈烟云与了了空寂,不禁又觉出它的好来。我甚至不无主观地觉得,梵净山,果真也是一味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