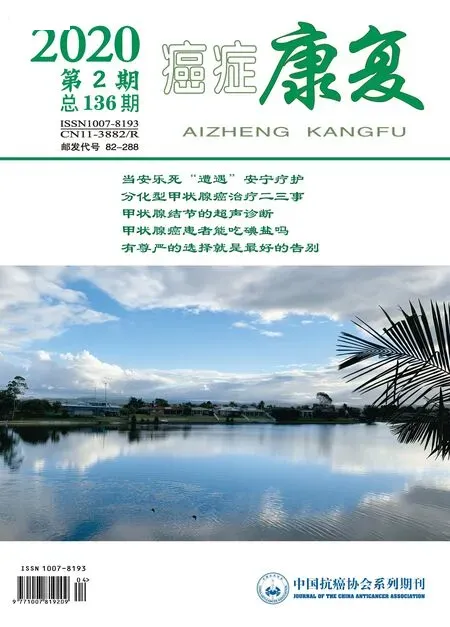有尊严的选择就是最好的告别
□王玉梅
一个月前,我和心理咨询师丁老师在病房接待了一位特殊的患者家属。她是一位中年知识分子,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她高度焦虑和恐慌的脸,眼神中透着期待。刚落座,她就急着介绍她母亲的病情和诊治情况。她母亲因为无法忍受晚期肿瘤带来的疼痛,趁大家不注意,用刀刺向了自己的腕部,流血持续了10多分钟后,母亲意识到还没有与家人做最后的告别,就打电话联系了她,后来母亲被送到急诊室缝合止血抢救过来了。她自责地说她现在已经走投无路,渴求帮忙。我向她详细介绍了我们的专业理念和能够提供的帮助,并和心理咨询师一起对她和母亲的境遇表示理解和担心,希望在收入院后能够真正帮助她们。
这是我在11年安宁疗护临床实践中接触到的为数不多的因无法忍受病痛自杀未遂的案例,也是个充满挑战的案例。我和丁老师探讨后初步达成共识:首先详细了解和评估病人身心社灵各方面的状况,找到她自杀的原因和家庭面临的创伤,以家庭治疗的方式支持与陪伴。
第一次探访是在病人入院的第二天上午。走进病室前,默默地提醒自己:今天的访谈注定是艰难的,一定要注意把控好情绪。一进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包裹在病人右手腕上的醒目的白纱布,我心里一阵难过。简单寒暄后,我在病床边坐了下来,认真地“阅读”病人的脸。病人看起来很平静,也很健谈,她说昨天入院后感觉好多了,因为我们这里安静、温暖、有人情味儿,医生技术也好,她一点儿都不疼了,说着便开心地笑了起来,这给我增加了进一步沟通的勇气。我问她是否介意谈谈有关自杀的事情,她没有拒绝,说主要是太遭罪了,从得病开始,刺骨的疼痛伴随了她一个多月,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一想到要在这样无休止的痛苦中煎熬,她就绝望了。她老伴儿从结婚开始就忙于工作,她一个人家里家外地忙着,不仅抚养了一双优秀的儿女,作为娘家的老大,还尽最大的力量照顾父母和弟弟妹妹们,这一辈子净为家人活着了。尤其是几年前,老伴儿突发脑梗,她跑前跑后,担惊受怕,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好了,感觉自己快撑不下去了,但还是没有向任何人求助,独自承担照顾老伴儿的责任。她说儿女们在事业上都很优秀,在各自单位都承担着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不希望打扰他们,拖他们的后腿。这次自杀是她思考了很久的一个决定,但是很遗憾,在即将失去意识的时候,她想到还没有和家人说再见,就给女儿打电话,送到急诊室后又被抢救过来了。她为此很懊恼,特别后悔没有就此死去,所以内心很绝望。
病人和我谈了她的心愿,希望我能帮她说服儿女,无论如何都不再继续治疗了,一切顺其自然,只要能够把疼痛控制好就行。我和她探讨了下一步治疗的打算:因为她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肾积水,可以尝试着找泌尿外科或介入科会诊,通过肾造瘘的方式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否则,她可能不会存活多久。她表示,坚决不再做任何有创和维持生命的治疗,希望自己能够保持身体完好无损地尽快离开这个世界,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希望大家都能尊重她的选择,理解她。
她的谈话让我看到了一个满布疮痍的破碎心灵,正如伦理学家Lisson所言:“疾病可以伤害肉体,而疼痛可以摧毁灵魂。”尽管我希望尽量做到感同身受,但我深深懂得,我所感受到病人的痛苦可能还不及实际的百分之一。
我把这个情况和丁老师进行了沟通,丁老师初步判断病人是因为没有完成与家人的预期分离而感到遗憾,所以才没有在最后关头决然离开。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别需要更加深入地沟通,需要我们的陪伴和支持,导引她和儿女之间建立连结,让彼此体认亲情、爱与尊重的价值和温暖,尊重病人的意愿,儿女心甘情愿地放手。
第二天上午,丁老师到病房服务,我把患者的女儿请到心理咨询室,我们坐在一起交流,引导她谈与母亲的关系。她流着泪告诉我们:母亲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六个弟弟妹妹,外婆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母亲从小就很压抑,既要照顾弟弟妹妹,又得听从外婆的指责和强迫,一生隐忍,为了家庭活着,还没来得及好好爱自己就患上了这要命的疾病。看到妈妈这样,她很心疼,但又帮不上忙,这种感受很煎熬,心里留有很重的创伤,一心想着尽可能陪伴母亲,但又不忍看到她的痛苦,更没有勇气在她活着的时候和她告别。这次母亲自杀她特别自责,有深深的无力感和愧疚感,因为过度焦虑而睡不着觉,她觉得自己要崩溃了。
丁老师很耐心地听她讲完,回问了她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母亲的生命权应该交给谁?”女儿想了一会儿,回答道:“理智地说,应该交给她自己。”“那你们现在是否干涉了她为自己作决定呢?”丁老师问。女儿沉思片刻,抬起头若有所思地说:“您说得太对了,我和弟弟都不敢触碰不好的事情,总是期待着出现生命的奇迹,按照我们的意愿安排妈妈的治疗,从没有想过问妈妈的感受。”丁老师接着问:“你能说几件具体的事情吗?”
“妈妈曾经说过不想继续治疗了,因为每一次的治疗都很痛苦,可是我们觉得如果不治怎么能控制住病情呢?所以走遍了全省最好的医院,找到了最好的医生,尝试了很多种方法,每次治疗时妈妈都呕吐、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我们就跟她说如果不吃饭还怎么活啊!我们每天从家里做一大堆妈妈过去喜欢吃的东西带到病房,她经常是吃了吐,吐了吃,有时吐得眼泪都出来了。”
“得病以后,妈妈和你们相处时态度有没有变化?”丁老师接着问。
“变化特别大,经常无故发火,有时故意和我们作对,经常一个人躺在床上发呆,不和我们说话,疼得厉害时总说不想活了,我们就鼓励她一定要坚强,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妈妈。”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生病的人是你,家人这么对你,你会怎么样?”
女儿有点吃惊地看着我们,这是她从未想过的问题,她低下头,两只手在不停地搓着,看得出来,她的内心极不平静。过了大约5分钟,她抬起头来,眼里噙满泪水,哽咽着说:“我现在明白妈妈为什么要自杀了,因为她就像一个木偶一样被我和弟弟掌控着,我们根本就没有顾及她的感受和她的痛苦!我知道以后怎么和她相处了,我们以前做的事情是满足了我们自己的需求,以后一定要先问问妈妈,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和弟弟再也不能强迫她了,我们错了!”
“想好以后怎么和妈妈相处了吗?”
“我想和她一起回忆我和弟弟小时候的事情,告诉她我们是多么感恩她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养大;告诉她我们以前做错了,请妈妈原谅;告诉她我们会不离不弃地好好照顾她,凡事都和她商量,不会再逼迫她做任何一件她不想做的事情。”
访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擦眼泪的纸巾用去了半盒,女儿轻松了很多,她很感恩我们的专业支持,帮助她找到了之前的误区,也让她变得有力量了。我们叮嘱她一定要在妈妈生命最后的这段时间好好沟通,共同完成道歉、道谢、道爱、道别,如有需要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帮忙。女儿在千恩万谢中离开了咨询室。
在这之后的几天,经常会看到女儿在病床旁边和妈妈聊天,说到有意思的事情时两人会笑出声来,家庭气氛变得柔和温暖,儿子也尽可能地请假陪伴在妈妈身边。多么温馨的一家人啊!有一天在走廊遇到女儿,她告诉我:“妈妈现在很平静,也很满足,我们按照她的想法帮她准备了寿衣,请亲戚帮忙挑选墓地,对家里的钱、房产和对卧病在床的爸爸也都作了交代,她还嘱咐我一定要经常去单位看看,我们姐弟不上班也改变不了结局。您说我能去单位吗?”
我告诉她,照顾者需要有短暂的休息,适当放松一下,而不是成天紧绷着机械看护,时间久了就会耗竭,不但帮不了妈妈,还会增加她的精神负担。妈妈的想法是对的,她很有智慧。
女儿说她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有时候放手也是爱,自己现在的状况是妈妈不想看到的,她会和弟弟商量轮流去单位上班,调整好状态,这样才能让妈妈放心。
三天后我去查房,进门时看到儿子正在为妈妈洗脸,儿子的动作很轻柔,像在照顾年幼的孩子,母子俩还时不时温柔地对望一下。在窗外暖暖的阳光映衬下,画面是那样的温馨和谐,让人心里暖暖的。病人说自己越来越平静,尽管有过自杀行为,但相信死后也会到天堂的,因为她有一双好儿女,有这么好的照护团队,大家会把她平安地送到那里的,她一点儿也不害怕,很欣慰自己没有像案板上的肉一样任人宰割。她唯一的遗憾是不能和卧病在床的老伴儿当面道别,好在每天都会和老伴儿视频交流,该说的话、该交代的事情也都了结了,她可以安心上路了。她很感谢这段时间我们对她儿女的疏导和专业支持,他们一家人都不再彼此猜忌、埋怨,也不会自责。她觉得捆在自己心里的绳索被渐渐打开,如果那天真的走了,就无法看到儿女们的成长,更不可能感受到获得精神自由的那种愉悦和惊喜了,这种如获新生的感觉让她不再绝望,获得了真正的尊严。
两周后,病人陷入了昏迷,在儿女的悉心照料中平静地离开了。家人在有条不紊地处理后事,儿女在低声啜泣,虽然很悲伤,但感受不到压抑。
患者去世一周后,她女儿来病房找我,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感恩我们在妈妈生命的最后时光给予他们全家人的爱与支持,帮助他们度过了整个家庭最艰难的阶段。她说妈妈走后她感到心中很痛,但并没有被压倒,因为她已经在妈妈离世前完成了道爱、道歉和道谢,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勇气抓住最后的时机和妈妈说再见。她说她会在今后的每一个忌日都告诉妈妈,她是多么想念她,多么爱她,她会好好活着,让妈妈放心,她会教导自己的孩子不要重蹈覆辙,只有还生命以自由,生命才能获得尊严。
这才是最好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