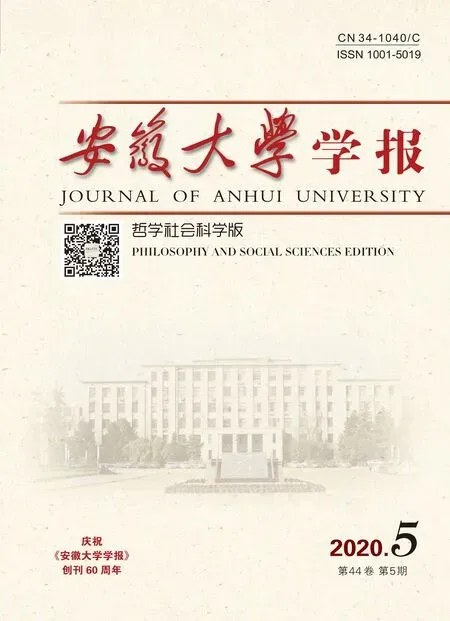清代徽州的基层科举参与和社会流动
——以道光休宁县王百龄府试讼案为中心
叶 鹏
科举作为明清时期社会性统一考试,在阶层流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本文在此仅举何炳棣、艾尔曼二位学者的思考代表两类主流观点,相关学术史梳理可见张天虹《“走出科举”:七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流动研究的再思考》,《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何炳棣等学者认为科举制极富竞争性,有效促进了古代中国的社会流动(2)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255-266; 中译本见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注,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第317页。;艾尔曼等则以为科举带有极强的精英主义色彩,参加考试需较高的文化水平与应试技巧,并要求有长期稳定的经济投入,阻碍了社会底层向上流动,在社会上层、下层内部各自形成了一种循环(Circulation)(3)Benjamin A. Elman,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0, No.1, 1991, pp.7-28; Benjamin A. Elman, “The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400-1900”,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Vol.8, No.1, 2013, pp.32-50; Benjamin A. Elman, Civil Examinations and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95-125.。但由于各地区之间社会阶层关系的差异,科举引发社会流动的形式、状态、程度也会呈现出不同特色,因而有必要将基层科举考试落实到具体地域中予以考察。
社会各阶层如何参加科举,能够很好地反映地方社会的阶层面貌及相互关系。参与科举分为训练、报考、应试等多个环节,其中报考是关键一步,这一过程中势必会将部分人群排除在外,谁能参加考试便决定了谁能有机会成为科举精英。通过复原科举报考环节,我们能够对地方社会的科举参与有更深刻的认识。幸运的是,新近出版的民间文献为此提供了丰富资料。
《清道光休宁县王栋县试讼案文抄》(下文简称《讼案》)抄本1册,共69面,原无题名,现题为文献整理者所拟(4)《清道光休宁县王栋县试讼案文抄》,王振忠主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29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9~187页。分卷编者将此文献定名“县试讼案”似乎不够准确。按清代科举童试分为县试、府试、院试三层,涉事童生王百龄已参加县试,考中第177名,夏友春、刘炜等人阻止的是其参加府试,整个诉讼也都围绕王百龄能否参加府试、如何补考府试展开,故而称为“府试讼案”较为确切。。根据用词来看,该文献很可能出自休宁县衙的记录,其内容主要反映了道光九年(1829)前后,休宁童生王百龄参加府试受阻,其父王栋与阻拦者之间的诉讼。本文即以解读这一文献为核心,复原讼案前后经过,参照类似案例描绘清中后期徽州的社会阶层关系,并希望讨论社会关系如何具体影响科举应试资格的获得。
一、廪保、冒籍与徽州科举社会
由于清代实行严格的定额入学制度,每一官学能够录取的生员数量极为有限,这便意味着对功名的竞争十分激烈。尤其是文风昌盛之地,数千人应试的场面屡见不鲜。福建沿海的兴化府、泉州府便曾出现过万人应试的奇特场景,虽然当时府试连开多场,其中应有许多改名换姓以期多次应试之人,但应试风气之盛是毋庸置疑的(5)(清)冯钤:《奏陈闽省考试情形请特加清厘以肃体制折》,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辑,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第74页。。
若想限制参与科举的人数,在报考环节以一定标准进行初筛是极佳选择。按清代规制,得以报考者,不仅要户籍明确,且需身家清白,无“刑丧过犯”,出身并非“倡优隶卒”或奴仆。但问题在于,清王朝其实无法实现对每个人有效的户籍管控,也就无从要求童生应试时提供具有唯一性的身份证明进行核验,因而只能寄希望于依靠中间人证明报考者具有相应的应试资格。《讼案》中休宁县官称,“捐纳身家清白与否,一凭族邻甘结为据”,也就是说,身家清白必须依靠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人为担保来证明。除了“族邻”担保、童生互保之外,最重要的担保形式还是当地廪生保结(6)(清)素尔纳等纂:《钦定学政全书》卷22《童试事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第29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371~372页。。《清稗类钞》中《廪生保童生》一条便强调了廪保在核查身份中的重要作用:“如孩童有身家不清、匿三年丧冒考以及跨考者,惟廪保是问;有顶名枪替、怀挟传递各弊者,惟廪保是问;甚至有曳白割卷、犯场规违功令者,亦惟廪保是问。”(7)(清)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99页。廪保责任之重毋庸置疑,将其视为科举资格核验的核心环节亦不为过。廪生往往在地方上颇有名望,作保过程中又难免受各方因素影响,概述式梳理未能展示相关制度运作的复杂性(8)李世愉、胡平:《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22页。,所幸已有部分案例生动呈现了清代科举报考资格的核验机制。
由于报考需要明确的身份证明,科举报考纠纷多以冒籍为主题呈现出来,廪保则是其中核验身份最重要的手段。土客间利益纠葛甚多,尤其是客民挤占本地学额,极易引发冲突,以往研究多聚焦在这样的地域中,如赣西北(9)吕小鲜:《嘉庆朝江西万载县土棚学额纷争案》,《历史档案》1994年第1期。相关研究如谢宏维《棚民、土著与国家:以清中期江西万载县土棚学额纷争案为例》,《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郑锐达《移民、户籍与宗族:清代至民国期间江西袁州府地区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66~77页;杨歌《学额纷争、移民族群和法律实践:以嘉庆朝广东新安县和江西万载县为例》,《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珠三角(10)[日]片山剛:《清代乾隆年間における科挙受験資格·戸籍·同族:広東省の事例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第47巻第3号(1988年12月);[日]片山剛:《清代中期の広府人社会と客家人の移住——童試受験問題をめぐって》,山本英史編:《伝統中国の地域像》,東京: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0年,第167~205页;[日]片山剛:《広東人社会と客家人:一八世紀の国家と移住民》,塚田誠之、瀬川昌久、横山広子編:《流動する民族:中国南部の移住とエスニシティ》,東京:平凡社,2001年,第41~62页。。论者所关心的议题在于土著与客民间对有限文化资源分配的行为逻辑。童生入学既然须廪生保结,在客民到来之前当地廪生势必均为土著,那么假使存在土客矛盾,土著廪生当然不会乐于为客民童生担保。从处理的结果来看,万载县另设棚民学额,令棚民童生“自相互保”,而无须土著廪生保结(11)(清)恭阿拉等纂:《钦定学政全书》卷41《寄籍入学》,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335册,海口:海口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41页上、第344页下。。珠三角地区则是在江门以南单独设立赤溪厅以安置客民,同时在广州府学内划出2名学额专供客民入学,亦无须原廪作保,待将来有客民廪生之后再归廪生保结(12)此案载于光绪年间重修的《学政全书》稿之中,可参见清代官修《学政全书》,台北:广文书局,1974年影印本,第576页。。此述两例基本上是通过专设学额、绕开原有廪保的办法来解决客民入学问题。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台湾。当地在清代吸引了大量闽粤移民,先至的闽籍移民被视为土著,独占入学资格,后至的粤籍移民便被视为客民。此题相关著述不少(13)孔未名:《清代台湾粤籍举人的由来》,《历史档案》2004年第2期;李文良:《学额、祖籍认同与地方社会——乾隆初年台湾粤籍生童增额录取案》,《台湾文献》2008年第3期;李祖基:《冒籍:清代台湾的科举移民》,《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蔡政道:《清代台湾科举中的“粤籍”与“粤籍举人”述论》,《台湾研究集刊》2019年第2期。,而重点考察廪保运作机制并做出精彩解析的,要首推林淑美的研究(14)林淑美:《清代台湾移住民社会と童試受験問題》,《史学雑誌》第111巻第7号(2002年7月);《18世紀後半の台湾移住民社会と童試不法受験事件:受験の諸条件と廩保》,《東洋学報》第86巻第3号(2005年12月)。俱收入林淑美《清代台湾移住民社会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7年,第67~132页。。她根据台湾入学资格被“闽人”垄断,“粤人”长期无法入学的情况,指出在传统中国社会,由于身份证明体系的不完善,保结式主观核验的制度漏洞极易被人利用,导致身份核查出现偏向,甚至被地方上某一群人把持。
上述三例均着眼于土客矛盾,而在缺少外来移民的地域中是否仍会有这样的身份分化呢?答案便是科举报考舞弊的另一个侧面——冒贱为良。
20世纪90年代初经君健对于科举身份“以贱冒良”的研究堪称经典(15)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6~252页。。他梳理了堕民、丐户、渔户、疍户、乐户等冒充良民参与科举的情况,最后还谈到了清代五次开豁皖南佃仆的条例,基本理清了开豁世仆的历史脉络,提示了清代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放松的趋势。其后,刘希伟也对冒籍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清代“贱民”等级的应试权益发生了从“基本缺失”到“有限改良”的变化(16)刘希伟:《清代科举冒籍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8~203页。。而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则从地域社会秩序及观念史的角度阐发了对“贱民”应试的理解,认为其实在明代末年贱民入学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太大震动(17)[日]岸本美緒:《明清時代の身分感覚》,[日]森正夫等編:《明清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7年,第403~427页。。但她着重强调了雍正帝身份政策改革对于社会秩序的影响(18)[日]岸本美緒:《雍正帝の身分政策と国家體制——雍正五年の諸改革を中心に》,中国史学会編:《中国の歷史世界——統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発展》,東京:東京都立大学出版会,第269~300页。,明确提出职业是否具有“服役性”是能否获得捐考资格的重要标准,即获得捐考资格的人在道德层面上具有较高地位,与服役性职业的卑贱身份是相斥的(19)[日]岸本美緒:《清代における「賤」の観念:冒捐冒考問題を中心に》,《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44册(2003年12月);[日]岸本美绪:《冒捐冒考诉讼与清代地方社会》,邱澎生、陈熙远主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利与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委员会、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第145~173页。。
上文综述式地梳理了学界相关讨论,可以发现,无论是地域身份层面还是社会身份层面,科举应试资格的获得虽有统一标准,但追求客观的身份凭证最终只能通过主观的人为担保实现,为廪保舞弊提供了上下其手的空间。上述几案的分析均称精彩,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徽州地方文献颇丰且长期存在佃仆制度(或称“大小姓”)(20)早先学界关于佃仆制的研究已有详细梳理,此不赘述,见邹怡《徽州佃仆制研究综述》,《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王振忠《徽学研究入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近十余年来,对佃仆制的研究更加注重社会史脉络下大小姓的利益纠葛,以更为中性的大姓、小姓之称来取代具有明确从属关系的“主仆”一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在于,文献之中大小姓各自的历史书写、家世建构,让研究者难以判断彼此是否确有人身依附关系,因而不妨用更为持中的词语来表示二者的社会地位差异。陈瑞:《清代徽州境内大、小族对保甲组织主导权的争夺——以乾隆年间休宁县西乡十二都三图渠口分保案为例》,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学》第7卷,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115~130页;黄忠鑫:《清代徽州边缘村落的大小姓纷争——以〈跳梁记事〉为中心》,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学》第8卷,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240~251页;冯剑辉:《明代徽州“义男”新探——以嘉靖祁门主仆互控案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郑小春:《谱牒纷争所见明清徽州小姓与望族的冲突》,《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在这样特殊的地域社会中,不同阶层如何参与科举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21)以往研究明清时期徽州科举多在梳理科第成绩,近年来论者逐渐关注到了科举地域专经、宾兴、会馆、文会等话题,蔚为科举社会史研究之一大观,但对佃仆科举的讨论仍属寥寥。见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陈瑞《制度设计与多维互动:清道光年间徽州振兴科考的一次尝试——以〈绩溪捐助宾兴盘费规条〉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05年第5期;王丽君《清代徽州进士与徽州社会》,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丁修真《明代科举地理现象的再认识——以徽州府科举群体为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张小坡《明清徽州科举会馆的运作及其近代转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张小坡《清代徽州文会运作及其科举功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刘道胜《明清徽州乡村文会与地方社会——以〈鼎元文会同志录〉为中心内》,《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丁修真《兴衰倏忽:宋明时期徽州科举地理的演变——以〈春秋〉专经为视角》,《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丁修真《“小地方”的科举社会史:明代祁门科举盛衰考论》,《史学集刊》2019年第5期;孙鹏鹏《清代徽州宾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以往研究未能涉足此地,民间文献的发掘则为我们考察徽州佃仆应试提供了便利。
传统徽州社会自宋元以降便极重视科举,有论者提出这与徽州宗族发展及当地社会流动率较高所导致的不安感有关,科举近乎成为塑造地域社会秩序的主要途径(22)朱开宇:《科举社会、地域秩序与宗族发展——宋明间的徽州,1100—1644》,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4年,第385~394页。。经历了元代军功家族的短暂崛起后,明朝初年,被中断的科举秩序重新建立,在礼法、祀典多重影响下,伴随着符合理学规范的宗族先后成形,一个不同于宋代气质的科举社会又出现在徽州大地(23)章毅:《理学、士绅和宗族:宋明时代徽州的文化与社会》,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22~226页。。明清时期,徽州科举依然繁盛,但随着科举录取名额逐渐固定化,地方上对功名的争夺愈发激烈。“入学乃进身之始”(24)(清)素尔纳等纂:《钦定学政全书》卷22《童试事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第293册,第371页。,按清代规制,休宁县学学额共20名,廪生、增生各20名,两年一贡(25)(清)素尔纳等纂:《钦定学政全书》卷47《安徽学额》,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第293册,第880页。。其中学额指的是每次童试取进县学的附学生员人数,而廪增则指县学中总体供养的生员定额,这也就意味着,每次科考全县数百人应试要争夺的是区区20名入学定额,其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徽州府各县的科举水平差距极大,考取进士近半数都来自附郭县歙县,休宁稍弱也接近20%。据道光《休宁县志》所记,在道光朝之前的休宁进士,寄籍外地考取的有120余人,休宁本地考取的有70人左右(26)道光《休宁县志》卷9《选举》,《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150页下~155页上。。然而自嘉道以降,休宁文风渐不如前,嘉庆五年(1800)后,“三科秋闱竟无一报捷者”(27)(清)汪滋畹:《增捐乡试旅费记》,道光《休宁县志》卷22《艺文·纪述》,《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2册,第643页下~644页上。。面对科举成绩不佳而佃仆纷纷出户、要求应试的局面,地方社会中对于科举文风不兴的焦虑感势必被进一步放大。王百龄报考府试被阻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二、《讼案》所见王百龄府试纷争之经过
王百龄府试讼案的有关人员大致分为三个群体,分别为小姓王氏家族、大姓汪氏家族及其他牵涉其中的休宁生员。王氏家族一方,有童生王百龄,其父王栋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捐监,居休宁城厚街,一都八图立户。祖父王荣锡、曾祖王学佳分别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三十九年(1774)捐职,此外尚有其姑父休宁县廪生汪卿云参与此案。汪氏家族一方主要以汪明扬为代表,七都一图二甲立户,族居南坑。该家族成员汪克明在道光元年(1821)入休宁县学,是此案书写议墨之人。另外,王百龄县试廪保戴锡淳,为王栋邻居,立户于西乡十三都四图,阻考人夏友春、刘炜均系休宁县学生员。
道光九年三月十三日,家住休宁城厚街的监生王栋向休宁县学控诉,称其子王百龄欲参加当年童试,曾求邻居廪生戴锡淳作保,王百龄因而参加了当年县试并考得第177名,随之要继续投靠府试时,戴锡淳却忽然变卦,不再作保,致其未能及时考试。王百龄尚未弱冠,“无刑无丧”,而以上三代,曾祖王学佳曾照例捐职,祖父王荣锡曾“充案下库吏”并亦有捐职,父亲王栋则有捐监。也就是说,王百龄祖上三代皆有捐纳,理应允许报考。王栋便颇为恼火地质疑:“生祖、父及生既可报捐于昔日,而生子又何不可应试乎?”确实,按清代规制,无论是何出身,只要放出三代之后便允许一体报考应试。
那么,戴锡淳为何不再作保呢?据戴供称,其之所以没有在府试时作保,主要是由于此前生员夏友春、刘炜两人出面阻拦。他们宣称王栋并非土著,尚未入籍,且王家一无支脉,二无房族,王百龄是否休宁户籍、是否身家清白均有疑点。令戴锡淳更添顾忌的是,三月初九府试开考前,府衙门外“众廪保纷纷物议”,甚至有“揭帖内载冒昧应试等情”,由于无法承担如此巨大的舆论压力,戴锡淳最终选择“结单不押”,即便王百龄已前往府衙报到,仍不予担保。在王栋初次呈控半个月后,三月廿九日,徽州府批示,王百龄既已查明“三代报捐职监确凿,并无刑丧过犯”,且已参加县试,允许其补考府试。可惜,王百龄却在四月初三忽患寒症,无法动身。王栋愤而继续呈控,要求查清事实真相,严惩阻考之人。
阻拦王百龄应试的夏友春、刘炜两人均住休宁城内,“朝传即可刻至”,但却迟迟没有出现,直到王栋初次呈控三个多月之后,六月廿八日,夏友春方才到案。在府衙中,夏友春讲述了一个王栋“匿议掯捐”的故事,按其说法,休宁生员们本不同意王栋报考,只因汪卿云声称王栋愿意捐输1500两银,而勉强允许其入籍。这里提到的汪卿云是王栋妹夫、县学生员,徽州府多次要求其到案说明情况,但又过了一个半月,到八月初十,汪卿云方才来到县学。从他的口中,我们听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据汪卿云说,夏友春之所以百般阻挠,实意在敲诈王栋。有意思的是,两人供词中的时间节点有所出入。按夏友春所言,四月初六汪卿云即召集在城绅士于海阳书院讨论王栋入籍之事,至四月初八双方才达成妥协,打算四月初九日再次前往县衙商议,却不想王栋突然反悔;而据汪卿云所言,四月初六日只是海阳书院路师台提议请王栋捐资助学,四月初七朱子诞辰才向诸生说明情况,此时夏友春觊觎王栋家财,要求“公私两尽”,最终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此事不了了之。
其实,不论是夏友春还是汪卿云都选择性地忽略了对自己不利的内容,只陈述了部分实情。实际的情况是,四月初,生员们在海阳书院读书后谈起书院膏火不敷,又听说汪卿云姐夫王栋资产颇丰,于是让汪克明执笔写下一份捐输底稿,希望由汪卿云出面劝说王栋捐银生息,以助膏火。但王栋因其子应试被阻,心存怨意,不愿捐资,此事便最终作罢,汪卿云叫汪克明将手稿烧毁了事。
本来案件到此即可结束,本着息事宁人的精神,允许王百龄补考,再对夏友春等人予以斥责便可了事。但数月后,夏友春又前往府衙控告王栋,据称,休宁邑绅汪声在赴宿松县教谕之任前便在王栋家中看到过捐银合同,也就是说,王栋实际上是允诺过捐银的,只是后来王百龄无法应试,遂想赖账。同时,刘炜邀同生员汪克明投词呈控王栋冒籍,称王家乃是汪氏佃仆,有“仆人宗簿”为证,不料汪克明得王栋贿赂,当堂翻供,声称王栋是自家亲眷而非仆人。汪克明族人汪明扬等亦到县作证,称汪克明素行不法,不但在服丧期内生子,还对长辈多有不敬,指认其作伪证。为证明王栋家族确系佃仆,汪家拿出了一份雍正九年(1731)的官府判牍:
休宁县七都一图南溪地方汪世德、世恩支丁汪文易、汪景文、汪象民、汪汝公呈控逆仆王干寿、王大德、王顺德、王喜凤、王保、王三元叛主抗役一案。今奉县主正堂加三级青天丁老爷审结,赏立金参铁案。审得王干寿、大德等远祖,其为汪文易等二房仆人,已历数百年于兹矣。至雍正五(年)以后,干寿等抗不服役,经文易等二控前任未结,今本县庭讯之下,文易等将干寿、大德各家住屋、葬山字号土名开列甚明,且执伊等祖父甘约领状为据。干寿等止称赁地造屋,不能持出所葬何山,确有文契、户税可凭,而所有者惟是康熙五十三年买地一契,岂可以抵塞。当经责惩,着令照常服役。取各遵依附卷立案。
雍正九年 月 日
这里的王干寿即王栋曾祖,王三元又名王学佳即王栋祖父。雍正五年(1727)首次开豁世仆,而此处王姓出户是在雍正九年,似乎暗示这是在开豁世仆令影响下的一起佃仆逃役纠纷。此处汪家既有住屋、坟山证明,又有“甘约领状”也就是应役文书为凭,官府判决自然要求王姓继续服役。但是,倘若这一判决真实存在,且发生了效力的话,又怎么会出现四十余年后王学佳捐职的情况呢?休宁知县对此也大表质疑,认为汪姓将王学佳指认为王三元是故意诬陷,“不思报捐与考试并无二致”,并批:
如果王学佳即系王三元,现在老幼皆(知)。王学佳于乾隆三十九年捐职时,去雍正九年不过四十余年,迁居地方相离不过三十余里,逃后尚且不依,何以竟听捐职,并无一人呈控?王栋报捐较迟,姑且不论,王荣锡亦系乾隆间所捐,且未捐之先,曾充本县库吏,有粮之家,谁不认识?何以亦无人出控耶?迄今时隔百载,姑行控反,原卷无从检查,无印县谳,亦难足据,此外毫无指证,谁其信之。
可见当地县官的处理思路是十分清晰的,王姓三代捐纳时均未有人阻拦,很难设想真如汪姓所言王姓的佃仆身份“阖族老幼皆知”。更为重要的是,被汪姓当作铁证的雍正九年堂断并无官府盖印,难辨真伪。至次年春,即道光十年(1830)二月,诉讼依然未结,汪姓迟迟未到县听讯,《讼案》所载到此为止。
此案最终审判结果如何,我们已不得而知。但在《清道光休宁县学生员大课膏火簿》中仍见到了戴锡淳的名字(28)《清道光休宁县学生员大课膏火簿》,王振忠主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8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页、24页、28页、38页。,这份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二十四年间休宁县生员的点名册既有其名,说明其并未被褫革。按《学政全书》所载,文武童生“倘有冒顶等弊,将该廪保照例黜革治罪”(29)(清)素尔纳等纂:《钦定学政全书》卷22《童试事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第293册,第376页。,这似乎可以反证王百龄应试合法,也与前述休宁县判语明显的倾向性相吻合了。
综观《讼案》,汪姓诉王姓为其佃仆可谓证据不足,王姓要自证清白也颇为费力。王栋始终只能空喊“考捐只论三代清白,无论鼻祖远祧”,却不能提供更为直接的族谱、契约等依据来证明身份,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他对自家出身的不自信。据刘炜供,王栋曾自称其族来自休宁洽阳,但洽阳王姓不认其亲,王栋随之又“诈称”出自涨山王氏,亦无法证实,因而刘炜认为王栋并无宗族可依,根本不是土著。曾有论者提出,徽州小姓常以攀附先世或是与当地同姓大族通谱的手段提高自身地位(30)王振忠:《大、小姓纷争与清代前期的徽州社会——以〈钦定三府世仆案卷〉抄本为中心》,《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以新发现的民间珍稀文献为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9~137页。。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王栋所谓自己出身洽阳、涨山可能只是一种攀附行为。再查《休宁名族志》,洽阳即合阳,在邑东三十五里,该地王姓自歙县王村分出,南宋绍兴间迁入;涨山则在邑东十里,自祁门迁入。而汪氏居七都一图南溪,乃自南宋嘉定七年自渠口迁入(31)(明)曹嗣轩:《休宁名族志》,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638页、635页、236~237页。,方位在休宁县城西北。王栋自称的族人居地与汪氏居地完全是两个方向,或许也有刻意逃避关联的用意。
囿于材料不足,很难确证汪、王两姓是否真的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但根据两家族显著的规模差异,将其归为大小姓冲突应是合理的。我们自然不应事先就对王栋的身份有所预设,但不论其究竟是否为汪姓佃仆,被指控跳梁这件事情确实发生了。那么,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小姓或是业已出户的佃仆是否有资格参加科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一个童生是否能够顺利报考,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三、清代开豁世仆令与徽州佃仆应试
清代《学政全书》乃各省学政的工作指南,尤为侧重对基层科举考试的制度规定,其中言明凡“优娼隶卒之家”均不得报考(32)(清)素尔纳等纂:《钦定学政全书》卷22《童试事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第293册,第371~373页。。作为长期存在于徽州社会中的人身依附者,佃仆在科举考试中是几乎缺位的。据称,徽州社会中的主仆之分甚严,佃仆“即其家殷厚有赀,终不得列于大姓,或有冒与试者,攻之务去”(33)康熙《婺源县志》卷2《疆域·风俗》,《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稀见方志续编》第191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191页。,而“隶仆籍者不与通婚姻、不得应考试”的风气直到清末科举停废后方逐渐式微(34)民国《歙县志》卷1《舆地志·风土》,《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41页下。。显然,在科举这一实现社会流动、彰显社会地位的考试中,出户已久的佃仆仍难以得到平等待遇。
清王朝中央早已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在雍正五年四月颁旨开豁世仆(35)《清世宗实录》卷56,雍正五年四月癸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册,第863页下~864页上。,经三个多月的官文流转,当年七月这一旨意到达地方,并开始实施(36)与《清实录》相似的文字在雍正五年七月的婺源县官府文书中亦有呈现,可参见《告词》,清抄本,转引自王振忠《大、小姓纷争与清代前期的徽州社会——以〈钦定三府世仆案卷〉抄本为中心》,《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以新发现的民间珍稀文献为中心》,第121~122页。。但此时世仆开豁仍以应役文书为据,许多实际上业已出户的佃仆仍饱受欺压。相关规制在嘉庆年间出现变化,抄本《钦定三府世仆案卷》中载有嘉庆十年(1805)礼部尚书恭阿拉的一份奏议,可供我们了解当时佃仆报考的细节:
参酌旧例,嗣后安徽省徽州、宁国、池州三府细民,除仅佃田、住屋,并非典身、卖身者照旧开豁,仍准考试、报捐外,其有佃田主之田、葬田主之山,且与仆人通婚者,虽年久身契遗失,仍以世仆论,并不准充当地保、社长等差。如家主念其辛勤恭谨,准其赎身,情愿放出为民,令其先行报官,并咨部立案,俟其放出三代后所生子孙,许与平民一体考试、报捐,以示限制。(37)《钦定三府世仆案卷》,清抄本,转引自王振忠《大、小姓纷争与清代前期的徽州社会——以〈钦定三府世仆案卷〉抄本为中心》,《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以新发现的民间珍稀文献为中心》,第114页。
此处能够参与捐纳、科举的只有那些“仅佃田、住屋”而未卖身的人,倘若田地、坟山在主家且与仆人通婚者,仍需出户三代之后方可报捐报考(38)佚名《徽州典[佃]仆制与科举考试》一文谓其“在歙县资深藏家程振邦先生处”,见到一张嘉庆十年七月徽州府告示,文曰:“署江南徽州府正堂加三级记录三次邹为知照事……兹奉臬宪转奉抚宪,接准吏部覆转行到府,合就抄咨示谕,为此示仰府属军民人等知悉,遵奉部议,嗣后细民除仅佃田、住屋,并非佃身卖身者,照旧开豁,仍准考试、报捐外,其有佃田主之田,葬田主之山,且与仆人通婚者,虽年久身契遗失,仍以世仆论,并不准充当地保、社长等差。如家主念其辛勤恭谨,准其赎身,情愿放出为民,令其先行报官,并咨部立案,俟其放出三代后所生子孙,许与平民一体考试、报捐,以示限制。倘有妄行争控者,定行严加治罪,各宜凛遵毋违,特示!”http://www.66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07844&page=1&authorid=1242421.。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嘉庆十四年,据称当时有宁国县柳姓太学生被指为佃仆,然自称主家者却无法提供契据为证,亦未见有服役关系,所谓佃仆身份只因柳姓祖上附葬某姓之山而已,因而柳氏大吐苦水,称“今吾室小康,彼屡有乞求不遂,而以是诬”。时人高廷瑶亦评论道:“但借曾经葬山、佃田、住屋,即强抑为世仆,辄以分别良贱,挠其上进。彼被讦之家,户族蕃衍,未必尽系当日为奴者之嫡系,不能悉甘污贱,势将案牍纷争,日相修怨,其流弊伊于胡底?”(39)(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官箴书集成》第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26页。此案直接导致安徽巡抚董教增上奏开豁佃仆,当年年底议准,凡所谓世仆“统以现在是否服役为断”,倘若没有应役契约且并不服役者,“虽曾葬田主之山及佃田主之田,着一体开豁为良,以清流品”(40)《清仁宗实录》卷223,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庚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3册,第1009页。。自此,开豁世仆完成了从文契为据到现时服役为据的转变,也就为佃仆出户后的身份合法化提供了保证。但即便有官方规制为据,徽州佃仆参与科举之路仍充满坎坷。王百龄府试受阻时在道光年间,距嘉庆开豁尚近,直至清末徽州当地仍有阻碍佃仆报考之事。
清末民初的婺源商人詹鸣铎,光绪九年(1883)生于婺源庐坑,所著《我之小史》以自传体小说的形式记录了自身经历,文献价值较高,具有较强的可信度(41)王振忠:《徽商章回体自传〈我之小史〉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史林》2006年第5期;朱万曙:《近代徽商自传小说〈我之小史〉的价值》,《江淮论坛》2012年第2期。。其中一段关于佃仆应试的故事,可资参考(42)(清)詹鸣铎:《我之小史》,王振忠、朱红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33~134页。整理者在出版时依照詹氏后人意愿对该书进行了删节,隐去佃仆姓氏,此处据原稿作了补充。:
詹姓原有九姓佃仆,张姓乃其中之一。据称道光年间“为行乡人傩的故事”,张姓有无礼犯上之举,因责罚过重,致张姓逃役出户。虽不再服役,但对詹姓仍较尊重,称“官娘”“先生”“老板”“先生娘”等等。后张姓势力渐长,订立乡约,又与当地大族通谱,逐渐不受管控。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志政、张守礼、张德和、张之纪四人一同报考休宁县学武试,被同考此科文试的詹姓族人发觉,于是往府控告,要求不得允考。但时值科举将停,且开豁世仆令早已有之,休宁县学教谕于是规劝他们称,“目下功令,二十年不服役,一例开复为良民”。詹鸣铎对此颇为不忿,质疑道,“照他口气,世仆二字要打消了?”仍是极为重视名存实亡的主仆关系。不久,张姓又寻到休宁县张员外诈称同宗。据民国《重修婺源县志》中记,此员外名张星照,乃休宁县城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江南乡试举人(43)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15《选举》,《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第313页下。。有了这样一位士绅出面,张姓报考资格似乎有所保证。最终徽州府判决各打五十大板,令双方均不得参加此次考试。旋即科举停废,此事遂不了了之。
我们不禁要问,为何詹姓一定要阻拦张姓应试?据詹鸣铎自称,婺源考武学之人不多,张姓若是应试,“射中一二箭,就要入泮,这还了得!”事后为首阻拦的蔚璠也感叹:“当日如非合扣,则他们考武易得,定先迎学,我辈无地自容了。”詹鸣铎随之解释道,阻考者以为自己学问有限,难以考取,与其坐视佃仆考中,不如同归于尽,也不吃亏。可见,众人之所以要阻止张姓投考,并非完全出于维护主仆名分的考量,更直接的原因是为了现实的个人声誉。同样,王栋即使是佃仆后人,其祖父时便不再服役,至王百龄业已三代,不论曾经的佃仆身份是否属实,都毫无理由阻拦王百龄应试。夏友春、刘炜等人之所以阻考,恐怕也并非如其所言一般大公无私,很可能正是要借机勒索,因此才爆发冲突。
讨论科举制度运作时,我们必须考虑其在地方社会的具体展开。不同于前人研究关注的土客冲突,徽州大小姓无疑都是土著。在蕴含着明确社会层级的徽州地方社会中,小姓报考常常需要面对大姓阻拦、刁难。有论者这样总结,清代中叶以后的社会一方面是“贱民”希望改变自身地位,另一方面是民间观念在道德上对“贱民”给予严苛的规范和限制(44)何淑宜:《岸本美绪教授“明清社会与身份感觉”演讲侧记》,《明代研究通讯》2003年第6期。。这恐怕也就是即便清王朝中央屡次开豁“贱民”,允许出户三代后可自由报捐报考,而地方上却迟迟缺乏响应的原因。民间观念、地方人际关系网络的代际传递使得对“贱民”的歧视根深蒂固,加之担忧科举名额被挤占、社会地位被超越,多重因素叠加造成的焦虑感更促使大姓千方百计阻止小姓应试。
四、结 论
正如前文曾总结的,冒籍分为地域属性、社会属性两种,王百龄府试讼案中阻考者先以地域身份非本地攻击王家,失败后再以社会身份为佃仆对王氏施加压力。相较而言,地域属性的冒籍纠纷较易化解,按照制度入籍者亦能见到不少实例(45)清抄本《郑三乐堂请入籍案簿》便记录了一场科举冒籍纠纷的经过。道光四年(1824),浙江兰溪的徽州移民后代郑绍文应童试时遭土著攻讦,以其冒籍,不予应试。其父呈告称,家族自顺治年间即迁兰溪,且数代坟茔坐落、粮税完纳均在当地,祖籍地歙县已无亲属往来。这一呈文逐级转递,在兰溪县、金华府、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各级均获通过,以其与例相符,最终准予入籍考试。相关文献可参见蔡予新《清代徽州人入籍兰溪事件——以〈郑三乐堂请入籍案簿〉为例》,《徽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而社会属性方面则难以取证,常常成为污蔑他人的工具。嘉庆十四年宁国柳姓太学生被指为仆一案提示我们,皖南小姓致富后,很可能遭遇讹诈、诬陷,而王栋家资甚殷,一次性便要“捐资千金”助学,阻考者或许真的希望在王栋身上敲诈一番亦未可知。更重要的是,通过此案梳理,徽州地方秩序与科举应试资格的获得机制已基本呈现出来。
明清徽州地方社会存在两条基本社会秩序脉络,一条是“士农工商”的普遍阶层差异,另一条则是地方独有的“主仆”关系,前者为表,后者为里,徽州早期的主仆地位往往表现于所从事的职业层面。通过上文阐发,我们已能体会清中后期徽州社会秩序的变动趋势。随着佃仆经济地位的改变,并加之清王朝多次颁布“开豁世仆令”,到十八、十九世纪,曾经的“主仆”名分已然松动,但以科举为纽带的“士农工商”秩序仍较稳固,出户佃仆依然希望通过科举“正途”实现真正的阶层跨越。王栋家族应是通过经商致富,至少在经济层面已不受打压,进而希望子孙取得功名,从而实现社会身份的蜕变,而大姓汪家等人担心的应是主仆关系变动对“士农工商”秩序的冲击。有论者指出,清代基层民众参与科举之目的更在“保身家”,实现向上流动倒是其次(46)蒋勤:《清代石仓阙氏的科举参与和文武之道》,《社会》2018年第5期。。在此我们暂不揣测徽州大姓阻考的具体目的,但其中有维持自身社会地位的考量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看到,以廪保为主要手段的科举身份核验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社会人际关系的影响,这便为大姓把控科举这一最为重要的社会流动渠道提供了便利。直到科举制废除后,依赖科举秩序的传统士绅结构发生松动,佃仆饱受歧视之风方才渐息。
由此观之,科举考试在某些时候并不如我们原先所想,是一种富有竞争性的考试,至少在获得报考资格的时候,地方人际关系有着重要影响。这就导致科举考试带来的社会流动更趋近于庇护性流动(Sponsored Mobility),也就是必须有熟人担保、具备某种先赋性的特征方可参加考试,而非纯粹的竞争性流动(Contest Mobility)(47)“庇护性流动”概念来自特纳(Ralph H. Turner)对英国教育制度的研究,其内涵是社会上层类似于一种俱乐部,向上流动者需要获得老成员襄助引荐,或是具备某种特定的“品质”(Quality)。Ralph H. Turner, “Sponsored and Contest Mobility and the School Syst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25, No.6, 1960, pp.855-867.。对于徽州而言,这种特征的分野在于社会身份是“主”还是“仆”;而对于上文提及的“土客”争端来说,则在于是“土著”还是“客民”,是“闽人”还是“粤人”。与艾尔曼强调社会上层对文化资源的垄断不同,笔者在此希望提示的是,科举运作中对报考者的限制不仅在于考试技巧层面,固有的地域社会秩序亦会对报考者进行筛选,造成事实上的阻碍。
附记:本文2019年12月先后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第十一届青年学者论坛、复旦大学史地所第四届禹贡青年沙龙年度会议上宣读,得到与会者指教,复旦大学邹怡老师、暨南大学黄忠鑫老师、上海师范大学戴昇博士给予了建设性意见,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