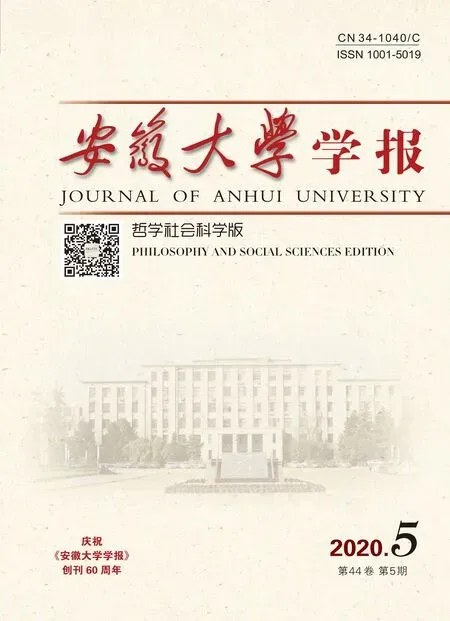从林黛玉到梅兰芳:现代红楼文化传播与鲁迅的文化理性
吕仕伟
学界对鲁迅与红学、鲁迅与梅兰芳的关系探讨可谓多矣。但值得重新注意的是,鲁迅与梅兰芳产生交集、交恶,此中的分歧源头实际在于各自不同形态的红楼文化阐释,对林黛玉形象的传播认同差异与大众文化思潮的流向引导尤其是此中问题的学理原点。梅兰芳显然以新编红楼戏特别是《黛玉葬花》引发了亿万中国大众的感性共识,但在鲁迅看来,“当鼓舞他们(群众)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1)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8页。,鲁迅显然是一位强调理性自觉的大众启蒙者。康德曾言:“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2)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41页。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探讨鲁迅如何在现代红楼文化传播中公开进行理性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一、书上的林黛玉与鲁迅的认知理性
理性思维在文学认知层面往往表现在主体会依据文学作品事实和文学理论逻辑做出文化判断,而印刷文化以降,对语词的强调往往使得文化接受者形成了线性的概念逻辑思维,阅读和书写赋予了读者理性识记的权利,在读与写的印刷媒介距离感中,往往形成相应的认知理性。
致力于将“本能的人”提升为“自觉的人”的鲁迅显然是一位理性思维者。鲁迅多浸淫在印刷文化中,尤其表现出对《红楼梦》,特别是对林黛玉文学形象的别样关注。作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红学阐释者之一,鲁迅的红楼文化理性首先表现在对书上的林黛玉及其社会影响的认知辨析中:鲁迅以切实的小说知识质询民国红楼文化的发生,洞见出《红楼梦》在民国社会文化语境下可能出现的文化意识形态内涵;鲁迅追问民国红楼文化阐释与《红楼梦》内在美学理想之间的差距,尤其在与诸种文学事件、文化潮流的离合中,展现了其思想中独有的文化理性品格。
第一,鲁迅往往以其小说史知识勘误民国小说研究出版物,对林黛玉在小说史中的形象流变进行知识理性指谬。
鲁迅最早提及林黛玉是在1924年1月28日发表于《晨报副刊》的《望勿“纠正”》中 。在此文中,鲁迅言及陶乐勤对《花月痕》石印本的胡乱纠正,指出陶乐勤在其新印版本中将“钗黛直是个子虚乌有,算不得什么……”一句中的“直”纠正为“真”,认为其错误纠正改变了小说的原意(3)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431页。。鲁迅在其后来的《中国小说史略》论及“清之狭邪小说”《花月痕》时又摘引此句。
在鲁迅看来,清代的狭邪小说是泛滥的《红楼梦》续作式人情小说的反拨,因道光之后的社会风尚再“不适于《红楼梦》笔意,故遂一变,即由叙男女杂沓之狭邪以发泄之”,因而《花月痕》这样的狭邪小说在内容上表现为“特以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而已”(4)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第271页。。正是从此种角度理解,“钗黛直是个子虚乌有,算不得什么”一句中的“直”字显示出狭邪小说“谈钗黛而生厌”的内容风尚,将“直”纠为“真”正是陶乐勤的误纠。鲁迅在《望勿“纠正”》中说:“印刷书本是美事,但若自己于意义不甚了然时,不可便以为是错的,而奋然‘加以纠正’,不如‘过而存之’或者倒是并不错。”(5)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432页。鲁迅的《望勿“纠正”》借狭邪小说的印本误纠显示了其追求知识确切的认知理性,这种认知理性正是基于林黛玉形象的小说史流变。
第二,鲁迅洞穿了小说《红楼梦》的社会认知价值,并以阶级话语质询“人性论”阐释与林黛玉形象之间的理论差距。
因为看出《红楼梦》在文化反思中的别样价值,鲁迅一直对《红楼梦》别有倾心,1925年8月3日鲁迅在《语丝》发表《论睁了眼看》,就特别谈及对《红楼梦》的倾心缘由。在鲁迅看来:“《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6)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253页。鲁迅认为正视社会的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而《红楼梦》中人们的终局“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可见鲁迅欣赏的正是曹雪芹文学创作中正视现实的勇气(7)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253页。。也正是因此,我们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在上海暨南大学的演讲中说对于“《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8)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第115页。。
鲁迅一直沉浸在静态的、能提供反思的林黛玉文学形象中,所以他在暨南大学的演讲中强调着“书上的人大概比实物好一点”,并觉得“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样高明”(9)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第115页。。区别于在舞台上塑造感性拟像林黛玉的梅兰芳,鲁迅是一位具备知识理性的文学行为者,以语言为中心的线性文本阅读、写作,加之知识接受过程中激荡的社会语境,使鲁迅成为具备理性反思精神、旨在现实启蒙的林黛玉阐释者。
同时,在鲁迅那里,文学并非鉴赏论层次那么简单:“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定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10)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第120页。三十年代的鲁迅接受了阶级论的观点,阶级论立场的文学阅读与文学实践真正使其“烧”在了社会中。
梁实秋曾作文《文学是有阶级的吗?》,以文学的人性论质疑文学的阶级论。在梁实秋看来,“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无产阶级的生活的苦痛固然值得描写,但是这苦痛如其真是深刻的必定不是属于一阶级的,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阶级的,例如,恋爱(我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的表现,可有阶级的分别吗?”(11)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的吗?》,《新月》1929年第2卷,第6~7页。鲁迅看到梁实秋的“恋爱无阶级”论后,借用《红楼梦》的人物质疑道:“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12)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第208页。鲁迅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在现代阶级社会中使用阶级论文学眼光是出于必然,可见三十年代的鲁迅更多以马列主义阶级论立场来看待《红楼梦》及林黛玉形象。鲁迅曾说:“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13)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第116页。“阶级”概念内含着更多社会本体论因子,使鲁迅对《红楼梦》做出更多社会本体论的思考。鲁迅以阶级论立场看到社会中林妹妹、焦大阶级分离对立的一面,“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显示了鲁迅独特的道德立场,对《红楼梦》人物的阶级论区分也构筑了鲁迅思想的文学认知理性维度。
第三,鲁迅反思了林黛玉形象在民国社会语境下的文化内涵,对林黛玉文学形象介入现代社会作出理性追问。
文学形象的接受过程往往是读者思想意识建构的过程,文学形象的社会流行显现了某种特定社会文化意识的生成。鲁迅曾在《看书琐记》中借着林黛玉形象的例子谈到文学的普遍性及其界限的问题,认为文学形象不会是永久的,文学会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14)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第560页。。正是因此,鲁迅观测到林黛玉形象在民国社会的传播引领着社会文化潮流,并对此做出自己的文化反思。
民国时代是鸳鸯蝴蝶派才子佳人小说流行的时代,而宝黛的爱情故事正是此类才子佳人小说的命题范式,《红楼梦》带来的文学命题介入、引领着民国时代的文化时尚潮流。鲁迅曾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谈及:“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角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15)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第348页。正是因此,鲁迅对《红楼梦》阅读带来的社会潮流异常敏感。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论及《红楼梦》与上海才子佳人式社会风气之间的关系:“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伤心、见月多病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处,样子很有些像《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16)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第298~299页。通过对宝黛形象的社会文化接受分析,鲁迅警惕着现代社会才子佳人思想意识的生成,呼吁小说阅读过程中读者自身的理性建设。可见鲁迅对林黛玉文学形象的接受中不仅有认知理性立场表达,书上的林黛玉形象更成为鲁迅理性审视社会文化的符号症候。
二、照片上的“林黛玉”与鲁迅的价值理性质询
理性思维不只表现为一种文学认知态度,理性更意味着一种关涉好坏的文学价值判断立场。而就文学生产来看,伴随着媒介技术的革新,文学经典形象在现代社会经受着视觉媒介的变形改造,图像媒介在现代社会赋予了传统文学形象新的文学价值。尤其是摄影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普及以来,经典文学形象通过摄影技术获得再生,文学经典人物借助摄影技术由文学形象变为照片拟像,再生的文学经典在与大众文化相互生成中再度经典化,人身拟像在大众传播中生成了新的文化潮流。应该说,从书籍印刷中的文字概念型形象到视觉技术映射的照片拟像,经典文学形象在媒介变形中产生了新的文学价值变量,基于不同文化媒介的文学审美价值差异也由此生成。而此中,言称红楼人物时表示“书上的人大概比实物好一点”的鲁迅正是文字概念形象与照片映射拟像的文学审美价值评估者。
可以看到的是,作为红楼文化经典人物,林黛玉形象尤其在民国社会经历着多种艺术媒介的形式改造,而此中梅兰芳的昆曲改编,特别是其《黛玉葬花》等红楼新戏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风靡一时。从国内大众文化风潮来看,随着梅兰芳红楼新戏的名声大噪,梅兰芳的旦妆照更是如杂志的封面女郎一般,在各大画报持续走红。由梅兰芳拟造的“照片上的林黛玉”一度成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京、上海两座大都市人们争相观看的时尚景观。
梅兰芳黛玉旦妆照的传播与流行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文化事件,尤其编码着大众的审美心理,照片上的梅兰芳也一度成为鲁迅审视中国大众文化发生、公开进行理性评判的重要文化案例。照片上的林黛玉与书上的林黛玉谁更美这一命题成为梅周公案的初始学理歧点。
第一,在现代视觉文化传播的社会语境下,梅兰芳以黛玉葬花等古装扮相将红楼文化的感性声色之美发挥到极致,梅兰芳尤其以其独特的人像性别阐释促成了现代视觉文化的大众流行热潮。
梅兰芳成为流行的视觉文化符号是值得玩味的。鲁迅曾言及梅兰芳在杭州的法会上与徐来、胡蝶等女明星同期同地表演歌剧,梅兰芳俨然与最流行的女明星有着同等的身份,梅兰芳的旦妆照以近乎画报女郎的效应引领着时尚文化潮流。但区别于画报女郎、电影明星,梅兰芳的旦妆照又并非仅传递美貌与身体的商业消费信息。梅兰芳的旦妆人像一方面是其个人的,其两性化的性别面孔吸引着性别消费的凝视;另一方面,梅兰芳的旦妆照具有重新编码传统文化、文学经典的价值,以其《黛玉葬花》照为例,林黛玉获得了一种新的视觉拟像形式,梅兰芳以他的身体赋予林黛玉受大众认可的形象。
作家徐訏回忆自己小时候时就谈到上海梅兰芳旦妆照的流行,在徐訏看来,“那时候要是来上海而不买一张梅兰芳旦装照相回去,那等于不买车票进车站一样的希奇。大概是不久以后,梅兰芳照相是做了小镜背面的点缀了;这些镜子是非常粗劣,价钱也非常便宜,这是在乡村闯门儿的货郎担上就可以便宜买到,所以那时在村妇们的梳头货里,这种镜子已成为一种流行性的时髦品”(17)徐訏:《梅兰芳论(上)》,《独立漫画》1935年第1期。。可见在徐訏那里,梅兰芳的旦妆照是一种大众文化不可缺失的消费影像,已经作为一种大众流行文化符号走进了大众的日常消费中。梅兰芳旦妆照增饰的廉价镜子都成为流行性的时髦品,可见梅兰芳创造的文化拟像已经成为民国社会大众审美心理的必需品、表达物。
第二,就鲁迅方面来看,正是照片上林黛玉的流行引起了鲁迅的警觉。鲁迅对梅兰芳的批判并非个人恩怨,鲁迅对梅兰芳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对其视觉拟像的价值评估。
1924年正是梅兰芳红楼戏及其衍生文化的火热期,鲁迅在此期间作《论照相之类》。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中呈现了照相技术在中国都市、乡村的接受状况,从照相行为的民俗反思到照片样式的文化凝视,鲁迅俨然一位中国现代社会摄影文化的观看者、反思者。以摄影文化为起点,鲁迅着眼于中国民众的视觉审美水平,透视中国现代社会视觉文化背后的审美价值问题,尤其以反讽方式揭露了民众的视觉蒙昧。在此中,鲁迅尤其将矛头指向了梅兰芳的黛玉葬花旦妆照,两度言及“盖出于不得已”“中国人实在有审美的眼睛”,鲁迅对梅兰芳黛玉扮相的价值评判显示了其思想理性的诸种面向。
在鲁迅看来,“盖出于不得已”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民众的视觉审美不得不与民国社会多变的政治环境联系在一起,文化的视觉审美不得不与政治的视觉审美并置。在鲁迅视野中,梅兰芳的“天女散花像”“黛玉葬花像”“确乎比那些缩小放大挂起挂倒的东西标致”,即此就足以证明中国人实有审美的眼睛(18)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195页。。鲁迅其实道明了在政治视觉审美中有一线文化视觉审美是难能可贵的。但又话锋一转说:“我在先只读过《红楼梦》,没有看见‘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时候,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为她该是一副瘦削的痨病脸,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个麻姑。”(19)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195页。鲁迅对梅兰芳麻姑式林黛玉扮相的嘲讽是其认知理性作用的结果,鲁迅曾用《红楼梦》举例时就说:“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见。”(20)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第560页。在鲁迅视野里,梅兰芳的林黛玉扮相并不符合《红楼梦》本来的林黛玉形象,也正是因此,在鲁迅看来“梅兰芳姜妙香扮的贾宝玉林黛玉并不怎样高明”。
第三,置身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大众流行文化思潮中去看待鲁迅对梅兰芳的批判,鲁迅对梅兰芳批判的着眼点在于大众对梅兰芳古装扮相的买账、追捧,乃至于盲目模仿,质询的是中国大众独立的审美能力。
实际上,梅兰芳对其红楼戏的改编、表演是非常精心的。一方面考虑观众的接受,如其所说:“《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反映了封建时代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由极盛渐趋灭亡的历史,多少年来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热爱熟知的作品。观众里面有不少人是熟读《红楼梦》的,如果演员不能把剧中人物的性格和内心活动作适当的描写,他们是不会满意的。”(21)梅兰芳:《梅兰芳全集》(第4卷),北京:北京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第322页。另一方面,梅兰芳尤其注意林黛玉的扮相,采取了极为精心的装扮,如其在服装上,葬花时上穿大襟软绸的短袄,下系软绸的长裙,腰里加上一条用软纱做的短的围裙,临上装的时候,把它折叠成的,外系丝带,两边还有玉佩;回房时外加软绸素帔,用五彩绣成八个团花,缀在帔上;在头面上:头上正面梳三个髻,上下叠成‘品’字形,旁边戴着翠花或珠花(22)梅兰芳:《梅兰芳全集》(第4卷),第322页。。如此精心的文化考虑与声色装扮,使大众对梅兰芳的旦妆扮相十分买账。但梅兰芳其实也意识到大众对红楼戏的追捧更多仅是出于扮相的新鲜,他在上海出演红楼戏时曾谈及:“其实上海的观众也还不是为了古装扮相和红楼新戏两种新鲜玩艺才哄起来的吗?”(23)梅兰芳:《梅兰芳全集》(第4卷),第324页。红楼新戏的古装扮相真正掀起的是古装模仿的大众流行文化热潮。
与梅兰芳对大众的疑虑相同,鲁迅对梅兰芳的批判正在于大众文化审美方面。诚如鲁迅所说:“然而只要一看那些继起的模仿者们的拟天女照相,都像小孩子穿了新衣服,拘束得怪可怜的苦相,也就会立刻悟出梅兰芳君之所以永久之故了,其眼睛和嘴唇,盖出于不得已,即此也就足以证明中国人实在有审美的眼睛。”(24)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195页。在鲁迅看来,梅兰芳以凸眼睛、厚嘴唇来扮林黛玉,是“出于不得已”的,但照相馆玻璃窗里高挂梅兰芳的“天女散花图”“黛玉葬花图”,大众在照相方面极力模仿梅兰芳式的《黛玉葬花》《天女散花》,拘束自己而作出照相时的“苦相”,大众东施效颦梅兰芳的古装扮相,实在并不是美的行为。
无论是戏剧观看还是照片凝视,乃至于照片模仿,民国社会大众对梅兰芳古装扮相的观看模仿行为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大众视觉流行文化的缩影。摄影能够制造出关于美的正典作品,摄影媒介能够制造美学经验,但当摄影制造出放大的消费影像后,影像亦开始决定并塑造规定的美的意识形态,拟像假设往往能制造美学权威,使社会群体丧失独立的理性思考能力。鲁迅对梅兰芳的林黛玉扮相的价值评估本身是一次关于美与真的关系辩证,从学理上来说,鲁迅并不是在质疑梅兰芳,鲁迅是在质疑照片上凸眼睛、厚嘴唇的梅兰芳是那个《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吗,鲁迅以文学价值理性质询的是国民到底有没有“审美的眼睛”。
三、梅兰芳红楼戏的感性共识与鲁迅的公共理性批判
应该说,出于昆曲表演经验,梅兰芳在戏剧议题、启蒙主题、文化受众、文化效果方面对中国戏曲有着独特的经验表达。而对于梅兰芳戏剧的社会接受来说,社会舆论对梅兰芳戏曲的话语建构与鲁迅对社会舆论的意识形态清理代表了中国戏曲艺术与社会公共意识达成沟通的重要环节。以此看来,梅兰芳如何使充满异趣的大众达成文化共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梅兰芳艺术又如何成为合理的公共文化议题,以梅兰芳戏剧为代表的中国戏剧艺术怎样获得合理的公共阐释,这些问题构成重审鲁迅、梅兰芳关系的重要方面。
其一,就梅兰芳的感性戏剧经验来说,梅兰芳借助昆曲媒介实现了红楼文化声色幻境的重现,有效推动了红楼文化的大众理解与接受并最终形成基于感性共识的红楼文化社会交往,这是鲁迅所忽视的。
在梅兰芳看来,“昆曲的词句深奥,观众不能普遍听懂,这是它最大的缺点。不过昆曲的身段,是复杂而美观的”(25)梅兰芳:《梅兰芳全集》(第4卷),第277页。,梅兰芳认为“艺术没有新旧的区别”,“我们要抛弃的是旧的糟粕部分,至于精华部分,不单是要保留下来,而且应该细细地分析它的优点,更进一步把它推陈出新地加以发挥,这才是艺术进展的正规”(26)梅兰芳:《梅兰芳全集》(第4卷),第277页。。正是因此,梅兰芳以视听形式的昆曲表达红楼一梦的情动主旨,昆曲式的视听艺术本身销蚀了阅读文化中《红楼梦》的审美距离,昆曲的《红楼梦》表达完全不给观众掩卷沉思的契机,其意在还原《红楼梦》本真冲动的梦境与幻觉;梅兰芳的红楼戏发展了以感官愉悦为唯一目的的程式表演和歌舞传统,红楼戏的编剧齐如山更帮助其明确了戏曲艺术“一切开口发声者皆为歌”“一切举动皆为舞”的认识;梅兰芳扮演的林黛玉、晴雯、袭人等角色本身表达出了语言无法表达的动心,他以视听的相似性模拟使《红楼梦》更接近人的感性欲望,建构了一种观看者与形象的拟像之间的可视关系,取得了受众与文学经典的可视性的辩证交流。作为表演者,梅兰芳通过昆曲形式构筑了《红楼梦》的“无我之境”,通过其独特的梅派艺术为观众构筑了一场戏剧幻境。
梅兰芳红楼戏的表现力却并不在鲁迅倾心的文学现实感方面,处于视听艺术中的梅兰芳显然已经通过昆曲这一媒介将鲁迅心中写实的小说《红楼梦》分散化、多元化,梅兰芳以其昆曲艺术在公共文化空间形成了基于听觉、视觉等审美感官且不涉功用的红楼文化感性共识。
其二,从社会文化交往来说,泰戈尔、萧伯纳的访华促使鲁迅、梅兰芳有了文化的交集,鲁迅会关注此间国内文化交流的社会话语表达,鲁迅保持着对这些文化时事的关注,尤其注重梅兰芳文化交流宣传中中国文化主体的话语表达,并对其作出文化观察。哈贝马斯、阿伦特等康德后继者更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从文学活动的公共性视角来理解理性,可以基于社会文化交往和政治文化实践来重新强调理性的文化规范维度。正是在此种意义上,鲁迅对梅兰芳的文化交往观察、对梅兰芳戏剧的意识形态清理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表达文化公共理性的重要案例。
在鲁迅有关泰戈尔、萧伯纳访华的话语中,都有伶界大王梅兰芳的身影,鲁迅在话语中流露着对梅兰芳的隐微不满。一方面,在泰戈尔访华时,鲁迅关注到: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然后够到陪坐祝寿地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对此,鲁迅不无嘲讽地说:“惟有这一位‘艺术家’的艺术,在中国是永久的。”(27)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195页。鲁迅对梅兰芳的男旦表演是否能代表中国艺术文化持保留意见态度。另一方面,在萧伯纳访华期间,鲁迅在致台静农的私人信件中说萧伯纳“与梅兰芳问答时,我是看见的,问尖而答愚,似乎不足艳称,不过中国多梅毒,其称之也亦无足怪”(28)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第375页。。鲁迅表达出在中西戏剧文化交流过程中,因梅兰芳未能精彩呈现中国戏剧文化话语的失望心态;鲁迅更将《文学》杂志将自己与梅兰芳在萧伯纳访华期间并称表示厌弃,特地作《给文学社信》对此加以正名。
而从政治文化实践来看,梅兰芳出访活动往往成为社会公共议题,公共话语与意识形态往往是同质同构的,鲁迅对梅兰芳的公开评价多以梅兰芳出国访问的公共舆论宣传为对象,鲁迅以其知识分子的理性眼光,展开对梅兰芳戏剧宣传话语的意识形态清理。
在对梅兰芳本人的公开定性上,鲁迅毫不掩饰,在鲁迅看来:“梅兰芳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29)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第453页。鲁迅称梅兰芳为博士显然隐含其访美受荣誉博士一事。在鲁迅的话语系统中,“文人之在京者近官,‘京派’是官的帮闲”,鲁迅正是在此种意义上称梅兰芳为“京派”。而事实也恰恰如此,如相关学者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苏关系的改善首先体现在绘画、电影、戏剧等文化领域,梅兰芳多作为官方文化代表出访国外,尤其是访苏行程促进了中苏关系的改善。
在梅兰芳访苏预备阶段,各大报刊对梅兰芳访苏有着程式性的话语宣传,鲁迅尤其关注梅兰芳访苏的话语宣传面向,并针对其中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公共批判。在《谁在没落》中,鲁迅观察到五月二十八日《大晚报》的梅兰芳访苏新闻宣传:“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鲁迅对新闻中的“象征主义”定位十分敏感,再一次出于认知理性,鲁迅辨别了中国戏曲动作程式与西方象征主义戏剧的区别,在鲁迅看来:“这是一个喜讯,值得我们高兴的。但我们当欣喜于‘发扬国光’之后,还应该沉静一下,想到以下的事实……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它除了白鼻梁表丑角,花脸表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那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深意义。”对这样的宣传程式话语,鲁迅是忧心的,他评价道:“这样的新闻倒令人觉得是‘象征主义作品’,它象征着他们的艺术的消亡。”(30)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第514-515页。
在梅兰芳的访苏公共宣传中,普遍将中国传统戏曲强行定位在西方象征主义的话语体系之内,鲁迅除了多次在自己的杂文中提醒中国戏剧艺术形式和象征主义的差别外,尤其注意到这种话语宣传背后的政治亲近意图。如在《拿来主义》中就不无反讽地说:“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31)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第39页。关于“象征主义”的用语,鲁迅有意揭底梅兰芳戏剧艺术沦为政治宣传工具的一面,于是才作出梅兰芳是“第三种人”的清醒论断:“梅兰芳先生却正在说中国戏是象征主义,剧本的字句要雅一点,他其实倒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也是一位‘第三种人’。”(32)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第612页。
鲁迅说梅兰芳是“第三种人”的原因正是他意识到在现代社会错综复杂的境遇中“为艺术而艺术”的不可能性,即使梅兰芳本人也未能脱离访苏的话语程式。鲁迅看出在梅兰芳访苏过程中,在宣传上用“象征主义”来强制阐释中国戏曲本身是中苏政治亲善意图的文化话语策略;鲁迅也看到,在宣传中用西方中心的“象征主义”话语来嵌套中国戏曲,政治意图压倒了文化交流的平等对话,暴露出本土文化宣传导向上的主体话语缺失问题。鲁迅对梅兰芳戏剧的意识形态清理出于其对本土文化话语理性建构的忧心,在亟须文化主体地位建构的当下,鲁迅的文化理性表达将为我们理性建构本土文化话语、重新认识民族艺术提供新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