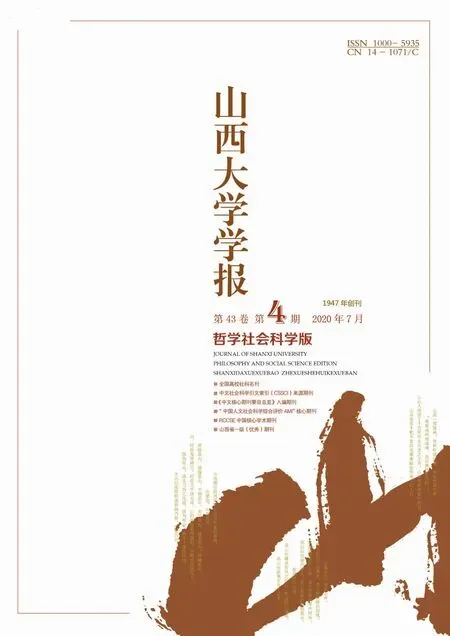神圣文本与以俗化俗
——“周元招亲”宝卷解读
姜剑云,尚丽新
(1.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2.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正德皇帝私行民间,俗称“正德游龙”或“正德微行”。今存最早的正德游龙故事是明万历年间的《嫖院记》。从万历直到民国,正德微行故事长盛不衰,相关的戏曲、小说、说唱、民间传说极为丰富。从宫廷到市井,从雅士到庶民,社会各阶层都参与了这一故事的虚构。华玮将清代民间流行的正德游龙故事的意义概括为:“清代民间舞台上的正德微行,在历史、政治、娱乐、伦理的交集中,呈现出复杂的艺术风貌,折射出清代文人与民间对皇权的想象、理解与期待,在艺术虚构中幽微地体现了清人情感与心理的真实。”[1]295其实这一论断也同样适用于晚明和民国。
正德游龙故事满足着不同阶层渴望物质、情感和权力的心理祈愿,它的主题是名利、风情、忠奸、颂圣、教化等的多元组合。如《嫖院记》的好货好色,《玉搔头》的至情追求,“游龙戏凤”的风情尽显,《玉殿缘》《落金扇》的忠奸与爱情的错落交织,《大明正德皇帝游江南传》《前明正德白牡丹传》的集大成等等。从万历到民国,正德游龙故事不断演变发展,其间受到时代变迁、社会阶层、流传地域、传播方式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周元招亲是正德游龙故事中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分枝。故事的中心内容是樵夫周元因用一只鸡款待正德而被赐婚赐官,轻松获得了荣华富贵。万历三十九年(1611)刊印的龚正我选辑的戏曲选本《摘锦奇音》卷五选录了明传奇《嫖院记》中的“出游投宿肖家庄”和“周元曹府招亲”两出[2]308,这是现存周元招亲故事的最早文本。此后,周元招亲或作为重要情节穿插于游龙故事中,或作为独立的故事单独发展。清初陈子玉《御殿圆》、蒲松龄《增补幸云曲》、道光年间刊刻的何梦梅《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同治年间重刊的吹竽先生《落金扇》、光绪年间刊刻的洪琮《前明正德白牡丹传》,这些戏曲、小说、说唱中都有周元招亲的情节。而在宝卷和一些地方戏中,周元招亲多是独立发展的。湘剧弹腔剧目[3]224、上海粤剧曲目[4]40中都有《周元招亲》。而“周元招亲”宝卷不仅版本众多,且极为独特。
一、周元招亲故事进入宝卷
与“正德游龙”相关的宝卷有三类。第一类是河西走廊的《正德白牡丹宝卷》,在方步和、谭蝉雪向车锡伦提供的田野调查中搜集的河西宝卷目录中有这部宝卷[5]267,但目前公开出版的河西宝卷中未见此卷,据题目来看此卷可能改编自晚清洪琮《前明正德白牡丹传》。此传敷演正德微服出游江南时发生的系列故事,周元故事只是其中的点缀。第二类是吴语区改编自弹词《落金扇》的《落金扇宝卷》。《落金扇》讲述书生周学文与小姐陆青云的爱情故事以及周学文等忠臣侠士与奸臣江彬的斗争,周元招亲故事被穿插其中。第三类是吴语区的专门演述周元招亲故事的宝卷,此类传世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正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著录演述周元招亲故事的宝卷有43种,名目极多,诸如《献龙袍宝卷》《呆中福宝卷》《周元招亲》《周元宝卷》《游龙宝卷》《游龙古典》《呆人得福》《樵夫遇圣宝卷》《周元招亲宝卷》《游龙戏凤宝卷》《正德游龙宝卷》《周玄宝卷》《天缘宝卷》等(1)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1394条《献龙袍宝卷》(又名《呆中福宝卷》《周元招亲》《周元宝卷》)著录抄本5种,1442条《游龙宝卷》(又名《游龙古典》《呆中福宝卷》《呆人得福》《樵夫遇圣宝卷》《周元招亲宝卷》)著录抄本29种,1443条《游龙戏凤宝卷》著录抄本1种、石印本1种,1516条《正德游龙宝卷》(一)著录石印本2种,1517条《正德游龙宝卷》(二)著录抄本2种,1536条《周玄宝卷》著录抄本2种,1088条《天缘宝卷》著录抄本1种。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332,343-344,344,362,362,366,264.。但内容大同小异,且文辞相近,各本中均有明显的吴方言特征。近年新出的宝卷书目又可增补不少,郭腊梅《苏州戏曲博物馆藏宝卷提要》(2)苏州戏曲博物馆共藏有10种游龙宝卷,《中国宝卷总目》遗漏2种。郭腊梅.苏州戏曲博物馆藏宝卷提要[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220-221.、吴瑞卿《傅惜华藏宝卷手抄本研究》(3)吴瑞卿《傅惜华藏宝卷手抄本研究》131条《正德游龙宝卷》著录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藏有7种,《中国宝卷总目》只著录1种,遗漏6种。吴瑞卿.傅惜华藏宝卷手抄本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8:304-307.二种书目可增入12种。近年出版排印本宝卷集《河阳宝卷》(《游龙卷》)[6]953-965、《中国常熟宝卷》(《滚龙宝卷》)[7]1889-1900中都有“周元招亲”宝卷。孔夫子旧书网上拍卖的抄本、石印本中亦有新出者,如石印本除《中国宝卷总目》著录的民国上海文益书局2种、惜阴书局1种之外,还有广记书局《正德游龙宝卷》《增像游龙戏凤宝卷》2种。加之很多图书馆的实际馆藏宝卷远超其早年编目。这样一来,“周元招亲”宝卷最保守的估计也有60种以上。
《中国宝卷总目》著录的最早的“周元招亲”宝卷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收藏的清同治三年(1864)抄本[8]332。在诸多抄本中,有30种有抄卷者的署名。一些抄本可以判断具体的产生地域。例如薛情表、王森逵、吴维淞、杨廷章是光绪或民国年间苏州地区的民间宣卷艺人[5]373-374,华绿绮是无锡人(4)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藏有22种由华绿绮抄写的卷本,从题记可知其为无锡人。华氏《献龙袍卷》抄于光绪十二年(1886)。,由此可知他们的抄本流行于苏州、无锡。再从近年出版的《河阳宝卷》《中国常熟宝卷》收有“周元招亲”宝卷可知其传播于张家港、常熟。“周元招亲”宝卷在吴语区的流行,与清代吴语区的正德游龙故事在各种文艺形式中的繁盛有密切关系。吴地的正德游龙故事不断在戏曲、小说、弹词中滋生,如清初李渔的《玉搔头》、陈子玉《御殿圆》、周稚廉的《元宝媒》、钱德苍编《缀白裘》中所收梆子腔民间小戏《戏凤》、嘉道年间黄治的《玉簪记》、何梦梅的《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同治年间重刻的吹竽先生的《绣像落金扇全传》,等等。面对如此丰富的资源,宝卷会做何种选择呢?嘉庆、道光以来,大量的俗文学故事被改编到宝卷中来。宝卷自身新编的故事很少,主要依靠改编。所以,对于世俗故事宝卷的研究来说,研究重心不在故事上而在故事的改编上。改编什么,怎么改编,是首先需要探讨的问题。面对吴地如此丰富的正德游龙故事的资源,宝卷是如何从中选择出周元招亲故事的呢?通过对“周元招亲”宝卷与吴地其他正德游龙相关文本的比勘,我们发现,“周元招亲”宝卷与陈子玉的传奇《御殿圆》和吹竽先生的南词《落金扇》中的周元招亲故事最为相近。《御殿圆》和《落金扇》构思相似,都是以才子佳人的爱情磨难为主线,以正德游龙为副线,展现爱情与政治的双重主题。陈子玉约1661年前后在世,吴县(今属苏州)人。《御殿圆》,又名《玉殿缘》《玉殿圆》《金銮殿》《金銮配》,国家图书馆藏有清抄本。吹竽先生生平不详,据《绣像落金扇》卷首序言“余自幼雅爱词曲,尤好南词,后随先君子历游楚、蜀、豫、粤任所,极一时丝弦檀牙之乐”可知,其酷爱弹词[9],游历多地。南词《落金扇》初刻于何时不可得知,今存最早的版本是同治癸酉(1873)重刻本。不过可以肯定,在《落金扇》刊刻之前,此剧已在民间流行。从清初到晚清,吴语区的周元招亲故事存在于传奇、弹词和地方戏中。客观上讲,宝卷若想从中改编是轻而易举的。《御殿圆》第二十四、二十五出和《绣像落金扇》卷三的“游龙”“赐配”“强婚”专写“周元招亲”故事,它们与宝卷中的“周元招亲”故事高度相似。三者的内容和情节基本相同,在文辞和细节上,宝卷与《御殿圆》更为接近。例如在“正德借宿”部分,二者的构思同出一辙:正德从周元口中得知朝中有刘瑾、焦阁老两个大奸臣,周元对这位京城来的客人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想象。宝卷在周元形象的设定上延续了《御殿圆》中“赋性痴顽,不知诗礼”的痴汉形象[10],同时又搬演了《落金扇》中周元入赘曹府时的各种滑稽事件。当然,三者的高度相似并不代表着宝卷直接改编自《御殿圆》和《落金扇》。一个流行故事会在不同的民间文艺形式中繁衍,彼此之间的借鉴模仿极为普遍,就像弹词、宝卷、锡剧、越剧中都有《落金扇》[11]290。这样看来,“周元招亲”宝卷对《御殿圆》和《落金扇》的改编,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更确切地说,它是整合了当地各种文艺中流行的周元故事而来的。
二、世俗故事的神圣演述
宝卷脱胎于佛教,是佛教化俗的产物,所以在文本形制、表演形式和流通传播上也极力模仿佛经。在民间,宝卷被等同于佛经,宣卷犹如讲经,传抄宝卷也如同流通佛经。抄卷、宣卷、传卷、藏卷都是功德。“民间的抄写宝卷与宣扬宝卷一样,都贯注着执行者对于宗教信仰的虔诚与热情,受到其极为庄重与认真的对待。”[12]51宝卷从产生之初就被视为神圣文本,在宗教宝卷时期作为宗教信仰的载体自然是神圣而崇高的。到了民间宝卷时期,大量的世俗故事经改编进入宝卷,这些世俗故事宝卷大多聚焦于家庭伦理、善恶报应上,与宗教教理、教义无涉,从文本内容来说,神圣性自然减弱了;而且,吴语区的部分宣卷人进入城市,成为职业艺人,他们的抄卷、宣卷活动带有明确的商业性,他们将宝卷视为谋生家当,秘不示人。尽管宝卷神圣文本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着,但它仍然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神圣性和积累功德的功能。个人或家族对待这些世俗故事宝卷的态度仍然是虔诚的,很多人的抄卷活动持续了大半生。无锡人华绿绮抄写了22种宝卷,他从光绪十二年(1886)21岁时开始抄写《献龙袍卷》,到1919年54岁抄写了《百鸟图宝卷》《洛阳桥》。常州、无锡之间的洛社镇的卫清泉从1938年到1954年抄写了31种宝卷。1938年抄写的《忠义宝卷》的题记云:“时值八一三,明年中日战争仍未和平,因此老人在家无事作消遣。幸老人精神强健,每日朝夕誊写,以作消遣也。年七十樵叟,诚不容易,阅者慎之乎!”[13]109这种“朝夕誊写”的执着,其实不会是单纯的“消遣”,必定有一种精神信仰的动力。
宗教宝卷和科仪卷天然属于神圣文本,民间宝卷时期产生的大量的故事宝卷仍然具有神圣文本的性质。依照故事主角的身份可以将故事宝卷分为神灵故事宝卷和凡人故事宝卷。神灵故事宝卷,例如靖江的圣卷,常熟的素卷、荤卷、冥卷,它们是演述当地主要神灵故事的宝卷;凡人故事宝卷,例如靖江的小卷(或称草卷)、常熟的闲卷,它们是根据其他讲唱文学(如弹词、鼓词等)唱本和通俗小说等改编的世俗故事宝卷。神灵故事宝卷自然是神圣文本,讲的是各路神灵修行得道的故事,最经典的如释迦牟尼成道的《雪山宝卷》和观音菩萨得道的《香山宝卷》。不过,大多数的神灵故事宝卷会使用凡人受难的模式,甚至将一些世俗的家庭伦理故事、民间传说稍做改编就升格成神的故事,例如靖江宝卷中《土地宝卷》改编自张世登一家人悲欢离合的俗文学故事,最后张士登变成了土地神;常州的《天库财神宝卷》改编自《警世通言》之“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宋小官摇身变作天库财神。这类世俗故事文本升格成神圣文本的情况并不仅见于宝卷,那些从民间信仰里发育出来的民间文艺,诸如宝卷、香火戏、童子戏、皮影戏等,习惯用流行的世俗故事来表达信仰。像江流儿的故事、刘全进瓜的故事均发展成强大的信仰文本。普通的世俗故事宝卷则套用修行模式、神灵救助模式,凡人在神灵的救渡下,经过虔诚的修行最终升入仙班,在修行成神这一点上世俗故事是向神灵故事靠拢的。可见在凡圣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所谓“神仙也是凡人做”。某些人本来就是因为种种原因谪入凡间的神,而凡人可以通过修行成为神,凡圣可以互相转化。神对凡人有深刻的了解和同情,神是亲切的,神能满足凡人的生活需求,神的审美趣味也和世俗凡人一致。这就是庶民社会对神的理解,是庶民信仰神灵的精神动力,也是世俗故事能够进入宝卷、世俗故事宝卷也可以成为神圣文本的民间信仰依据。“周元招亲”宝卷是世俗故事宝卷,它也加上了神灵救助模式和修行模式。曹小姐在洞房花烛夜将周元拒于门外并要他作诗,而痴愚的周元本来是不可能作诗的,这时过路的魁星“拿笔在周元头上一点,登时变得心灵志巧,乃是出言成诗”[14]。在故事的结尾处周元母亲富贵加身之后马上想到修行:“周太太思想昔年见苦楚,如今富贵双全,要修来世之福。周玄进京奏于万岁晓得(5)吴语“元”读作“玄”,故吴语宝卷中的“周元”多写作“周玄”。,立即造起观音宝殿。太太日日焚香点烛,功成行满,白日升天。”[14]吴语区的绝大多数的世俗故事宝卷最后都要落实到修行升天上,通过这种功果圆满的榜样力量来鼓励听众去虔诚地信仰和修行。因此草卷、闲卷这些世俗故事宝卷仍然具有神圣文本的性质。
更为重要的是,宝卷是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5]1,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具有仪式语境的文本。当它在仪式之中被宣演之时,它会受仪式语境的制约。在仪式中,更容易发挥“神圣”的作用。仅从周元宝卷的开卷偈和结卷偈来看,就会发现这部宝卷也是宣给神听的,神是高高在上的神秘听众。清抄本《游龙宝卷》的开卷偈是:“《游龙宝卷》始展开,一心恭敬念如来。闲言杂语休提起,家中闲事尽丢开。尽心端坐听宣卷,能消八灾免三难。”结卷偈有句曰:“游龙宝卷尽宣完,诸佛菩萨尽喜欢。”[14]民国文益书局的石印本《正德游龙宝卷》的开卷偈是:“游龙宝卷初展开,诸佛菩萨坐莲台。在堂有缘来听卷,大众尽心要虔诚。”结卷偈云:“游龙宝卷宣完全,诸佛菩萨喜欢天。佛天三界回銮驾,消灾集福保平安。诸尊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15]神的参与使宣卷不可能成为一种单纯的娱乐活动。在点烛焚香的虔诚膜拜中,在请神拜神各项程式中,在发自内心的和佛声中,信仰之心油然而生,其间收获的绝对不会是单纯欣赏一个故事的审美愉悦。不过,“周元招亲”宝卷这种世俗故事宝卷是草卷(小卷)、闲卷。清抄本《游龙宝卷》的结卷偈里也明确称其为“小卷”:“一本小卷尽宣完,各位客人还家转。时候到有三更宽,明日再来听宣卷。一本小卷不算期,明朝再要宣大卷。”[14]可见当时这部《游龙宝卷》在当地是放在整个仪轨程式的最后部分宣演的,明显带有娱乐的目的。较之圣卷(大卷),它的仪式性和信仰功能要弱一些。在清末民国的吴语区,世俗故事宝卷是置于仪式末尾或仪式中间来宣演的,例如靖江的草卷是在晚饭后到午夜前宣演,此前和此后宣演的都是圣卷和科仪卷。世俗故事宝卷在冗长的仪式过程中既配合、呼应着圣卷,对各路神明表达信仰,同时也具有显著的娱乐功能,往往成为宣卷仪式中的最受民众喜爱的部分。
三、凡圣同构下的以俗化俗
清末民国是世俗宝卷大盛的时期,世俗故事之所以能进入宝卷,得益于这样一个机缘:教派宝卷被民间宝卷取代之后,宣卷的目的由宣扬教理教义变为满足民众祈福禳灾的各种愿望;宝卷的主要内容也由教派的教理教义变为对民间信仰中各种神灵的崇拜,而在表达崇拜的方式上采取的是在仪式中讲述神灵故事的模式;神灵故事的生产多模仿或借用世俗故事,形成凡圣同构,由此造成了世俗故事进入宝卷的契机。部分世俗故事由于造神的需要被改编成神灵故事宝卷,更多的世俗故事则稍加改编后被纳入宝卷系统中,变为补充圣卷的草卷、小卷、闲卷。
民间宣卷里的这种凡圣有别是显而易见的。民间宣卷是有明确的祈福禳灾的信仰目的的,所有的仪式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整个过程是神圣的,那些插入其中的世俗故事宝卷起着辅助和调剂的作用。不可否认,世俗故事宝卷更具有娱乐性和艺术性。在持续的冗长的仪式中,插入流行的世俗故事、民歌小调来活跃气氛肯定会大受欢迎。越来越多的世俗故事被改编成宝卷,流行的民歌小调也加入进来,它们充满了世俗色彩,艺术化地再现着庶民的生活,迎合着民众的审美趣味,满足了民众娱乐需求,受到大众的追捧。“周元招亲”宝卷中充满各种滑稽情节,在周元这个痴汉身上满是笑料:周元初见正德之时误将正德的马认成了牛,还奇怪这头牛怎么不长角,试图骑“牛”却被“牛”踢;还把正德的“京人”误解为“金人”,“原是金人,只怕头金脚金身体也是金”[14]。在正德为他写赐婚圣旨时,他居然不清楚自己的年龄和属相,以为自己“好像属猫”。周元成亲时更是笑料百出,沐浴时把肥皂误以为是补充精神的“接力糕”吃掉,差点噎死;洗浴出来又被家仆视为“看家狗”险遭痛打;换上新衣帽之后又把衣服上的“补子”误为“果子”,把衣服上绣的“龙凤”认为“鸡”“蛇”,说道“我要脱下来哉,不要着,舍个前头一条蛇,后头一只鸡,倘然拨拉里咬穿肚皮”[14]。当然,这些滑稽情节是在吴语区戏曲、说唱中流行的周元招亲故事(诸如《御殿圆》《落金扇》之类)的基础上改编的。创造、加工、改编这类情节的是市民和乡野小民,而文人对此未必热衷,像蒲松龄《增补幸云曲》、何梦梅《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洪琮《前明正德白牡丹传》中,都没有这些滑稽情节。这种轻松、幽默、活泼的风格正是乡野草民所酷爱的,“周元招亲”宝卷将这种风格发扬光大,民众在神灵的注视中尽情欢笑,庄严与滑稽共存,由此达到神人同欢的目的。
除了独特的娱乐性之外,与其他民间文类中周元招亲故事相比,“周元招亲”宝卷还有一个特点——特别强调教化。吴方言区的各种民间文类中的正德游龙故事大多符合市民阶层的心理祈愿和审美品位,通常是集政治与风情为一体;但有趣的是,宝卷在正德故事中只选择了周元招亲。宝卷不会选择正德微行中最为耀眼的“游龙戏凤”,因为宝卷的信仰本质不可能接纳纯粹的爱情、风情题材,那些能够进入宝卷的情爱故事其实都被改编成伦理与信仰相结合的故事。周元招亲这样一个以一只鸡换来荣华富贵、低成本获得阶层跨越的故事,更能满足底层民众的心理诉求,故而以乡野小民为主要受众群体的宝卷,会在众多的正德故事中选择这一故事。不过,我们发现,宝卷中的周元招亲与其他文类中的周元招亲在主题上是不一样的。各种“周元招亲”宝卷的结卷偈都大同小异,例如清抄本《献龙袍宝卷》云:“奉劝大众气量宽,但看周家好团圆。杀鸡留客一顿饭,一朝富贵得安然。小气勿做大事业,大量方有金银传。土地何能住大殿,小鬼何曾做判官。弥勒尊佛肚皮大,看见小气笑不完。”[16]这个画龙点睛的结卷偈把主题归结为为人要大量、大气,周元由于奉献了视为家主婆的鸡而做了个“大买卖”,得到了一家的富贵团圆。这个解读显然并非高见,它所要传达的实际是一种带有一定功利色彩的、朴素的善有善报的思想。其实,进入宝卷的所有世俗故事都会被改编成一个善恶报应故事,在民众的意识里,神是善恶报应的执行者,凡人若不按照与神的约定来行善,就必然会遭到报应,凡人应当将行善作为信仰的践履和修行的主要内容。周元的杀鸡待客其实也是一种大善行,而正是这个善行才使他得到了满门富贵的善报。这样一个简单的因杀鸡待客而获得阶级跨越的故事,在不同阶层的不同文类中有着多元的解读。明传奇《嫖院记》中的“周元招亲”,传达的是市民阶层发迹变泰的得意,借周元之口喊道:“世人用了几多心机,读了万卷诗书,思量做官不能勾得,我不读诗书着锦衣。”[2]308清初蒲松龄《增补幸云曲》中的周元是最本色的、心思单纯的农民,初见正德时将其误认作要军钱的汉子,杀鸡待客时也没图回报,直言“我有一个媳妇,杀给你吃了罢”[17]918,到第二天一早就想着“不如我早着些叫他走了,我好上山打柴”[17]919。这个周元不痴憨,不张狂,本分又善良。蒲松龄还借周元之口揭露曹老爷、县官、军汉对小民欺凌压榨。《增补幸云曲》中的“周元招亲”,传达的是阶层压迫之下底层民众的艰辛和希望皇帝勤政爱民的愿望。清初陈子玉的《御殿圆》、吹竽先生的《落金扇》,是苏州市民文化的产物,都把“周元招亲”置于才子佳人故事之中,周元既有滑稽的一面,又有庄重的一面,符合市民阶层的心理祈愿和审美品位。何梦梅的《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和洪琮《前明正德白牡丹传》这两部集成性的正德微行小说中,周元招亲故事很乏味,周元是一个忠臣孝子,完全没有一点憨汉的愚痴。《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把周元招亲故事改写成一个孝子节妇故事,主导思想变成了对周元忠孝、周母贤德、曹小姐贞烈的褒扬。《前明正德白牡丹传》中周元仍是孝子忠臣形象,而周母是一个特别会算计的妇人,她认准了正德会给她家带来荣华富贵,所以她的种种慷慨都是为了讨封赠。周母身上体现的是下层文人和小市民的心计。这些世俗文本对周元招亲故事进行了多元解读,展现了权力阶层对忠孝的要求,文人阶层的情感理想和社会理想,市民阶层的精于算计,草民阶层对富贵的幻想,等等。然而,在宝卷这种神圣文本之中,把民众喜闻乐见的这个故事赋予善恶报应的主题,把一个巧遇天子的偶然性事件解读成一个善有善报的必然事件。这样,一个世俗故事,经过神圣加工,放置于仪式语境之下,在轻松、幽默、活泼的气氛中,实现了以俗化俗的教化目的。
四、结语
正德游龙故事是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共同制造的一个“历史”故事。这个故事产生之初,正德身上的人欲和理想就是明末市民阶层的欲望和理想,是明代后期的好货好色社会思潮的反映。随着正德故事的发展,各个阶层都加入进来,表达着各自的诉求。民众改变了历史上的真正德,制造了一段“假”历史。在这段假想的历史中,一面把一个情色故事进行或是纯情,或是风情的多样改写,一面上演着皇权崇拜和忠奸斗争的政治大戏。最终又将情色和政治都归结在君臣忠孝的皇权伦理之下,演变成可以迎合各阶层审美趣味的雅俗共赏的千姿百态的正德微行故事。
吴语区宝卷在吸纳正德故事时,摒弃了正德故事中最主要的情色风流和忠奸斗争,仅引入了最接地气的周元招亲。“周元招亲”宝卷加入了神灵救助模式和修行模式,将世俗故事纳入神圣文本,并在仪式语境中宣演,染上了浓重的信仰色彩。“周元招亲”宝卷吸收了幽默诙谐的市民文化,突出了周元的愚痴憨顽形象,强化了娱乐性和艺术性,又加入善恶报应的主题,融入了宝卷教化功能。由此实现了信仰、教化、娱乐的完美统一。
像周元招亲这类世俗故事宝卷,其留存的数量在南北宝卷中都非常之多,目前出版的各种影印、排印本宝卷集中,世俗故事宝卷占了一大半。这部分宝卷很容易被定性为说唱故事,仅做文学上、艺术上的研究,而忽略其神圣文本的特性;而这部分宝卷都是改编世俗故事而来,没有原创性,所以文学性、艺术性的研究也很难展开。如能改变思路或角度,将其与世俗文类文本进行比较,在宣卷仪式上、文本形式上以及教化功能上,对其做具体细致的剖析,可能会为世俗故事宝卷的研究,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河西宝卷整理的回顾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