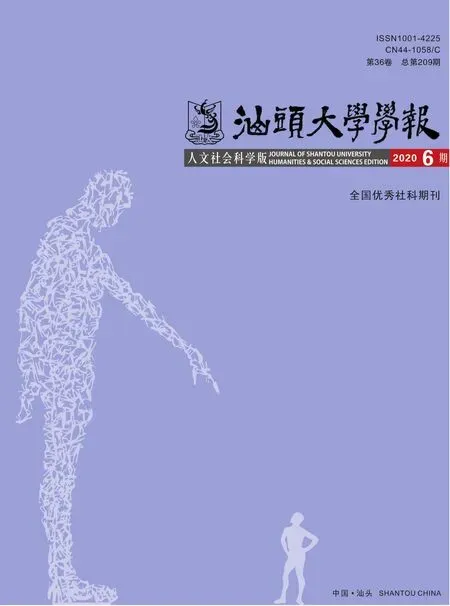从女性主义地理学看李清照和朱淑真的创作
林晓娜,李胜男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女性主义地理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派特·波纳特在1973 年发表的《性别与城市结构》,标志着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初步诞生,随后琳达·麦道威尔的《性别、认同与地方——女性主义地理学概说》、金·英格兰的《女性主义地理学:理论、方法论和研究策略》等都推动了此学科的发展。该学科主要研究女性与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身体空间、工作场域、家空间、公共空间对于女性性别身份的塑造作用[1]。本文以女性主义地理学为切入点,从空间对女性的塑造、女性身体空间的特质、女性诗词作品的风格三个部分展开,探讨李清照、朱淑真代表的女性作家的文学价值。
一、空间对女性的塑造
“女性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2]309。社会空间、家庭空间、闺阁空间,均对女性性别特色的形成具有极大影响。
(一)社会公共空间对女性的限制
分析社会公共空间对女性作家的具体影响,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和社会风气尤为重要。李清照出生于北宋而逝于南宋,此说向无争议。朱淑真的生平资料匮乏,生卒年众说纷纭,如況周颐的北宋说、冀勤的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说、孔凡礼和黄嫣梨的南宋说,据朱淑真对李清照、宋徽宗及张孝祥等诗词的化用,诗词中全无干戈之虞,却有对政府关心农事的歌颂等方面,作者认为南宋说较为可信。
无论南宋或北宋,女性的活动范围比男性小得多,大多囿于闺房、庭院之内。司马光《书仪·居家杂仪》就曾对此作过详细叙述:“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3]191,妇女的活动范围被中门隔于内室之中,与男性在中门以外的广阔行动场所内外有别。李清照的诗词共有七十六首,近六十首属于闺阁之作,细读其词,能发现她对被限制的生活范围常有不满情绪,在描写闺阁庭院前多缀有“寂寞”、“萧条”、“深幽”一类的形容词,在描写闺阁庭院后常附上“恨绵绵”、“愁千缕”、“吹动浓愁”等表示低落心境的话语。当然,李清照所接触的社会空间远比朱淑真广阔。李清照经历了巨大的家国变故,靖康之难、流寓江南使李清照尝尽离乱之苦,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给她带来强烈的精神冲击,其词作虽仍是写闺阁情思,但却有全然不同的风景情致,如作于流落江浙时的《添字采桑子》上阕写室内看芭蕉“阴满中庭”,下阙写枕上听雨打芭蕉,“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江南特有的连绵不断的雨声,使国难、家破、夫亡种种打击齐涌心头,“不惯起来听”道出多少对故国故土故人的追思。朱淑真所传三百三十七首诗中仅有四首出游诗,便可见其生活范围之狭小。
宋代女性在婚姻选择上并无权利可言。由于中门将男女隔于内外,两性之间少有接触的机会,结婚嫁娶的选择权就落在了双方父母或男性家长手中,女性在婚姻中无自主选择权。魏仲恭为《断肠诗集》所作序言中言及“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乃嫁为市井民家妻”[4]1,朱淑真不具备婚姻自主选择权,其父母又所择非人,故而一生凄苦。关于李清照再嫁一事虽难有定论,但《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中曾提到“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5]305,徐培均解读为“谓弟迒轻信张汝舟骗婚的谎言”,“巧簧之舌、似锦之言”不是把易安惑,而是使其弟惑,李清照再嫁之事乃其弟为其作主、从中斡旋。
宋代社会对于女性受教育一事有严格的限制。女性可以接受教育,但学习范围仅限于《孝经》、《列女传》等合于妇道的书籍,社会对女性读诗书极力反对,更遑论舞文弄墨、挥洒诗情了。朱淑真的一句“女子弄文诚可罪”印证了社会公共空间在文学领域对女子的制约。李清照虽有特殊的、宽松的家庭环境为其通读诗书保驾护航,但因女性不能参与社会活动,亦不能像男性一样凭借才华有所作为,故而发出“片石幽闺共谁语,输磨盾笔是男儿。梦回已弄生花管,肯蘸轻烟只扫眉”[5]273、“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5]132的无奈之声。
(二)家庭空间对女性的塑造
家庭空间是女性最主要的活动场所,对于女性的影响尤为直接、深远,“因为在那个女性没有社会角色的时代,家族的遗传以及家庭的教化培养,几乎是形成一个女子精神特征和文采修养的全部前提”[6]4。
在家庭经济方面,李清照与朱淑真皆出生于经济较为优渥的家庭,她们不需像下层社会的妇女一样为生计发愁,拥有大量的空闲时间投入文学创作。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在熙宁九年就进士及第,随后官居冀州司户参军,并娶当朝宰相王珪的长女为妻,李清照作为官宦之女,生活条件自然不差。建中靖国元年,李清照嫁为赵氏妇,此时赵明诚仅为太学内舍生,但其父赵挺之时任吏部侍郎,纵使《金石录后序》[5]334中曾言“赵、李族寒,素贫俭”,但“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去相国寺购买碑文果实,可知这对新婚夫妇的富余衣物甚多。朱淑真的父母、丈夫姓名不详,但家境殷实,“其家有东园、西园、西楼、水阁、桂堂、依绿亭诸胜”[7]110。此外,朱淑真的饮酒诗有40首,“付与酒杯浑不管”、“泼醅酒软浑无力”、“金杯满酌黄封酒”都说明她饮酒频率甚高,而宋代的酒价、酒税均重,非富庶之家绝不能经常饮酒。
在家庭教育方面,两人皆从原生家庭中接受了良好的文学培养。李格非是北宋的文章名流,《宋史·文苑传》称他“苦心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8]13122,这种文学修养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对李清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李格非曾大力推崇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词》,李清照也多处引用陶渊明的诗词,且“易安居士”一号就取自“审容膝之易安”[9]159。朱淑真之父“好拾清玩,凡可人意者,虽重购不惜也”[4]273,《寄大人二首》言“诗礼闻相远”[4]237,《和前韵见寄》言“把酒何时共,论文几日亲”[4]239,可知其父亲也是通晓诗书,性好风雅之人。另,朱淑真的《得家嫂书》中有一句“数行香墨健银钩”[4]149,透露出其嫂也是识字知书的女性。
(三)私密闺阁对女性的影响
由于女性长期被囿于闺阁内,闺阁生活大致可以分为夫妻共处和深闺独处两种状态。
在婚姻生活方面,两人的遭遇大相径庭。李清照和赵明诚在文学上十分投契,感情较好。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记叙两人的幸福生活:“相对玩味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决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在这种环境下她的文学素养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发展。朱淑真的丈夫却不通文墨,夫妻感情不佳。她在《舟行即事七首》[4]235中诉说其夫乏才,如“共谁裁剪入新诗”、“与谁江上共诗裁”,又在《愁怀》[4]130中直言“羽翼不相宜”,把丈夫比作鸥鹭,多有对婚姻的怨恨。
长期的闺阁独处生活,造成女性的审美空间狭窄,审美感受以孤独为主。李清照和朱淑真的诗词所呈现的审美空间结构,是一种以闺房为中心并向庭院外扩的模式,对室内物象的大量描写是这种幽闭空间结构的主要表现手段。如李清照《浣溪沙》(莫许杯深琥珀浓)中的“琥珀”、“瑞脑”、“辟寒金”、“烛花”,朱淑真《无寐》中的“窗纱”、“寒灯”、“凤钗”均为室内物象,这类物象承担着阐述作者隐秘心境的作用,“醒时空对烛花红”和“挑尽寒灯睡不成”,无不传达出深切的孤独感。李清照的《声声慢》起头连叠七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接着写独自饮酒、独看雁过、独赏黄花、独守窗儿、独听细雨,皆以闺阁内的物象、活动写无法排遣的凄凉孤独。朱淑真《减字木兰花·春怨》开篇直呼“独行独坐,独倡独酬还独卧”,后以“情谁见”、“梦不成”讲述孤闷难遣的心境。
社会空间从限制行动范围、剥夺女性对婚姻的自主选择权、限定文学教育范围这三个方面牵制着李清照和朱淑真的发展,家庭空间的经济优裕与教育优良为二人提供了良好的文学基础,闺阁空间里的长期独处造成二人的审美空间狭窄和审美孤独感,然而良好的夫妻关系促使李清照在文学领域内更进一步,朱淑真的不幸婚姻则导致其诗词多幽怨之声。
二、女性身体空间的特质
梅洛·庞蒂曾言:“要想真正理解空间,必须先理解身体;要想真正理解身体,必须先理解身体存在的空间性;要想真正把握身体存在的空间性,必须将身体还原到身体经验本身之中。”[10]144女性文人通过写作这一身体经验来展示身体空间中的女性特质,故在此采用追源溯流的方法,通过李清照和朱淑真的诗词来寻找二人的女性特质。
(一)女性特质之一:多情
女性多情的特质主要体现在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古代女性无法走出闺阁建功立业,又无法脱离男性成为经济独立体,爱情就变成了女性的首要追求,爱情始终是她们诗词最为主要的主题。而男性文人写爱情,不一定真写爱情,爱情之外往往寄托着对仕途、命运的思考,抒写的是士大夫的情志。李清照和朱淑真写爱情,纯粹是用女性经验浇灌的纯爱情之作。
观李清照的爱情诗词,可以归纳出发展线索:相恋——相思——伤悼,“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是年少写情浓时的欢乐;“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是独守空闺时的相思哀怨;“吹箫一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是夫君逝去后的哀悼。朱淑真的爱情诗词也同样具有明晰的时间线索,即“婚前——婚后——出轨”,“门前春水碧于天,座上诗人逸似仙”是少女时期对爱人的憧憬;“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是婚后对无才丈夫的不满;“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是与相爱男子重逢时的欢快。快乐、相思、哀怨、苦闷等多种情感,少女、少妇、老妪等多个时期,统统被这两位女性文人写在笔下,最终形成了独具女性特色的、贯穿女性一生的纯爱情诗词。
共情是女性多情特质的主要表现手法,女性文人常年被囿于闺阁庭院,只能与狭窄空间内的景物产生共情,花草树木是庭院之内的常有物象,又具有繁荣凋谢等反映生命代谢的特点,故而成为女性文人书写情感的重要介质。
李清照共有词五十九首,而涉花涉木词就占了五十一首,朱淑真共有诗三百三十七首,亦几乎首首涉及花木。她们的涉花涉木之作并非简单地对花木形态进行赞颂,而是将自我之情思注入花木之中,使花木也能拥有女性的娇俏、清高之品性,与作者产生共情性的对话。如两人都极爱品梅,李清照的《渔家傲》写梅之品格“此花不与群花比”,这便是清高少女的自得之言。朱淑真有《冬日梅窗书事四首》,梅之形态有“未容明月横疏影”,梅之品格有“梅花描摸雪精神”,而梅与淑真之间亦能产生共鸣,“幽香特地成牵役”,情随梅香而起不能自主,落得“偏恼幽闲独睡人”的结局。
此外,两人写黄花,亦可见黄花与人之相契。李清照的“人比黄花瘦”、“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皆是把自我之情思注入黄花之中,无论是形态之形销骨立,亦或是无人摘取之孤寂,既是写花亦是写人。朱淑真的“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把自己对人生、对爱情、对自由的坚守统统注入此花之中,不仅有人懂花之感,亦含唯有花懂人之哀。花草树木无意,而女子有情,以女子之情思注入无情之花草树木,便达到了共情的效果。
李清照和朱淑真的多情特质,在于爱情是她们情感激荡的最重要领域、共情是她们情感表达的最重要方式。
(二)女性特质之二:敏感
女性文人比男性文人更能捕捉到极静状态下细致、微小的景物变化,擅于描写极静状态下的细微景物之动。李清照爱写香、烛、影一类难以捉摸的细微意象,如“斜飞宝鸭亲香腮”、“夜阑尤剪灯花弄”、“重簾未卷影沉沉”,而朱淑真更爱写萤、蝇一类的微小动物意象,如“静数飞萤过小园”、“流萤明灭绿杨中”、“静看飞蝇触晓窗”。恰如胡元翎所说:“如果不是一个被幽闭闺中无聊无助无所事事的可怜女子,谁能留意于‘砌下幽蚕’?谁又能呆立良久‘静数飞萤’、‘静看飞蝇’?[11]73”李清照《行香子》中的“草际鸣蛩,惊落梧桐”和朱淑真《伤春》里的“莺声惊蝶梦”有异曲同工之妙,草际蛩鸣、梧桐叶落、莺歌、蝶舞都是寻常景物,蛩鸣声小,落叶声悄,在女性文人眼中却是蛩鸣之声惊落叶,蛩鸣声瞬间有振聋发聩之效,又衬得所处背景的极静。莺声惊醒女子的睡梦,亦让人联想到莺声惊动熟睡的蝴蝶,整个世界为之静寂,只听见莺歌和蝴蝶煽动翅膀的声音。柳永的《女冠子》(断云残雨)也写蛩鸣萤照之类的细微景物,“华星明灭,轻云时度。莎阶寂静无睹。幽蛩切切秋吟苦。疏篁一径,流萤几点,飞来飞去”[12]20,但他在写这些细微景物时采用点染手法,天上华星闪烁、草中幽蛩鸣叫、空中流萤几点,营造了清幽夏夜之景。与柳永所写之细微景物不同,李清照、朱淑真所描摹的更具有女性的观察入微和敏锐感受,更注重把个人的情感映射到物象上,且喜在字词上着力,使用富有情感意蕴的字来传达款曲。
例如李清照的《小重山》(春到长门春草青)写花影是“花影压重门”,花影有形却无重量,但以“压”字形容之,反倒似有千钧之重,象征着千愁万绪压心头,而作者无能反抗,只作默默忍受。此一“压”字大有以花影写人之感,人与景实难两分。朱淑真的《春日杂书十首》云:“日移花影上窗香”,花影有形却无味,然则朱淑真却用通感的手法把视觉与嗅觉纠缠在一起。恍若一女子孤寂、无聊时长久地盯着窗上的花影,日移花影动,光与影的变幻使得女子似乎闻到了花香。要之,李清照和朱淑真的敏感特质,在于两人都擅长捕捉极为微小的景物、发现微小事物间的隐秘关联,并通过对字词的敏感使用来表达女性的幽微心境。
三、“雌雄同体”和“纯女性书写”
女性身体空间的特质对文学作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促使作品风格的形成。从女性文学的角度来看,朱淑真的诗词把多情、敏感的女性特质灌输其中,并能以闺阁女性的独特视角反思世间万物与人生,进行“纯女性书写”。试以《秋日行》为例分析:
萧瑟西风起何处,庭前叶叶惊梧树。
万物收成天地肃,田家芋栗初登圃。
杳杳高穹片水清,一点秋鵰翥云路。
凄凄空旷雨初晴,凉飇动地收残暑。
高楼玉笛应清商,天外数声新雁度。
园林草木半含黄,篱菊黄金花正吐。
池上枯杨噪晚蝉,愁莲蔌蔌啼残露。
可怜秋色与春风,几度荣枯新复故。[4]178
开篇便以“萧瑟”奠定了情感基调,“起何处”隐藏着闺阁女性对于广阔世界的未知感,又以庭前梧树惊风自答,如此一来,屋内与屋外就被隔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一边是女性熟识的狭小天地,一边是广阔神秘的外部世界,而闺阁女性在小天地里通过登高远眺、思绪漫游来观照天地万物,并调动细腻的感官去感受自然,天高水清是目光所见,凄雨凉风是肌肤所感,玉笛度雁是耳有所闻,高远景物融入了闺阁女子对于自然世界的想象和羡慕。接着,女子的思绪收回眼前,以“含”、“吐”、“枯”、“愁”、“啼”等软媚字眼写园林草木篱菊、池边鸣蝉败莲,最终又把悲秋与伤春结合起来,发出时光流逝、人世代谢的感慨。闺阁女性的命运恰如岁时节令之转变,无法逃脱,无从抗拒。整首诗无论视野、用字、修辞,传达的都是女性特有的敏感、多情、孤独的特质。
李清照和朱淑真都具有多情、敏感的女性特质,然而二人的诗词风格却有所不同,李清照在女性书写的同时,经常还透露出一股名士气,如果说朱淑真的诗词创作是“纯女性书写”,那么李清照的诗词创作则是“雌雄同体”。
李清照的诗词作品不是简单地对于男性文学作品风格的模仿,她的多情、敏感、好奇且好胜的性格特质,把男性文学作品的豪健与女性文学作品的细腻揉为一体,最终又超越了性别,形成“雌雄同体”的独特风格。李清照的诗歌有丈夫气概,豪迈遒劲,这已是共识,姑且不论,便是词中,李清照也展示出一股名士风度,《渔家傲》可谓雌雄同体的典型之作。开篇“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展示了漫天云涛晓雾,银河光转,似千帆竞渡的阔大境界,接、连、转、舞等动词将万物载入流动状态。“仿佛魂梦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徐培均对“帝所”的注解是“天帝所居之处,此指高宗行在”,不论是与天帝语还是与高宗语,这种大胆的设想毫无疑问带有男性作者的豪情,而“归何处”又带有闺阁女子的思维模式,即丈夫或爱人离开后产生的一种真实存在却又似乎无处可寄托的迷茫之感。下阕“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既写国家前途漫漫却飘摇欲坠,又写我之道阻且长而身已老衰。“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篷舟吹取三山去”一改前之迷茫、无可奈何,转而以一种势不可挡的豪迈之气冲破层层迷雾,向上而去,表达出一种哲学上的彻悟与豁然。这层突破,不以士大夫的归隐为结局,也不以弱女子的情爱为归处,而是阐释出一种超越性别局限的、对于人生的根本反思。
李清照作品中呈现“雌雄同体”的原因,可从内外因素寻找。内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李清照所受的教育与个性,尤其是其具有一般男性所特有的争强好胜特质。李清照的好胜首先表现在文学方面,从《词论》可发现。李清照学词,不独学一家,而是涉猎百家,既读李氏君臣的“亡国之音”,也看“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的柳词,还看“虽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的数家之作。转益多师,并对众词进行评价,敢于立论的好胜之态备显。《金石录后序》自叙与赵明诚赌茶斗书,因“性偶强记”而往往胜出,言语中不无自矜自得之意。其次表现在游戏方面,“予性喜博”,从李清照《打马图经序》、《打马赋》、《打马图经命词》中透露出来的热衷,亦可见其对游戏的争强好胜。好胜使得李清照有别于传统女性,也正是这一反女性化的特质,使得李清照的作品风格具有”雌雄同体”的特征,不同于朱淑真的“纯女性书写”。
至于外因,则跟李清照的人生经历有莫大关系,读其南渡之后的词作,普遍具有“雌雄同体”的特征。如《菩萨蛮》中,上阕写早春所见所感,“夹衫乍著心情好,睡起觉微寒,梅花鬓上残”,女性特有的敏感细腻尽显无遗,可下阙一转,“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沉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沉痛的故国之思、怀乡之情,须借酒浇之,酒未消即愁不散,这是男性文人惯有的表达方式。又如一般被系年于建炎三年的《临江仙》,此词以欧阳修“深深深几许”之句开头,“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常扃”,抒发深闺寂寞,年华空度的愁闷,下阙“感风吟月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则把个人飘零的悲叹与家国蒙难之恨一同托出,道出多少仁人志士渴望恢复中原的心情。靖康南渡之后,李清照把坎坷飘零的人生写进词中,而这种抒写,不可避免地促使其创作体现出“雌雄同体”的特征。
总之,从女性主义地理学来看,空间塑造女性的特质,女性特质又促进了诗词风格的形成。李清照和朱淑真都受到社会空间的局限,也因家庭空间的宽松而走上文学创作之路,闺阁空间的束缚产生了以孤独为主的审美感受。这两位女性作家都具有多情、敏感的女性特质,而李清照比朱淑真多了一份好胜之心,因此李清照的诗词具有“雌雄同体”的风格,朱淑真的诗词具有“纯女性书写”的风格。
——作品比李清照还多的才女朱淑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