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诞的反抗
柳宗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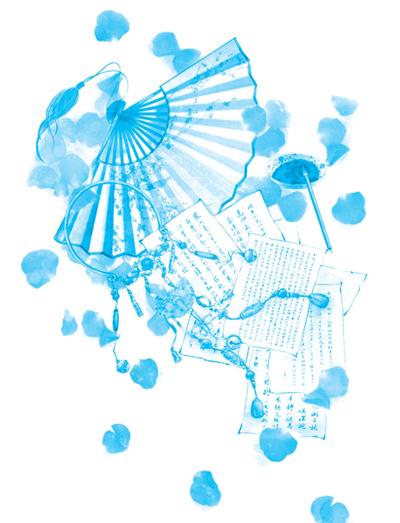
汪兆骞先生在《民国清流》中有一句精到的总结:
中国文人有放诞传统,民国时尤多尤烈。
平日里置身于虚拟网络生态之中的人们,也不时地会撞见些“牛鬼蛇神”抑或有悖常理的“荒诞之举”。而商家更着眼于部分人的猎奇心理,费尽心思反复发掘、勾勒,打造出一条上下游齐备的完整产业链。戏谑与轻佻的话语系统不断消解着传统的严肃语境,而公共视线中那些反复申说“严谨”“审慎”之士,却常常被讽以“伪君子”,牢牢贴上“不合群”的社交标签。这似乎预示着当下的一种“万物皆可戏说”的舆论生态已然构建完成。人们不再关心事实的原貌,只有“可消费”的“半真相”才能博得关注。
当代社会,《娱乐至死》中“文化成为一种滑稽戏”描述的情境,似乎正在咫尺之处上演。
相较于当下戏谑招摇的滑稽戏,民国时期新潮学者、报人以及国学大儒的放诞却更有其独特的时代内涵,昭示着背后更为深刻的严肃意义。人们也可以从中更为明晰地认识到,当下的社会中为什么“戏谑”盛行——一路走来,我们究竟遗失了什么。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或可作为当时军阀割据局面的真实写照。然而于此“刀光火色衰微”中,“生在南洋,學在西洋,仕在北洋”的怪才辜鸿铭仍旧甩着旧时代的发辫,唱着《马赛曲》穿梭于花街柳巷“八大胡同”;袁世凯殁命,政府下令居丧三日,辜鸿铭却串胡同、搭戏台,听着花花绿绿的生旦净丑唱戏唱得热闹非凡。
与一味执着于牢骚抱怨的积愤积忧者不同,辜鸿铭“不怨天,不尤人”,以欢腾当头迎击压抑的缄默。有别于醉生梦死之辈的颓靡,他时刻清醒,并凭借其“怪才”想方设法对黑暗的现实予以别出心裁的反讽式回击。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中曾论及:“知识分子不必是没有幽默感的抱怨者。”辜鸿铭的“放诞”是一种更为高明的顽童式反抗,而民族情结与广博学识自然而然成为他有力的锥刺,笑中带骂地直直对着那真正荒诞的暗幕刺将去,麻利、轻松。著名教育家张中和先生曾如此评价辜鸿铭:“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辜鸿铭拖长辫教训毛姆,章太炎将袁世凯授予的勋章做扇坠,金岳霖与鸡共舞,这种种行为所代表的是一种清醒而又睿智的放诞,借以蔑视愚昧与不公。
民国时的论战则是另一种“放诞”,显得更为有条理,其势尤大。反观当今舆论场上的种种怪象:情绪取代理性,零星小事便上纲上线,部分人热衷于追逐“朴素正义观”,进而使劲将事实、真相推开,于是满屏充斥无所依凭的观点,情绪过载引发的戾气久久难以消散开去。“万物皆可杠”与“万物皆可盘”彻底重塑了“摆事实,讲道理”的典型话题生态,这一变化在前段时间的“肖战事件”中也稍露端倪。
胡适在答章士钊的信中提到“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常相亲不相鄙”,为我们描摹了民国论战的真实景观:在“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奋进不舍与“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的豪气壮阔之间,清晰可见清流们“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的平和心胸。在所谓的“文人相轻”的刻板认知之外,更有“文人相惜”的人性关怀,这一份宽和大度也是当今几近不堪的“情绪战场”上所真正稀缺的。论辩从来只为反思,而非滋长对立与冲突。
从其实质上审视,这种“放诞”反映的其实是一种“赤子其人”的真性情的流露,即《孟子·离娄下》中提及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当时以蔡元培、胡适、钱玄同、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等为代表的一批民国知识分子,于此新旧交织的变局之中,发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呐喊,以极具个人特色的方式“相与鏖战公敌,以放一线光明于昏天黑地之中”。放诞中略显戏剧性的成分只是特殊时代附加的奇异色彩,去色揭幕后,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赤诚良知——胡适曾言“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他们并未选择明哲保身,而是以身试烈火,在震荡的时代作文化漫游、文化守望,昭示他们的文化存在和文化思考的独立意义。
我们常常呼唤“时代巨人”,似乎其所居甚遥,被一道万仞深沟与当下时代分隔开来,须得大声疾呼才有听清的可能。我们为何失去一座座“精神高地”,在无休止的论战中被迫辗转——此刻已经明了,恰如陈丹青先生在东南大学百年校庆的演讲中严肃地提及的那样:“我们几代人失去了常识与记忆。”
而我们也能够透过一代民国清流的放诞,目光放远,越过嬉笑怒骂,看到一种“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担当和人性良知的延续——而我深信,此种良知,正如顾城所说:
在玫瑰停止的地方,芬芳前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