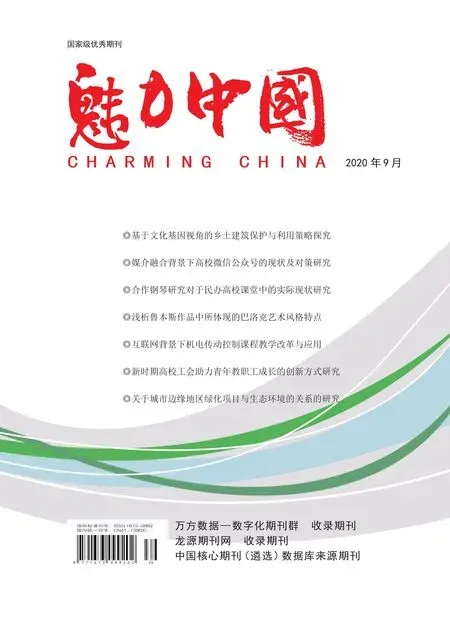仲雍南奔过程中的欲望处理
魏园
(常熟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苏州 215500)
仲雍在南奔过程中对于自己的欲望做了处理,而这种处理并不为欲望主体所自知,但是其行为却符合深层欲望的规律。
一、欲望的两种认同领域:
在想象界,人的欲望就是他人的欲望,“主体最初不仅是以自身的镜像为中介,而且是以同伴的躯体为中介来定位和辨认欲望的,恰恰是在这个时刻,人的意识以自身意识的形式辨识出自身。”人的欲望通过他人的欲望而呈现出来,但是在想象界,人的自我欲望总是试图占据直至取代他人的位置,于是和他人处在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这个层面在仲雍的行为中基本处在被压抑的状态下,但是并非不起作用,它以一种隐性的方式起着明显的作用。
在象征界,欲望进入并依附于象征秩序,主体的欲望就从对于镜像的依附转变为对于语言的依附:“言语就像水车轮,人类欲望在此通过进入语言系统而不停地受到调停。”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会寻求压制自己的原始欲望,而使得欲望的满足呈现为一种扭曲和改变的形状。
南奔中的主要行为在表面上看来都是欲望的第二种认同,即对于象征秩序的认同。也就是不得不在习俗和伦理的大环境中做出唯一可以做出的选择。仲雍和泰伯一起,在政治斗争中处于一种尴尬境地,他们在丧失了君父的好感,为了再次得到他人的承认,他们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出奔,让贤之名会使得他们在他人处重新获得一定程度的承认。
但在此过程中,主体的欲望不可能完全获得满足,甚至是永远不可能获得满足的。这显然是因为,仲雍和泰伯采取的方式只是他们的欲望达成的一种替代方案,聊胜于无。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欲望已经被多次压抑并扭曲了,这在另一个层面上,即“想象界”的认同上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并且这也是几近无效的象征秩序认同的替代物,同时是欲望对象的替代物。这种双重替代导致了仲雍南下之后的某些作为。
二、想象界的镜像认同以及仲雍对于吴国的改造
象征界的象征秩序认同再让仲雍的欲望获得某种满足的同时也压制了他的原始欲望,他在故国周国的一切尤其是他在周国所获得的他人的认可——这也是欲望可被满足的主要方面——几乎丧失殆尽,虽然他和泰伯通过南奔在想象中获得了一定的补偿,但是杯水车薪。与其说这种补偿让他们的内心稍感平复,倒不如说使得他们未被满足的欲望被压抑的更加严重,并等待一次机会获得表达。这种表达在想象界的镜像认同中呈现了初来。
新建立的国家“勾吴”即是这种想象界的欲望对象,这种欲望对象一开始是表现为象征界的秩序的。在泰伯去世后,仲雍继承了新国家的君主职位,但是他一改前朝的向模仿故国礼法的做法,而采用了一种颇为令人不解的方式:“泰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仲雍自然知道这是不合乎周国礼法的,但是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第一任君主泰伯采用的是以自我为主、教化当地人的方式,而第二任吴国君主仲雍则反其道而行之,采用了压抑自我、入乡随俗的方式。这个过程自然可以使用上边两种解释方式,但是如果从欲望角度解释,则可以看出这里了有一个曲折的欲望的表达和满足的过程。
仲雍心底对于故国的怨恨在断发文身中表现了出来,“从其所朝向的对象的观点看,主体的欲望只有通过一种竞争,通过同他人的一种绝对敌对性才能在这一关系中得到确证,并且每当我们走近某一给定主体中的这一原始异化,最根本的侵凌性就会出现——这就是欲望他人的消失,因为是他支撑着主体的欲望。”在继承君位、手中具有了一定权力之后,仲雍开始了他的欲望复仇,这种复仇即使是连他本人也没有察觉到的。他断发文身,脱掉了故国的“端委”,剪掉了受之父母的毛发,用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方式,和故国的一切断绝了关系,这是一种对于曾经占据他的身心全部的“他者”,而现在,他通过一种侵凌性的做法实现了自己能做的复仇,在此可以看到仲雍的欲望表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而他的外在行为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正像是对于欲望的无法满足所做的补偿一样,看上去似乎有效,实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注释:
[1]Jacques Lacan,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Book I,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1954,ed.Jacques-Alain Miller,trans.John Forrester,Cambridge: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47
[2]Ibid.,p.179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1641.
[4]Jacques Lacan,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Book I,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1954,ed.Jacques-Alain Miller,trans.John Forrester,Cambridge: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70
———无锡泰伯墓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