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是重生,而不是活过来
尤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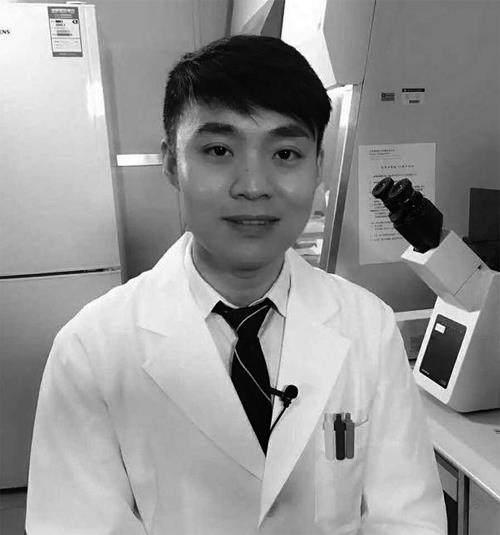
2020年1月20日,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发生暴力伤医事件,三名医护人员被砍伤,另有一位患者受伤,出诊医生陶勇受伤最重,后脑勺、胳膊多处被砍伤。
几个月后,陶勇渐渐度过暗黑时刻,现在,他已经回到诊室,恢复出诊。而经历过这件事,他觉得自己不是“活过来”而是“重生”了。
伤后,陶勇给盲童写了首诗,希望有一天可以带他们去巡演。“盲童也需要一条自食其力的路。他们眼中无光,心中应有光。”他受邀在网上讲课,如果不能再拿手术刀,他想以后就做科研,带学生。他还想过,今后或许会写个小说。陶勇一直喜欢写东西,之前,但凡有空,他都会写写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和事。
陶勇就这样“出圈”了——“陶勇超话”阅读量过亿,还有专属的“桃花源”粉丝群,粉丝们喜欢喊他“陶三岁”……
“桃花源”的slogan是“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暗合了陶勇的成长心路。陶勇说自己就是个普通的青年医生,有点成绩,成长不易。“我现在的流量大概是昙花一现,但也算带给过大家正能量。”
名利之间,看个人想要什么
陶勇病情稍稍稳定,就用没受伤的右手打完了《眼内液检测》的后记。这是他8年经验的总结,“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都是舶来品,到了我们这代人,有责任做一些原创性贡献。”
从学生时代开始,陶勇就不喜欢灌输式的机械教育,认为这容易埋没独立思考的能力。医生王惠从进入医院就跟著陶勇学习,“他最与众不同的就是爱思考,带学生是引导式、启发式,而非灌输”。
1997年,陶勇考入北京医科大学(现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专业。他的同学、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儿科医生左英熹说:“他是个很单纯的人,我和他从本科到研究生都是同学,觉得他至今都没怎么变。”没有变的,一指心性,二指相貌。
左英熹记忆里,陶勇一开始并不显山露水,成绩也在中等。“他不是那种大学里特别出挑的男生,不谈恋爱,也很少参加社团。”陶勇属于厚积薄发型,5年里,他坚持不懈地学专业、搞科研。保送研究生时,97级5年制临床医学中只有陶勇一人进入北大人民医院眼科,“金眼科,银外科。保研竞争非常激烈,成绩特别优秀的才有机会报考眼科”。
医生不是一个可以用性价比衡量的职业,尤其身处公立医院,王惠觉得“总是需要一点理想支撑的”。陶勇不是没有想过高薪酬的私立医院也是一条路,但那里没有公立医院丰富的病例,“这犹如名与利之间的选择,看个人想要什么”。
因为科研做得好,陶勇受到医院重视,31岁时已经做了几千台手术,这对于博士毕业仅3年的医生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对于一件一辈子都要干的事,应该学会享受每天多积累一点的乐趣。”陶勇说。
他把医学当成修行之道。一次手术中,陶勇刚把患者眼睛打开,显微镜的灯就灭了,怎么办?陶勇说,必须沉着冷静,继续完成手术,而整个过程中患者完全不知情。“上学时,老师就说过,如果遇到手术中停电,肚子已经打开,血还在流,慌乱的话就不知道刺哪了。”这就是心理素质的培养,能让人保持坚毅的心性。
一纠结就干了这么多年
陶勇的同学经常开玩笑,他们这个班如果能出大师,就指望陶勇了。专业上陶勇确实在同年龄段医生中一骑绝尘:35岁晋升主任医师,37岁担任知名三甲医院科室主任,成为博士生导师。陶勇觉得是自己“幸运”,但事实并非这样轻松。
陶勇选择了眼科的一个冷门专业——葡萄膜炎。全国从事葡萄膜炎治疗的医生凤毛麟角,朝阳医院渐渐成为该病患者的首选。很多患者专门为了挂陶勇的号从外地赶来,“陶主任周一的门诊不限量,经常晚上9点或10点才送走最后一位患者”。通常,陶勇一天要接诊六七十位病患。周二手术日,从早晨7点半开始,他要连续做十几台手术。
认知心理学家安德斯·埃里克森说,想成为一等一的高手,最重要的内在因素就是心甘情愿地长时间接受千锤百炼。要出类拔萃,必须有努力不懈的意志。
“真正成为医生后,才觉得学医的过程不算苦,从医才真的苦。”陶勇觉得那些千锤百炼固然有专业上的探索与精进,也有心性、意志在动摇与坚定间的不断循环。
每次出完门诊,陶勇都有“不干了”的冲动。“我火车票都买了,能不能让我先看?”“我一大早就来了,我能先看吗?”……一拨拨患者围着他,时不时吵起来。葡萄膜炎本就复杂,需要医生静下心仔细询问、诊断,“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集中精力”。而一旦碰上不讲理的病患,陶勇想抽身都难。
晚上,陶勇常带着一大堆负面情绪入睡,总爱做噩梦。第二天,他有时还会气呼呼的。但下一次出门诊,陶勇依然雷打不动地准时出现。他每一次都纠结:本来做葡萄膜炎的医生就少,这些患者就是奔着自己来的,如果他都放弃了这些人,就等于眼睁睁看着患者瞎了,他于心不忍。
王惠和左英熹能感觉到,陶勇打心眼里喜欢做医生、热爱医学。很多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喜欢做手术甚于做科研,经常会以各种理由推脱科研项目,而陶勇至今一共发表了98篇SCI论文。
时间哪来的?两台手术之间,换台子或消毒的十几二十分钟,他不是查文献就是写文章。陶勇总爱跟年轻医生说,要把时间利用起来,年轻的时间就这么短,过去了就没有了。
承担起社会责任
每一次伤医事件发生,舆论中总会混杂着多种声音——身处医疗圈内的人抱团取暖,圈外有人出离愤怒但也有人幸灾乐祸。
生气吗?“要是这样就生气,我不得气死?”即便刀已经砍向自己,陶勇依然觉得,出现异样的声音很正常。医患之间,不仅仅是信任那么简单,它是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
同时,起源于巫术的医学一定程度上又是一门经验主义科学,离不开“信则灵”的法条。陶勇经常遇到患者家属拿着一张写满问题的A4纸,要求他逐条给出明确结论。然而,坐了长途火车或飞机“投奔”医生的患者和家属通常会失望,因为“医学很大程度上是经验科学,与物理学不一样,无法通过公式推导出结论”。
最怕的是遇到患者和家属不信医生。一位患白塞氏病的小伙子被父亲带到陶勇的门诊。当时,患者双目接近失明,陶勇为其制定了治疗方案。两个月后,陶勇又一次接诊了这个小伙子,发现他的治疗效果不明显。陶勇觉得奇怪,追问之下才知道,患者的家人自作主张改了治疗方案,“患者的父亲和哥哥比着拿主意”,就是不信医生。
当然,医患之间的不信任不是一时半会可以解决的,要一步一步来。受伤后,陶勇呼吁安检措施在医院落地,“上天给我留了条命,是要我承担起这个社会责任,让善良的医护不再受伤害,这比我继续眼科事业还重要”。
“一再发生的伤医事件,希望到我这里,可以画上句号。”陶勇还希望,疫情期间,大家不要“捧杀”医护人员。因为抬高公众对于他们的心理期待,很可能在回归正常秩序后成为医患矛盾的导火索。
(摘自《新周刊》2020年第7期)

